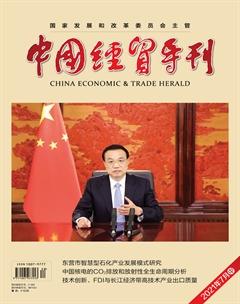中國核電的CO2排放和放射性全生命周期分析
韓梓豪 周勝 秦旭映 朱軍兵 陳福冰



摘?要:建立了用于分析我國核電環境影響的全生命周期評價模型,基于公開發表的文獻數據計算我國核電全生命周期CO2排放,并對核電生產帶來的放射性排放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我國核電全生命周期CO2排放量為12.19g/kWh,在“燃料開采”和“廢棄處理”環節的CO2排放量占比最高,核電全生命周期對公眾的放射性排放量為4.62人.Sv/(GWa)。基于此,核電產業應利用合理模型和透明數據,定量分析核電技術的環境優勢,提高公眾對核電的接受度;加快核電生命周期各環節的技術升級與進步,降低相關行業的整體能耗水平;對各環節物料進行循環再利用,減少溫室氣體及放射性排放。
關鍵詞:核電?全生命周期評價模型?CO2排放?放射性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核電、風電、光伏發電等清潔能源發電量增速較快,消納水平也不斷提高。2019年,全國全口徑發電量、清潔能源發電量分別為7.33萬億kWh和2.39萬億kWh,同比增長分別為4.7%和10.4%。其中,核電發電量為3487億kWh,同比增長8.6%;風電發電量為4057億kWh,同比增長10.9%;光伏發電量為2238億kWh,同比增長26.5%[1]。
為了適應低碳化能源結構轉型、進而實現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我國的電力供應體系將持續優化。在裝機容量方面,預計煤電裝機容量逐步下降;氣電裝機容量不斷增長,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水電裝機容量增速下降,但仍將平穩增長;核電、風電和光伏發電等清潔能源的裝機量將快速增長,替代傳統火電的趨勢明顯。預計2035年,清潔能源裝機容量為20.2億kW,較2017年新增12.5億kW,占新增裝機容量的78%;2050年,清潔能源裝機容量達到33.9億kW,較2017年新增26.2億kW,占新增裝機容量的91%[2]。
在發展核電的過程中,核電帶來何種水平的環境影響、核電的環境影響如何與其他發電方式相比對,是國內外業界十分關注的問題。國外有一些研究采用全能源鏈分析法(PCA)計算了從鈾礦開采、冶煉、鈾濃縮、燃料元件制造、運輸、核電廠建造、運行、退役等相關活動中的能耗和溫室氣體的排放。Beerten等使用生命周期分析法(LCA)計算了核燃料循環的溫室氣體排放,分析了整個核燃料循環過程中的溫室氣體排放,計算了比利時核燃料循環前端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3];Voorspools等采用生命周期分析法、全能源鏈分析法計算了比利時核電廠建造、運行和退役階段的溫室氣體排放,并與風電站、光伏電站、化石燃料發電站的計算結果進行了對比[4];Tahara采用生命周期分析法計算了日本可再生能源發電廠(核電、水電和光伏發電)以及傳統化石能源發電廠(煤炭、石油和液化天然氣)在建設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5];Tokimatsu使用全能源鏈分析法計算了日本托卡馬克聚變反應堆核電站的整個核燃料循環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與其他類型反應堆、日本目前使用的其他發電能源進行了比較[6];Meier等使用生命周期分析法計算了化石能源發電(煤炭、石油)、核能與可再生能源發電全生命周期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評估不同燃料結構來應對美國電力行業不同水平的碳排放限制的可行性[7];Siddiqui等使用生命周期分析法分析了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核電全生命周期對環境產生的影響,其中包括二氧化碳、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顆粒物等指標,并與風電、水電全生命周期對環境產生的影響進行比較[8];Weisser基于公開發表的結果,綜述和比較了近年來化石能源、核能與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的全生命周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9];Fthenakis和Kim使用生命周期分析法計算了歐洲、美國等地區核電生命周期中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低、中、高結果,并認為其差異源于鈾濃縮、核電廠建造及運營等方面的不同[10]。
國內關于核電鏈對環境影響的研究開展得較早。馬忠海等使用我國90年代中期已投運的秦山核電站和鈾礦開采與冶煉的典型數據,估算了我國核電鏈的溫室氣體排放系數,計算了核電鏈中主要相關材料的溫室氣體排放系數、各環節的溫室氣體排放系數[11,12];姜子英建立了核電鏈的外部成本計量框架,計算了核電鏈各環節的放射性流出物排放以及核設施在建造和運行維護期間間接排放的非放射性大氣污染物[13];宋海濤與瞿惠紅等分析了核電鏈全生命周期的溫室氣體排放,并分析了在不同碳排放價格下,核電在生命周期內碳排放對電價的影響[14];劉勝強基于國內外資料文獻,核算了核電生命周期溫室氣體排放系數的變化區間,并與火電進行了對比分析[15];周杰與周溪嶠通過計算核電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的排放、污染和資源消耗量,運用歸一化的綜合指標分析了核電全生命周期造成的環境負荷[16];姜子英等使用全能源鏈分析法和生命周期分析法,對我國核電鏈的生命周期溫室氣體排放進行分析,計算了現階段我國核電鏈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17];楊端節等結合廠址環境特征,對我國2001-2013年期間我國核電鏈生命周期放射性排放進行了評估與比較,并提出了一些建議[18]。
目前,國外的研究分析偏重其所在國家或全球的情況,但是各個國家的情況與中國的情況并不完全一致,全球的情況則側重宏觀或者文獻綜述。國內的研究工作方面,有一部分基于較早期的數據,而當時相關技術尚未成熟,比如近年來鈾礦開采與冶煉技術的提高已減少核電鏈生命周期溫室氣體的排放,另一部分是以方法學和有限案例的方式開展。此外,已有研究往往只研究核電鏈生命周期的溫室氣體排放、常規污染物排放、放射性排放其中一種參數,關注的環境影響評價指標不夠全面。
基于上述情況,本研究采用歸一排放標準分析模型,即全生命周期分析模型,基于公開發表的文獻數據,分析核電生產各個環節的能源消耗、物料消耗,據此計算每千瓦時核電對應的溫室氣體排放,并根據公開發表的文獻數據,對放射性排放進行比對分析,為核電與其他電力能源形式的生命周期評價的比較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