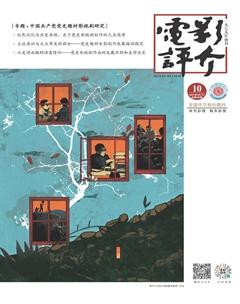從創作理念到話語表達:21世紀中英兩國兒童電影的宏觀考察
邢娜
在成年人作為主流話語建構者的現代社會中,被認為心智尚不健全的兒童對成人而言,既是未來社會話語的建構者,又是象征著人類原初的“空白”狀態、在與社會逐步接觸前處于長期“失語”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在21世紀圖像成為信息傳達主流模式的當下,在多種媒介平臺上播放的電影都以新穎的形式、寬廣的內容和影響范圍對兒童的成長起著傳統媒介無法替代的作用。兒童電影無論是對兒童經歷的生活與成長困境的揭露,還是以天真的兒童角度去評判成人的社會環境與道德,抑或關注兒童的社會化和心理健康、消除成長中的障礙都具有重要意義。文章從創作理念、話語表達等角度出發,選取21世紀中英兩國拍攝的兒童電影,探究兒童電影在當代兒童成長及關于兒童的話語建構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為當今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兒童電影的創作、制作和傳播予以新的啟示,并促進兒童電影走向發展與繁榮。
一、兒童電影創作理念的多個面向
真人實拍電影、實景配合電腦特效電影、木偶劇或特攝劇、純動畫等形式在內的“兒童電影”在電影研究中屬于一個較為寬泛范疇。兒童電影的理論研究者與批評者一般從“兒童”與“電影”的關系出發,在兒童電影的概念中囊括了“以兒童為主要表現對象的影片”“以教育兒童為目的的影片”“以兒童為預期受眾的影片”等約定俗成的基本角度與創作理念,它們相互影響,各有側重。“以兒童為主要表現對象的影片”通常以成人視角出發觀察兒童的表現,其中的“兒童”多結合兒童自身的表現與成人世界對理想兒童形象的期待,兒童形象的極端理想化即是完全處在語言秩序之外的嬰兒與幼兒。
以21世紀中英兩國的多部兒童電影為例,中國香港電影《寶貝計劃》(ROB-B-HOOD,2006)以正邪兩方對嬰兒的爭奪為線索展開,一事無成的中年人“人字拖”與游手好閑的不良青年“百達通”組成了偷盜小組,兩人一次在醫院得手時意外救下了洪家懸賞3000萬元的嬰兒,可愛的嬰兒激發了偷盜小組的良知,在充滿戲劇沖突和喜劇意味的接連行動中“引導”著本性善良的二人重回正軌。這部兒童電影中的主要角色是迷途知返的成年人,而嬰兒雖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表演,但被仇家控制后的一聲“爸爸”卻使男主角幡然醒悟,成為情節陡然轉折的關鍵性要素;電影導演陳木勝還利用嬰兒這一關鍵“道具”在動作場景中制造驚險效果,相同的高空跌落、車輛追逐等香港動作片場面在添加了“兒童”要素后起到了加強情緒渲染的效果。歐洲新浪潮電影大師特呂弗曾言:“孩童很自然地會帶進詩意,我覺得在兒童電影中,應盡量避免引進詩的成份,要讓詩情自然流露,它是一個結果而不是手段,甚至也不該是一個目標。”[1]這樣的處理方式僅僅是以成人的視角與姿態去憐憫或同情與兒童相關的事件,其主要轉折和矛盾在于成人通過兒童發生改變,而這一改變與兒童本身無關。另一方面,《寶貝計劃》這個發生在香港——曾經的英國殖民地的、落魄但善良的主人公從強大敵人的手中奪回寶寶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對香港本身歷史的隱喻。這部電影雖然以兒童為主角,但表層敘事是成年人的迷途知返,深層寓意則與地理空間的隱喻有關,因此并不一定適合兒童觀看,也不一定具備教育兒童的作用。
“以教育兒童為目的的影片”則以寓教于樂為目標,通常以普通平凡的兒童為主人公,以主人公視角經歷兒童的日常生活或奇幻冒險,在結交朋友、改正錯誤等推動性事件的幫助下使主人公的人格走向健全,使兒童在確認自身安全的條件下經歷危險緊張的安全性事件,讓兒童在換位思考與替代性滿足中釋放焦慮、獲得愉悅感。2007年,中國電影集團公司根據張天翼長篇童話及同名黑白影片翻拍了《寶葫蘆的秘密》,故事以天真活潑、富于幻想的小學生王葆的視角展開,具有普通小學生煩惱的普通少年王葆結識了擁有神奇能力,希望助人為樂卻缺乏判斷力的寶葫蘆,兩“人”結為伙伴,王葆也認識到了自己的種種缺點與不足。這部電影采用了最新的電腦圖形特效技術將原作中代表腐朽生活誘惑的寶葫蘆塑造為另一個想要結交朋友的兒童形象,將原著里寶葫蘆變給王葆的花生、冰糖葫蘆等小吃置換為21世紀初在兒童中間流行的快餐,在改革開放前的保守主義價值觀與改革開放初期的混雜中完成了外圍的“時代置換”,重新具有了教育意義。相比之下,英國影片的教育主題影片則情緒更為上揚開放,主角雖然經歷情緒低谷,卻不一定是在懺悔或改正中完成的。以表現礦工之子比利·艾略特實現舞蹈理想的故事《跳出我天地》(Billy Elliot,2010)為例。影片雖以1984至1985年英國礦業工人大罷工為背景,暴露了英國社會中嚴重的階級分化和貧困問題,但勇敢追求舞蹈夢想的比利在偏遠閉塞、人心惶惶的貧窮礦區卻成為一抹象征理想主義與樂觀主義的亮色。這部影片不僅鼓勵兒童克服社會偏見與家庭的阻礙勇敢追求理想,也啟發了工人階級或處于較低位置的成年人要對生活充滿信心。
最后,以兒童為預期受眾的影片則通常具有鮮明的形式化特征,對形象辨別能力遜于成年人的兒童而言,符號化的形象差異性與個性化特征都更加明顯。因此,這部分兒童片常常以動畫、實拍木偶劇等非真人表演形式進行敘事,或采用高度奇幻化的敘事手法講述兒童或青少年的奇幻歷險故事。21世紀以后,中國出現了大量以兒童為預期受眾的動畫片,在2000~2010年主要以電視動畫改編的系列長片為主,例如《喜羊羊與灰太狼》系列、《熊出沒》系列、《巴啦啦小魔仙》系列、《鎧甲勇士》系列等;而從2010年至今則出現了大量優秀的獨立動畫電影作品,如《魁拔》(2011)、《龍之谷:破曉奇兵》(2014)、《西游記之大圣歸來》(2015)、《大魚海棠》(2016)等。這些優秀動畫電影雖然以兒童為預期觀影人群,但在實際放映后往往以其優質成熟的敘事同時吸引了青少年乃至成人觀眾。而英國以兒童為預期受眾的影片則以真人奇幻特效片為主,例如全球知名的《哈利·波特》系列、《納尼亞傳奇》系列與《小飛俠》系列等。在創作理念上,這三者相互聯系和補充,共同構成了常見的兒童電影概念。
二、中英兩國兒童電影話語表達的特征
中英兩國兒童電影均擁有多樣的題材類型與豐富的理念。而在“話語表達”的角度對中英兩國兒童電影進行比較則會發現,中國兒童電影有著悠久的現實主義傳統,自20世紀第一代、第二代電影導演開展民族電影實踐以來,《孤兒救祖記》(1923)、《兒童之光》(1934)、《迷途的羔羊》(1936)、《三毛流浪記》(1949)等影片就將兒童命運與歷史劇變下急速崩解的家庭倫理關系與現實時代問題相結合,通過普通兒童的生活反映當代社會問題。21世紀以后,兒童電影批判現實的特征不再明顯,取而代之的是兒童視角對自身生活的體驗。社會主要矛盾的緩和使當代中國兒童電影不再具有以往濃郁的批判與悲情色彩,而是通過溫情或詼諧的方式展開對兒童生活的觀察,或者不斷提高兒童的認知水平和倫理觀念。身份多元的兒童角色也攜帶著與新社會接觸的多種經驗,出現在不同形式、不同類型的影片當中。如表現城市家庭父子關系的《和你在一起》(2002)、反映農村家庭情感的《暖春》(2003)、關于青少年安全教育的《關愛明天》(2003)和《紙飛機》(2003)、引起社會對農村兒童求學問題關注的《上學路上》(2004)等。
相較于中國的現實主義體系與原創劇本,英國兒童電影最為明顯的特征是借鑒了大量優秀的英國兒童文學作品,在現實主義與奇幻主義風格上都進行了長足的探索,并在電影產業上形成了以本土IP結合歐美其他國家電影工業體系的合作作品,呈現出多元化和全球化的話語特征。例如改編自劉易斯·卡羅爾童話的《愛麗絲夢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2010)、《愛麗絲夢游仙境2:鏡中奇遇記》(Alice in Wonderland 2,2016)、改編自羅爾德·達爾小說的《查理與巧克力工廠》(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2004)、改編自C·S·劉易斯小說《納尼亞王國編年史》(The Chronicles of Narnia)的《納尼亞傳奇》系列(The Chronicles of Narnia,2005~2010)、改編自詹姆斯·巴里小說的《彼得·潘》(Peter Pan,2003)和小飛俠:幻夢啟航《PAN:Every Legend Has A Beginning,2015》等作品都廣受全球兒童及成年觀眾喜愛。“傳統經典故事總會被反復使用,人們熟悉這類作品的敘事結構,也就是說創作者不需要花太多精力考慮角色塑造及動機心理。觀眾對故事有著既定的期待,因此,動畫導演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在表演形式及作品設計上。”[2]這些兒童片不僅對兒童的精神成長起著潛移默化的引導作用,使兒童逐漸獲得成熟的自主認知、自覺的情感和道德的自律,而且融合了多種類型元素,在多國合作的基礎上表現出人類共通的價值利益及心理情感。另一方面,采用有一定觀眾基礎的經典作品進行翻拍不僅能減少兒童電影的投資風險,而且在不與任何社會輿論和道德規范相抵觸的方針下,這樣保守的價值觀和“適合”兒童觀看的內容往往易于迎合一般父母溫和保守的教育態度。這種相對保守的策略是來自于文化、經濟和社會三重影響的結果。
在這樣的主流背景下,中英兩國也各有較為例外的作品。英國兒童片也有非翻拍的原創現實主義影片,如《跳出我天地》(2000)、《百萬小富翁》(Millions,2005);也有翻拍自漫畫作品的非合拍影片,如《倫敦一家人》(Ethel and Ernest,2016)。而中國兒童片也有大量珍貴的傳統故事和民間文學作為改編資源,《西游記》《哪吒》和《封神演義》故事的動畫化都進入了中國兒童影片從業者的視線,“西游IP”“封神IP”的開發和改編也帶來了諸多現實問題。“美術片的題材中,童話、神話、民間故事占很大的比例,因為這些題材的藝術規律與美術片相似,常常描寫變了形的內容,帶有很大的寓意、假定與象征的因素。這就為美術片揚長避短、施展夸張和幻想,提供了廣闊天地。”[3]與此同時,21世紀的中英兒童片同時存在反思成人社會問題的內容,雖然批判的尖銳性大不如前,但以兒童視角觀察社會問題的影片某種程度上值得成年觀眾深思。在張元導演的《看上去很美》(2006)中,得不到小紅花的小學生方槍槍在獎懲制度下變得內向抑郁,最終遭到了其他同學的孤立。在被評為12A級(12歲以下兒童觀看需要有家長陪同)的英國影片《穿條紋睡衣的男孩》也觸及整個歐陸文明至今難以撫平的反猶傷痛,德國軍官之子布魯諾為了幫助集中營中的猶太少年塞穆爾永遠停在了天真的童年時期。無法再現的歷史記憶在毒氣室外更衣室的拉遠鏡頭中戛然而止,為故事與現實的闡釋都留下了巨大空白。這部將鏡頭對準兒童的影片并不是常規意義上的兒童片,有的觀眾認為它不適合兒童觀看,也不應該用于教育兒童。這部電影嘗試借助兩個孩子的視點去觸碰即使在成人邏輯中也難以自洽的歷史謎題,展現“兒童眼中的歷史”;另外,平和燦爛的自然中童年自身也順理成章地顯示,盡管個人的生命面對歷史洪流是如此渺小,而納粹暴力機關又是如此冷酷而強悍,但是“歷史眼中的兒童”仍然是影片的重要落點之一。
三、“消逝”中的兒童:全球化視角下的兒童電影
兒童電影的多元化發展使中英兩國都產生一批優秀影片,而這批跨越了東西方文化鴻溝障礙的兒童電影也恰恰印證了全球化背景下兒童教育與社會構成的單一性。從現代社會家長或教育者的社會角度來說,這些電影中的兒童角色不一定具備其長輩與教育者期待中善良聽話、善解人意等“傳統美德”,影片立意也不一定指向對不符合觀眾期待的“壞孩子”的教育內容。在全球許多成人觀眾都就兒童電影不再適合兒童觀看而提出批評時常忽略的一點是,現代世界的“兒童”并非生物學的范疇,而是一種社會產物,是我們生活的時代中經常隱藏于成人世界的鮮活信息。任何一種生物性的文化都不可能忘卻自己需要再生和繁衍的現實,然而“兒童”卻經常作為重要的社會概念被遺忘。西方學者尼爾·波茲曼①在《童年的消逝》中運用了大量歷史學和人口學的資料,指出童年是晚近的發明,作為社會結構和心理條件的“兒童”的發現伴隨著文藝復興對人性的發現,而“兒童”的誕生是因為新的印刷媒介在未成年人和成人之間強加了一些分界線,未成年人必須通過印刷品的世界才能成為成人,因此必須進入學校接受教育;而傳播媒介的崛起與全球化傳播,再度使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線迅速模糊,兒童電影的概念也隨即遭到“童年的消逝”的影響與沖擊。在娛樂至死的讀圖時代,兒童電影是否能為兒童的健康成長保留一塊未經污染的精神凈土,抑或本身就作為一種視聽媒介加速了這一進程呢?尼爾·波茲曼并未提及電影領域的童年是否同樣“消逝”,然而從中國創作者對影片題材與內容的自律性選擇,及英國業內就未成年人的心理保護制定的分級制度來看,成人在不在兒童面前使用某些語言或展現某些畫面前達成了統一的公約。相對地,兒童也被期望不在成人面前描述那些畫面,社會倫理要求在成人和兒童的符號之間保持公開的區別,它所代表的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社會想象。至今兒童電影給許多觀眾的印象依然是樂觀陽光、輕松無害的。從成人方面來看,對語言和符號的約束反映了一個社會理想,即試圖保護兒童不受粗俗骯臟或憤世嫉俗態度的影響;從兒童方面來看,這種約束反映了他們理解自己在社會等級里的位置,尤其是理解他們還沒有公開權利表達那些態度。在這一層面,中英兩國兒童電影都有成人內容的兒童化表述。“從兒童的視角看某問題”潛在的話語是“兒童”在其中扮演的是天真無邪、沒有分辨能力的“空白畫板”,因此暗藏著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這種合理性其實又是成人借助兒童之口進行的、“成人從兒童視角看某問題”的意識形態話語表達,中國的《看上去很美》借小學生視角對市場化初期功利主義的反思、英國的《穿條紋睡衣的男孩》試圖以兒童之間友情的角度審視納粹與二戰的歐洲文明之殤都是其實例。伴隨著童年一同消逝的,恰恰是兒童電影在全球背景下的消逝。
全球化時代也是一個信息日新月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兒童認知中權威和好奇之間的微妙平衡被信息和圖像的涌入所打破,成年人不能在兒童面前扮演導師的角色,長輩和成人對年輕人或晚輩的經歷,并沒有年輕人自己了解得更多,導師資格的喪失導致了一種知識和信仰的危機。[4]在各種圖像媒介成為兒童對世界認識的主要來源之后,成年的權威和童年的好奇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據,因為“羞恥”和“禮儀”都根植于秘密,但圖像媒介將兒童原本還不知道或將要知道的社會生活全部提前令其知悉,電影與電視替代了成人成為當代兒童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面對心理早熟的兒童與成人知識權威的消逝,很多兒童電影作為成人世界生產的、與成人權威等價的文化教育品進入兒童世界,試圖為喪失“導師”資格的成人找回教育者的權威;而作為接受者的兒童具備觀看和解釋圖像的能力,卻無法完全掌握圖像的歷史背景及其中的意識形態話語,這反向又使成人重新思考對兒童電影表現內容的自我審查。最終,兒童電影本身就形成了攜帶著種種東西方矛盾立場與社會話語的問題場域,而非解決全球化下代際沖突和教育問題的方法。
結語
優秀的兒童電影能夠使兒童觀眾通過觀影中的夢幻體驗獲得愉悅的情緒體驗,釋放成長過程中的精神壓力,起到寓教于樂的作用。然而21世紀的現代圖像媒介卻使兒童與成人、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角色區別日益模糊,兒童電影不僅滿足了兒童讀者的認知啟迪、情感熏陶、道德教化、倫理身份認同等功能,還重新創造了未成年觀眾內心深處潛藏的種種無意識欲望。與兒童電影的成人化趨勢并駕齊驅的,是現實中兒童過早成人化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陳宛妤,烏蘭.兒童電影──導演與兒童的真誠對話(下)[ 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1996(01):54.
[2][英]莫琳·弗尼斯.動畫概論[M].方麗,李梁,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30.
[3]余又晨.編劇札記:幾則學習心得.美術電影創作研究[C].中國電影出版社,1984:37.
[4][美]瑪格麗特·米德.文化與承諾:一項有關代溝問題的研究[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