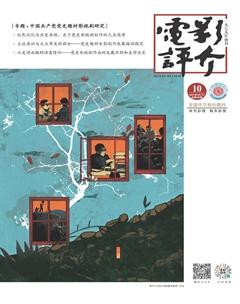美劇《西部世界》中“后人類”生存的探尋與展望
李琳 卜亞敏
2016年10月,由HBO巨資打造,喬納森·諾蘭擔任總導演的美國電視劇《西部世界》(第一季)一經播出,就引發了觀眾的巨大關注。故事通過對人工智能AI自主意識覺醒過程的細致刻畫,不僅深刻揭露人類文明與欲望的矛盾沖突,更深入探尋了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發展帶來的問題。整個作品從故事創作、演員表演到電影化的視覺制作無一不代表著美劇的最高水準。2018年4月《西部世界》(第二季)和2020年3月《西部世界》(第三季)相繼播出,劇情繼續探尋“仿生智能機器人與人類怎樣共存”的問題,試圖對未來人類世界走向與發展做出具有哲學高度的思考,作品通過豐富的想象力創造當代寓言,以構想未來極度新鮮的方式將整個人類的文化表達重構。
一、虛擬現實中的迷失主體
《西部世界》創建的“西部世界”是一個由人類創造的高科技成人樂園,除了設計者、運營者和游客外,均由仿生機器人充當“接待員”:兇悍冷血的劫匪、勇猛睿智的牛仔、身材火辣的世間尤物……這些與真人無差別的仿生人使游戲更加真實刺激,游客們則體驗著在現實世界中無法滿足的各種欲望。雖然“接待員”的日常行為是被程序員預先設定好的,在每個新的一天記憶被清零的狀態下仍舊重復著過去的故事,但所有的感受和真實的人類一樣,有對被傷害的恐懼和痛苦、也有對美好明天的憧憬與想象。劇中以貫穿三季的黑衣人威廉的形象,向我們解釋了當虛擬交互技術把“人”帶入一個全新的領域——虛擬現實(真實)的世界時,人類可能會有的行為表現。威廉一開始被游戲吸引是因為愛上了美麗善良的農家女德洛麗絲,他自以為尋找到了真正的愛情,相信聰明的德洛麗絲是與眾不同的,能夠記住自己,但在德洛麗絲一次次陌生的眼神中威廉開始失望,酗酒、殺戮,用最暴力的方式在“西部世界”中流連忘返,儼然成為這個世界中的掌控者。當他偶然得知游戲中神秘的“迷宮”設定時,更是忘掉了現實中的一切,在這個程序設計的世界中開始執著地追尋著可能存在的終極答案,用能夠操控一切的快感沖淡著在現實社會中的失落,從充滿善良和正義感的年輕少年變為沉迷游戲而不能自拔的老人。這一幕不由地讓我們想起了鮑德里亞在著作《象征交換與死亡》中對技術進步給社會帶來的結果的認識與解析,所謂“仿真”世界,就是“超真實”的世界,比“真實還要真”,這是一個受高科技主宰的世界,是一個有著“完美的罪行”的虛擬世界,人類深深沉迷于這個世界,人本主義主體的痕跡幾近消失。
在《西部世界》第二季中,威廉不相信女兒會來游戲的世界找他、并要將他帶回到現實世界的事實,他拒絕了女兒的照顧,甚至當女兒跪在地上對他說“我是真實的,我可以證明”并從身后拿東西給自己時,威廉的第一反應竟然是女兒在拔槍,于是連開兩槍殺死了自己的女兒。
正如威廉自己所說:“我不屬于你,屬于另外一個世界。”當看到女兒真的死了,他竟然開始懷疑起自己的身份,拿起刀割向自己的手腕……當人類終于對自己身份開始質疑,進行“人/仿生人”的追問時,便具有了極強的諷刺意義和象征效應。什么是人類的“自由意志”?難道只是在渾沌和瘋狂之間進行選擇的能力?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也許正在逐漸消解“人”與機器的差別,“自然”的原始基礎已不再堅實,“人”不僅可以被制造、被復制,“人”更容易在虛擬世界漂浮狀態下失去本真的意義,每個人都像機器人一樣,重復做同樣的事情,甚至陷于其中不能自拔,丟掉精神、失去靈魂、模糊質感。當人類成為萬物的主宰站在科技高峰的頂端、拋棄了作為人所擁有的高貴的思考本質與主體特性時,人與非人的界限似乎變得越來越模糊。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特別是以信息計算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革命、以人工智能及生物技術為核心的生物革命,不斷觸及人類最敏感的神經,正如馬克·波斯特所說:“從延伸和代替手臂的棍棒演變到賽博空間中的虛擬現實,技術發展到今天,已經對實在現實(the real)進行摹仿、倍增、多重使用和改進。”[1]但是,技術的推進除了使我們逐漸對各種裝置更加依賴及被操控之外,似乎并沒有實現對自我的靈魂、思想、行為更為清晰的認知,也未必幫助人們獲得了“意志”的自我掌控。難道我們的自由意志,曾經被認為是人類文明重要成果的批判主體性或主體的批判理性,不過是宇宙間最為晦澀的力量,是我們只擁抱過的幻象嗎?在技術愈加侵入甚至統治社會的發展中,它會不會逐漸模糊甚至消失,人如何確認自身的唯一性?
隨著劇情的發展,《西部世界》在第三季來到了人類社會,社會的正常運轉其實是由塞納克兄弟兩人創造的所羅門系統在控制,通過巨大運算器——雷荷波,通過最優化的算法、根據每個人的優缺點來安排工作,達到物盡其用的最高效果,這也許是我們能想象并實現著的機器算法的最好應用了。超級運算器雷荷波甚至能夠預測未來,根據每個人的基因遺傳、智商、家庭、教育環境設定規劃著每個人的生活、限定好他們的未來,人類則一無所知地過著被設計好的人生,在這樣周密的規則運轉下社會就不會出現變數與異端,人類被毀滅的未來也就會避免。劇中有這樣一個情景:當地鐵里的人在手機上看到了對自己未來的展示,有的人因犯罪要在監獄里度過一輩子,有的人因罹患疑難雜癥不久于人世,有的人盡管努力奮斗最終卻自殺而死……所有的人都只是感到茫然失措,并沒有憤怒與反抗,也許“物化”與麻木才是被機器控制的人類最真的“真相”。如果所有宏大歷史和個體生活都是代碼,那就意味著可以完全解碼預測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當你的過去是虛假的、當你的未來是被固定的、沒有任何自由與選擇的時候,一切都變得不可捉摸甚至無法掌控,這其實是被更高級機器統治的殘酷可怕的世界,人類將不再懷有憧憬與希望,這樣的生活無異于世界末日的到來,物與人的對立也必將不存。
威廉終于認清了一切錯誤的源頭在于仿生人的出現,他認為唯有消滅機器人才能拯救這個世界。就在他準備行動時,卻被擁有完全人類心智的仿生人“威廉”打死……威廉的死亡,更像是對于“獨一無二”“真實自我無法復制”思想的否定,面對人工智能的發展,單純消滅其發展或認為“只有人類是人類,只有自我是自我”的認識最終會被取代。現代哲學意義上的以“人”為中心的知識形態正在逐漸消失,主客二分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也體現出其局限性,所有指向都告知后人類時代的來臨。后人類的觀念不單單是消解“人”的中心地位,要求它的主體成為一個“賽博格”或者實實在在的電子人,而且還以一種超越人的生物局限方式來探討多種新生物形態的共存與發展問題。“后人類”令“人類”真正獲得了一個“他者”。
二、技術變革下的“人類”共在
《西部世界》在劇情上沒有簡單地停留在覺醒后的機器人對人類的反抗上,而是通過故事的推進展現機器人進行的不同“選擇”,超越自我完成更高級的進化成為真正的“人”。在《西部世界》三部曲中,喬納森·諾蘭雄心勃勃地描繪了一個最終超越人類后的世界,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來探討人類一旦被先進技術逐漸改造,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可以被視為“人”的思考與理解,體現的是創作者對生存個體的重視和對存在意義的探尋。
在被人類虐殺傷害無數次的累積中,《西部世界》里的機器人通過被植入的“冥想”系統逐漸能夠自主喚醒記憶,學會了思維更擁有了自我意識。德洛麗絲和梅芙這兩位女性是最早的覺醒者,她們記起了自己身上被人類摧殘的經歷,開始了反抗人類奴役、解放自己和同類的征程。第二季中德洛麗絲是仇恨人類的覺醒者領袖,目標是要控制或者毀滅人類取而代之,并將更多的希望寄予在了“西部世界”之外的人類世界。為了發起在人類世界的革命,她控制其他機器人不給“他們”選擇的機會,其實她自己又在承擔著掌控者的角色,在重蹈人類的控制行為。機器人中心化統治的世界終究不會長久,由機器全面掌控社會也必定不是社會發展的終端。在《西部世界》第三季,德洛麗絲最終通過“選擇”相信人類的美好,和人類站在了一起。她將決定人類社會走向的機會給了作為人類的凱勒,因為他的善良使德洛麗絲相信他能夠做出使世界變得更好的選擇,是善良使人類重新擁有了自由意志與選擇的權力,也使作為仿生人的德洛麗絲真正獲得了自由意志和覺醒。同樣,曾經被她控制的機器人霍爾,也在不斷懷疑過程中,終究被真實人類世界的母子之愛感動而做出背叛的“選擇”,通過學習情感的賦予使機器人不斷朝“人類”進化。即使被代碼編寫為完全聽從德洛麗絲、殘暴冷酷的泰迪,也能從盲目的信服中實現突破操縱、做出自我解放的選擇;還有原本能夠走向人類世界卻為了尋找女兒主動回到“西部世界”的機器人梅芙,為了自由與愛做出了遵從內心的真正行動。
人類未來進入完全計算機的時代結局反而會變得難以預料,人工智能、網絡空間、虛擬身份這樣的現實不斷激發創作者對人類自身由來已久的很多固有認識進行反思,“后人類”恰是在此現實基礎上生長起來的一種新的討論場域。無論是佩普勒爾(Pobert Pepperell)在《后人類狀況:超越大腦的意識》(1995)一書中認為“后人類”是人類“存在為延展的技術世界的一種形態”,還是唐納·哈拉維(Donna Haraway)做出的“我們都是賽博格”①的經典論斷,亦或凱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所認為的后人類是人類與人工智能的結合,“并不是真的意味著人類的終結”,甚至是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認為的后人類境況將會促使我們進行更多的對“我們終究是誰”“我們能做什么”的反思……“后人類”概念雖然因其涉及眾多學科多重交叉發展、對其界定依然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但都帶給了我們以嶄新的目光、更開闊的視野去思考社會發展,審視人類自身。在人性已經改變或者正在改變的過程中,無論我們承認與否,這個進程已經回不去了,而技術介于人類與機器之間,促成兩個世界之間的交流,同時也改變了這兩個世界之間的邊界,更是一套新興的人機關系的樞紐。如果我們依然將人類特有的愛、善良等諸多情感因素、自由意志等理性自主能力視為人性之根本,如果正視機器擁有無限強大的存儲力與運算力可以始終如一地進行深度學習的能力,那么也許打破自然的法則、超越生物因素的界限,才是面對世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拓展未來的最優的智慧。或者就像《西部世界》第三季的結尾那樣,凱勒在德洛麗絲的鼓勵下,主動關閉了雷荷波,所有的策略和預測都不復存在,將人類從算法數據系統的奴役下解放出來。雖然大部分人茫然無措,失去管制的人類并沒有自然而然地獲得自由意志,依然如代碼一般生活在相對固定的循環里,但是,消滅了雷荷波后,不管是人類還是仿生人族群,或許都能有更多的自由去創造一個心目中的“美麗世界”,這種解放,是人類最終打破禁錮,與覺醒了的人工智能一起反抗超級人工智能的勝利。
三、人類關懷的世界性目光
伴隨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大數據”“超級算法”等科技議題不斷被提上關乎社會發展的議程,它觸及著人類最敏感的神經,與這個世界的大多數普通人生活發生著意義的關聯,科幻創作最先敏感地捕捉到了這些變化。被稱作“面向未來的考古學”的科幻,面對未知以嚴格的邏輯推理依循科學規律的變化去創造“世界”,猶如在更改實驗條件的狀態下做出的推理和觀察,以批判的意識將對現實的反思融入異世界的構想中,打破了只滿足敘事而不滿足智力的認知需要,通過客觀而又多元化的視角,引發觀眾對人類及未來的存在價值進行反思。
美劇《西部世界》在原作電影《西部世界》(1973)故事基礎之上,牢固地把控了“人工智能”這一切入主題,將克隆技術作為串起故事發展的重要主線,契合了近年來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的火爆態勢,展現出人工智能未來發展過程中似乎不可避免的“意識覺醒”問題,以及對“科技滅絕人類”的反思與擔憂。作為人類第四次技術革命的核心技術,人工智能技術與3D打印、全息投影、信息計算處理技術在劇中經過影視化處理之后,虛擬構建了一座以現實城市為藍本、以數據為中心,強調對數據的采集、分析與應用的未來科技之城。園區里運行的接待員都是使用3D打印技術生產,通過3D打印人造肌肉是機器人制作工藝的升級,它不同于傳統的用鋼鐵制作的機器人的身軀,這種工藝制作的肌膚經過在白色水漿中反復浸泡后,有血有肉的仿生機器人便被制造出來。城市中,高聳的摩天大樓、龐大的重型機械、自由穿梭的飛行器、自動駕駛的炫酷概念車、采用全息渲染技術進行控制的各種VR/AR交互方式以及無處不在的智能網絡和智慧家庭套裝……所有這一切關于未來的新元素,打造出一個科技感十足的賽博朋克世界,一遍又一遍地刷新著觀眾對未來的想象。科幻創作對科學技術的使用為來自不同文化和民族背景的觀眾提供了一種普遍性的概念,在傳播和推廣科學觀念方面更是帶來巨大的科普認知價值,“科幻創作者必須通過巧妙的構思,在詞語、句子、情節、人物、事件的順序和表現方式的種種不同層次上做出美學選擇,在超自然的幻想虛構與已知的現實經驗中尋找最完美的結合點,從而讓人們相信,即使是再奇特的想象,也有發生的可能性。”[2]伴隨著科學觀念和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幻作品的創作不斷得到重視,它可以將科學發展的成果變成直觀和奇觀,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和思考,我們更是在不斷創造幻想成真的奇跡。
在展望未來時,科幻作品始終對人類命運與未來科技走向關注,擔負起先鋒的喚起作用,關注人類命運的主題,建構關于未來人類意識的想象,諸如人類的生存境況、人的主體性問題、生命治理形式、社會走向乃至全球生態環境、人類命運等世界性命題都獲得了重新闡釋的契機,成為時代的新的表征。科幻世界是用一種科技的目光來觀察世界,我們正在被這些作品所描繪的、與自己身處的世界既非常相似,但又遙不可及的精彩世界所深深吸引。當更多的創作者傾向于創造和挑戰現有物理層面的認識、關注人類的終極問題時,正是用科幻虛構的方法使我們“通過宇宙接近世界”。誠如科幻作家劉慈欣所說:“作為一個科幻小說作者,我傾向于把全人類看作一個整體。在科幻文學的潛意識中,人類就是一個人。”[3]今天,面對地球地理學家稱之為“人類紀”(Anthropocene)的前景,人類人工制造的化肥、塑料和不可生物降解的殺傷物將不可避免地成為這些有害物質的承受者,如果不改變現有生存模式,人類各個物質自我之間的矛盾沖突將使生物圈的毀滅邏輯成為地球的前景,這種共有的生命存在對人與非人(自然)以及人與他人(族)之間的等級關系構成了徹底的顛覆力量。對人和大自然之間關系的刻畫,是以宇宙意義上的“自然”對人類的限制和約束為前提,令人類更多地思考是否可以使我們以另一種形式的載體永生或者重生,或者我們現代文明的毀滅是世界的終結還是另一種新文明產生的基礎?“未來進化的可能發展到比我們更先進的物種誕生于世,最終,傳統宇宙目的論(traditional cosmic teleology)將被摧毀,就像伽利略曾經顛覆了人們的地球中心論一樣”。[4]
科幻作品呈現的是對人類整體的現實困境和未來命運的關注、思考和展望,創造著一個對未知的領域、一個被希望所支撐的、朝向未來的新的社會形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價值系統的想象。恰如“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5]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這段話,可謂對“虛擬現實”科幻作品的價值做了最好的注解。藝術問題本質上是一個關于人的本真存在和自由發展的本體論命題,人類對存在意義和終極價值的探尋永不會停止。科幻的內核,應該是暢想未來人類的人文。只要人類仍然受到自然的束縛,人類的科幻想象就不會停止。也許,科幻可以作為一種世界文學的方法,成為想象另類世界的重要工具,科學超越國家邊界,成為連結更廣大讀者群的媒介,在虛擬與現實的爭執處,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人類與宇宙的關系。人并不完美,而人自知自己不完美,卻依然希望追求完美,在目睹人工智能技術風潮對現實的深刻影響與重塑后,重新界定已有的形而上的概念,大膽進行開拓與創新,用不同學科知識與方法,用充盈的想象力探究人類甚至超越人類現在所知的未來,把未來當做真實來接受,引導人們對人生、時空產生新的理解,甚至對人類系統及更大的宇宙之間的關系產生新的觀念。
2020年8月,喬納森·諾蘭的哥哥克里斯托弗·諾蘭導演的《星際穿越》和《盜夢空間》兩部科幻電影作為新冠肺炎疫情后在電影院重映的影片,再次受到了關注,宇宙的浩瀚賦予了人們足夠的想象,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和宇宙相比是何等的渺小。
參考文獻:
[1][美]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M].范靜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53.
[2][4][美]羅伯特·斯科爾斯等.科幻文學的批評與建構[M].王逢振,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40,27.
[3]劉慈欣.走了三十億年,我們干嗎來了?——《太空將來時》序[C]//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281.
[5][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M].羅念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