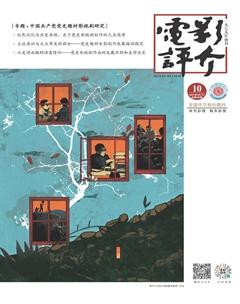從文本記述到戲劇表達
張菁洲
王陽明作為實現儒家圣哲“三不朽”理想的歷史人物具有傳奇性和代表性,這是王陽明形象戲劇化的必要前提。早在戲曲藝術飛速發展的明清時期,藝術創作活動便將視角深入王陽明的傳奇人生,如山陽道人編撰的南戲《王陽明平逆記》、明正德十五年后根據《王陽明平逆記》改編的《寧王》本,其后又有《護國記·點化陽明》或《陽春記·點化陽明》即許真君點化王陽明之劇目,可見人們對王陽明的人生經歷頗感好奇。進入現當代時期,以王陽明為對象的戲劇、影視創作拉開了新的序幕,戲曲類如余姚市姚劇保護傳承中心的姚劇《王陽明》,話劇類如貴州省話劇團與浙江省話劇團聯合創排的話劇《此心光明》,影視類有陳曉雷導演的電視連續劇《王陽明》,以及網絡大電影《巖中花樹》。從年譜傳記等文本記述的神異圣哲轉為舞臺形象的鮮活人生,王陽明形象經歷了時代需要的改編,戲劇化的王陽明形象通過舞臺藝術和情境表現內化為“良知”主體的理解與實踐,以文本記述為歷史依據通過不同場景的選取與布置,掌控人物、情節焦點與舞臺語言,在演員與觀眾共建的意義場域下完成王陽明心學的認知與接受。基于文本記述的王陽明形象在傳記、年譜等文獻的作用下樹立王陽明的人格形象,內在地遵從傳記體例以及經典文獻的歷史需要,在還原王陽明歷史地位的同時呼喚文本閱讀體驗的情感認知。隨著王陽明形象不斷被戲劇影視化,藝術創造的場景選擇支撐了王陽明形象的具體表現,在“再現”“重構”“借取”的場景構建活動中,王陽明戲劇形象以貼合時代需求的藝術面貌呈露“良知”心體的現代價值,實現哲學與藝術的聯動。
一、心像世界的戲劇場景塑造
戲劇表演模式以“人”的表演“空間”,也即舞臺的展露為敘事過程,在受眾的注視與關注下,演員將人物動作及語言神態運用于意義構建,其講述故事的功能除人物的主導外,還需要信息元素的場景進行全方位配合,場景的截取和組合構成敘事藝術在講述故事情節上的完整性,是戲劇表演的重要環節。戲劇藝術對場景的塑造與文本記述的關系又分為“再現式”“重構式”“借取式”等不同情形。
(一)“再現式”場景選取:王陽明歷史形象的真實回顧
第一種是再現關系的場景敘述,“再現”即對文本內容的忠實呈現,選取文本中有矛盾張力和代表性的場景,復制文本中的主題元素、人物關系以及環境內容,將文字文本具象化為舞臺語言。如貴州師范大學的話劇《王陽明》選取王陽明被貶、講學、平亂、病逝等代表性場景勾勒王陽明的傳奇一生,首幕便刻畫出王陽明上疏直言得罪宦官劉瑾而被迫下獄的場景,舞臺上的王陽明立于兩名士兵之中,士兵神情嚴肅、氣勢逼人,王陽明則一身白袍、頭戴綸巾立于其間,神色自如、正氣凜然,通過王陽明與士兵行為舉止的對比,刻畫出一個身陷囹圄卻真實自然、灑脫忠貞的忠臣形象,將王陽明的立場態度、情感認知與價值取向一并托出。“再現式”場景的選取和塑造為觀眾還原歷史上的王陽明的情感態度以及思想環境,“再現”關系中戲劇表演對文本記述的符合程度較高,最大程度上尊重并保留了文本記述的內容和風格,再現生活環境、故事情節,以摹寫復制的行為還原文本中的主題思想及審美感覺。“再現式”場景對王陽明作為歷史人物的真實體悟和客觀反映重在重塑王陽明的光明之心,戲劇形象的王陽明面對執杖和責罰的磊落以及語言表情的坦蕩立足于王陽明道德本原的自然流行,德性的力量在既定環境中通過行為活動而獲得新的意義。
(二)“重構式”場景選取:王陽明心學思想的具象再造
“重構式”場景的選取在歷史事件與人物關系的干預中尋找藝術表演的生成形態,重構關系下的場景塑造并不完全遵從文本記述,而是對文本進行加工性的再創造,加入新的主題和元素,制造新的矛盾沖突,使之整體更加符合戲劇藝術的內在邏輯和表演需要。影片《巖中花樹》對“陽明格竹”的場景塑造,就體現了文本世界向具象世界的再生,據錢德洪《年譜》載:“先生始侍龍山公于京師,遍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眾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1]《年譜》此言記載了王陽明早年間思想的曲折變化,為日后“良知”之悟埋下了伏筆。在《巖中花樹》中,王陽明說:“不是以眼睛為鏡子去照竹子,而是以心為本體,下功夫擦亮心鏡。”影片將王陽明在龍場悟道時的系列要素移借到“格竹”事件中,有意淡化時間線索和人際關系的牽絆,突出心學思想體系中“本體”與“功夫”之關系的探討,在王陽明這里,良知主體是致良知工夫的本原根據,本體作為工夫的出發點也是工夫展開過程的規范,影片選取“格竹”場景作為“致良知”過程的具體展開,以“格竹”事件為中介,顯現出“致良知”過程的存在形態,表現了“王陽明”作為良知主體在致知過程中的生命力量及價值意義的獲得。“格竹”事件展現了主體認識活動化對象世界而進入意義世界的過程,“竹子”作為片中王陽明的意識結構的代表,其被理解的層面就關聯著王陽明精神結構的思想水平。通過戲劇化的藝術形式,影視劇中的王陽明形象與文本記述的王陽明主體一道,見證了其精神活動的歷史過程,同時,戲劇以“格竹”串聯起人物的心理歷程,把真實的舞臺與抽象的情感傳遞給觀眾。
越劇《王陽明》同樣采用“重構式”場景塑造,借虛構女性人物婁婈之口問王陽明:“圣人哪有情愛啊美人啊這些滿是人間煙火的事兒?”王陽明回答道:“人人都能有愛情,圣人也是人,當然也可以有愛情。”“內圣”之境是理想的人格境界,具有超越性的存在價值和崇高的道德意義,程朱理學以摒棄“人欲”為到達“天理”的必要手段,而在王陽明這里,“圣人也是人”,首先肯定人的現實價值,人格培養也即成圣過程應注意不同主體的個性特點,將個人心體作為成圣的出發點,劇中通過王陽明人物的臺詞傳達出心學視域對真實人格的關注,讓“圣人”接受自然情愛實際上是對外在矯飾的規避,“讓普遍之理落實于心體,化外在的規范為內在德性,從而使行為不再僅僅依照形式化的理性規范(儀節),而是真正出自內在的道德本體。”[2]圣人情愛的肯定是以普遍之理關照個人之心,將心與理融合的人格擔保,主體情義是至善境界的德性發用,王陽明的心即理貫通了感性與理性,共同構成主體的道德境界。
(三)“借取式”場景選取:王陽明形象的藝術改造
戲劇影視中也不乏借取關系的場景塑造,“借取”模式的視域下,戲劇表演與文本記述仍有一定關聯,文本記述作為戲劇創作的靈感來源以材料支撐,以文本中的信息元素、價值觀念的借取作為存在形態,把文本編碼按照戲劇表演的需要進行改編和置換,其場景的塑造表現出較大的自由性和變異性。如戲劇《王陽明龍場悟道》的“荒山瘞旅”一節以王陽明所作《瘞旅文》為材料支撐,通過王陽明對生死離別的思索以及人生際會的思考,引發龍場悟道的現實可能,劇中人物王陽明有臺詞云:“如今葬人有陽明,他年誰人葬陽明。”借用《葬花吟》的文學藝術元素,突顯王陽明的哀憐與感傷以及對生死的感慨。此處場景中的《葬花吟》已經脫離了林黛玉的自憐自艾,而是被灌注了剛健開朗的生命力量,對生命存在的思考引導王陽明對主體存在意義的把握,他首先思考的是“人”的本質存在與內圣人格之關系,心體作為理性與感性、形上與形下、先天與后天、普遍與個體等維度的交融,內在地規定了精神本體與個體存在的統一,個體的發展受到本質的規定和制約,但作為個體的存在本身又有多種可能,于是,王陽明“以心體轉換性體,同時蘊含著從形而上的本質向個體存在的某種回歸。”[3]“人”與“陽明”都是個體存在的道德主體,生命的消逝并不構成“人”作為主體類別的存在意義和現實價值。文學藝術的借取在一定程度上“軟化”了歷史記述中王陽明作為獨立個體的棱角,為王陽明心學思辨的哲理性闡釋空間提供了藝術氛圍。
二、心學體悟的鏡像化戲劇語言
以“場景”建構為代表的戲劇語言在藝術形式的展露中貫徹心學體悟的過程,鏡像化的戲劇語言分解為哲理的思辨。
(一)王陽明心學視域下的言意關系
語言作為對世界的指涉具有一定開放性、即時性,作為此時此刻的此在,語言在“在場”中充分營造了屬于自身的意義世界,它可以是主體自我思考的自行指涉,也可以是社會交往的即時溝通,言說成立的可能建立在主體間共同的存在基礎上,具有人的認知功能、交流功能、思想需要,既是言說存在的前提,也是本體存在的體現。因此,言說與存在的關系成為本體存在的一個主題。在王陽明的思想體系中,“致良知”作為成圣的過程和依據同時也涉及名與言、思與說的邏輯關系的思辨,他認為“致知”的過程是一個無法言說的過程,因為“心之精微,口莫能述”。[4]心體需要言說把握,但不能限制于言說構成的語意空間,這種語意空間并非明覺的主體,心體需要達到更理性的明覺,這樣,王陽明將言說置于主體的底層,“作為一個‘說不得的過程,自悟具有超明言的性質,而所悟的對象(心體)則亦似乎被置于超名言之域。”[5]心體具有能知的功能,但其所知必須實現主體明覺的內在超越,也即將外在言說中的一般道理轉化為內在精神主動知覺的完善,言說世界的混雜和繁瑣遮蔽了純粹的心體感知,言說越是活躍詳細,其對心體也就越是疏離,王陽明在《五經臆說序》中明言:“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圣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與糟粕耳。”[6]他對“道”與“言”關系的理解與莊子、王弼等人的思維方式是一致的,認同對“道”的超越語言文字的體悟,然而,與一般意義上的“道”不同的是,王陽明的“道”更多地指向心體良知的德性,當主體的明覺意識修養為道德的智慧境界,境界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主體認知活動的出發點和立腳點,參與到知識、文化、思想、信仰的建設活動,由此,主體又在言說構成的歷史世界中得到顯現。
(二)戲劇場景敘述:作為心體主宰的物質外化
1.《巖中花樹》的場景敘述
影視戲劇藝術是視覺與空間的藝術,需要場景與人物的配合傳遞文化信息、情緒體驗,戲劇藝術內在地包含自身的“道理”,這種“道理”不是《老子》式的“無名沉寂”,也非《莊子》式的“順化自然”,其“道理”是真實存在于社會人生、行之有效的普遍規范,以普遍規范的樹立為核心,外在地依托于戲劇中的不同人物形象、不同主題、不同情感得到表現,戲劇的“本心”包裹在被外化、外放的諸多復雜形式和客觀規定之下,“場景”要素的運用便作為“本心”的具象化而得到實踐價值。“場景”的塑造遵從人物關系、社會歷史、形象性格的發展脈絡,制造一個故事發展及人物成長的基點,以“點”帶“面”,將人物在場景中的動作言語置于人物社會關系下進行再現,通過人物活動的動態基礎賦予角色間的對話、行為在時間線性模式流動下的動態性,其動態性具體展露為人事關系的倫理道德規范,最終傳達出精神向度的“德性”自覺傾向,引起人們對劇中人物言行、境遇的深刻思考,引發對人類生存問題的普遍自覺。以網絡電影《巖中花樹》為例,影片選取了王陽明被貶龍場、石棺悟道以及格竹致知等具體情節構建場景,將王陽明傳記資料中文本記述的貶謫、悟道、講學等人生經歷進行戲劇性處理,把王陽明的言語、動作分解到舞臺的環境設置、物件擺設,如洞室、石山、庭竹等具象性鏡頭信息中,帶出王陽明行為動作的情節內容,通過聲色光影的視覺力度滲透到觀賞者心靈,突顯出王陽明求道之不易、為人之堅貞,引發情緒共鳴,在審美情緒的調動下與王陽明影視形象一道感悟“心體”的力量。
2.“場景”模式語言化
“場景”的塑造是間接化的符號語言運用,“場景”塑造作為必要的情感傳遞方法,其在戲劇表演中的敘述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場景呈現故事情節發生的時代背景;第二,展現故事情節中的社會關系,包括人物與人物之間的親疏遠近、矛盾沖突等;第三,講述作品中發生的事情,包括過去的、現在的和將來的;第四,強化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等等。”[7]顯然,在“場景”的視域中,“情節”“關系”“矛盾”“性格”等抽象性要素被分解到場景的設置中,“場景”在運動中的影像里以畫面為語言,也即“鏡頭語言”,除了像《巖中花樹》般把“格竹”等片段處理為空間場景的方式外,還通過具體物質的空間顯現訴諸觀眾視覺,以此表明人物與事理間的關聯性。影視戲劇也以空白畫面為手段塑造形象,“空鏡頭”實際上是一種藝術化的鏡頭語言,與真實立體的空間場景相比,《巖中花樹》的“空鏡頭”語言比《王陽明年譜》更加具有審美感,激發觀眾思考,這便與文本記述的意境營造產生“同構”聯動,它們都以虛幻的筆法生發韻味。文本記述依靠語言關系塑造形象、傳遞情感,語言文字的認知性、語義的模糊性就決定了其信息傳遞的模糊性、多義性,當基于文本記述的人物形象進入戲劇表演的空間呈現,文本的象征意蘊與審美情調則展現為波瀾壯闊、真實可感的心理沖擊,色彩構圖和光影聲色成為替代語言文字的另類符號,其最終目的的指向卻是“殊途同歸”,通過場景符號形式傳遞“真理”與道德體驗,把認“知”變成真“識”。
三、王陽明文本形象與戲劇形象的差異
王陽明的藝術形象來源于文本記述的文化空間,二者具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和傳播需要,然而戲劇藝術的表演場域與文本文獻的語言場域之不同,邏輯上證明了王陽明文本形象與戲劇形象的差異存在。
(一)詮釋等級的傳統差異
傳播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環境下都會引發傳播觀念的變化,隨著文化認知以及立場態度的需要而改變。中國古代的秩序觀念、等級意識滲透到社會文化的各個側面,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特征就是等級性的延展。戲劇藝術誕生初期便成長于敘事結構、表現方式和審美功能等文化構建的需要,從本質上來看,影視戲劇是民俗藝術形式的極端發展,繼承了民俗文化中粗放、親切而富有感染力的特質,而依托于文本記述的傳播環節則以古代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文化為底蘊,二者在詮釋領域具有鮮明的等級差異。戲劇藝術脫胎于民俗文化活動,延續“儀式”的組織形態與信息傳遞功能,發展為民俗生活的主要力量,原始“儀式”遺留下來的通過祈求神靈獲得生命的安養、欲望的滿足等歷史信息正好吻合普通民眾的一般需求,以戲劇藝術為代表的民俗文化活動在民俗文化的歷史活動中主體通過儀式得到精神的啟示,引導社會成員的心理活動及行為規范,通過民俗活動的歷史性、地域性和傳承性體現民間社會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從而創建了一個與知識分子文化空間不同的社會民俗文化空間。基于文本記述的王陽明形象被視為傳統儒學心性復古的代表,以傳統精英文化的視域為基點,在后學的“造神運動”與歷史境遇下走向了神化形象的歷史進程,王門后學以傳記文本、畫像銅身、經典文本、從祀孔廟等一系列活動進行盛大的“造神運動”,最終確立王陽明的神化形象與神圣地位;被戲劇化的王陽明形象找尋民俗信仰的精神家園,塑造親和、通俗、貼近民眾生活的王陽明形象,更能引發情緒共鳴,傳導精神信息。不同傳統、不同立場的文化態度在理解、表現、闡釋形象的過程中具有各自的復雜性,當文本記述的語言文字通過聲影藝術得到傳播時,也導致了二者在文化性格、社會需求上的融合,其主導的文化觀念也在悄然改變,于新的影視戲劇形象中建構新的時代精神和審美理想。
(二)敘述視角與時空差異
在王陽明的傳記年譜等相關資料中,文本記述的時空以王陽明人生經歷和明代歷史的推進為內在邏輯,而戲劇藝術為了表演以及情感表達等需要突破了一般歷史視域的時空限制,在藝術自覺的邏輯下靈活安排時空要素。影片《巖中花樹》中“格竹”事件被分解為王陽明與小仆躺石棺、蓋草席以及在石棺中思索等場面,影片將王陽明在龍場悟道時的系列要素移借到“格竹”事件中,在錢德洪等后學所編撰的《王陽明年譜》中王陽明“格竹”時方15歲,而影片突破時空限制將“格竹”作為王陽明心學思想發展的重要轉折點,突出心學思想體系中“本體”與“功夫”之關系的探討,在戲劇中為王陽明“格竹”的歷史時間的真實感需要服從矛盾張力的原則。又如話劇《此心光明》采用了敘述體戲劇的方式展開全劇敘事,將敘述主體從王陽明延展到其親屬、學生、仆從,又借鑒西方戲劇“唱詩班”的形式在劇中加入了歌隊的吟唱,戲劇形式的安排將敘述功能以及敘述視角分散到不同的人物,在每個人物的獨立事件中轉換了敘述關系,使敘述者走出原定的時空關系,同時也改變了原先文本記述的看讀關系,強化了“聽導”的視聽關系,文本記述中較為客觀的閱讀視角被代入到敘述者的意義揭示主導活動中,一切光影在時空序列的安排下都被賦予意義指向,王陽明形象的主體意義參與到不同敘述者的敘述活動中。
(三)受眾心理差異:心學語境的戲劇接受
文本記述作為傳統學術氛圍的再現追求真實、肅穆的知識與史料記載,引起讀者的理性思考,而戲劇化的主體形象則是藝術化的手段,在觀賞中引發觀眾的情感共鳴,帶動觀眾進入一個理想的藝術境界。以姚斯為代表的藝術理論家十分看重讀者對作品的反饋與再創造,藝術創作的完整環節以戲劇表演作為直接呈露性的藝術形式,將人物關系、情節沖突以及社會歷史等元素融合在舞臺的時空中傳達給觀眾,觀眾的期待觀看時的心理狀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舞臺形式的影響,接受主體的觀眾對戲劇信息的反饋促成了藝術形態的最終完成,觀眾總是用全部的心靈和智慧去感受和解讀作品的全部。于是,戲劇影視以活像的展演獲得觀眾的同情,而文字記述則更多地傳遞書寫者的情感和意識,引發讀者的情感體驗。
1.文本記述的閱讀體驗
文本由文字媒介構成,使用固化的約定俗成的符號及意義表現事件和歷史時空的關系,讀者作為孤獨的閱讀主體在文本中獲取信念和知識,在主體自我的干預下形成獨特而個性化的閱讀體驗。同樣面對王陽明文獻的年譜記述,有的讀者會引發好奇心理,有的讀者會感到不真實而拒絕接受,還有的讀者則會深受感染,這既與文本記述的王陽明形象較為神異有關,也受到讀者的知識水平、閱讀能力影響,面對同樣的《王陽明年譜》,深受程朱理學浸染的傳統士大夫可能會自覺地以“性”與“理”的內在邏輯進行閱讀平衡,并且對文本記述的王陽明活動進行反思和質疑,而心體較為開放的士人則更容易進入《王陽明年譜》的閱讀,尋找文本記述中王陽明心體呈露的內在過程,并以此作為知識經驗的習得,內化為閱讀行為的能力積淀。基于文本記述的王陽明形象更多的外化為“良知”主體的思想符號,王陽明形象在不同文獻中的流變,體現了宗教內質結構與神話外在要素的文化意義;同時,王陽明形象“從人到神”的歷史進程也是“神化”王陽明、“神化”心學的歷程,讀者通過閱讀行為進入王陽明的歷史世界,體驗“良知”主體的生成過程,并自覺以“良知”的內在體悟檢視自身的現實價值。
2.戲劇觀賞的心理獲得
戲劇敘事以場景的構筑為紐帶,在場景中展開情節的組接,呈現時空的變化和推移,演員以具體可見的語言神情推進敘事。戲劇藝術必須迎合普通觀眾的審美期待,通過有意味的形式引導觀眾全身心地進入藝術世界,在舞臺與觀眾的互動中激勵審美心態漸入佳境,進入忘我的心理體驗。話劇《此心光明》表現了王陽明獲罪劉瑾、下獄受杖責的歷史事件,舞臺道具、服裝以及演員表演的聯動讓觀眾體會到王陽明的真實痛苦,流露出同情、悲戚的情感共鳴。姚劇《王陽明》直接體現了王陽明在龍場陽明洞中的“悟道”過程,舞臺以石棺的鎖閉為表現形式,安排劇中的王陽明與古圣先賢通靈相遇,在王陽明與圣哲的問答、對話中,較為直觀地還原“悟道”的心理動因及思想活動,觀眾通過人物之間的對話感知到“悟道”歷程及人物思想狀態的發展,省卻了抽象思維的頻繁運用,幫助觀眾更加直觀地把握“良知”心體的核心意念。
結語
在戲劇形象的傳導下,觀眾所接受的是經過選擇、過濾的思想形態,在某種程度上引導觀眾接受戲劇中的王陽明,看到人物的情感和內心的掙扎,這個王陽明已經不再是構造歷史的真實人物,而是迎合當下社會的價值觀傳遞。王陽明戲劇形象的創制通過心理活動的具體展現引導人們對當下現實進行自我反思、自我提升,是現代人精神境界的主動探求,用藝術的眼光和表現方式倡導內在超越的人生追求,保證人類生命主體的永恒存在。
參考文獻:
[1]束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58-59.
[2][3][5]楊國榮.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72,5,177.
[4][6]王曉昕,趙平略.王陽明集:卷四文錄一[M].北京:中華書局,2016:149,742.
[7]張穎.略談戲劇和影視藝術中的敘事性場景[ J ].新世紀劇壇,2018(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