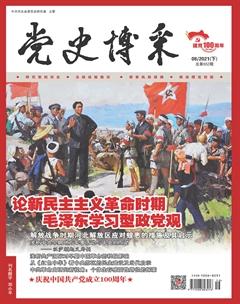淺析中共早期地方軍事活動與中央的互動
[摘要]中共重慶地委領導的瀘順起義,是早期地方黨組織領導開展的重要軍事活動之一,被看作是南昌起義的預演。這一時期,中共中央也成立了以周恩來等為領導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事部)。起義前后,中共重慶地委與中共中央進行了“形”與“神”的互動,推動了大革命運動在四川的蓬勃發展,同時也為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關鍵詞]瀘順起義;中共重慶地委;中共中央;互動
[作者簡介]任小虎(1988-),男,河南平輿人,中共重慶市沙坪壩區委黨史研究室,學士,研究方向:中共黨史。
[中圖分類號] D235[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6-8031(2021)08-0012-04
早在1922年,周恩來就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①1924年10月中共兩廣區委軍事部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軍事工作的開始。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提出在中央設立軍事委員會,開始在中央層面設置軍事機關,并指導包括重慶在內的多個地方省委(區委)陸續建立起軍事組織。
1926年2月,楊闇公、童庸生、冉鈞等人在重慶成立中國共產黨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中共重慶地委),統一領導四川境內的中共黨組織及其活動,直屬中共中央領導。11月,成立以楊闇公為書記,朱德、劉伯承為委員的中共重慶地委軍事委員會。1926年12月初,中共重慶地委領導和組織了四川瀘(州)順(慶)起義,劉伯承擔任起義軍各路總指揮,在瀘州、順慶、合川等地的四川軍閥部隊中發動了一次大規模軍事起義,起義前后持續了半年時間。歷史證明,瀘順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革命武裝、舉行武裝起義的一次勇敢嘗試,是牽制敵人、配合北伐的重大軍事行動,成為黨在大革命時期爭取改造舊軍隊的一個范例,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②
一、中共重慶地委貫徹中央精神的生動實踐
1924年至1927年,以推翻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北洋軍閥為目標的大革命席卷中國大地。1926年7月,中共擴大的四屆二中全會第一次作出關于軍事運動的決議,指出:“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參加武裝斗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并漸次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③中共重慶地委積極貫徹中央決議精神,對在地方開展軍事運動進行了較早的謀劃:如在1926年8月中共重慶地委報送給中共中央的《四川軍事調查》中就詳細記錄了四川各軍閥的槍支概數、防地甚至指揮者性格喜好等;中共重慶地委軍委成立后,即派黨員到瀘州、順慶、合川等地川軍中開展政治宣傳工作,為發動起義打下堅實基礎。對此,中共中央曾高度評價:“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奮斗的精神,更為有別省所不及者。”④
(一)響應國共合作配合北伐戰爭。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早期工人運動中,逐漸意識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僅僅靠工人階級孤軍奮戰是不夠的,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1923年6月,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中共三大決定進行國共合作,次年1月,孫中山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推動形成了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新局面。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共重慶地委與左派國民黨人士密切合作,廣泛動員和組織各階層人民群眾投入反帝反封建斗爭,推動大革命在四川的發展。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確定黨應從各方面準備北伐戰爭。9月,北伐軍進軍武漢時,軍閥楊森派四個師出川側擊武漢,對北伐軍造成了嚴重威脅。為“響應北伐,會師武漢”,爭取楊森易幟,在萬縣,朱德帶領數十名政工人員加緊做楊森部的策動和改造工作,試圖拉出一支部隊,作為一個方面的突破。同年11月,北伐軍殲滅孫傳芳的主力,占領九江、南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瀘順起義有效緩解了北伐軍的西線壓力,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四川軍閥側擊武漢國民攻府的行動。
(二)積極爭取對起義部隊的政治影響。“中國目前是帶民族革命色彩的軍事勢力與反動軍閥武裝沖突的劇烈時期。在帶民族革命色彩的軍事勢力中,客觀上至少可以進行相當政治宣傳。”⑤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軍隊政治工作:如在黃埔軍校中,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等共產黨人就先后擔任政治領導工作,中國共產黨也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
正如劉伯承后來所說:“軍閥們的武器很好,有的軍事技術也很高,但他們還是被我們打垮了。為什么?就因為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有我們這樣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力量。”瀘順起義期間,中共重慶地委積極開展政治宣傳,在部分軍隊中發展共產黨員,大大提高了起義部隊的戰斗力。瀘州起義部隊被軍閥圍困期間,在城內市民和社會各界的積極協助下,多次打退敵軍;為了提高士兵政治軍事素質,劉伯承在瀘州創辦“瀘納軍團聯合軍事政治學校”,并親任校長,選用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執教,培養具有政治素養的軍事人才,力圖將舊軍隊改造成由共產黨領導的新軍隊。
(三)領會中央指示精神靈活開展軍事斗爭。中共重慶地委充分領會中央軍事思想,進行了積極的地方軍事活動實踐。中共在早期即已開始嘗試掌握部隊,如1925年11月,在周恩來指導下,以原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為基礎建立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共產黨員葉挺、周士第分別任團長和參謀長,團設黨支部,連有黨小組,獨立團成為中共領導的一支正規部隊。瀘順起義爆發之時,四川各軍閥部隊近20萬人,而中共重慶地委所掌握和影響的軍隊僅1萬2千余人,發動武裝起義的艱難可想而知。在四川,發動瀘順起義即是中共重慶地委在川中“扶起朱德、劉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軍隊”戰略設想的勇敢嘗試。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統戰工作,第一次國共合作即是在大革命中建立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的勇敢嘗試。中共重慶地委充分領會、貫徹中央統戰思想,利用吳玉章、朱德、劉伯承等人在國民黨及川軍中的影響力,積極開展軍事統戰工作。軍閥內部派系林立、矛盾甚多,中共重慶地委領導人充分利用這些矛盾對其進行分化瓦解,削弱反動勢力,爭取更多支持。瀘順起義期間,朱德、陳毅受黨的派遣,深入四川萬縣開展對楊森的爭取工作,并組織社會各界發動了反對英帝國主義制造的九五慘案的斗爭。
二、中共中央對瀘順起義的指導和幫助
瀘順起義并非是地處西南一隅的孤立斗爭,中共中央對此次起義前的準備工作、起義的進行,以及起義后的經驗教訓總結等,均進行了密切關注及指導。
(一)為開展地方軍事運動提供理論指導。中共中央探索軍事運動的理論及實踐,為地方黨組織提供了理論指導和行動示范。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重要創始人之一的周恩來在1925年第一次東征軍回師途中向黃埔軍校學生作的《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講演,就闡述了軍隊的性質和組織,“軍隊是壓迫階級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壓迫階級的工具”、“軍隊的組織有很重大的意義,是實現我們的理論的先鋒”⑥,為開展軍隊政治工作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之后,中共中央又制定了《組織問題議決案》(1925年10月)、《軍事運動議決案》(1926年7月)等文件,從不同角度對開展軍事運動作了詳細的理論闡釋。這一系列關于軍事運動的方針及政策,構成了中共重慶地委領導發動瀘順起義的理論依據。
除了高屋建瓴的宏觀指引,中共中央還多次對四川軍事運動進行細致的分析和指導。中共中央內部刊物《中央政治通訊》就多有記載:收到中共重慶地委呈送的《重慶來信——中共重慶地委報告四川各派軍閥的動態》(1926年8月3日)和《四川軍事調查》(1926年8月)兩個報告后,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致重慶信——對四川軍閥之態度及工作方針》(1926年8月23日)進行了回復,針對四川軍閥的現狀及特點,就如何開展軍事運動及民眾運動提供了詳細的指導,如“可以插入軍中去作政治宣傳,可以有在舊軍隊中培種新的力量的機會”、“倘若我們把這幫人看得太高明了,過于責望他,過于信賴他,都要發生很大的危險”⑦;在聽取了童庸生報告川中情形后,中共中央當日即作了《中共中央聽童(庸生)同志報告后的結論——關于四川的軍事運動等》(1926年9月10日)的回復,并作了“四川工作現在十分可以發展”的指示;中央軍事特派員王一飛也針對四川軍事工作向黨中央專門報告……
(二)積極爭取對瀘順起義的政治支持。國共合作的政策增加了瀘順起義的政治影響力。中共重慶地委成立之初,地委委員、瀘順起義領導者之一吳玉章受中共中央指示留在國民黨中央工作;1926年7月,朱德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以廣州國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軍閥楊森部開展軍事統戰工作;8月,廣州國民政府批準成立“四川特務委員會”,委員會由李筱亭、吳玉章、劉伯承三人組成,專門負責川中軍事工作;同年10月中旬,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根據吳玉章提議,授劉伯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軍事特派員名義,回四川負責籌劃軍事運動;歐陽欽、陳毅也分別由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區委派到四川協助工作。⑧這些都為在四川開展軍事活動、策劃起義提供了便利。
中共重慶地委與國民黨(蓮花池)四川省黨部的積極合作,增加了開展地方軍事活動的政治合法性。如瀘順起義的總指揮劉伯承,既是中共重慶地委軍委委員,也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軍事特派員及國民黨(蓮花池)四川省黨部特務委員會委員。國民黨(蓮花池)臨時省黨部還成立了“國民革命軍北伐四川國民后援會”,敦促川軍轉向和參加北伐,還主持了同四川各軍閥代表的談判,簽訂《六條協議》,從政治上對川軍加以約束。⑨
(三)為地方軍事活動提供了策應。大革命時期,全國工農運動蓬勃展開,客觀上為瀘順起義提供了策應。如1926年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即開始組織上海工人進行武裝起義,雖然由于條件所限,第一、第二次起義失敗,但1927年3月21日,在周恩來任起義總指揮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下,上海工人成功發動了第三次武裝起義,并成立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1926年9月,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同年11月,毛澤東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指導全國多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
同樣,在四川,黨組織也看到了工農運動的巨大革命能量。如中共重慶地委書記楊闇公就曾講到:“要使四川的革命基礎穩固,不致于為假革命所動搖,應扶助在全川人口百分之八十幾的農民的發展才能得到真實的動力。”⑩1926年底,重慶周邊的南川、涪陵等地黨組織決定聯合抗敵,組成農民自衛軍進行武裝暴動,于次年1月首先攻打南川縣城,并組成以李蔚如、王懋遷為首的暴動總指揮。這些農民運動“作為中共重慶地委直接組織領導的革命運動,不但有力地配合策應了劉伯承領導的瀘順起義,還為革命斗爭積累了可貴的經驗,造就了一批堅強的骨干力量,鍛煉了革命群眾”。?
三、瀘順起義時期中共重慶地委與中央互動的意義
早期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在軍事活動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但面臨復雜形勢還缺乏足夠的斗爭經驗,加上經費、武器不足等客觀條件,導致了瀘順起義等軍事活動的失敗。同時,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為代表的優秀共產黨人通過艱苦努力的工作,不斷開辟軍事斗爭的新境界。
(一)中共重慶地委與中央互動的歷史局限性。瀘順起義時期,中共重慶地委與中央進行了“形”與“神”的互動,但不可避免,這種互動也具有巨大的歷史局限性。從實際情況來看,早期中共中央在軍事工作上的薄弱,客觀上導致了對各地軍事活動的支持不夠。如中共中央軍事部成立之初,由張國燾兼任部長,但是,這時的中央軍事部還只是一個“空架子”,主要是從報紙上搜集軍事情報。?這種局面至1926年9月周恩來接任中央軍事部長后才有所改觀。
針對策劃起義,中共中央雖認識到四川軍閥的不可靠,但未能提出根本的解決辦法;對起義過程中出現的困難也缺乏物質上、軍事上的直接幫助。中山艦事件之后,蔣介石開始走向反共,中共中央未采取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正確建議進行反擊,反而采取妥協政策,中共逐漸喪失了對國民革命軍的領導權。之后,右傾主義逐漸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關于軍隊中黨員組織,不僅在國民革命軍中不發展黨的組織,不便有黨支部,對于其他軍隊,甚至在反動軍隊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黨的支部組織”?。1927年,重慶“三三一”慘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相繼發生,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從實際力量對比上,也難以組織起有力的反抗,更難以對同時期發生在四川的瀘順起義進行實際的支援。
(二)由爭取軍閥易幟到創建人民軍隊,推動了革命的發展。瀘順起義與南昌起義具有漸進深入的武裝革命實踐的歷史邏輯關系。大革命時期,中共黨組織大多在軍閥中進行政治宣傳,爭取軍閥易幟,支援北伐戰爭,可以絕對控制的武裝力量寥寥無幾。由于新舊軍閥的反動性和大量國民黨右派勢力的存在,使得革命的大好形勢下潛藏著反革命的洶涌暗流。雖然瀘順起義和全國的大革命運動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聯合絞殺下走向了失敗,但為黨發動南昌起義,建立革命武裝并獨立自主地開展武裝斗爭提供了可貴的經驗及教訓。
通過瀘順起義和其他早期軍事活動,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張響應了廣大人民的共同呼聲,黨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迅速擴大,黨的組織也得到發展,為將革命斗爭推向新的階段準備了必要的條件。中國共產黨逐漸意識到創建人民軍隊的重要性,開始探索新的軍隊建設思想及實踐,通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等一系列武裝起義,開始走上了農村包圍城市,工農武裝割據的嶄新革命道路。
(三)地方與中央的互動,體現了共產黨人的接續奮斗。1927年3月31日,軍閥劉湘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對四川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實施大屠殺,楊闇公等中共重慶地委主要領導不幸遇難。4月,各反動軍閥結成反革命同盟,對瀘州進行圍攻。瀘州起義軍召開萬人群眾大會,聲討反革命禍首劉湘等,同時加強戒備,積極備戰,多次打退了敵軍的進攻。“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敗。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委會正式決定在南昌發動武裝起義,8月1日,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下,黨所掌握和影響的軍隊2萬余人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瀘順起義領導人朱德、劉伯承、陳毅等與周恩來一起,都成為中共軍隊的主要創建者。
大革命失敗后,瀘順起義播撒的革命火種也并未熄滅。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四川地方黨組織領導了蓬溪起義等數十次武裝起義,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游擊隊及川南游擊隊等,創建了游擊地區;參加了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斗爭,為支援中央紅軍長征作出了一定貢獻。以瀘順起義為例,開展早期地方軍事活動的領導者,不論是去中央,或者就近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都體現了共產黨人的接續奮斗。
四、結語
瀘順起義時期,中共重慶地委未能在起義軍隊中成立黨的組織,對起義部隊沒有絕對控制,個別起義將領關鍵時刻不服從黨的正確領導,直接導致了起義的失敗。南昌起義后,中共中央召開八七會議,毛澤東提出“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1927年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進行改編,提出“支部建在連上”,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瀘順起義雖告失敗,但在當時“驚破武人之迷夢,喚醒群眾之覺悟,影響川局,關系至巨”?。起義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初心的堅守,如楊闇公面對酷刑和威逼利誘時堅貞不屈的信仰、作為起義總指揮的劉伯承“行軍不坐轎,宿營不睡床”的優良作風、朱德在軍閥中進行統戰工作時的黨性修養、周恩來開創軍事工作的艱苦努力、毛澤東對人民群眾的極端重視等,都是新時代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注釋]
①周恩來早期文集(下卷)[M].中央文獻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85頁.
②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第224頁.
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17頁.
④中央局關于最近全國政治情形與黨的發展的報告(1926年9月20日)[M]//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
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17頁.
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74頁.
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70頁.
⑧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瀘順起義[M].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第4頁.
⑨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瀘順起義[M].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第5頁.
⑩中共四川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瀘順起義[M].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第65頁.
?中共四川省涪陵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涪陵地區簡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7年:第45頁.
?雷淵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沿革[M]//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4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第219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3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406頁.
?向時俊致順瀘革命軍電[N].新蜀報,1927-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