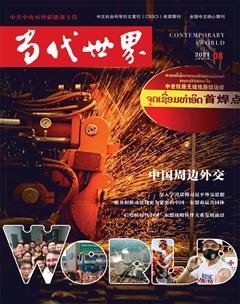瀾湄合作:制度設計的邏輯與實踐效果
盧光盛

瀾滄江(IC photo圖片)
2021年是瀾滄江—湄公河合作(簡稱“瀾湄合作”)全面啟動5周年。5年來,瀾湄國家在瀾湄合作框架下多領域合作取得顯著成果,瀾湄合作機制也成為區域內最具活力的國際制度之一。瀾湄合作強勁的生命力及其賦予區域發展的巨大能量,與其制度設計的前瞻性、科學性和實效性密不可分。
瀾湄合作制度設計的特點
作為新興的區域性國際制度,相較于區域內其他國際制度,瀾湄合作在制度設計上有著鮮明的特點。
一是以構建命運共同體為導向。湄公河地區被視為“制度擁堵”的區域,在區域內眾多的國際制度中,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和湄公河委員會(MRC)是影響力較大的兩個。前者的目標在于推進地區經濟一體化,后者則致力于加強地區水資源管理、推動可持續發展。這些目標決定了二者的制度設計是以功能性、技術性的區域合作為導向,其匹配的具體合作機制更多是問題解決機制和單一部門的功能性合作機制,這也是區域內其他既存國際制度的共性。在瀾湄合作首次領導人會議中,“打造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被明確為瀾湄合作的目標,這一以構建命運共同體為導向的目標,使瀾湄合作從啟動之初即具有超越性。功能性合作及單一部門的一體化和共同體建設是瀾湄合作的階段性目標,瀾湄合作在制度設計上涵蓋了實現上述目標相應的具體機制,同時圍繞打造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建立了相應的制度運行機制,形成了“領導人引領、全方位覆蓋、各部門參與”的合作格局。
二是合作框架覆蓋多領域。以命運共同體為導向,決定了瀾湄合作的框架設計不局限于單一部門或單一領域。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要一環,實現區域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也是構建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瀾湄合作的框架設計即以此為綱,構建了以政治—安全、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社會—人文為三大支柱,以互聯互通、產能、跨境經濟、水資源、農業和減貧為優先合作方向,進一步拓展合作領域的“3+5+X”合作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盡管“3+5+X”合作框架覆蓋的范圍全面涵蓋了既有區域性國際制度所涉及的合作領域,但是瀾湄合作并不是這些國際制度的“替代品”,而是以命運共同體構建為指向的“升級版”制度。
三是大國推動下的共同建設。在瀾湄合作成立之前,瀾湄區域內既有的合作機制多由美日等域外大國推動,域外大國往往通過駕馭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成為這些合作機制的隱形“主導者”,這些合作機制是域外大國隱蔽實現自身利益的平臺,相應的制度設計和安排也更多體現了域外大國自身的偏好。瀾湄合作由中國首倡且積極推動,至少有兩點不同于以往,一是中國作為湄公河上游國家屬于域內大國,二是中國在該合作機制中扮演的角色是“引領者”而非“主導者”。有別于域外大國推行的“制度霸權”,中國的參與體現了負責任大國的積極作為。在制度設計中,瀾湄六國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共擔責任、共建規范、共享利益。

湄公河(全景圖片)
瀾湄合作制度設計的邏輯與成效
瀾湄合作雖是新興的區域性國際制度,但展現出較高的成熟度,這源于其制度設計的嚴謹性和科學性——既遵循了國際制度發展的一般規律,又緊密結合了本區域的歷史和特點。具體來說,瀾湄合作制度設計的邏輯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融匯多重利益的最優分配。共同利益是國際合作得以實現的基礎,瀾湄國家基于地緣的共同利益廣泛而深厚,但是客觀上各國間也存在著發展水平、部分歷史傳統和文化價值的差異,因此現階段各國在國家利益方面既有較多同向的交集,又有部分負向的交集。瀾湄國家在非傳統安全和經濟領域存在較多同向利益交集,而在“水問題”上相對分歧較大。湄公河委員會試圖處理域內“水利益”分配及其衍生問題,但是“水問題”相對復雜,利益分配可選方案有限。因“水”問題未得到很好解決,湄公河委員會進入發展瓶頸期,類似問題也普遍存在于偏重功能性、技術性合作的區域機制中。瀾湄合作的制度設計則充分把握國家利益的多元性和動態性,抓住安全與經濟發展這一地區主要矛盾,兼顧其他次要矛盾,以解決主要矛盾促進次要矛盾的處理,規避某一次要矛盾被過度放大的風險。“3+5+X”合作框架的設計,在融匯多重利益下追求最優分配,使瀾湄國家在關涉利益分配的問題上有更大的回旋空間,合作不為單一部門或單一領域問題(例如“水”問題)所牽絆,避免單一部門、單一領域的利益“死結”導致機制失靈。
二是形式集中化下的軟性約束。在國際制度中,權力相對集中的運行機制設計有利于提高執行力和合作效率。然而,這樣的設計同樣存在靈活性較弱的缺點,此模式下國際制度的發展往往受到主要參與國國內利益訴求變化的影響,英國“脫歐”即是最新案例。不過,權力相對集中的運行機制也是致力于實現一體化的區域性國際制度走向成熟的標志,其存在的缺點主要是國際制度發展與區域合作實際的協調問題。瀾湄合作在運行機制設計方面借鑒既往的經驗,以構建命運共同體為導向,設置了政治級別較高的運行機制,同時分別設立理事會、聯合委員會、秘書處等運行機構。從制度設計的形式上看,權力集中化程度較高。與此同時,瀾湄合作也充分考慮到本區域現實情況,在當前階段實際運行中,形式上權力相對集中的運行機制較少推出“強制性指令”,更多的是作為議事協調機制,通過“共同期盼”進行軟性約束。這一設計既確保了現階段合作機制的順利運轉,又為將來實現更高程度的機制化預留了接口和平臺。
三是規范區域化下的動態包容。在規范建設方面,瀾湄國家將一般性的國際規范與本區域的“區情”有機結合,推進相關規范建設。各國根據既往相對成功的國際制度發展的歷史,在把握規范生成、演進的一般規律下,共同推進合作規范和區域規范的“自然生成”。這一規范并非是預置的,而是基于本區域歷史現實又超越歷史現實、著眼“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而動態生成的,如“湄公精神”和“東盟規范”是“瀾湄規范”的重要歷史和現實來源。瀾湄合作規范“建設”與其說是一種“建設”,不如說是一種“生成”,之所以叫“建設”,更多是為體現其規范建構的“過程性”。這一“過程性”賦予瀾湄合作巨大的包容性與開放性,使其具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能量與活力。
在上述制度設計邏輯下,瀾湄合作在運行中取得了良好的實效。
首先,瀾湄合作基本實現了共同利益與個體偏好有機調和。遵循融匯多重利益的最優分配原則,瀾湄合作在不斷擴大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通過“補償原則”滿足瀾湄各國不同訴求。例如,在水資源利用開發上,瀾湄國家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然而水資源的獨特性又使得各國在開發利用方面存在較大的利益分歧。湄公河下游國家在水資源開發上,普遍追求單方面利益最大化,使得水資源開發利用的問題膠著化。不過,水資源的開發利用歸根結底是發展權益的問題,瀾湄合作提供了多重可持續發展權益選項,部分在“水利益”上“受損”的國家,在“水”之外的合作中獲得的收益遠遠大于在“水”上的損失,這令各國能夠不拘泥于單一的“水問題”而保持較高的合作意愿并持續推進瀾湄合作,其他部門或領域合作的深化又反過來促進了“水合作”及“水問題”的解決。瀾湄合作在處理“水利益”分配上的經驗表明,在利益分配“總體平衡”的條件下,將不同領域的利益打包捆綁進行協商是可以令各方接受的一個較好的利益分配選項。各方在分享合作帶來的利益增量的同時,可以更好地兼顧存量利益的分配。不過這樣的處理方式也是基于瀾湄區域擁有較好的合作基礎,能否由特殊案例推廣為一般經驗尚待觀察。
其次,瀾湄合作為解決區域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議事平臺。這一形式上權力相對集中的制度運行機制,使瀾湄國家有足夠強勁、高效的議事平臺,使區域共同問題在瀾湄合作框架下能夠得到及時有效回應。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發,瀾湄國家在第一時間依托外長會平臺充分溝通,明確“共同應對疫情”,使瀾湄各國在全球第一波疫情沖擊中取得了較好的“戰績”。在瀾湄合作第三次領導人會議上,各方重申“加強公共衛生合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挑戰”,并以瀾湄經驗呼吁各國共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2021年6月8日,瀾湄合作第六次外長會圍繞“團結戰勝疫情,共促疫后發展”主題,進一步明確了未來瀾湄國家抗疫合作的行動內容,為瀾湄區域徹底戰勝疫情奠定了堅實的合作基礎。
最后,瀾湄合作與其他國際制度形成良性互動。基于規范歷史的、本土的、指向未來的“過程性”建構,瀾湄合作具有極高的包容度。瀾湄合作不是域內其他國際制度的“替代品”,也不是對東盟的分裂,而是對既有合作的升級和對東盟共同體建設的補充。作為瀾湄合作的重要推動者,中國始終注重推動瀾湄合作與域內其他國際制度的對接與合作。中方表示,要繼續加強各機制交流互鑒,推動瀾湄合作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三河流域機制、湄公河委員會等機制間的交流合作。2018年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達成的《區域投資框架》涉及200余項重點項目,其中三分之一與中國直接或間接相關。2020年10月,中國水利部和湄公河委員會簽署了《瀾滄江全年水文信息通報協議》,兌現了瀾湄合作第三次領導人會議所作出的相關承諾。打造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使瀾湄合作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開放的地區主義,瀾湄合作與域內其他國際制度總體上形成了良性互動。在瀾湄合作的發展帶動下,瀾湄區域正逐步形成制度競合的互動模式,即制度競爭與制度合作相融合,這一模式既有利于克服制度競爭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有利于避免單純制度合作產生的效率低下問題,促進域內各國際制度實現共贏,進而實現區域的整體繁榮。

2019年4月16日22時,一輪明月懸掛在湄公河上空。由中國中鐵承建的中老鐵路老撾瑯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橋正在緊張施工。(IC photo圖片)
瀾湄合作制度設計的啟示
瀾湄合作取得的成效檢驗了瀾湄合作制度設計的有效性,瀾湄合作的階段性成功也為未來區域性國際制度的創設帶來諸多啟示。
第一,以發展為導向協調利益關系。在全球化時代,各國發展離不開與外部世界的交流與合作。共同利益是各國合作的基礎,而各國對個體利益與合作收益關系的認知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際合作的成敗,決定了一項國際制度的興衰。國際合作和國際制度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往往源于參與國片面強調某一部門、某一領域的個體利益。瀾湄合作的成功經驗表明,發展是全面的而不單單是物質層面的,增長也是全面的而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以綜合發展為導向拓展多領域共同利益的制度設計,可以超越單一領域、單一部門問題的“死結”,要在解決問題中推動發展、在推動發展中解決問題,進而促進國際制度良性可持續發展。
第二,循序漸進推動機制化。機制化程度是國際制度發展水平的重要檢驗標準,合作政治層級和相應機構的設立則是機制化程度的重要檢驗指標。瀾湄合作的經驗表明,在推進國際制度機制化的進程中,不妨采取“動靜結合、先易后難”的策略。“靜”,即高標準地創設運行機制,預先建立機制化的運行機構,為推進國際制度機制化預埋“靜態的”路線接口;“動”,即機制化的過程可以是“試驗性”的動態過程,在“靜態的”運行機制下根據時間、空間的條件,動態、彈性地調整機制化水平,根據不同的時空環境,既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進三退二”;“先易后難”,即優先在低政治敏感度領域實現較高的機制化水平,在高政治敏感度領域適度推后機制化日程,待合作得到深化后再根據參與國意愿陸續推進機制化建設。
第三,以多中心治理方式促進區域合作。區域性國際制度是區域治理的產物,區域治理針對的大多是共性問題,因此區域性國際制度具有國際公共產品的屬性。以往的區域性國際公共產品主要由實力較強的某一大國供給,其生命力也嚴重受制于該國,或面臨“私物化”的風險,或由于供給國對自身提供公共產品收益的認知變化而面臨供給的不可持續。瀾湄合作的經驗表明,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創設的區域性國際制度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下共擔責任、共建規范、共享利益的多中心治理可以保證參與國的“主人翁感”和“獲得感”,從而為區域性國際制度注入多元的動力,同時也使區域性國際制度猶如“雙發戰斗機”一般,不因“單發”的失靈而失效。

中國路橋承建的柬埔寨11號公路改擴建項目位于柬埔寨中部,連接磅湛和乃良兩個重鎮,是柬埔寨放射型交通廊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柬埔寨經濟社會發展和深化中柬友誼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中國路橋圖片)
當然,瀾湄合作在制度化機制化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優化空間。未來瀾湄合作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制度優化設計:一是進一步聚焦合作議題。“水”是瀾湄國家的重要合作紐帶,以往水資源的分配成為瀾湄國家合作的“痛點”,也是域外勢力挑撥瀾湄國家關系的切入點之一。隨著瀾湄國家多領域合作不斷深化、合作面不斷擴大、合作基礎不斷夯實,參與國可以在共抗新冠肺炎疫情營造出的良好合作氛圍下,借水文信息共享帶來的水資源合作新契機,主動推動合作議題再聚焦,將“痛點”打造為“亮點”,圍繞“水合作”推動相關合作再深化。二是進一步推動機制的差異化發展。在“3+5+X”合作框架下,當前瀾湄合作在多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下一步可以適時推動各領域有差異地提升機制化水平,倡議各國率先在諸如衛生、教育、環保等領域探索創設具有較強約束力的實體運行機構。三是進一步強化制度對接。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是唯一得到域內所有國家正式確認的區域命運共同體,這為區域內國際制度的對接奠定了堅實的共識基礎。瀾湄合作在多領域與域內其他國際制度存在較大的合作和對接空間。未來參與國可重點采取“下沉”策略,以項目對接為起點增進各制度間對接程度,從項目對接層面入手淡化各制度間的“異質性”,降低對接的早期阻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不斷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六國的共同努力下,瀾湄區域整體保持了良好的發展態勢,瀾湄合作也發展成為區域最具活力的新興國際制度之一,為其他區域推進多邊合作提供了國際制度創設的模范樣本。瀾湄合作的活力源于其良好的制度設計,但從根本上講,更源于其“初心”——打造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進而建設周邊命運共同體,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斷變為現實。
本文是2017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與瀾湄國家命運共同體構建研究” (項目編號:17ZDA042) 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