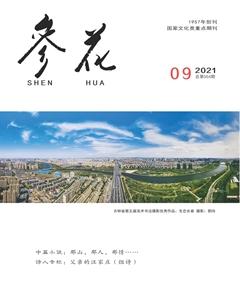淺析電影鏡頭下舞蹈語言的藝術表達
李順陽 梅耀元
摘要:伴隨時代的進步,新媒體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電影鏡頭使舞蹈煥發出新的活力,大量的舞蹈電影、舞蹈紀錄片、舞蹈電視節目等新形式百花齊放。“鏡頭下的舞蹈,舞蹈中的電影”,在鏡頭下舞蹈與媒體的融合與磨合產生了一種新的語言表達方式。無論是DV8身體劇場的舞蹈影像作品還是BBC的影像舞蹈計劃,它們都更加趨近于“影視”作品。筆者通過整合鏡頭基本語匯與舞蹈藝術相通之處的臨界點,進行一次更加趨近于“舞蹈語言鏡頭化”的探究和解構。
關鍵詞:舞蹈語言 鏡頭 電影 藝術表達
一、電影鏡頭的選擇
陳凱歌認為“電影是導演的藝術”,鏡頭是觀眾的眼睛,它可以帶著觀眾進入不一樣的世界。在電影藝術中,畫面的角度對于導演拍攝一部電影是至關重要的,例如導演婁燁獨愛“手持攝影”,往往想表達的是一種氛圍感而特意忽略故事線本身,因為過于“先鋒”所以很多觀眾不買賬,但這種實驗藝術著實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存在。第五代導演所拍攝的鏡頭角度和第六代導演的鏡頭角度截然不同,光影畫面構造、位置關系以及情感傾訴的方向都大相徑庭。視角的變化會直接、間接地滲透觀眾的心理,可作為調節氛圍的一種手法。導演要通過畫面與觀眾架構橋梁,就要去考慮怎樣才能讓觀眾真正理解而不是曲解,這在舞蹈藝術編創中也是值得認真探索和研討的。
眾所周知,電影中常見的六個經典角度分別是:平角、仰角、俯角、正面角度、側面角度、背面角度。常見的鏡頭運動又分為:推、拉、搖、移、跟、升、降、變焦等,這二者結合使用的頻率極高。但也有例外,電影《芳華》中戰爭畫面長達6分鐘的一鏡到底就是極為可圈可點的表達方式。在電影《誤殺》中更是將“蒙太奇”這一鏡頭剪輯手法進行全方位闡釋。影片中一個特寫鏡頭只有主人公在看電視,電視上正播出肖申克出逃的一個片段,接下來另一個關鍵角色被全景鏡頭帶出,李維杰說:“看過一千部電影,就會發現世界上沒有離奇的事情。”此時鏡頭拉近加以光影凸顯,快速拉成一個遠景,使觀眾準確捕捉到兩人立場的對立,這正是導演手法的高明之處。劇情中鏡頭角度的不斷變化加上光線明暗對比形成了平行時空蒙太奇畫面,在剛剛好的時間點加以留白,給觀影者一次恍然大悟的震撼感。同理,在舞蹈藝術中光與影的藝術呈現也極為重要,燈光舞美能夠使舞蹈在最終呈現上再提升一個層次。電影中所有的鏡頭都意味深長,脈絡清晰,結局也不落俗套。《誤殺》的成功不是一個偶然,劇情、配樂、演技和臺詞等都可以是一部電影成功的因素,而《誤殺》關于鏡頭的選擇正具備了這些因素。
二、舞蹈與鏡頭“璧合”的趨勢
舞蹈作為一種空間流動的藝術,在早期人們通常采用刻畫拓印的方式去記錄,隨著古人智慧的不斷進化,他們對舞蹈的記錄已經不局限于刻畫壁畫、舞俑等方式,除手口相傳外,逐漸形成了舞譜等專業化文字繪畫記錄方法。盡管能夠得以傳承,但仍有珍貴資料并沒有完全得以記載,只能任其流傳于坊間逐漸遺失,后人只得借這短短只言片語去試想前人之風姿。
時至今日,新媒體時代賦予了舞蹈以新的活力和記錄方式。簡單的媒體鏡頭就可以把復雜的動作、律動、音樂等留存下來。舞蹈藝術與鏡頭藝術的世紀相遇,二者理所應當地成了一種共存的關系。在這段關系中,鏡頭為舞蹈提供延續生命力的保障,同時,鏡頭也得到了舞蹈反饋于它的獨特魅力。早期舞蹈影像所呈現的大多是“一鏡到底”式的樸素鏡頭,沒有影像剪輯手段的跡象,只起到了記錄的作用。雖然在畫面美感上過于單調,但它的確能夠記錄下最純粹的瞬間,不曲解舞者所呈現的動作狀態并具有復盤的價值意義。舞蹈影像的出現能夠使舞者直觀地感受自己在動作技巧上所存在的問題,以便做出調整。這便是舞蹈影像的雛形。
在這之后出現了“電視舞蹈”“舞蹈紀錄片”等新興媒體形式。舞蹈界最具標志性的莫過于《舞蹈世界》,1999年在中央電視臺綜藝頻道推出了第一檔舞蹈綜藝節目。《舞蹈世界》第一次打開了舞蹈的區域性限制,以一種全新的傳播方式去使廣大觀眾了解舞蹈藝術,使舞蹈離生活不再遙遠。此后,大量舞蹈綜藝在市場涌現。近年來出現的《舞蹈風暴》更是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它利用了“360時空凝結技術”,使舞蹈在技術的加持下以的方式輸出。《舞蹈風暴》不僅使世界上的舞者都能因此建立聯系,更是拉近了舞蹈與觀眾的距離。2003年,由彭文淳執導的舞蹈紀錄片《歌舞中國》講述了年輕舞蹈人的追夢路程,它以獨特的鏡頭語言鏡頭視角來還原那個時代舞蹈傳播停滯不前的現狀,把中國“新舞蹈”傳播的本來面貌完完整整地公之于眾。
舞蹈紀錄片的出現見證了一個時代舞蹈人的堅韌與執著,它已經不是冷冰冰的影視資料,它承載的是幾代舞蹈人最真摯無華的熱愛,鏡頭就是數字化時代賦予舞蹈藝術最好的禮物。
三、舞蹈藝術“鏡頭化”
筆者在前文提到,在電影藝術與舞蹈藝術相融合的產物中大多是以影視鏡頭為載體把舞蹈影像寓于其中,其中也包括AI等數字科技所涉及的“動作捕捉”文化產品,這類“融合技”大多應用于3D動漫或CG奇幻電影當中。而筆者所提出的舞蹈藝術“鏡頭化”則更加趨向于“舞蹈藝術導向型”,通俗地說即“以舞為主,以影為輔”,讓舞蹈來作真正的載體。這里筆者將以韓真、周莉亞編導作品《永不消逝的電波》為例,來闡釋“鏡頭下的舞蹈,舞蹈中的電影”。
1958年橫空出世的諜戰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在播出后曾轟動一時,今時今日依舊被奉為最經典諜戰影片,很多電影導演和話劇導演曾嘗試去翻拍它,以使其精神一直代代流傳。但2019年秋天,《永不消逝的電波》以舞劇的形式走向劇場,這在舞蹈界無疑是一次不小的轟動。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因其已經達到一個高度難以超越,換句話說,提及“瀟湘妃子”人們立刻會想起名著《紅樓夢》,一旦在腦海中形成概念就很難去改變。一部深入人心的紅色題材作品往往給觀眾前期灌輸鋪墊良多,一部家喻戶曉的影視作品被作為舞劇搬上舞臺,真的很難讓觀眾買賬。但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做到了。
個別人寧愿去電影院看一場普通的商業片,也不愿意坐到劇場去欣賞一場舞劇、話劇,當然這也涉及大眾喜好問題。藝術本身就帶有雅俗共賞的獨特性質,需要在劇場中表現的藝術作品,所有的表達方式、表現形式不應只是展示,或者說不能只停留在表演層面(傳統藝術京劇等除外),電影受眾廣泛的因素之一就是導演通過作品去與觀眾交流溝通。漢斯·羅伯特·姚斯提出的“接受美學”中講到藝術家通過藝術作品來向受眾進行闡釋,接受美學的落腳點就在觀眾身上,藝術作品因為有觀眾欣賞才具備了它存在的意義。《永不消逝的電波》不僅做到了使“鏡頭”現于舞蹈之中,更使觀眾看懂舞劇從而達到了以心傳心的審美升華。
電影鏡頭藝術經過百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一門具有獨特魅力的美學藝術,鏡頭語匯也是它與其他各門藝術間區別的形式和特點,導演通過鏡頭來訴說,觀影者透過鏡頭來傾聽,這與舞蹈并無二致。韓真、周莉亞的“鏡頭思維”早在《沙灣往事》時已初顯苗頭,運用大型裝置懸吊式屏風去分割畫面鏡頭,使舞臺出現多個時空。它把電影剪輯手法“蒙太奇”融于舞劇之中,前文中提到的電影《誤殺》中就包含多重蒙太奇鏡頭剪輯手法。蒙太奇作為一種鏡頭剪輯方式具備兩大功能,分別為敘事手段和表意方式。其中包括敘事蒙太奇、表現蒙太奇和理性蒙太奇,每個手法下面還包括平行、交叉和顛倒等諸多形式。開場的“傘舞”就運用了蒙太奇思維,黑色的傘由形色各異的人群撐起,錯綜起伏的傘一舉一落,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借助舞臺調度,把演員變成流動的道具去構成一個新的畫面。這與《沙灣往事》中的傘舞天差地別,《沙灣》的傘被嶺南女子的舉手投足、一顰一笑演繹出婉轉柔腸的綿綿情意,而《永不消逝的電波》則是步步為營,暗藏殺意。舞劇高潮部分編導運用了交叉蒙太奇的方式去分割舞臺,舞臺被劃分成兩半。上場口半邊表現的是李俠的家被間諜搜調后的畫面,舞臺上這時放出鐘表滴答的聲音,時間在倒流一切恢復到間諜未來之時,而此時另一邊妻子蘭芬正坐著黃包車隱匿于舊上海的阡陌巷道,緊接著舞臺畫面靜止,只有蘭芬慢慢從黃包車上站起。她發現面前的黃包車夫居然是搜查她家的那個間諜!蘭芬害怕極了,她顫抖地握住手中的槍“砰”——她槍殺了這個間諜。這時觀眾因為這個絕妙的反轉而沸騰,舞劇的“愛國情懷”引起了觀眾的共鳴。
《永不消逝的電波》不僅僅是一部舞劇作品,它更是舞蹈語言鏡頭化的一種趨勢。在今天這個文化多元、藝術盛行的時代,舞蹈藝術要想走向更寬廣的舞臺,就不能故步自封、凝視回望,舞蹈藝術理應積極吸收和借鑒其他各門各類藝術的特點與相通之處,來豐富充盈自己。如此,舞蹈藝術的明天將會更加輝煌。
參考文獻:
[1][美]史蒂文·卡茨.電影鏡頭設計:從構思到銀幕[M].井迎兆,王旭鋒,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
[2][澳]肯沃斯.大師鏡頭[M].魏俊彥,譯.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3.
[3]張蓀.鏡頭中的舞蹈——淺析舞蹈在鏡頭中的二度呈現[J].舞蹈,2013(03):20-22.
[4]凌繼堯.藝術鑒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作者簡介:李順陽,男,專科,吉林藝術學院,教授,研究方向:舞蹈編導與教學;梅耀元,女,碩士研究生在讀,吉林藝術學院,研究方向:舞蹈編導)
(責任編輯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