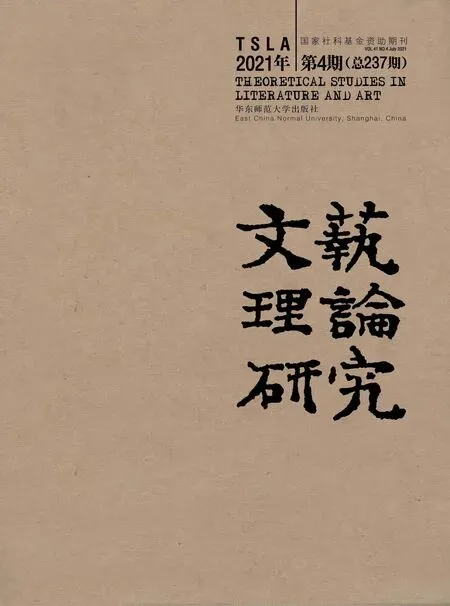王世貞的“文人”身份認同及其意義
熊 湘
古人對“文人”一詞的運用極為廣泛,在史家、儒者、官吏的評價中,“文人”逐漸凝結一些負面含義,衍生出一代代論者討論不絕的話題。文人無行、文人無用等言論在古代典籍中屢見不鮮,成為古人對文人的常見認知方式,此可視為文人之“污名”。儒學、德行、世用、際遇是文人“污名”產生的四個主要領域。如果僅把這些污名當作古人對文人的偏見,那為之辯駁也就成了理所當然之事,從中我們并不能挖掘出多大意義。遠比話題是否屬實更重要的是話題傳播的思想動機、輿論效應,及其與當事人處世心態、身份認知、創作主張之間的相互作用。換言之,只有關注到文人直面身份定位時對污名集中反應、辯駁的過程,才能揭示其根植于社會政治土壤的獨特意義,此類文學批評話題的現實效用和內涵才能全面展示。在搜檢材料的過程中,我們將注意力集中于明后七子的核心王世貞身上。縱向來看,王世貞及其周圍士子對文人身份認同的表達與書寫,對文人污名的反應與辯駁,無論在密集度上,還是強烈程度上,都是極少見的。更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貞等人的文人身份認同直接關乎其處世心態、文學思想和共同體意識,且與中晚明政治環境、思想潮流、文壇格局密切相關。文學批評話題所激起的群體效應,及其尚未被重視的文學史、批評史意義由此能夠得到清晰的認識。故本文以王世貞為中心,探討其文人身份認同和群體意識,并揭示其意義。
一、 “文人無用”觀念下的辯白及心路歷程
嘉靖二十六年,王世貞進士及第。當時聚集在京師的大都是像他這樣的新晉進士,傾心于詩文創作,時常結社唱和,“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張廷玉7378),頗有文人習氣。由于初入仕途,政治上尚未大展身手,這一批已被打上文人烙印的士人不免在吏治、世用方面遭到質疑。王世貞就曾受到“文人少年,不習為吏,第飲酒賦詩為豪舉耳”(王錫爵160)這樣的評價。即便多年后,能聲著于都下,士人仍有“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陳繼儒199)之嘆。因此,我們首先要考察的,就是王世貞對這些批評的反應。
王世貞考中進士不久,便為將要到新喻任知縣的李先芳作序。文中提到:“[有人認為]詩人之累,多高曠,少實,好怪奇而不更事。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者,彼以為必有。而至其所自得,以為斷然而必可行者,乃不可施之于舉步。”(《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32)以詩人疏于吏道,認為李先芳不堪新喻之任。對此,王世貞從兩方面予以反駁。一是強調《詩經》中有大量反映民事、治道的詩歌,足可為吏治之用。他說:“是故豳風,詩也;周公,詩人也。”(《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32)試圖為詩人從政尋找強大后盾。二是指出李先芳既然能以殫精竭慮的態度來作詩,同樣也能以殫精竭慮的態度來處理政事。李先芳赴任后,王世貞又聽聞不利于李氏的傳言,他不予置信,并在《送孫元之明府之新淦序》中重申前言,批駁“以詩厲政”之說。
嘉靖三十二年,蔡汝楠在京師與王世貞相見。他與唐宋派王慎中、唐順之交好,文學主張也相投契。王世貞在寫給李攀龍的信中,提及蔡汝楠對李、王的責難,以及王世貞的反駁。當時李攀龍剛出守順德,蔡汝楠以李攀龍為文人,“易事自喜,宜不稱為守”(《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47),其中暗含文人不善政治的觀念。王世貞通過《史記》《漢書》在辨風土民俗、敘循吏等方面有益于治理郡國,政事與文章無二,政事屬于一時,而文章乃萬年之業等主張,對蔡汝楠之論予以堅決的辯駁。
這幾次辯駁發生在王世貞中進士后的頭幾年,我們除了看到他對朋友的維護,還能感知他所堅守的文章本位、文人本位的立場。王世貞受家庭背景影響,懷揣仕進之心。初入仕途,風華正茂,對文人用世抱有積極的心態和強烈的愿望,深信文人(詩人)能夠勝任吏治。細細分析論辯的內容,我們會發現王世貞的反駁完全避開了重點。對方立論點是文人因習性不佳,不能擔當官職。王世貞閉口不說習性問題,抬出《詩經》《史》《漢》,講了一通“周公詩人”“文章不朽”等高標獨立的話。他對文人不善吏治說法的反駁停留在理論層面,具有些許不切合實際的理想化色彩。
上述理想化認同方式并未維持多久,我們將其與《喬莊簡公遺集序》相比較,會發現明顯的變化。該文約作于嘉靖四十年,開篇言成化弘治朝重文偃武,喬宇從學于李東陽、楊一清,又與李夢陽、王陽明相切磋,善為古文辭。用簡明的語言勾勒出一個文人形象。接著說喬宇任吏部郎中,轉而認為他“有大臣風業,不以文士少年目之矣”(《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153)。隨后又言喬宇在任職期間喜為詩文,多游歷題詠之作,于是“稍復疑喬公文士,少實用”(《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153)。在此疑問下,作者敘述喬宇的功業,將其與立功西北的楊一清、平定寧王之亂的王陽明相提并論,并言“而后文士之用可知也”(《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154)。王世貞將對喬宇文章功業的介紹穿插在文人身份認同的邏輯理路中,用喬宇的實際行動來證明文章與政事可以兼備,而不再像早期那樣借助經典立豪言壯語。“文人-世用”的敘述套路在古代詩文集序中雖不少見,但王世貞秉持文人立場,以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多重轉折來推出自己的主張,其思路和用心都較為特別。這種有意為之的敘述模式突出了傳主在文人與政事(實用)之間的反復回環,甚或揭示出涉世多年的王世貞面對“文人無用”的傳統說法時,內心的體認和思考過程。
對文人世用描述的前后不同,折射出王世貞經歷世事之后的心態變化。就在為喬宇集作序的前幾年,王世貞遭遇了不少打擊。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韃靼兵多次入侵,王世貞之父王忬因戰事不利而被停俸、降職。加之王氏父子與嚴嵩矛盾加劇,王世貞仕途受挫,心里惴惴不安,作《挽歌》三首,說自己“預探所遇,以待叵測”(《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7冊285),序首云:“在昔文章之士多不待年,昆岡一炎,并命玉石。”(《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7冊285)大有借古人之際遇,抒發一己感慨的意味。嘉靖三十八年,王忬論罪下獄。王世貞設法營救卻又無能為力,頓生心灰、挫敗之感,在寫給俞允文的書信中深有感慨地說:“虞昃日之將逮,悵尋壑之無機。嘆文人之鮮永,測功業之難終。”(《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9冊157)對文學與功業雙美的強烈渴望,在現實遭遇面前變成無可奈何的喟嘆。王世貞將自己視為文人,他于人生波折、宦海浮沉中的深切體悟,與其對文人的身份認同密切聯系,使文人世用與文人命窮綰結成一對不可分割的話題。由此催生出“文章九命”的話題也是理所當然的。
王世貞的“文章九命”,實際上是“文人九命”。現今能看到的《文章九命》主要有兩種版本: 王世貞《藝苑卮言》本、晚明華淑《閑情小品》本。《藝苑卮言》本《文章九命》是王世貞自己編定并不斷修改、調整的,最后收入《弇州四部稿》。與《閑情小品》本相比較,《藝苑卮言》本更貼合王世貞的思想和心態。僅從體例和材料編排方面分析,就能發現王世貞的用心之處。首先,整個敘述籠罩于“詩能窮人”主題之下,每一則均反映出文人不佳的命運。其次,每一則幾乎都是選取大量的事例(典故),以排比的方式呈現,且每一則最末都會列舉明代的事例。可以說,王世貞有意識地在《文章九命》中集中反映文人的悲慘命運,如其所言:“循覽往匠,良少完終,為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羅仲鼎389)如果說“愴然以慨”還是以旁觀者的角度感慨他者的命運,那么“肅然以恐”則表明文人悲慘的命運會與自己及朋友密切相關。《藝苑卮言》本《文章九命》就提及了友人宗臣、梁有譽的早逝。所以說《文章九命》浸透了王世貞對文人悲慘命運的深切體悟和思考。
早逝只是一種極端悲慘的命運,圍繞在王世貞周圍的,更多的是自己及友人坎坷的經歷,包括仕途的挫折。萬歷三年,汪道昆請告歸里。萬歷四年,王世貞被彈劾,罷歸里中。萬歷五年,吳國倫中讒言,自大梁罷歸。自己及友人的遭遇使王世貞深有所感,他在寫給徐中行的書信說道:“造物者頗汲汲我輩,第文士尚未脫陽九,若登匡廬頂,上有朗照而蒙氣下蔽。”(《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9冊67)在寫給林近夫的書信說道:“公亦知文士運否,猶在陽九,蒙氣未滌。伯玉請急,遂成高臥。明卿憎口,頓爾削籍。家弟與李本寧俱妒,金馬三尺地,僅一子與碩果耳。”(《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2冊535)在寫給范欽的書信也說道:“念徐生之碩果,悵文士之百六。”(《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2冊455)
自始至終,王世貞對文人無用之說耿耿于懷。盡管時不時會說一些文章不朽之類的話,但經歷仕途坎坷,甚至無意仕進后,在文人世用問題上,不再像初入仕途時那樣高標獨立。他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文人不善吏事的說法,卻又心中不平,于是將世用之眼光投射到周圍,通過觀察友人的仕進來建立文人世用的自信。萬歷二年,王世貞為汪道昆作五十壽序,其中說道:“吾雖孱弱不自立,然不敢信文士無用于天下,則于汪伯子征焉。”(《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108)這句話頗可反映王世貞自己不行,求于諸友的心態。所以他才會對徐中行說:“文人無用,須足下洗之。”(《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9冊65)評價宗臣“差為文士吐氣”(《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364),晚年對屠隆也說道:“仆生平愧文人無用一言,今日賴公吐氣。”(《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2冊705)此類例子甚多,不再贅舉。盡管王世貞晚年醉心佛道,欲謝筆硯,自悔雕蟲,但他對文學與文人的態度并無太大變化。總之,通過王世貞對文人世用、命運的書寫,可以探知其在仕宦之中的心路歷程,也得見王世貞對文人的深切體悟和認同。
二、 德·才·情: 王世貞對“文人”身份的內部認同及價值取向
“文人無行”是一個囊括力極強的話題,文人輕薄、自大、不務實、虛言浮詞等都是其中應有之義。甚至文人不推尊儒道,違背儒者之義,也可視作“文人無行”。王世貞對文人德行有深刻認識。萬歷元年,王世貞除湖廣按察使,其間作《湖廣策問》,其中一篇問及事功、文章、節義、理學四者孰益孰損。他自己的策文詳細分析了該問題,認為:“文士類多沾沾自喜,上者厭薄一切,而下者相傾為競也。自喜則途分而不為黨,厭薄一切則多避而無所營,相傾為競則各露其短而不能掩。故其為損淺也。”(《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9冊46)這是一段為文人辯護的話,辯護的方式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文人性格、言行上的缺陷,然后再指出這樣的性格使得文人坦白直率、不結黨營私。這以退為進的辯護方式完全揭示了他的立場。該文中,王世貞對文士“少伸而多抑”不以為然,這除了他念念不忘的文人世用之外,應當還有其他原因。
對此,我們能從《文章九命》中看到更多信息。第三則“玷缺”集中討論文人無行的問題,起首引用《顏氏家訓》對文人輕薄的敘述。顏之推完全是站在旁觀者角度,列舉大量事例,批判文人無行。在顏氏之前,劉勰《文心雕龍·程器》列舉“文士之疵”,并通過打破文人與污名的必然關聯來反駁這一成見。相較而言,王世貞立場與顏之推相反,認同方式又與劉勰有別。他對文人輕薄予以承認,在引用《顏氏家訓》的敘述后,又增加了很多文人無行的事例。最后說:“寧為有瑕璧,勿作無瑕石。”(羅仲鼎397)這與王世貞在策問中的論辯路徑相似,先承認文人之污名,然后以退為進,在別處尋找文人的價值根基。大致而言,“有瑕”與“無瑕”是德行層面的問題,“璧”與“石”是才性(包括文才)層面的問題。這句話等于是將文人身份屬性——文才——視為體現文人價值的主要標準,以突破傳統以德衡人的價值判斷方式。這是以王世貞為代表的文人在尋找自我認同標準時的典型表現。再如第五則“流貶”云:“窮則窮矣,然山川之勝,與精神有相發者。”(羅仲鼎404)第七則“夭折”云:“蘭摧玉折,信哉!”(羅仲鼎409)這都是在文人蹇運主題下突出作者對文才的重視與憐惜。
王世貞不諱言文人德行的玷缺,但“有瑕璧”“無瑕石”之說不免含有意氣之言的成分。首先,重視文才,不代表輕視德行。在《(湖廣)第四問》中,王世貞對節義之士評價甚高。其次,文才解決不了社會交際和道德評價中出現的問題,以文人自任的王世貞,必然會對“文人無行”產生辯白的心態。“無瑕璧”(即有德行之文人)成為潛在的渴望。所以他才會說“文人無行,賴于鱗一吐氣”(《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9冊65)。萬歷十二年九月,宋世恩大宴賓客,屠隆與之,宴上酒酣作樂。刑部主事俞顯卿劾其淫縱,屠隆因此被罷官。王世貞致信魏允中,提及此事,為之嘆息:“才之為人害也,即盡明州東湖水,何能洗文人無行四字,為之悵然。”(《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2冊732)在朋友的仕途遭遇面前,他沒有鼓吹“有瑕璧”。是以文才只能在面對文學作品,以作為文人的角度來看時,才具有超越“德”的可能性。現實世界中,德行的玷缺時時影響著人們對文人的認識和判斷,這與王世貞對文人文才的重視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萬歷十四年,王世貞在寫給王錫爵的信中說道:“文人落魄,弟故憐之;文人無行,卻不能諱。奈何奈何。”(《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2冊466)這句話雖然由他事而發,但確能照見王世貞對此矛盾的無可奈何。
關于王世貞及后七子重視修辭、才情的問題,已有研究者予以闡發。需要補充的是,王世貞等人多以“才”“情”并稱,從內涵上講,前者偏向文章的創作能力,后者指涉文章的情感內容。王世貞又將“才”“法”并舉,他評價宗臣:“[其詩]足無憾于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于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134)這里“才”的含義應為創作主體融合學識、主觀體悟、文辭表達后得心應手的創作能力,傾向于無意和自然的表達。“法”則是指“才”之外的詩文創作法度,傾向于刻意地追尋創作規則。質言之,“情”代表內容,“才”與“法”偏向形式,文辭理所當然屬于“才”與“法”的范疇。重文辭確實被王世貞視為文才的核心內容。王世貞文以明道的觀念比較淡薄,在修辭與明道之間,他多強調前者的作用。《贈李于鱗序》中探討“辭”與“理”之關系,反對唐宋派“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46)的創作風尚,就是典型的一例。他說揚雄自悔雕蟲,乃是因作賦不及司馬相如而發出的“謗言欺人”的藏拙之語(羅仲鼎89—90)。說作詞“寧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9冊411)。這都突出了他對文學本位的重視。“文以明道”已成極為強勢的批評話語,于理學家口中,大有以儒道(理學)覆蓋所有詩文創作之勢。王世貞這類文人創作的很多作品無關乎儒家道義。有友人批評王世貞“弊精神于小技”(《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2冊613),王世貞說道:“孔子稱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若僅以忠孝二言,或粗征其實以示天下,后世安能使之感動,而得其所謂興與群與怨也。[……]藉令深山一田父偶創此語,又孰聽而孰傳之也。”(《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2冊613)他借圣人之言為自己辯護,說白了就是為自己喜好文辭找一個理由。即便是闡說忠孝,也當用力于文辭,使之有傳播與交流的效用。文人的作用就在于有效地運用文辭,在借助文才傳播道理的過程中,說粗實之語的人、深山田父,均不與焉。
由上可知,與德行、儒道相比較,王世貞有意突出文才的重要性。他將修辭與粗語對應,將“才”視為區分文人與非文人(田父、傖父)的標準。這意味著并不是人人都能作文,也不是人人都能成為文人。為了給予王世貞以充分合理的定位,我們將其與唐順之的觀念作一對比。
唐順之重視儒道,后期更是鄙薄文辭、沉溺心學。嘉靖二十四年,他致信陳昌積,為其“有可以一變至道之資力,而僅用之于文”(277)感到可惜,同時自罪于“文士”雕蟲篆刻之好。唐順之鄙棄雕蟲之文士,卻試圖從另一個角度去挖掘文人、作家的內核。他在《與陳兩湖主事》中說道:“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于筆墨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后可以語此。”(277)后來又在寫給茅坤的書信中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折,自有專門法師,至于中間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與此。”(295)其所云“正法眼藏”“精神命脈骨髓”超越了“文法”,成為作家、文章家創作的內在價值,這也是唐順之“本色論”的核心。文章以有本色為最上,那么文人則當以本色為鵠的。所以他在寫給蔡克廉的書信中,給予文人較為理想化的界定:“自古文人,雖其立腳淺淺,然各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語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于言語文字之間,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謂之文人。”(300)唐順之此言的目的不在于以文士自任,而是表明自己的文章不夠格,以拒絕為自己刻文。不過他對文人的認定與前述“作家”“文章家”同一思致,是文章“本色論”的人格化表達。
關于唐順之的本色論,左東嶺先生指出: 道、風格、法則等外在因素都被他置之度外,“作家的自我心靈成了最高的權威。這是對‘法’的否定或曰超越,是對形式的忽略或曰顛覆”(461),這與典型唐宋派以道衡文的方式有別。然而,唐順之強調內在精神的多樣性,并不意味著儒家之“道”在他心里被完全去除。他推崇“文人”之精神,卻也說自己的文章未能如古人“闡理道而裨世教”(300)。質言之,唐順之深受陽明心學影響,其“文人論”一方面充分重視自我心靈、精神的重要性,頗有我手寫我心的意味;另一方面仍有世教理道橫亙其中,尚未完全降落到個人性格與感情上。此外,明代的心學自王陽明始,主張向內心尋求道理。經王學左派的闡揚,“百姓日用即為道”“人人可以成堯舜”等成為消弭等級、身份界限的理論支撐,而情與欲作為人類共通的內核被充分強調。在至情說中,“情”成了文學的絕對主導。因為情之共通性(人人有情)的存在和被強調,文學及其文人之邊界便有消弭的危險。如黃宗羲所說:“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19)這與王世貞的觀念截然對立。王世貞敬服王守仁,但對才情的重視與王學左派以至重情說的發展基本不在一條路線上。總而言之,唐順之試圖從自我精神的角度提升文人價值,卻犧牲了文人文學的純粹性。至情說過于強調情對文的主導性,消弭了文人與傖父的差別。王世貞強調才情,是對文人屬性的合理認識,以及對文人邊界的有效維護。
三、 王世貞的“文人”共同體意識及其與政治之關系
不論是辯駁“文人無用”,還是喟嘆“文人無行”,都可以說是在為最廣泛的文人群體說話。不過,王世貞的回應超出了一般的泛泛之談和套路化表述,其身份認知似未停留在這一泛化的文人群體上。根據《弇州四部稿》(不包括《文章九命》)及《續稿》,王世貞從世用、際遇等角度對以下同時代士人冠以文人之名: 李攀龍、宗臣、張九一、徐中行、汪道昆、吳國倫、屠隆、張佳胤、魏允中、李維楨、王世懋、陳宗虞、顧孟林、丁應泰。顯而易見,絕大多數都是后七子群體中人。盡管王世貞未完全將“文人”所指限定在后七子群體中——《文章九命》就是如此,但他當是有意在文人身份的框架下建立與同道友人的身份認同,從而體現較為明確的共同體意識。
對此,王世貞與魏允中之間的一段故事值得稱述。萬歷十一年,王世貞將趙用賢、李維楨、屠隆、魏允中、胡應麟列為“末五子”,作《末五子篇》。他致信魏允中,附上該詩作。魏允中卻明確表示不愿位于末五子之列。面對魏允中的回絕,王世貞倒是很寬容。他說:“仆近有五子篇擬,魏懋權似不欲以文士名也。”(《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0冊297)在寫給魏允中的信中也說:“向草五子篇,覺猶以文士名兄,宜兄之不我肯也。”(《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2冊731)作為后七子核心的王世貞,向來有結盟的意識。而后七子正是以文事結合而成的群體,“文人”是他們相互認同并向外宣稱的基本身份。以此推之,在他的關系網絡中,非但“末五子”以“文士”為名,“五子”“后五子”“廣五子”“續五子”“重紀五子”等均被視為與自己一體的文士群。
考察王世貞等人身處的環境,會發現其文人群體意識的形成與加固,并不純粹是文學內部的作用。大致而言,“文人無用”的觀念可追溯到漢以前,并在經世致用的儒家理念主導下不斷發揮。“文人無行”的話題自南北朝始就蘊含著不能用于世、招致人生禍敗的理論傾向,對文人蹇運的哀嘆,對文人不通儒道的批判,均可歸結到世用上來。故世用問題是文人諸多負面批評的關鍵,它已然觸及古代士人最為敏感的神經。因此,王世貞的文人群體意識須從世用即政治角度切入分析。在古代政治史上,士人結黨現象實屬多見,黨派間的互相攻擊一定程度上加固了本黨派的群體認同感。后七子中人多有結黨的性格,不同的是,他們以文事相交,非政治派別,卻又深陷政治斗爭當中。其文人群體意識在政治場域下就有了較為特別的形成機理。
嚴嵩是對后七子人生影響最大的政治人物,他們之間既有文學層面的矛盾,又有政治層面的沖突。政治層面的沖突當然是最劇烈、最直接的,但我們更關注以下問題: 政治因素和文學因素如何關聯,以達成嚴嵩對后七子的壓制?盡管已執國柄的嚴嵩最終未能像楊士奇那樣將文柄攥于手中,但身為內閣首輔,其文學話語權和文壇地位也是相當重要的。王世懋《徐方伯子與傳》說道:“相嵩者貪而忮,亦自負能詩,謂諸郎皆輕薄子,敢出乃公上。相繼外補,或斥逐。”(359)從中能感知到嚴嵩借用國柄來左右文壇,甚至操持文柄的意圖,這在他有意扶植、拉攏唐宋派的行為中表現得更明顯。換個角度看,后七子所受到的政治打壓也可能通過文學批評層面的因素表現出來。政治的對抗往往伴隨著語言的攻防,比如王世貞對嚴嵩時有譏刺之語,嚴嵩也稱其為“惡少年”“輕薄少年”。就后七子一方來說,他們入仕之初結社唱和,視當世無人的姿態已招致“狂傲”“輕薄”的批評。在政治對抗中,其一貫的狂放之態極易成為對立者攻擊的口實,文人“輕薄”“無行”“無用”等“污名”也就隨之被當作對立者語言攻擊的武器。后來王世貞也承認自己“負輕薄文士名”(《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2冊540)。作為內閣首輔,嚴嵩有更強大的手段來對付后七子,這種輿論實在算不上什么。然而,對后七子來說,在政治沖擊之外橫加一層輿論沖擊,其壓力不可小覷。“文人無用”“文人無行”等傳統批評話語介入政治對抗當中,一方面加強了后七子與文人身份的關聯,另一方面配合政治打壓,起到了強化后七子凝聚力和文人群體認同感的效果。
面對這些輿論,王世貞或可作言語上的攻防。但當面臨真正的政治打擊且無能為力時,之前的言語攻防也就轉換成對文人命運的哀嘆。這在其父王忬從入獄到被殺的那幾年表現得很明顯。總之,王世貞的文人群體意識是在嚴嵩執政時期建立并加固的。嚴嵩倒臺后,后七子的境遇有所好轉,但也非一帆風順。王世貞致信張九一,說道:“邇來鼎革一新,某生啟事,藥物殆盡,然多采似籠爾。詳步雅語及性命二字,便得要官。此曹厭薄文士,以為無尺寸用。”(《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9冊99)張居正柄政,推行改革,敦本務實,重用循吏,形成強調吏能、實干的政治大環境,這既使文人無世用的輿論效果加劇,又在實踐層面對文人的仕途造成了一定打壓。王世貞也曾說“江陵相當國,頗左抑文士”(《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1冊696),“今廟堂之不右文士久矣”(《弇州續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22冊510)。基于這一認知,王世貞時常在致友人的書信中稱贊對方能洗“文人無用”之恥。再如王世懋致信張佳胤,說:“仆居常扼腕眾口謂操觚者豈辦作吏。見足下繼踵家兄,領天雄節,稍稍為向來文人吐氣。”(550)張佳胤致信張九一,認為王世貞、王世懋等友人將“洗文士無用之誚,是一快也”(669)。屠隆《上汪宗伯》專門反駁“文人不善吏治”之言,致信丁應泰時又說:“此后有譚文士無用者,野夫當舉足下揶揄其面。”(328)李維楨、胡應麟等人的文章中也有類似的表達。這種言說策略表面上是友人之間的互相吹捧,實則是王世貞等人在政治環境和輿論壓力下,通過文人世用的話題不斷表示對方是自己人,由此維護著他們之間的身份認同。
受政治環境及傳統觀念的作用,“文人無用”等話題會不斷發酵,同樣,后七子的言論反制也會得到一定的擴散與延續。與王世貞、屠隆等人相識的士人,如梅鼎祚、梅守箕、蔡獻臣、王穉登等都曾重復同樣的話題,對“文人無用”之說頗有微詞。由此形成晚明相對立的兩股輿論風潮。陳懿典《螢囊閣集序》就說:“世每嗤文士為鞶帨,無益殿最。而詞人又自夸為麟鳳之不可少。”(687)后七子之一的宗臣就有以文章之士比靈鳥、麒麟之言。僅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雙方的爭論沒有為“文人無用”的批評話題增加新內涵,然而,我們卻能通過后七子觀察到一幅特別的圖景。在這里,“文人無用”“文人無行”不是停留在文學批評層面的理論話題,它們成為社會輿論,進入政治場域,切實地與這批重視文學本位的士人發生了作用,并強化了王世貞等人的文人群體認同感,使其對文人污名的強烈反應具有了根植于嘉靖萬歷特定政治土壤的獨特意涵。
四、 王世貞“文人”身份認同的文學史意義
文人與其他社會身份的不同之處在于,文人作為“文章創作者”,其身份認同直接關乎認同者的文學觀念,而古代文學觀念又時常受到政治、儒學的深度影響。也就是說,文人遭受的負面批評和標簽主要立足于政治、儒學場域下,古人對文章創作行為及創作傾向的價值判斷。王世貞的身份自任以及對文人污名的辯駁,在以自己的文學觀念為支撐的同時,也與明代學術思想產生了密切關聯。
文道關系是古代文學的核心論題。中唐古文運動就已標舉“文以明道”的主張,宋代理學進一步強化“道主文從”“道本文末”的觀念,創作無關乎儒道的閑篇章、重視修辭、文辭艷麗虛浮等成為古人對文人的成見。士人回避,甚至否定文人身份的情況也就時常出現。元明之際的宋濂、方孝孺等都明確表示不愿為文人,即是理學影響下文道觀念與身份認同的延續。明初,理學被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它所統屬的文學價值觀占據絕對的話語優勢。這種價值觀具有居高臨下的姿態,通過文官培養制度、科舉制度等途徑不斷由中央向下層和地方滲透。理學、政事、文章合一——從身份角度視之,即儒者、官員、文人三者合一——隨之成為官方意識主導下的理想人格范型。臺閣文臣作為明前期文壇權柄的執掌者,不論在實踐層面還是理論主張層面,都力圖展現并宣揚理學、政事、文章合一的形態。在這三者之中,文章的附屬地位顯而易見。“道主文從”“重道輕文”等觀念也使得臺閣文臣不會以偏重文辭的文人名世。前七子群體以郎署身份奪取文柄,同時,其出現打破了臺閣文學主導下理學、政事、文章合一的局面。重氣節,反對理學及虛偽化道德,未必意味著反對官方意識下的文道觀,前七子中就不乏有人重視理道,強調“道主文從”的論述。然而,前七子的復古思想確已顯現出向重視“文”這一方向滑動的跡象。羅宗強先生在比較明代兩次復古運動的差異時,指出:“第一次文學復古常提及道的問題。[……]第二次文學復古,則并道亦不提。”(859)其實非但不提“道”,王世貞以文壇巨擘之地位強調修辭,重視文才,并以之為文人身份的基礎,建立文人身份認同和群體意識,這表明后七子在“重文”的方向上比起前七子更進了一步,從明代復古序列來講,后七子可以說是達成了從重道向重文的轉移。王世貞“代表了士學中‘文’與‘道’選擇的分離”(李思涯44),這在中晚明文學思想史上,自是不可輕忽的重要變化。不過,描述出這一變化并非我們的最終目的,思想分化所帶來的不同觀念的沖突更值得關注,從中或能深入把握王世貞文學觀念、身份認同的時代內涵和意義。

可以想見,王世貞的復古運動及觀念所受到的正統文學價值觀的沖擊是相當大的,他晚年自悔雕蟲,也難免有這一層外在因素的影響。從重修辭、重文才的立場出發,站在王世貞對立面的,不僅是具有卑衍之弊的唐宋派文風,還有根深蒂固的、隸屬官方意識形態的文道觀念。傳統的“道主文從”觀及“復古道”思想所要解決的往往是道德倫理和政治改革方面的大問題,故而具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而后七子的文學復古主要就文學內部進行,不涉及政治革新、儒道弘揚層面的問題,從客觀上說,確實更具文人質性。以文人的身份逆迎傳統文道觀,試圖占據文壇核心和文學話語權,并進入官僚體系和理學場域,這必然帶來不通理道(文人無行)和不習吏事(文人無用)的批評。因此,后七子標舉復古,重視修辭,確實需要相當大的勇氣。
將此勇氣簡單歸結于李攀龍、王世貞等人的狂傲作風,尚屬皮相之論。狂者的個性施之于外,是激烈的言辭、傲放的行為;見之于內,則是對自我本心的肯認。后者得到明代心學家的反復闡說和發揮,已然成為狂者人格的思想基礎。王畿《與陽和張子問答》稱贊“行不掩言”的狂者,就是因其具有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349)的人格精神。樊獻科《子相文選序》評論宗臣“意氣多激昂,不能諧俗,獨自信其心,淡然忘毀譽也”(宗臣452),“自信其心”這一評語放在李攀龍、王世貞身上也是合適的,對他們來說,狂傲的言行和自信本心的精神兼而有之。不過,心學主要是在思想層面上激發此種人格,心學之外,榜樣的樹立和士風的熏染是“自信其心”的精神得以散播的重要因素。比如,同舉復古旗幟的文壇前輩李夢陽的“狂直”性格對后七子的影響就值得重視。再如,王世貞“寧為有瑕璧,勿作無瑕石”一語就出自明初頗負狂名的解縉,我們雖不能僅憑這一句就將解縉與王世貞的個性強行關聯,但從中確能看到“自信其心”的精神在士人之間的傳延。王世貞文集中還有類似的表述,如《徐汝思詩集序》論及詩歌復古的問題時說:“寧玉而瑕,毋石而璠。”(《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135)《宗子相集序》提到宗臣在詩文創作上“寧瑕無碔”(《弇州四部稿》;《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118冊133)的態度。此種取舍所蘊含的不隨俗論、跟從本心的自主人格,才是后七子不顧浮議、力倡復古的內在支撐。由此還可看到,張揚自我的主體精神滲透到了文學師法路徑的選擇、創作態度的堅持、文人身份的認同等層面,比起通過強調氣節、真情、性靈來展現明代士人主體精神的一貫路數,這更能凸顯明代個性思潮在拓展士人言行和精神空間方面的作用。
上述思路可繼續用來觀察明代文學。明代士風和心學思想很大程度上促發了重情的文學思潮,情與理的對抗成為明代文學和文論發展史上一條顯豁的脈絡。然需注意,理學主導下的文學觀主要有兩個表現: 一、通過“理道”來鉗制個人真實情欲的表達;二、強調“理道”在文學創作中絕對重要的地位。因此,對理學主導下的文學觀的反駁會從“以情反理”和“重文輕道”這兩個方向展開。明前期,重視文辭的觀念多被官方話語壓制,或潛藏于創作實踐當中,難以得到價值論方面的伸張;明中晚期,李夢陽、楊慎,以及以祝允明為代表的吳中士人在“重文”路向上有所推進,但又容易被重情、重性靈的思潮所掩蓋。王世貞等人的理論主張及身份認同突顯了明代文學思想史上“重文”的思想脈絡,這不但激化了“文”與“道”的沖突,還使得“重文”與“重情”“重性靈”的潛在矛盾浮現出來。從“重文”的角度來看,“重情”“重性靈”與傳統理學文學觀均從文章思想價值角度立論,強調主體精神在學文、作文中的關鍵作用。它們在相互對立的表象下,遵循著一以貫之的文學批評邏輯。唐順之本色論,李贄“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276—277)的言論即與理學家“道盛文自生”的觀念同一思致,強調的都是主體精神的主導地位,這與“重文”思想的取向明顯不同。晚明士人批評前后七子模擬,可以說正是在“重理道”“重情”思想與“重文”思想對立的框架下展開的。
“重文”與“重情”“重理道”等思想因矛盾而產生的碰撞、調適與融合,深刻影響著彼時的文壇格局及發展態勢。一方面,晚明部分士人盡力調適“文”“道”間的矛盾,如李維楨重新主張文儒合一的人格范型,再如科舉制藝的書籍既要指示具體的學文路徑,又要貫徹官方意識,也往往兼重二者。這些舉措都蘊含著“以道約文”的路向,進而向官方、正統文學觀靠攏。另一方面,王世貞等人遭受的“文人無用”“文人無行”的批評說明這樣的文學觀和身份認同不適合在理學和政治場域展開,也不符合官方意識下士人培養的要求。“重文”思想因疏遠官方意識,強調適性,又與“重情”“重性靈”思想有融合的可能。因此它們在與官方意識沖突之后,其勢下潛,體現出向下的,疏離理學、政治場域的傾向,在走向地方,走入市井、山林的士人那里得到發揮,形成一種有學識、重文才、具個性的文人風貌。晚明吳中文人華淑《題文章九命后》說:“彼肥皮厚肉,坐擁富貴者,類皆聲銷氣沉,寒煙衰草其歸滅沒。獨文人詩士,其流風余韻,尚與山川花月相映不已。”(13b)此論雖非獨創,卻可代表王世貞的文人身份意識和文學觀念在晚明地方及中下層人士中的推揚與流衍。由此視之,在重情、性靈論已占上風的中晚明文學史上,“重文”思想依然關乎明代文學流派的更替演進,中央與地方文學的對峙、交流、互動,以及明代文壇的某些發展動向,仍舊是值得考掘和深究的潛在的脈絡。
注釋[Notes]
① 文人在際遇方面的污名主要包括蹇運、命窮等,它是對文人經歷、命運共性的認定,與儒學、德行、世用等根據主體能力與個性的認定方式有別。嚴格說來,命窮不一定是污名。因為文人對“薄命”之說完全可以站在“理解與欣賞”的角度來認識。(參見吳承學: 《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0—91頁。)本文考慮到蹇運、命窮是對文人際遇不好的描述,且影響深遠,足以有與前三者相提并論的分量,故仍將其納入污名之中,以方便下文的論述。
② 對于文人在儒學、德行方面遭受的批評及其發展過程,及相關話題的產生演變,參見黨月瑤、熊湘: 《文人與德行: 中國古代相關話題的生成與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5(2018): 155—162。熊湘: 《儒者視閾下的“文人”及其批評理念的演進——以唐宋為中心》,《新疆大學學報》4(2019): 89—95。經筆者考察,王世貞以前,為文人正名,強調文人的正面價值的論者不少,如王充、劉勰等,但他們要么留下的相關文字不多,要么論述零散,要么沒有與個人遭遇相結合。從這個角度來說,王世貞對文人的認同具有前所未有的價值與意義。
③ 對此,參見鄭利華: 《論王世貞的文學批評》,《復旦學報》1(1989): 34—35;《前后七子研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47—458,473—476頁。
④ 關于嚴嵩與后七子的沖突,參見廖可斌: 《嚴嵩與嘉靖中后期文壇》,廖可斌《詩稗鱗爪》,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87—194頁。葉曄: 《嚴嵩與明中葉上層文學秩序》,《中華文史論叢》3(2018): 157—160。
⑤ 關于李夢陽及前七子在明代學術思想史上的意義,參見張德建: 《論“血氣義氣”與“文章氣節”——以李夢陽為中心》,《蘭州大學學報》6(2018): 52—56。
⑥ 楊士奇《前朝列大夫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解公墓碣銘》記載解縉“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見楊士奇: 《東里文集》,北京: 中華書局,1998年,第257頁。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陳繼儒: 《見聞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244冊。濟南: 齊魯書社,1997年。
[Chen, Jiru.The
Sketch
Book.
Collection
of
Works
Mentioned
in
the
Catalogue
but
Not
Includ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Part of Philosophy. Vol.244. Ji’nan: Qilu Press, 1997.]陳懿典: 《陳學士先生初集》,《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78冊。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7年。
[Chen, Yidian.Collected
Essays
of
Chen
Xueshi.
Banned
Books
from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es: Part of Literature. Vol.78.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1997.]華淑: 《題文章九命后》,《閑情小品》第3冊,明萬歷間刻本。第13頁。
[Hua, Shu. “Postscript toNine
Kinds
of
Fates
of
Literati.
”Essays
Read
in
Leisure
Time
. Vol.3. Block printed edition in Wanli period of Ming Dynasty. 13.]黃宗羲: 《明文案序上》,《黃宗羲全集》第10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19頁。
[Huang, Zongxi. “The Preface ofCollected
Essays
from
Ming
Dynasty.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ang
Zongxi
. Vol.10.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18-19.]李維楨: 《大泌山房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0冊。濟南: 齊魯書社,1997年。
[Li, Weizhen.Collected
Essays
from
Hill
House
of
Dabi.
Collection
of
Works
Mentioned
in
the
Catalogue
but
Not
Includ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Part of Literature. Vol.150. Ji’nan: Qilu Press, 1997.]李思涯: 《胡應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Li, Siya.A
Study
of
Hu
Yinglin
’s
Literary
Thought
.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2.]李贄: 《童心說》,《李贄全集注》第1冊,張建業主編。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276—277頁。
[Li, Zhi. “The Theory of Childlike Innocence.”Annotations
to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 Zhi.Vol.1. Ed. Zhang Jianye.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0.276-277.]羅仲鼎: 《藝苑卮言校注》。濟南: 齊魯書社,1992年。
[Luo, Zhongding, ed.Critical
Annotations
to
Plain Word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Ji’nan: Qilu Press, 1992.]羅宗強: 《明代文學思想史》。北京: 中華書局,2013年。
[Luo, Zongqiang.A
History
of
Literary
Thought
in
Ming
Dynasty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四庫提要著錄叢書》。北京: 北京出版社,2011年。
[Series
of
Abstracts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2011.]唐順之: 《唐荊川先生集》,《叢書集成續編》第144冊。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第207—441頁。
[Tang, Shunzhi.Collected
Essays
of
Tang
Jingchuan.
The
Sequel
to
The Series Library Integration. Vol.144. Taipei: Shin Wen Feng Publishing Co., Ltd., 1989. 207—441.]屠隆: 《屠隆集》第6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Tu, Long.Collected
Essays
of
Tu
Long
. Vol.6.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2.]王畿: 《龍溪王先生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8冊。濟南: 齊魯書社,1997年。
[Wang, Ji.Collected
Essays
of
Wang
Longxi.
Collection
of
Works
Mentioned
in
the
Catalogue
but
Not
Includ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Part of Literature. Vol.98. Ji’nan: Qilu Press, 1997.]王世懋: 《王奉常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3冊。濟南: 齊魯書社,1997年。
[Wang, Shimao.Collected
Essays
of
Wang
Fengchang.
Collection
of
Works
Mentioned
in
the
Catalogue
but
Not
Includ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Part of Literature. Vol.133. Ji’nan: Qilu Press, 1997.]王錫爵: 《王文肅公文集》,《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7冊。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7年。
[Wang, Xijue.Collected
Essays
of
Wang
Wensu.
Banned
Books
from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es: Part of Literature. Vol.7. Beiji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1997.]魏允中: 《魏仲子集》,《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845冊。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Wei, Yunzhong.Collected
Essays
of
Wei
Zhongzi.
Series
of
Rare
Books
in
Stack
Room
of
Former
National
Beiping
Library
. Vol.845.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3.]張佳胤: 《居來先生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51冊。濟南: 齊魯書社,2001年。
[Zhang, Jiayin.Collected
Essays
of
Ju
Lai.
A
Supplement
to
Collection
of
Works
Mentioned
in
the
Catalogue
but
Not
Includ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51. Ji’nan: Qilu Press, 2001.]張廷玉等: 《明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
[Zhang, Tingyu, et al.A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宗臣: 《子相文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6冊。濟南: 齊魯書社,1997年。
[Zong, Chen.Selected
Works
of
Zongchen.
Collection
of
Works
Mentioned
in
the
Catalogue
but
Not
Included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Part of Literature. Vol.126. Ji’nan: Qilu Press, 1997.]左東嶺: 《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Zuo, Dongling.Wang
Yangming
’s
Theory
and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