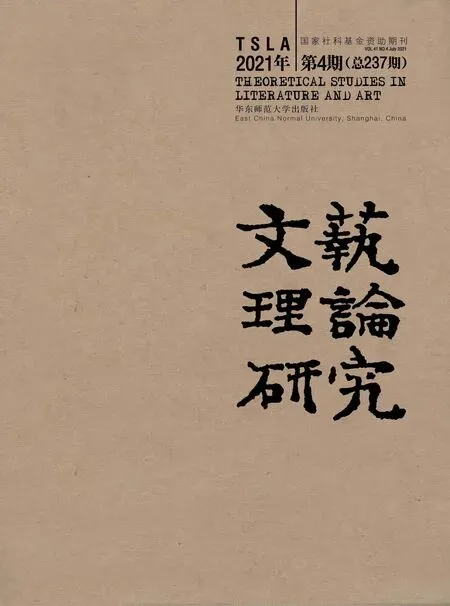法國當代攝影觀念研究的三大范式
陸一琛
在2000年出版的《攝影觀念的誕生》(La
naissance
de
l
’id
ée
de
photographie
)中,弗朗索瓦·布呂內(Fran?ois Brunet)借助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分離并界定了攝影研究領域一個全新的話語對象: 攝影觀念。“攝影觀念”不同于“攝影”,是作為實踐和影像的攝影在其散播和被接受過程中形成的、以陳述話語內在規律性為表征的概念網絡。從“攝影”到“攝影觀念”實現的不僅僅是概念上的位移和轉換,還意味著(歷史)分析和書寫模式的變遷,尤其是對傳統攝影史書寫(以“攝影技術史”和“影像藝術史”為經典范式)的質詢與解構,以及對被正統攝影史邊緣化的對象的關注。一方面,攝影觀念史顛覆了“攝影技術史”所秉承的發展、演進邏輯。該歷史書寫很大程度上受制于19世紀初以來盛行的技術決定論,認為經過改進的攝影器械不斷突破先前攝影實踐的限制,延展攝影技術上的可能性。正如喬弗里·巴欽(Geoffrey Batchen)所言,以相機裝置及其局限和創造的可能性為核心敘事的攝影史致力于原創性和創新性,技術發展的歷史性是使攝影得以歷史化(historicizing)的主導模式(《更多瘋狂的念頭》19)。另一方面,攝影觀念史完全背離了“影像藝術史”(或者說“照片的歷史”)所奉行的同一性闡釋邏輯。以博蒙特·紐霍爾(Beaumont Newhall)大作《世界攝影史: 從1839年至今》(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From
1839
to
the
Present
, 1949年)為代表的編史模式注重攝影影像的藝術性,參照了繼瓦薩里和溫克爾曼以來藝術史寫作的典型范式,在突出個體攝影師地位的同時強調大師們背后某種起到統攝和奠基作用的時代精神。正如福柯所言,這種與時代密切相關的“心態”或“精神”可以在某個既定時代的同時的或連續的現象之間建立某種意義同一體,某些象征聯系(《知識考古學》21)。就“觀念”一詞而言,弗朗索瓦·布呂內意義上的“攝影觀念史”或許很容易導致某種可以預見的誤讀,即認為“攝影觀念史”隸屬于更廣泛意義上的“觀念藝術史”。但兩者在研究對象和方法論層面有著顯著的不同。高名潞在《西方藝術史觀念》中這樣定義觀念藝術史中的“觀念”:“對藝術歷史敘事的主觀性構想”(110)。這種構想由清晰的原理所統領,把不同時期的不同人物、作品和事件編織在一個有機聯系的系統中。此外,觀念藝術史基于藝術史家“先入為主的預設”(111),遵循一般意義上的演繹邏輯: 強調根據“預設”篩選出的作品之間的同一性,從而進一步論證其構想的有效性。可見,觀念藝術史寫作的“內聚力”源自“至高無上、起構造和奠基作用的”(福柯,《詞與物》譯者序12)主體,即藝術史家。這也造成了觀念藝術史書寫一系列無法規避的問題。而《攝影觀念的誕生》中建構的“攝影觀念史”書寫模式則恰恰相反。通過聚焦不同領域(社會、政治、經濟、文學等)的話語實踐規律,尤其是不同概念之間的差異性和流動性,攝影觀念史淡化了話語實踐中的“主體”標記,消解了主體性的建構功能,構筑了一個不同概念型的共存空間。這也是本文的寫作意圖: 在弗朗索瓦·布呂內創設的“攝影觀念史”理論框架下,分析由保羅·愛德華茲(Paul Edwards)、菲利普·杜布瓦(Philippe Dubois)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的三個攝影觀念(史)的闡釋范式,聚焦某些高頻概念的出現、變化、轉換和復歸,描述構成攝影觀念的概念網絡,展示支配這些概念的規律性聯結,以便建立一種重新思考攝影的方式。借用巴欽的話,攝影的觀念“銘寫在差異的動態作用(延異的作用)之內,它拒絕停留在身份辨識的任何一個適用的極點上”(《熱切的渴望》253)。
一、 保羅·愛德華茲范式: 從“自然”(nature)到“文化”(culture),從“自為”到“人為”
在《黑太陽——攝影與文學: 從攝影誕生至超現實主義》(Soleil
noir
,photographie
et
litt
érature
des
origines
au
surr
éalisme
, 2008年)中,基于以1839—1939年(即攝影誕辰第一個百年)在英法兩國發表的、與攝影及其概念隱喻密切相關的文學作品為對象的比較研究,保羅·愛德華茲在導言中提出了撰寫一部“攝影觀念史”(Histoire des idées de la photographie)(13—19)的設想。選擇“攝影觀念史”而不是“攝影史”,顯然與愛德華茲該專著的寫作立場有關。愛德華茲認為: 一方面,英美的攝影史以英美史料為主,忽視了法國方面的重要文獻;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時期的英美攝影史更偏重攝影媒介的紀實性、社會性和政治性,強制性地將攝影納入權力話語體系,忽視了攝影作為想象、反思與虛構之載體的藝術表現力。誠然,后現代主義話語對于意義實現之關鍵因素——“語境”的過分強調導致普遍覆蓋攝影史的工具理性論調。這類話語傾向于把攝影認知為意義與權力實踐、實現的場所與通道,如英國批評家約翰·塔格(John Tagg)在《攝影記錄與國家成長》中提出的:“攝影本身并沒有身份。它作為一種技術的地位隨著賦予它的那種權力關系而變化。它作為一種實踐的本質,有賴于定義它并令它發揮作用的機制和使用者。”(63)而愛德華茲則認為,在攝影領域,存在著另一種與權力話語主導的紀實攝影相對立的、以某種“虛構性”(即反紀實性)為本質的“攝影”,我們姑且將其命名為“虛構攝影”(photographie-fiction)。此類攝影以三種形式存在: 虛構影像、作為概念隱喻的影像以及文學插圖。愛德華茲意義上的“攝影觀念史”以第二種攝影形式為書寫對象,旨在建構與攝影密切相關的概念隱喻(concept-metaphors)體系。以文學文本為研究素材也成為愛德華茲攝影理論最令人矚目,也最飽受爭議的原因之一。其實,早在1936年,喬治·波托尼埃(Georges Potonniée)就曾在《攝影發現史》(The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of
Photography
)中將最早有關攝影的想法定位于一部18世紀中葉出版的文學作品中。在此,我們或可借用福柯的話語: 對攝影的認知“可以像貫穿科學的文本那樣,貫穿‘文學’的文本或者‘哲學’的文本”(《知識考古學》204),而不應當被局限在有關攝影的“論證”中。因為作為話語對象的攝影完全有可能出現在其他如故事(歷史、文學陳述)、思考、敘述,甚至行政制度和政治決策等異質的陳述中。愛德華茲大膽地將文學文本納入攝影研究,不僅凸顯了其理論獨特的研究視角,更豐富了話語實踐的取樣層次,擴大了研究的有效性和適用性范圍。在以“攝影觀念史”為主題的章節中,愛德華茲從與攝影相關聯的文學話語實踐中提煉出了四個概念節點:“自然”(la Nature)、“科學”(la Science)、“人”(l’Homme)和“生成”(le Devenir)。這四個概念架構了文學話語思考攝影的基本范式。首先是“自然”。在其誕生之初,攝影被認為是借助化學手段固定暗箱中自然之影像的方式。在《攝影小史》中,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曾指出作為攝影起源原動力的這一渴望:“有心人不約而同地都向同一目標努力邁進: 都想把投射在暗箱內的影像固定住。”(3)而巴欽在《熱切的渴望》中進一步剖析了該渴望背后的隱意: 當時的人們將攝影視作自然的,甚至是上帝的魔法,“自然”被認為是攝影實踐的對象和施動者(“對暗箱收到的自然的影像進行自發的復制”“大自然繪制的素描”(88))。“人”,及其所代表的自由能動的主觀性在影像生成的過程中是缺失的。攝影成為宗教意義上“不經人手的圖像”。這一觀念盛行于攝影誕生初期,但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完全消失。愛德華茲強調,攝影作為自然的產物逐步成為“多格扎”(doxa)并在整個19世紀不斷復現。這與攝影背后強大的宗教隱喻體系不無關聯:“光”,作為攝影影像生成的必要條件,也是上帝的法力與仁慈的隱喻。攝影生成的過程與上帝創造自然的過程存在著形式上的同構性: 如果說自然就是上帝(創造)的藝術,那么攝影就是“自然”(創造)的藝術。
第二個認知范型關鍵詞是“科學”。即便在19世紀二三十年代,推動攝影技術專利國有化的法國議員弗朗索瓦·阿拉戈(Fran?ois Arago)早已預言了攝影在科學領域的巨大發展前景(Freund27-28),但攝影真正作為科學的象征深入人心緣于實證主義理念的興盛。在讓-克勞德·勒馬尼(Jean-Claude Lemagny)和安德烈·胡依(André Rouillé)主編的《攝影史》(Histoire
de
la
photographie
, 1986年)中,喬治·迪迪-于貝爾曼(Georges Didi-Huberman)曾寫道,攝影使“對可見世界的絕對認知”(71)成為可能。以照相機為象征的全新視覺機制——技術性觀視拓展了人類視覺的極限,極大地改變了觀察的方式和理念,使觀察逐步成為19世紀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首要研究方式(謝宏聲57)。高名潞也注意到,19世紀中期,“在各個科學學科領域中,對本質真實的追求逐漸讓位于機械客觀性”(103)。而攝影的“科學性”恰恰體現于影像(機械/自動)生成過程所暗含的這種“客觀性”: 作為觀察工具的照相機懸置了觀察主體的主觀介入。雖然攝影技術依舊是觀看行為的中介,但這一中介的本質屬性是機械的,不受主體意志操控的。動搖“攝影=科學”這一觀念等式的是19世紀末“畫意攝影”運動倡導的藝術審美訴求。自此,攝影開始陷入藝術性(主觀性)與科學性(客觀性)的兩難境地。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前攝影部主任彼得·加拉西(Peter Galassi)甚至認為:“攝影絕不是科學留在藝術的門外石階上的私生子,而是西方繪畫傳統的合法子嗣。”(2)但這并不意味著攝影與科學這一概念聯結頃刻失效。攝影自其誕生之日起始終與科學所代表的精準性、實證性和工具理性緊緊相連。只是在“圖像化生存與技術性觀視”(謝宏聲84)日漸成為生活常態的今日,我們逐漸失去了對作為技術中介的攝影(媒介)的感知。此外,作為能動創造者的“人”(主體)的概念在攝影領域的崛起與攝影對其藝術身份的追求息息相關。攝影是技術還是藝術,是自為還是人為?影像成形過程是否有人的介入?評論界至今仍莫衷一是。雖然在《攝影影像的本體論》(“Ontologie de l’image photographique”, 1945年)中,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依然固執地認為攝影“完全滿足了我們把人排除在外而單靠機械復制來制造幻想的欲望”(4);而美國哲學家斯坦利·卡維爾(Stanley Cavell)甚至認為攝影滿足了某種人類的夙愿,即“借助自動性,把人類的作用從再現的舉動中清除了出去”(23)。但愛德華茲顯然站在了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一側,后者在《觀察者的技術》(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 1990年)中提到“形塑19世紀觀察者的最大影響源,在于主觀視覺模型成為優先”(16)。主觀性視覺的興起在哲學層面意味著“啟蒙時代的眼見為實,即客觀性,[……],被納入了主觀意識的認識范疇之中”(高名潞101);而在實踐層面,攝影不再是自主進行的逼真復制,轉而成為某種基于主觀性再現的藝術詮釋活動。這一過程是攝影師的可見性(visibility)與存在感(從幕后走到臺前)不斷提升的過程。攝影師替代了先前的上帝與能動的“自然”,成為攝影影像獨一無二的創造者。攝影師也是第四個關鍵階段——“生成”中最核心的概念。愛德華茲在這個環節著墨不多,但很明顯,該階段是第三階段的延續。新影像生成的過程也是作為造物主的“人”進行創造性實踐的過程。實驗性攝影實踐是使攝影擺脫“畫意攝影”興起以來以繪畫藝術為模板的刻意改造,逐步走向媒介獨立的重要路徑。從“自然”到“科學”,從“科學”再到“人”,愛德華茲的攝影觀念敘事邏輯凸顯了人不斷馴化,進而全面掌控攝影技術的過程。換句話說,技術“正在替代上帝的原理,成為人創造和把握完美性的能力”(高名潞25)。
二、 菲利普·杜布瓦的符號范式: 從“像似符”(icon)到“規約符”(symbol)再到“指示符”(index)
與愛德華茲相反,菲利普·杜布瓦在《攝影行為與其他論文》(L
’acte
photographique
et
autres
essais
, 1990年)中展現了人逐步被攝影技術規訓的過程,同時也是人受制于以符號為核心的表意實踐規則的過程。在杜布瓦這里,被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符號概念表征的攝影觀念不斷徘徊在真實與再現的邊緣,并逐漸切斷了與“自然”概念的臍帶式關聯,徹底淪為人造之物,直至其“指示符”屬性被重新發掘。當然,杜布瓦范式基于攝影批評和理論文本。相較于愛德華茲,杜布瓦的理論范型顯然更超前、更抽象。此外,杜布瓦很大程度上直接沿用了皮爾斯符號學體系現成的概念框架,必然忽略了攝影某些不可化約的非符號屬性,這也構成了該范式受到指責的重要原因。但不可否認,攝影的符號屬性是進一步理解攝影觀念無法繞過的關卡。如果說愛德華茲范式巧妙地避開了作為西方藝術哲學領域之重要概念的“再現”問題,杜布瓦范式則根植于再現范疇,聚焦攝影影像與“真實”之間的關聯。攝影是否能再現“真實”?影像如何指涉、再現“真實”?如果說“再現的核心是如何通過藝術作品的形象呈現某種真實”(高名潞238),那么攝影所呈現的“真實”將如何界定?為了回答以上問題,杜布瓦重塑了攝影批評理論發展路徑的三個階段: 作為“真實之鏡像”的攝影(La photographie comme miroir du réel);作為“真實之形變”的攝影(La photographie comme transformation du réel);作為“真實之印跡”的攝影(La photographie comme trace d’un réel)。
將攝影視作“真實之鏡像”這一論斷基于圍繞攝影產生的最原始的批評話語: 模仿論。蘇格拉底就曾如此定義藝術家的工作: 藝術家模仿或者制作“擬像”,如同鏡子折射周圍事物一樣(高名潞85)。杜布瓦也注意到了攝影的發明在藝術界,尤其是繪畫圈引發的危機和革命。顯然,最早期的藝術評論家們無法準確理解攝影影像的生成機制,卻極力試圖將攝影影像納入已有的、以模仿為核心的藝術認知框架中。攝影,由于其機械屬性和精準復制的能力,被認為是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藝術的模板與極致。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在《現代公眾與攝影》(“Le public moderne et la photographie”)中借早期攝影沙龍觀眾之口說出的一席話充滿諷刺意味:“我認為只有對自然的精準模仿才能稱得上藝術。”(615)可見,攝影所代表的是一種極為原始的、近乎自然主義的現實主義風格,僅僅注重對外在現實可視層面的直接感知與模仿。這也解釋了批評話語中廣泛存在的攝影與現實主義風格之間的捆綁關聯。按照杜布瓦的說法,以模仿論為核心、以繪畫藝術為參照的攝影評論話語主導了整個19世紀。但此類話語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銷聲匿跡。羅杰·米尼耶(Roger Munier)在《反圖像》(Contre
l
’image
, 1963年)中依舊認為攝影作為完全透明的媒介在紙或屏幕上再現了現實世界的即刻的真實(qtd. in Dubois28);而巴贊則認為“照相術[……]把造型藝術從追求形似的頑念中解放出來”(4)。形似,尤其是視覺層面的相似確實是早期攝影觀念成形的重要影響因素。但20世紀伊始,“真實”的概念就開始不斷被質詢、解構和重構。“真實”逐漸遠離“自然”“本真”等哲學概念范疇,轉而成為文學藝術作品所追求的某種“效應”或“效果”。“真實”概念的疆域被另一個對立概念——“現實”所界限。亨利·范·利耶(Henri Van Lier)對這兩個概念的定義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杜布瓦提出的“攝影=真實之形變”范式。范·利耶認為“現實”(reality)是遵從某種意識秩序、被納入符號體系并受其控制的“真實”(real);比較而言,“真實”就是脫離“現實”概念之外者,是所有在“現實”之前、之后與當下的東西(范·利耶54)。換句話說,“真實”是未被我們的技術、科學和社會關系所馴化的“現實”;“現實”是被藝術媒介再現(“如果說藝術再現了什么,那就是再現了意識給外部世界規定的某種秩序”[高名潞6],的“真實”。
在杜布瓦提出的理論框架中,照片所呈現的就是“現實”,即被編碼了的“真實”。這里的“形變”可能是形式上的,也可能是內容上的。正如羅蘭·巴特在《攝影信息》(“Le message photographique”)中提到的影響攝影影像意義生產的六種圖像處理方式: 攝影特技(truquage)、姿勢造型(pose)、拍攝對象(objets)、獲得上鏡效果的技術處理(photogénie)、審美(esthétisme)、影像(兩張及以上)排列句法(syntaxe)。六種技術“寓意”手法(前三種屬于涉及內容層面的改變,后三種屬于形式層面的調整)對“真實”進行編碼,使其成為“可讀”信息。事實上,標志這一攝影認知轉向的正是濫觴于19世紀中后期“畫意攝影”運動,古斯塔夫·勒·格瑞(Gustave Le Gray)等攝影師們通過上述各種圖像處理手段將“攝影與繪畫一樣同屬于藝術”這一終極所指編碼在所有作品中。杜布瓦認為“真實之形變”的范式從屬于三類批評話語: 第一類是以阿恩海姆、克拉考爾為代表的,以“視知覺與心理學”為研究對象的影像批評話語;第二類是以于貝爾·達彌施(Hubert Damisch)、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電影手冊》(Les
Cahiers
du
cin
éma
)團隊為代表的,以意識形態為研究對象的影像批評話語;第三類是基于攝影影像之人種學維度的批評話語(Dubois32)。這三類話語無一例外地遵循一個預設: 影像是被符碼的信息。杜布瓦認為,“真實之形變”范式使“真實”的概念發生了位移,影像所展現的“真實”是某種“內部的真實”,即影像忠實再現的不再是世界的表象,而是藝術家的意識,或者說藝術家想要賦予真實世界的某種秩序。如果說將攝影視為“真實”的鏡像和被符碼的“真實”之載體(或者更確切地說,作為象征意義的承載物)恰巧對應皮爾斯符號體系中的“像似符”(icon)和“規約符”(symbol),那么第三個范式“真實之印跡”昭示著20世紀80年代攝影批評話語的“指示性”(index)轉向。這顯然伴隨著對皮爾斯符號體系中“指示符號”的再發現,同時也意味著某種無法被編碼的“真實”的回歸。早在《攝影小史》中,本雅明面對早期肖像照片時就曾感嘆:“不管攝影者的技術如何靈巧,也無論拍攝對象如何正襟危坐,觀者卻感覺到有股不可抗拒的想望,要在影像中尋找那極微小的火花,意外的,屬于此時此地的;因為有了這火光,‘真實’就像徹頭徹尾灼透了相中人。”(14)攝影者的技術和拍攝的姿勢都屬于巴特指出的攝影寓意手法,但“真實”之火光燃盡留下的印跡卻“意外地”“不可抗拒地”被保留了下來。按照本雅明的說法,“因為對相機說話的大自然,不同于對眼睛說話的大自然: 兩者會有不同,首先是因相片中的空間不是人有意識布局的,而是無意識所編織出來的”(14)。換句話說,相機捕獲的“真實”(自然)不同于“現實”(被符碼、被賦予預先設定意義的自然),攝影影像呈現的是真實的“無意識”狀態。杜瓦爾則列舉了《電影手冊》評論帕斯卡爾·博尼策(Pascal Bonitzer)的例子。博尼策在反思阿蘭·貝爾格拉(Alain Bergala)針對“傘下哭泣的越南人”影像進行的意識形態批評時曾指出:“照片中總有某些東西永久地抵制著(意識形態)分析,[……]照片和繪畫沒有任何關聯: 拍攝對象被捕獲的方式全然不同[……]照片,首先是借助化學手段再現的、以直接的方式提取的、真實的切片。”(30—31)但在這一章中,出現頻次最高的引文源自羅蘭·巴特。巴特以攝影為主題的著作《明室: 攝影札記》(La
chambre
claire.
Note
sur
la
photographie
, 1980年)不僅印證了攝影理論的指示性轉向,即攝影的認知范式如何從“真實之形變”轉向“真實之印跡”的過程,還從觀者角度開辟了另一條認識攝影的路徑。為了避免重復,我們將在下一環節中繼續杜布瓦提出的“指示性范式”的討論。三、 羅蘭·巴特范式: 從反對闡釋到記憶情感層面的“心理圖式”(mental schemas)
毋庸置疑,對攝影與真實之間的“指示性”關聯理解最為深刻的是羅蘭·巴特。巴特在《〈明室〉,另一部攝影小史》中曾提到“最好不要[把《明室》]當作批評理論著作來閱讀,而是要當作一部攝影史”(《更多瘋狂的念頭》10)。更確切地說,《明室》是一部足以概括整個20世紀的攝影觀念史。巴特在《明室》中提出了用于理解攝影的兩個主題:“研點”(studium
)和“刺點”(punctum
)。研點是“攝影師意圖”在影像上的展現,其依據是“創作者和欣賞者之間簽訂的[……]契約”(37)。“創作者”利用巴特在《攝影信息》中提及的攝影領域特殊的寓意手段“迫使”影像承載自己創造的意圖。而“欣賞者”則憑借相關的文化符碼解讀攝影師的想法。很明顯,“研點”從屬于杜布瓦理論系統中“形變后的真實”,也是皮爾斯符號體系中的“規約”。但從“研點”出發解讀了一系列報刊上的照片之后,巴特并未成功地發現攝影的真諦。這也是促使巴特改變研究方法的契機。事實上,早在1961年發表的《攝影信息》中,他就提出了攝影信息由“外延信息”(無符碼信息)和“內涵信息”(符碼信息)以某種有待考證的方式疊合的論斷(130)。“外延信息”實則特指攝影的“指示符”屬性,借用皮爾斯的話:
照片,特別是那種即時性照片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因為我們知道這些照片在某些方面極像它們所再現的對象。但是,這種像似性(resemblance)是由照片的產生方式所決定的,也即照片自身被迫與自然逐一相對應。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照片屬于符號的第二類(指示符),即借助物理聯系(physical connection)的那一類。(54)

對光子物理屬性的認知,尤其是對攝影成像原理的了解有助于更好地界定攝影的“指示符號”屬性,也極大地影響了對攝影影像的感知。如果說之前對于攝影的認知(這一認知型仍然存在于普通大眾的攝影觀念中,甚至占據主導地位)只關注攝影作為“像似符”和“規約符”的符號屬性,即影像與拍攝對象視覺層面的相似和作為象征意義載體的影像,那么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后,對攝影的“指示符號”屬性的再發現極大地改變了攝影影像的解讀方式。皮爾斯在定義指示符號特性時,曾提到:“指示符是這樣一種符號或再現(representation),它能夠指稱它的對象,主要不是因為與其像似或類似[……]而是因為[……]它與那些把它當作符號的人的感覺或記憶有聯系。”(56)換句話說,“從心理學來講,指示符號有賴于毗鄰的聯想(association by contiguity)”(巴特,《更多瘋狂的念頭》22)。作為指示符的攝影所指涉的事物激活了觀者通過感知或記憶渠道產生的聯想,進而帶來了極為私密且個性化的審美感受與體驗。這正是《明室》第二部分中巴特觀看母親年幼時拍攝的“溫室庭院照片”時的經歷。
巴特采用了某種主觀現象學,即以觀看主體的體驗為中介來揭示攝影本體論層面的特性。和胡塞爾現象學要求的懸置、體認和破譯的認識過程相類似,為了使客體“顯像”“顯真”,巴特意義上的“無拘無束的現象學”首先要求觀看主體拋棄一切以共同文化為基礎的認知契約、一切闡釋符號話語的解碼系統:“我是個野蠻人,是個孩子——或狂人。我丟掉了一切知識,一切修養,我不讓自己接受另一種眼光。”(《明室》68)巴特提到的“孩童”或者“野蠻人”的目光是藝術批評領域的慣常概念,即脫離了所有預先設定的認知、釋意框架的眼光。其變體非常多見,如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提出的“眼睛的天真狀態”(innocence of the eye):“也就是一種孩稚般的知覺,看到色斑,就當它是這樣,不會有意識來解釋這意味什么。”(27)這種目光將視覺感知從意義解讀的艱巨任務中解放出來,更強調藝術品引發的感知層面的全新體驗,而不是藝術品傳達隱含意義的中介功能。其次,巴特贊同卡夫卡的說法,認為觀者應該“閉上眼,就是讓圖像在寂靜中說話”(《明室》73)。因為“絕對的主觀性只能在竭力保持安靜的狀態下才能達到”,只有這樣,被稱之為“刺點”的細節才能回到“富有情感的意識中來”(73)。顯然,“富有情感的意識”有助于激活皮爾斯意義上的“毗鄰式聯想”,觸發范·利耶意義上的“呈螺旋形增多的心理圖式”(64),直至個體感覺或記憶的重現。范·利耶提出的“心理圖式”概念原本指的是符號解讀過程中存在于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心理路徑。在被符號秩序支配的世界中,能指與所指之間有一個特定的心理圖式在起作用。而攝影是“一種心理圖式的特別觸發器”,可以引發多種,且因觀看個體經歷不同而極為個性化的心理圖式。和本雅明一樣,范·利耶更強調攝影觸發的心理圖式之“潛意識”——“照片更接近于夢而不是想象”(64),甚至“無意識”維度。而在巴特那里,這類心理圖式屬于情感和記憶層面。這就是為什么巴特一再強調“為了感知刺點,任何分析對我都是無用的(不過,也許記憶會有用……)”(《明室》57)。
結 語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并沒有在“攝影觀念史”所暗含的歷時性框架下討論以上范式,因為三位攝影理論家都不約而同地強調各大范式共存于當下。從嚴格的方法論層面上講,我們進行的是針對攝影觀念的知識考古。但根據“真實”和“人”(主體)這兩個高頻概念的出現、變化、轉換和復歸,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個具有歷史性維度,同時也符合鐘擺邏輯(兩個概念極端之間的往復運動與折返)的結論: 攝影被接受的過程是“真實”概念(19世紀中葉之前的“自然”概念)不斷被規訓、符碼,并向“現實”演進,最終以情感或潛(無)意識層面的“真實”回歸的過程;也是作為創造主體的“人”不斷嘗試掌控“真實”,將世界秩序化、符號化的過程,而攝影是“真實”負隅抵抗的最后陣地。正如巴特所暗示的,所有的寓意過程都是強迫性質的,是“反知覺”的。談論攝影或照片就必須拋棄所有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強制賦予的內涵和意義,尋回未受規訓的“天真之眼”。這也驗證了范·利耶的精辟論斷:“雖然人類發明并使用了照片,但照片卻是天外來客。”(56)
注釋[Notes]
① 見《熱切的渴望: 攝影概念的誕生》,第46頁: 喬治·波托尼埃的《攝影發現史》中推測:“最早有關攝影的想法,人們在大約18世紀中葉一部諾曼人蒂費涅·德·拉·羅謝(Tiphaigne de la Roche)的著作中找到了。[……]這部著作就是寫作于1760年的寓言小說《吉凡提》(Giphantie
),1862年被邁耶和皮爾遜重新發現,而且經常被人們拿來重溫其中‘攝影’的部分。蒂費涅把一座大廳比作一個暗箱,大廳的墻壁上有一幅‘畫’,無論是色彩還是動感,都如實地表現了躁動的海景。某些‘元素精靈’能夠把這些‘轉瞬即逝的影像’固定在一塊在一種‘非常微妙的物質’中浸泡過的金屬上,最終形成的永久影像‘更加準確,任何人無法做得出來,而且又是如此完美,時間也無法把它摧毀掉。’”
③ 參見《攝影哲學》第七部分“心理圖式之觸發”,第57—67頁。
④ 參見蘇林《朝向他者的哀悼與攝影——解讀德里達的〈羅蘭·巴特之死〉》中的第二部分“攝影里的死亡與幽靈”及結語,第36—42頁。
⑤ 在《羅蘭·巴特之死》中,德里達談及“研點”與“刺點”的關聯時曾說:“研點中有刺點,死亡的他者在我之內存活。攝影的概念拍攝出了所有概念的對立,在對立中隱藏著或許構成一切邏輯的縈回關聯。”(Derrida27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arthes, Roland. “Le message photographique.”Communications
1(1961): 127-138.羅蘭·巴特: 《明室: 攝影札記》,趙克非譯。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 -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 Trans. Zhao Kefei.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1.]喬弗里·巴欽: 《熱切的渴望: 攝影概念的誕生》,毛衛東譯。北京: 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6年。
[Batchen, Geoffrey.Burning
with
Desire
:The
Conception
of
Photography
. Trans. Mao Weidong. Beijing: China National Photographic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6.]——: 《更多瘋狂的念頭: 歷史、攝影、書寫》,毛衛東譯。北京: 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7年。
[- - -.More
Wild
Ideas
:History
,Photography
,Writing
. Trans. Mao Weidong. Beijing: China National Photographic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7.]
安德烈·巴贊: 《電影是什么》,崔君衍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7年。
[Bazin, André.What
Is
Cinema
? Trans. Cui Juny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瓦爾特·本雅明: 《攝影小史》,許綺玲、林志明譯。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
[Benjamin, Walter.A
Short
History
of
Photography
. Trans. Xu Qiling and Lin Zhiming.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9.]Bonitzer, Pascal. “La surimage.”Cahier
du
cin
éma
270(1976): 29-34.Cavell, Stanley.The
World
Viewed
:Reflections
on
the
Ontology
of
Film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喬納森·克拉里: 《觀察者的技術》,蔡佩君譯。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
[Crary, Jonathan.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 Trans. Cai Peiju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7.]Derrida, Jacques. “Les Morts de Roland Barthes.”Po
étique
47(1981): 269-292.Dubois, Philippe.L
’acte
photographique
et
autres
essais
. Paris: Nathan, 1990.Edwards, Paul.Soleil
noir.
Photographie
et
litt
érature
des
origines
au
surr
éalisme
.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8.米歇爾·福柯: 《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
[Foucault, Michel.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 Trans. Xie Qiang and Ma Yue.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7.]——: 《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2017年。
[- -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 Trans. Mo Weimin.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7.]Freund, Gisèle.Photographie
et
soci
ét
é. Paris: Seuil, 1974.Galassi, Peter.Before
Photography
:Painting
and
the
Invention
of
Photography
.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1.高名潞: 《西方藝術史觀念: 再現與藝術史轉向》。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Gao, Minglu.Concepts
of
Western
Art
History.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urn
of
Art
History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Lemagny, Jean-Claude, and André Rouillé, eds.Histoire
de
la
photographie
. Paris: Larousse-Bordas, 1988.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 《皮爾斯: 論符號》,趙星植譯。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2019年。
[Peirce, Charles Sander.Peirce
on
Signs
. Trans. Zhao Xingzhi.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19.]Ruskin, John.The
Works
of
John
Ruskin
. Vol.15. London: George Allen, 1904.Schaeffer, Jean-Marie.L
’image
pr
écaire.
Du
dispositif
photographique
. Paris: Seuil, 1987.蘇林: 《朝向他者的哀悼與攝影——解讀德里達的〈羅蘭·巴特之死〉》,《文學評論》6(2019): 33—43。
[Su, Lin. “The Other in Mourning and Photography: An Interpretation of Derrida’sThe
Deaths
of
Roland
Barthes
.”Literary
Review
6(2019): 33-43.]Tagg, John.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8.亨利·范·利耶: 《攝影哲學》,應愛萍、薛墨譯。北京: 中國攝影出版社,2018年。
[Von Lier, Henri.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 Trans. Ying Aiping and Xue Mo. Beijing: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2018.]謝宏聲: 《圖像與觀看——現代性視覺制度的誕生》。桂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
[Xie, Hongsheng.Image
and
Seeing
:The
Birth
of
a
Modern
Regime
of
Visuality
.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