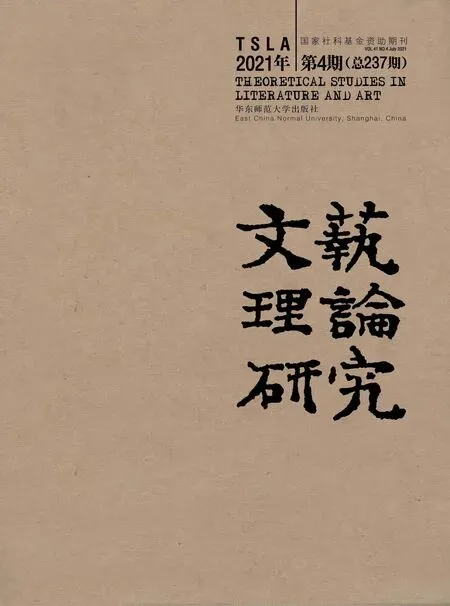“時間轉向”的三重維度:西方當代藝術的“當代性”理論及其問題
董麗慧
“時間轉向”(temporal turn)作為一個術語,是相對于20世紀前期的“語言學轉向”(lingustic turn)和20世紀后期的“圖像轉向”(pictorial turn)等人文學科研究范式的轉變而繼起的,這一表述在近十余年逐漸成為一種理論研究趨勢和當代藝術的重要議題。在藝術創作和藝術史研究中,主要指從專注于以后現代解構和后殖民身份政治為主要方法和議題的圖像闡釋,轉而在質疑以往默認的線性時間敘事的基礎之上,從多個維度探究與時間相關的議題,圍繞諸如錯時性(anachronism)、當代性/同時代性(contemporaneity)等關鍵詞,展開了豐富的藝術創作實踐、藝術理論建構和藝術史書寫的嘗試。
在當代藝術領域,這一趨勢和議題自世紀之交以來日益顯著。隨著當代藝術實踐的活躍,研究者在學理層面的探討亦漸趨深入,歐美學界對“當代藝術”在概念、時間、性質上界定的爭議激增,“當代藝術”作為一個術語被賦予了不止于字面“當下的藝術”的諸種特指內涵,而試圖對“當代藝術”進行理論闡釋或質疑的“當代性/同時代性”(contemporaneity)一詞,也被賦予了不止于字面所謂“當下藝術的屬性”的更多重內涵。尤其自2004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召開的“現代性≠當代性”(Modernity≠Contemporaneity)學術研討會及2009年關于“當代藝術”的集中討論(October
調查問卷和e
-flux
同名專題討論)以來,“當代性”成為歐美當代藝術學界熱點之一,“當代性”一詞也已從丹托意義上指稱當下的狀況或當代藝術的屬性這一作為形容詞“當代的”(contemporary)名詞含義,轉而成為具有特定內涵的,且處在不斷爭議中的術語(高名潞526—538)。就目前英語學界對當代藝術的“當代性”討論而言,影響最為跨界的,當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對“當代性”(或譯“同時代性”contemporaneità)的論述,指“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特關系”,既依附時代又與時代保持距離,源自一種“不合時宜”(untimely),這一觀點在當代藝術界廣為引述;格羅伊斯(Boris Groys)則基于對數字媒體藝術的研究,認為“當代性”體現為一種“共時性”(synchronization),“當代”是“時間的同志”(zeitgen?ssisch/comrade of time),當代藝術是“與時間在一起”(with time)的藝術;英國哲學家彼得·奧斯本(Peter Osborne)在其關于當代藝術的哲學中提出,“當代性”不僅是“在單一時間之中”(in time),更是“關于時間的復數”(of times),是作為“當下多種時間的斷裂統一體”(a disjunctive unity of present times)存在的“虛擬”(fiction)敘事。
綜觀上述關于當代藝術的“當代性”理論,可以看到,雖然其建構模式和側重點各有不同,但均圍繞“時間”(time)展開,或與時間斷裂和脫節(阿甘本),或化身為時間流本身(格羅伊斯),或從諸種時間中提取出某種虛擬性(奧斯本),共同經由對西方現代時間觀和進步觀的抵抗和逃逸,展開了三重試圖掙脫現代時間的當代“時間轉向”(temporal turn)。在西語語境中,“當代性”與時間的這一密切關系,一方面源自“當代”一詞的拉丁詞根“時間”(tempor),另一方面又是對此前“現代”時間觀及在此基礎上西方“現代藝術”范式的反抗與超越,力圖為“當代”開辟偏離現代線性、單一、 單向度時間敘事的可能性。
放棄“現代”一詞,轉而求助于“當代”,這不僅是字面上的新舊更替,而是回到了各自的拉丁詞源。“當代”(contemporarius/contemporalis)意味著“與時間同在”,而“現代”(modo/modernus)意味著“剛剛發生”,前者直指當下這個“現在”,后者卻停留在已經發生過的“剛才”。如果作為“剛才”意義上的“現代”已不可挽回地被線性發展觀附著而掏空了當下的可能性,那么作為“與時間同在”的“當代”則既是對未來的反抗,也是對未來的敞開。其中,前一個要移除的未來,指的是現代時間觀中以犧牲當下而可預期、可操控卻永不可到來的烏托邦未來,后一個要重塑的未來,指的則是“時間轉向”后,有著多元維度和多重可能的開放式未來,而無論這兩個未來有什么區別,“現代”始終是“當代”及“當代性”理論研究的一個基本參照物。基于“現代”的基礎反抗“現代”,在這個意義上,“時間轉向是非進步的(non-progressive): 它的進步性在于對現代進步的重審”(Ross 6),它終結的是通過許諾未來而抽空當下的“現代”時間,開啟的是通過回溯過去而指向當下的“當代”時間。
本文認為,“時間轉向”是理解西方語境關于“當代性”理論的一個關鍵,而厘清圍繞這一“時間轉向”展開的諸種代表性嘗試路徑,是進入當代藝術的“當代性”理論討論的前提。鑒于目前漢語學界對“當代性”的使用和討論,要么仍沿用世紀之交以觀念性、后現代性、對抗性為特征的觀點,要么更注重時代性、創新性、對當代問題的關切性等外部特征,而尚未對其西語語境中內在的“時間”維度展開充分解讀(王林98,盛葳36—37,時勝勛11—13),本文即從當代藝術理論中的“時間轉向”這一議題入手,對近年來引起爭議的歐美“當代性”理論及其具有代表性的三種歐美“當代性”理論、其構建方式及存在的問題進行檢視和梳理,以期對“當代性”問題的探討有所啟發和推進。
一、 “時代錯位”和“同時代性”
當代性(或同時代性contemporaneità/contemporariness)就是指一種與自己時代的奇特關系,這種關系既依附于(或忠于adhere to)時代,同時又與它保持距離。更確切地說,這種與時代的關系是通過脫節(out-of-jointness)或時代錯位(anachronism)而依附于時代的那種關系。(Agamben 41)
阿甘本關于“當代性”的這段話,問世十余年來已為學界廣為引述。此文出自2007年威尼斯建筑大學哲學研討班開課之際,阿甘本作的題為《什么是當代》的演講。這篇演講稿于2008年以意大利文出版,2009年英譯結集出版,2010年中譯見刊。與阿甘本的演講同步,此時的藝術界正值對“當代”和“當代性”討論熱度的上升期,急需對“當代”概念更為理論化的思考(Foster 10),在這樣的語境中,阿甘本對“當代”的論述也迅速進入當代藝術界。
2009年,在配合上海當代藝術展(ShContemporary)舉辦的“什么是當代藝術”同名講座中,知名策展人奧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即以阿甘本對“當代”的論述開篇和結尾,尤其強調了阿甘本以考古的方式考察當代的方法,“作為當代意味著返回到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當前時刻,通過破裂和不連續性來抵御時間的同質化”(e-flux 68)。2011年,時任《藝術論壇》(Artforum
)主編的蒂姆·格里芬(Tim Griffin)在談到“過去五年”藝術界愈加令人困惑的“當代”一詞時,稱“如果有一種關于‘當代’的實在感,那應該就是哲學家阿甘本所說的‘脫節’: 成為當代意味著時間的斷裂,意味著總是同時‘太早’又‘太遲’——或更準確地用現在的藝術(art now)來表述,意味著含有它自身的時代錯位的種子”(Griffin 288—289)。其中,中譯多將原文“當代”(contemporary)和“當代性”(contemporaneità/contemporariness)譯為“同時代”和“同時代性”,突顯了阿甘本賦予這一詞匯的獨特內涵。可以說,與中文日常用語中通常所說的作為一種時代精神和緊隨時代的價值選擇、與求新和追求社會進步密切相關的“當代性”恰恰相反(Gao 149),阿甘本的“當代性”首先主張與時代保持距離,通過“時代錯位”才能夠“把握時代”,反之,“過于契合時代的人,在所有方面與時代完全聯系在一起的人,并非當代人”(Agamben 41)。
概括而言,阿甘本的“當代性”及其“時代錯位”指向三層含義。這一“當代性”首先是一種與時代的復雜關系。既依附于時代,又與時代保持距離;通過與時代錯位、脫節和保持距離,關切和實現對所處現在時代的依存。這一關系與本雅明筆下的“游蕩者”既觀察時代又冷漠、與時代格格不入,以及布萊希特通過“間離效果”以保持距離的方式喚醒觀眾的觀看一脈相承。成為阿甘本意義上的當代人,或具有當代性,一方面意味著與時代斷裂和脫節,“既不與時代完全一致,也不讓自己適應時代要求”。在阿甘本看來,“正是通過這種斷裂與時代錯位,他們(指真正的當代人)比其他人更能夠感知和把握他們自己的時代”。而成為當代性的另一方面要素則是,這些“才智之士”(intelligent man)不能是避世隱居的懷舊者,他們明白,“他無可改變地屬于這個時代,無法逃離他自己的時代”(Agamben 41)。正是在阿甘本“當代性”的這層含義上,蒂姆·格里芬贊同真正當代的藝術就是要么“太早”要么“太遲”的、從時間中斷裂而出的藝術(Griffin 289)。
其次,阿甘本的“當代性”進而強調一種與眾不同的(即真正當代的,或同時代的)時間體驗。只有能夠“感知”并深深“凝視”自己時代的“黑暗”(指“力圖抵達我們卻又無法抵達的光”),并且能夠不斷回溯(“返回到我們在當下絕對無法親身經歷的那部分過去”)的人,才是有“當代性”的人。正因為“當下”(present)不僅是最遙遠的存在,也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抵達我們的”(Agamben 47),真正的“當代性”才是一種“回歸到我們從未身處其中的當下”的體驗(Agamben 33)。這一對不可能抵達的真理之光的凝視和對無可親歷的過去的追溯,與阿甘本“無功用性”(inoperasità)理論一脈相承,凝視和追溯本身即是“無功用”的懸置,是線性的、功用性時間的切片和斷裂,是在不再憧憬一個清晰可見的未來之后,對未知和“未經體驗”之物在經驗上的敞開,以此呈現被日常遮蔽的運行機制,從而面向更多或有的可能性,是阿甘本對現代進步時間觀的一種抵抗策略。
最終,阿甘本“當代性”的實現指向一個“彌賽亞時間”(messianic time),即恢復與神共存的“使徒”(而非指向未來的“先知”)所生活的“當下時間”,它是瞬間達成的永恒,以不期許一個可預期未來的方式隨時降臨,是真正“關于現在的時間”。這一時間與通常意義上的“編年時間”相對,阿甘本稱之為“剩余時間”(the time that remains),它是線性編年時間的停止和斷裂,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褶皺與相遇,是“時間和時間的終結之間剩余的時間[……]既不是今世(olamhazzeh)的時間,也不是來世(olamhabba)的時間,它毋寧是這兩個時間之間的時間”(阿甘本論友愛49—50)。通過引入這一“非同質性”時間,阿甘本分割了世俗意義上的時間,“在不同時代(times)之間建立一種特殊關系”,打破“了無生機的同質性”(Agamben 53),以回溯而非進步的方式,嘗試著對線性時間觀的超越。這一與同質和線性時間的斷裂,為我們指出向“多重時間”敞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泰瑞·史密斯認為阿甘本最具創造力的觀點,即“多重時間之間的某種當下聯系組成了一種新的歷史現象”(Smith 283)。
可見,理解阿甘本“當代性”的關鍵在于時間觀的超維度,或(與格羅伊斯和奧斯本相比)可稱為升維: 從現代進步的二維線性時間觀,升級至具有“當代性”的三維“彌賽亞時間”。這一“當代性”始自“時代錯位”的不合作態度,經由無功利的時間體驗,以隨時可進入的“彌賽亞時間”為“當代性”的真正實現。
阿甘本不僅將時間分成“編年時間”和“剩余時間”,還以此區分了以這兩種不同方式體認時間的人群,只有能夠跳出“編年時間”而以“彌賽亞時間”的三維時間觀感知這“剩余時間”的人,即少數作為幸存者的“余留人”(remnant),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當代人”:“前者(指活在編年時間中的人)任由時間流逝,滿足于過著周而復始的機械生活;而后者(指活在剩余時間中的余留人)則是積極地、‘彌賽亞式’地捕捉時間(讓彌賽亞就在現在到來)。”(阿甘本,《剩余的時間》21—22)至此,可以看到,一方面,處于同一個時空的同代人,被阿甘本劃分成了少數“真正的當代人”和其他無知無識庸碌之人;另一方面,阿甘本卻并無意于將“當代性”與“現代性”加以區分,其“關于現在的時間”的“當代性”與本雅明“現代作為救世主時代的典范……時間的分分秒秒都可能是彌賽亞側身步入的門洞”(本雅明276)的思想資源可說是一脈相承的。因而,泰瑞·史密斯指出,阿甘本的“當代”只屬于哲學家、詩人這些所謂能夠理解當代性“真正本質”的思想者(Smith 281)。而如果“真正的當代人”只能來自思想者或“才智之士”,將之平移至當代藝術創作中,那么實際上,這一以“時代錯位”為特征的“當代性”理論不僅仍是尼采、波德萊爾、布萊希特、本雅明等“現代性”理論的延續,也仍是黑格爾至丹托一脈哲學對藝術褫奪和終結、思想大于創作的延續。
因而,在泰瑞·史密斯等更為關注當代藝術實踐、個案和現場的研究者看來,作為哲學家的阿甘本,其理論構建的“當代體驗”,在本質上仍是一種與現代性一脈相承的“普遍體驗”(universal experience),而并不具有針對當下的實在性: 阿甘本的“當代性”既尚未實現,也不可能實現,雖比現代性的短暫流變更為短暫流變以至虛無縹緲,卻仍是現代性體驗換之以當代名義的“重演”(replay)(Smith 283)。畢竟,不僅阿甘本對時代晦暗的“當下”體驗與波德萊爾關于“惡之花”的發現,和對過渡、短暫、偶然的現代性體驗(以及上述本雅明和布萊希特的現代主義理論)有著顯見的一脈相承,實非當代特有;阿甘本關于“當代性”行文中的文藝理論引證也皆來自“現代”,導致其所述“當代體驗”實際上更接近抽空現實的形而上玄想。因而,史密斯認為,這一“當代性”體驗并不能勝任“當代藝術”鮮活的“當代性”。
此外,阿甘本“當代性”的另一個問題在于,憧憬一個排他性宗教的“彌賽亞時間”,往往導致其對最新奇、最具問題性、最活生生的諸種當下現實(亦即最能啟發思考的“當代”本身)的抽離。在這個意義上,阿甘本式“防御性的彌賽亞主義”被指責為不僅不能勝任“直面當代性的任務”,反而閉合了向著更多可能性的敞開,歷史和現實恰恰被一言以蔽之地抽空和簡化,導向了阿甘本試圖反抗的時間的同質化(coevalness): 阿甘本式強調與時代錯位、期許一個彌賽亞時刻的“當代性”,雖力圖將二維線性時間敘事升維,且引領著當代藝術界針對不同時間并置展開了新的思考,但遺憾的是,最終卻仍為一種限定性的時間觀所統攝(Erber 44),而吊詭的是,這一處于永恒的將臨而未臨狀態的時間觀,至少從字面意義上看,恰恰是古老而排他的,是與“當代”格格不入的。
最后,如果跳出理論語境的推演與思辨,重返當下藝術現場,可以看到,就對當代藝術研究領域的針對性而言,阿甘本的“當代性”在概念生成和實踐生產兩方面分別具有先天和后天的不足。一方面,如泰瑞·史密斯所指出的,阿甘本“當代性”理論的提出,先天仍是建基于“現代”藝術案例,而非扎根于活生生的“當代”藝術現場。另一方面,就阿甘本式“當代性”理論落地于當代藝術實踐而言,可以看到,這一理論在應用于當代藝術創作、當代藝術研究、當代藝術史的書寫等方面,均無力提供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而不止于此的是,阿甘本關于“當代性”的文字,在現行當代藝術體制內,更常見的用法則是類同于某種流行理論或標語口號,反而為阿甘本反對的固化的當代藝術范式持續提供看似正確,卻缺乏實質內涵的理論依據,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奧布里斯特(HUO)對它的使用——然而,作為當代藝術“時尚界”的新權威,奧布里斯特的權威本身也已被視為當代藝術范式化生產的推手而遭到質疑(Balzer 25—59)。
二、 “共時性”和“時間的同志”
我們的當代與其他所有已知歷史時期至少在一個方面是不同的: 人類從未對其自身的當代性(contemporaneity)如此感興趣。中世紀對永恒感興趣,文藝復興對過去感興趣,現代性對未來感興趣。我們的時代主要對自身感興趣……全球化進程、信息網絡的發展(它告訴我們實時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造成不同地方歷史的同時性(synchronization)。我們的當代性正是這一共時性的結果,一次又一次使我們產生震驚感。震驚我們的并非未來,而通常是我們自己的時代(time),詭異(uncanny)而怪誕(weird)。(Groys,In
the
Flow
137)2009年12月,在為在線藝術雜志e
-flux
“什么是當代藝術”專輯撰文時,格羅伊斯即以“當代性”開篇:“只有表明自身的當代性(its own contemporaneity),當代藝術才配得其名,這不是僅憑最新制作或展示就能實現的。”(Groys,Comrades
of
Time
1)在格羅伊斯這里,“當代性”是“當代藝術”得名之所在,是“當代藝術”區別于其他藝術(包括其他時代的藝術和同時代的其他藝術)的特性,這看似與丹托式“當代性”和“當代藝術”的同義反復類似,但二者在內涵和外延上均不相同。一方面,二者在時間、地域和媒介界定上有著明顯差異。丹托將“當代藝術”(或后歷史時期的藝術)及“當代性”的出現定位于20世紀70年代中葉的歐美藝術中,而格羅伊斯區分了整個20世紀以機械復制為特征的現代藝術和以數碼復制為特征的藝術的“新時代”,并將后者定位于21世紀之交基于全球互聯網的數碼藝術。另一方面,就“當代性”和“當代藝術”與當下時代的邏輯而言,丹托式“當代性”和“當代藝術”同為時代感受的影射,某種程度上仍是反映論的延續。與之相比,格羅伊斯以“自身的當代性”界定真正配得“當代藝術”之名的藝術形態,從作為時間自身的“時間流”(time flow)角度,找到了最契合、最能揭示當代時間本身的藝術形式——“基于時間的藝術”(time-based art)。其中,對“時間”的理解仍是關鍵。與阿甘本引入無功用的時間維度以超越世俗線性時間類似,格羅伊斯引入現象學對時間自身如其所是的呈現,試圖以藝術的方式揭示被遮蔽的真正的時間,以區別于從事現代社會生產的、指向功利和有用性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時間。正是在這一對待時間的不同態度上,格羅伊斯訴諸時間“自身的當代性”與丹托反映當下的“當代性”出現了本質的差別。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格羅伊斯從德語“當代(zeitgen?ssisch)”一詞引申出“當代”作為“時間的同志(Zeit-genosse/comrade of time)”的含義。在格羅伊斯看來,“同志”意味著彼此互助排憂解難,成為當代即意味著與時間本身的合作,而“當代性”既是“共時性”(synchronization)的結果,也只有通過與時間本身攜手同在的“共時性”才能真正實現。
從字面上看,這與阿甘本強調“時代錯位”(anachronism)的“當代性”對時間的態度恰恰相反,但實際上,格羅伊斯的“共時性”并非走到了阿甘本的反面(即完全與時代契合),而是同樣受到海德格爾式作為存在的純粹時間的影響,其呈現“懸置時間”(suspended time)、“多余時間”(excessive time)的訴求也與阿甘本有類似之處。如果說二者在“當代性”問題上對時間的態度有什么不同,那么主要在于通往時間切口或打開本真時間的路徑不同。阿甘本通過與時代疏離,期待一個真正當代的“彌賽亞時間”對世俗編年時間的終結和面向更多可能性的敞開,而格羅伊斯的路徑則是以藝術的方式回歸時間本身,可以說,就對當代藝術實踐的針對性而言,格羅伊斯的“當代性”比阿甘本更進一步。
與阿甘本對“當代性”未與“現代性”加以區分的使用不同,格羅伊斯明確劃分了“現代性”和“當代性”的不同特征,并指出其各自對應的藝術形態。在格羅伊斯看來,“現代性”屬于機械復制時代,世界以可見的“圖像”(image)形式存在,原作和副本有視覺相似性,原作因其獨一無二的在場和歷史性而具有“靈韻”(aura),副本則因缺乏語境和歷史性而沒有“靈韻”。與之相比,“當代性”屬于數碼復制時代,世界以不可見的“圖像檔案”(image file)形式存在,原作是以代碼存在的數據,副本是代碼經由顯示屏轉譯后的視覺呈現,副本與原作不具視覺相似性,每個副本都因用戶屏幕等具體承載媒介存在差異而不具同一性,因而可以說每個副本都是視覺意義上的原作,用戶的身體性觀看和使用賦予其“靈韻”(即具體語境、歷史性和在場性)。這一原作和副本關系的徹底改變,在格羅伊斯看來,即是“現代性”和“當代性”斷裂的標志(Groys,In
the
Flow
144)。格羅伊斯認為“現代性”是“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而“當代性”是對日常經驗(everyday experience)和自然的回歸。就現代性的“化約主義”而言,格羅伊斯梳理出前衛藝術家和現代思想家兩條不同的化約之路,前者將藝術化約為去精英化的工業復制品。對后者而言,鑒于機器取代人工的自然生產方式、機械性能挑戰人性,回歸自然本性(nature)和本源(origin)成為20世紀包括本雅明、阿多諾、海德格爾、格林伯格等現代思想家對現代商業大眾文化反抗的資源,生發出對“靈韻”、原創性(originality)、起源(origin)、被遮蔽的自然本真和原初(original)的懷念。然而,這一對自然本源的追溯卻反而被化約為“靈韻”時刻,“在由機械復制定義的現代性范式中,現在的在場只在某一時刻能得以體驗,即革命性的時刻,化約的靈韻時刻[……]這就是為什么現代性是一個永遠呼喚革命的時代”(Groys,In
the
Flow
141-142)。如果說阿甘本與使徒同在的“彌賽亞時間”也是這一現代性“靈韻”時刻的當代復臨,那么,格羅伊斯的“當代性”既不回溯過去也不憧憬未來,既不是終結也不是開始,既不是瞬間也不是永恒,它只專注于自身,隨時間流動。在“當代”不同于“現代”,并且“當代性”不同于“現代性”這個意義上,格羅伊斯認為,現代追逐永恒,以進步、行動、目標清晰為特征,它指向未來、抽空當下,現代產品的生產,以犧牲和失去時間為代價,產品和時間分離。而當代不再是過去向未來的轉折點,當下不再指向任何可翹首以盼的未來。當代是懷疑的時刻(time of doubt),是在無聊、遲疑、重估中的“永久性重寫”(permanent rewriting),當代的時間是沒有方向的、重復的時間,以此反抗線性歷史,格羅伊斯稱之為“非歷史的多余時間”。而最能反映這種時間狀況的、最具“當代性”的,就是將這一“非歷史的多余時間”主題化的、成為“時間的同志”的“基于時間的藝術”(time-based art),即與傳統基于空間的繪畫、建筑、雕塑等“再現空間的藝術”(即萊辛意義上的造型藝術)不同的視頻和數碼藝術。

Comradesof
Time
9-10)。那么,問題是,在人人都是當代藝術家的“當代”,職業的當代藝術家何為?為回答這一問題,格羅伊斯引入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區分了兩種展示空間不同的“基于時間的藝術”: 一種是觀者在電腦前,靜觀(指觀者身體不動)隨時間流動的動態影像;另一種是觀眾在博物館空間,在行走中動態瀏覽藝術家展示的動態影像。前者因觀者身體的低感知度(虛擬互動只存在于想象中而非實體身體性的)和對網絡信息的高聚焦度,成為麥克盧漢意義上排斥參與的“熱媒介”;后者則因觀眾身體自由走動的高參與度、在動態中瀏覽動圖的低清晰度,成為麥克盧漢意義上更具參與性的“冷媒介”(Groys,AGPA
30—31),即格羅伊斯稱之為“冷沉思”(cool contemplation)的藝術: 既不同于傳統冥想式的“熱沉思”,也不同于現代意義上以“行動的生活”對冥想式沉思的反抗——“冷沉思不以生產審美判斷或選擇為目的。冷沉思僅僅是觀看姿態的永恒重復,意識到通過全面的沉思而作出明智判斷所需的時間的匱乏。以時間為基礎的藝術在此顯示了無法被觀者吸收的、徒勞的、多余的時間‘糟糕的無窮盡’”(Groys,Comrades
of
Time
10)。那么,照此進一步推演下去,格羅伊斯將這一“當代性”的時間特質與博物館的空間特質相結合的主張就順理成章了: 正是當代博物館空間,將現代意義上功利時間的匱乏,轉為無功利時間本身的重復,使觀眾感知時間的無意義,得以體驗自身的身體意識,從而成為當下存在本身。至此,可以得出結論,視頻影像和互聯網裝置這種隨時間流動的、“基于時間的藝術”,加之在需要觀眾身體性參與的特定空間(如博物館)中展出,即“冷沉思”的藝術,才是在格羅伊斯看來最具“當代性”的藝術。
可以看到,格羅伊斯提出的“當代性”,不僅要求呈現“基于藝術的時間”(即當代藝術“此時此地”的時間性本身),還要求將該時間置于一個“去蔽”(unconcealment)的空間之中,即格羅伊斯所說的當代藝術作為“裝置”(installation),“這一裝置是為了實現如下目的的一種空間: 在這里,‘此時此地’得以浮現,對大眾的世俗啟迪得以發生”(Groys,Politicsof
Installation
6)。因而,針對當代藝術現場,可以說格羅伊斯的“當代性”理論天然具有對特殊時間性和空間維度的雙重限定——它明確指向召喚觀眾的視頻影像和互聯網藝術,并因對直面公眾的強調,而區別于服務藝術市場、直面買家(而非公眾)的、滿足于維系日益僵化的當代藝術范式的體制化“當代藝術”。正是在這一抵抗意義上,格羅伊斯的“當代性”與行動主義藝術(activism art)在抗拒主流當代藝術的整體審美化等方面合流(Grois,In
the
Flow
43)。后者尤以2011年藝術家參與“占領華爾街”事件為標志,在近年來直接引出了試圖從命名上超越范式化“當代藝術”的“后當代藝術”(postcontemporary art)議題(Mckee 784),不過,其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 試圖以化身政治行動的方式拯救泥潭中的當代藝術,這樣的嘗試在現代藝術史上屢見不鮮,卻既未能長遠而有效地拯救危機中的藝術,還時常陷藝術于更決絕的毀滅之中。三、 “當下(多種)時間的斷裂統一體”和“虛擬的當代性”
[……]當代性(contemporaneity)的結構是自我變化的。甚至當代性作為一種狀態這個想法也是新的。與此同時,這一術語的廣泛傳播已將它置入被抽空的危險之中: 從持續增長的復雜時間、社會和政治含義中抽空,僅被用作一個簡單的標簽或時代分類。其備受關注的原因是,當代性(con-temporaneity)獨特的概念文法,最恰切地表達了過去幾十年歷史不斷變化的時間特性(temporal quality)的獨特和重要性——這不僅是“在(單一)時間之中”(in time),更是“關于(復數的)時間”(of times): 我們并非僅僅與我們的同時代人(contemporaries)一起生活或生存“在(單一)時間之中”,就仿佛時間本身對這一共存毫無差別;更確切地說,當下越來越以有差異但同樣“在場的”時間性(different but equally “present” temporalities)或“多種時間”(times)為特征,是一種處于斷裂中的時間統一體,或稱之為當下(多種)時間的斷裂統一體(a disjunctive unity of present times)。(Osborne 22-23)
彼得·奧斯本2013年出版的《無所不在或根本沒有: 當代藝術哲學》被認為是第一本試圖為當代藝術建構理論體系、全面探討“當代藝術”的哲學(而非當代的“藝術哲學”)著作,一經出版即引起了當代藝術界的關注,2019年仍被評價為“至今為止”哲學家最翔實且最持續介入當代藝術及“當代性”理論的著作(Smith 293)。奧斯本認為,雖然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了藝術哲學的復興,但并沒有真正建立起關于“當代藝術”的哲學,而現行討論的失敗則在于未能哲學地把握藝術的“當代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非歷史性和重返美學。在奧斯本看來,既不存在非歷史的藝術本體,也不存在當代藝術的純“美學”,二者一方面導致對當代藝術的討論停留在不涉及真正“當代性”的觀念狀態(conceptual condition),另一方面又造成“當代藝術”這個詞本身并無可供批判性討論的學術內涵,而僅僅用來指稱當代藝術界激進、異質的經驗整體,陷入了“平庸的經驗主義”(indifferent empiricism),這是目前進行“當代藝術”研究的最大障礙。鑒于此,奧斯本即嘗試為當代藝術提供批判性的理論話語。具體到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就奧斯本對當代藝術“理念”(idea)的批判式建構而言,這一“批判”是康德意義上的、重溯早期德國浪漫主義哲學的批評傳統;另一方面,就其對體制和審美的批判而言,又追溯至本雅明、阿多諾一脈,奧斯本稱其為“后阿多諾”式的研究方法,是阿多諾意義上“超越哲學的哲學”(Osborne 8-17)。
那么,奧斯本認為他的研究方法既是反對“非歷史”傾向的,也是“反美學”的。所謂“反美學”,即既反對回到審美經驗的經驗主義傾向,也反對以美為審美對象和評判標準的非政治化傾向,而試圖以政治哲學的方式建構一個“更為普遍的當代概念”,是當代藝術哲學得以進行的前提。奧斯本認為“當代”應當是一個具有結構性和歷史內涵的學術概念,而“當代性”則是“當代藝術”最具批判性意義的體現:“當代(the contemporary),首先,在結構上,呈現為一種理念(idea)、問題(problem)、虛構(fiction)和任務(task);其次,就歷史而言(以其最近形式),呈現為全球性的跨國時代。當這一構想轉移至藝術領域,當代藝術在最具批判性的意義上,則呈現為當代性(contemporaneity)的藝術結構及其表現。”(Osborne 20)那么,具體而言,奧斯本意義上的“當代藝術”和“當代性”指的是什么呢?為回答這一問題,結合反對“非歷史”的研究方法,奧斯本主張首先以概念史的方式對“當代”一詞進行“歷史性”溯源。
根據奧斯本的研究,英文“當代”(contemporary)一詞出現于17世紀中葉,源自拉丁文“與時間在一起”(together with time),意指時間上的共存和同時發生,更接近于“同時代”的含義。直到二戰之后,英文“當代”一詞“才開始獲得它最近的歷史和批評性的含義”: 先是作為“現代”(modern)這個詞的一部分,指稱“最近的現代”(the most recent modern),之后逐漸成為與“現代”相對照的、新的時間分期概念。具體就英文“當代”一詞指稱“藝術”的時間軸而言,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后,出現了“當代的藝術”(contemporary arts)這一表述方式,泛指“最近的藝術”,但直到60年代,西歐、北美和南美的英、法、西葡語境中才廣泛使用這一詞語。不過,到70年代,“當代藝術”仍然指稱“最近的現代”藝術的延續,而非可供批判性使用的新概念。80年代以后,隨著“后現代”逐漸成為區別于“現代”的指稱,“后當代”(post-contemporary)也隨之出現,成為“后現代”的另一稱謂,此時,“現代”一詞已經成為對剛剛過去的歷史時間段的指稱,而不再對當下有效。直到“最近十年”,即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后現代”一詞對當下指稱的失效和過時,“當代”這一稱謂才真正作為一個批判性的概念進入學界討論。其中,奧斯本認為,戰后“當代”一詞含義的轉折,可能正是始自戰后歐洲一體化及其共享時間觀的成形(Osborne 21-23)。
除以縱向概念史維度梳理“當代”一詞之外,奧斯本繼而以地緣政治視角,指出“當代藝術”這一稱謂在不同政治文化語境中的不同內涵,而其共性和合流的節點之所在,才是奧斯本意義上具有“當代性”的當代藝術之開端。首先,奧斯本指出,現行通用的“當代藝術”詞義,誕生于冷戰政治的歷史語境: 首次使用“當代”一詞明確指稱與“現代藝術”不同的藝術形態,并非發生在西歐北美,而是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陣營,盧卡奇以“當代現實主義”(contemporary realism)專指與歐美頹廢的“現代藝術”不同的、最先進的、總體性的藝術,而直到80年代,伴隨藝術市場的繁榮和拍賣行業的分類需求,西歐和北美語境中對“當代藝術”(或“1945年以后的藝術”)的使用,才逐漸與作為歷史現代主義的“現代藝術”區別開來,專指抽象表現主義以來的,且區別于社會主義陣營的歐美新藝術形態。
在“當代”概念史時間軸和地緣政治基礎上,奧斯本將通常意義上的戰后“當代藝術”分成“新前衛”(neo-avant-gardes)、“后觀念藝術”(post-conceptual art)、“后前衛”(post-avant-gardes)三個階段。就這三個階段而言,20世紀60年代(即第二階段)因其作為全球化的開端和對文化政治等當下語境的參與,被奧斯本稱為“當代藝術”的開端,在這個意義上,“當代藝術就是后觀念藝術”(即超越了第一階段強調媒介自律的“觀念/概念”(conceptual)藝術)。不過,這一時期“當代藝術”的“當代性”仍是“國際化的美國霸權”的全球擴延,只有進入全球一體化、基于國際性展覽等當代藝術新體制的“后前衛”階段(即第三階段),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奧斯本意義上以“有差異但同樣‘在場的’時間性”為特征的當代藝術的“當代性”。
至此,可以看到奧斯本對“當代藝術”和“當代性”二者在具體時間上的區分是不同的: 奧斯本意義上的“當代藝術”是始自20世紀60年代、延續至今的“后觀念”藝術;而作為“當代藝術”最具批判性的、全球意義上差異共存的“當代性”,則始自1989年冷戰結束之后,且持續至今。其中,奧斯本明確指出,對包括“當代藝術”和“當代性”在內的“當代”概念的批判,是從事一種“時間的哲學”,一種既非經驗主義的,也不是包含一切時間的,更不是非歷史的“時間的哲學”(Osborne 8)。那么,如何從時間維度理解奧斯本意義上的“當代性”?其“有差異但同樣‘在場的’時間性”,又何以作為一個“統一體”而存在?
實際上,奧斯本對“時間”議題的關注,與他在20世紀90年代對現代性作為一種“時間的政治”的研究一脈相承。而與以“歷史時間的總體化”(totalizing temporalization of history)為特征的“現代性”相比,奧斯本的當代藝術哲學則提出“當代性”是“當下(多種)時間的斷裂統一體”(a disjunctive unity of present times)。這一“當代性”的悖論,在于它既多元異質、彼此斷裂,卻又能成為一個“統一體”,而這一悖論的存在,正依賴于當前全球化的藝術生產體制。
一方面,全球當代藝術的在地實踐是多元異質的,它們共時性的創作于世界各地,這些地域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差異,造成了這一同樣“在場的”(present)時間實際上在發展和觀念等諸多方面是不同步的、異質的,即所謂“有差異但同樣‘在場的’時間性”。但這樣的“異質共存”,至遲在19世紀上半葉拉美獨立戰爭、拿破侖建立統一歐洲帝國的失敗中就已發端(Liam 22),并不能構成“當代性”的獨有特征,因而,奧斯本的“當代性”得以成立,更重要的還取決于另一方面,即與多元在地實踐悖論性共存的,是全球當代藝術體制的趨同。全球當代藝術的展示、批評、交易等體制漸趨成熟,國際藝術雙年展即為此中顯例,奧斯本所謂當代性“統一體”的形成,正是這一持續趨同的當代藝術運行體制促成的,奧斯本稱之為自我“虛擬化”(fictionalization)。在這個意義上,奧斯本的“當代性”是呈現多元異質的“虛擬當代性”,是經由當代藝術體制建構的“虛擬”敘事。
雖然,在明確將“當代性”與“現代性”的時間觀區分開來這一點上,奧斯本與阿甘本不同,但在對現實疏離與批判的意義上,奧斯本的“虛擬當代性”與阿甘本的“同時代性”仍有著一致的訴求,即將“當代性”構想為一種不合作態度、一種“拒絕”。不過,二者的“拒絕”方式各不相同: 在阿甘本看來,這一“拒絕”通過脫節或時代錯位實現;而在奧斯本看來,這是“一種對其自身發展觀的、可預期的、投機的基礎的拒絕,其實現方式是一種真正的‘(多種)時間的整合’(total conjunction of times)。這是通過直面當下,而拒絕(可操控的)當下的未來;本質上是對政治的拒絕”(Osborne 29)。正是在這一批判性意義上,奧斯本的“當代性”是“施行中的虛擬”(operative fiction),當代是多種時間共存的、非實存的、作為一個整體的虛擬,不僅被動反映、呈現現實的諸種當代情境,更主動創造、投射出作為一個“統一體”的“虛擬當代性”。
可以說,奧斯本的“當代性”理論是其對現代性整一時間哲學研究的延續,與單一、總體、同質性的“現代性”時間不同,“當代性”時間是多種、斷裂、異時共存的,二者分別指向兩個不同的時間體:“現代性”指向總體化的時間統一體;“當代性”則是作為虛擬敘事存在的“多種時間的斷裂統一體”,其中,“多種時間的斷裂”以其共同對抗單一線性時間和現代進步時間觀的訴求,而構成了一個虛擬的“統一體”。
不過,雖然奧斯本反對“非歷史性”,但他的這一“虛擬當代性”理論卻恰恰因其將現實抽空為一種“理念”(idea)和想象中的“虛擬”,及其延續的“本土與全球”“個人與普遍”等一以貫之的、持續存在于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中的二元對立模式,被批評為建構了一個當代的“烏托邦概念”(高名潞540)。究其原因,也正在于奧斯本對當代藝術的研究視野仍局限于西歐北美為主導的“再現代主義”(remodernism)藝術樣式,其對國際雙年展等“文化工業”的批評也被認為是對現代主義精英思維的復魅(Smith 293-298),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了啟蒙運動以來與全球殖民同步的西方中心主義理論范式。
四、 結論與啟示:“時間轉向”的三重維度
當代藝術就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時間實驗場。尤其在過去的20年,聲稱美學在根本上是關于時間的,這已是老生常談[……]時間研究對當代藝術至關重要,它在于發展出這樣一種美學: 將時間和歷史并置,將時間流逝的當代體驗和現代歷史的確有其事并置。當代性在這里努力改變著(transform)現代性。(Ross 4-5)
上述“當代性”理論呈現出三種具有代表性的“時間轉向”方式,亦分別從三重維度探討了“時間轉向”的可能性: 阿甘本的“當代性”試圖將時間觀升維,引入三維時間觀,為二維的線性時間敞開一個切面,以與“時代錯位”為特征,通過不合時宜的時間體驗,懸置指向未來的功利時間,最終實現當下每一個可能的“彌賽亞時間”;與之相比,格羅伊斯的“當代性”則試圖將時間觀降維,以與本真性時間的攜手互助(即成為“時間的同志”)為特征,回歸時間流本身,通過基于時間的當代數碼藝術及其在博物館中作為“冷沉思”藝術的特有展示方式,揭示當下無功利時間的運行機制,在這個意義上,真正具有“當代性”的不僅是“基于時間的藝術”,更是“基于藝術的時間”,“當代性”即是化身為藝術的時間本身;而奧斯本的“當代性”則直面現存的多種時間觀,試圖將現實世界基于不同歷史文化和地緣政治的多元時間軸并置,統合為一個反抗世俗政治和現代進步時間觀的“虛擬統一體”。
回到當代藝術場域,就上述三種“當代性”對當代藝術實踐的具體指涉和分期而言,阿甘本的“當代性”雖被當代藝術界廣為引用,但因并未明確其針對當代藝術的內涵,被質疑為既未對當代性和現代性加以區分,也未能有效作用于當代藝術的研究和實踐。與阿甘本相比,格羅伊斯的“當代性”理論對當代藝術更具針對性和現實相關性。格羅伊斯從當代藝術媒介這一視角明確指出其“當代性”屬于“靈韻”復魅的數碼復制時代(而“現代性”屬于機械復制“靈韻”消逝的時代),其真正具有當代性的“當代藝術”(“冷沉思”藝術),是在特定展示空間展出的、直面公眾(而非藝術市場)、需要觀眾在場體驗參與的視頻和數字媒體藝術。哲學家奧斯本則從時間政治角度明確提出“當代性”與“現代性”分別在時間觀的“虛擬性”和“總體性”上的本質差異,因此,奧斯本意義上的“當代藝術”指超越藝術本體[即奧斯本為“觀念藝術”(或概念藝術)限定的特性],而訴諸社會現實語境的“后觀念”藝術,相比之下,奧斯本的“當代性”則更為晚近,屬于冷戰結束以后的全球化時代。
可以看到,本文討論的上述“當代性”理論,均與當代藝術息息相關: 或如格羅伊斯式的“強聯系”(指理論生發自當代藝術現場,并始終關注和參與著當代藝術實踐),其中,作為“時間的同志”的“當代性”,以其日益激進的政治參與訴求試圖全面推翻范式化的當代藝術體制;而與這樣的“強聯系”相比,阿甘本式“當代性”與當代藝術的關系可稱為“弱聯系”(指理論雖并非生發自當代藝術現場,但在當代藝術體制內迅速流行),其中,作為“時代錯位”的“當代性”,成為持續流轉于范式化當代藝術體制內的時髦引文而缺乏阿甘本暢想中的反抗效力;或介于二者之間,如奧斯本式基于現行西方當代藝術史范式而構建的理論推演,其中,作為“當下(多種)時間的斷裂統一體”的“虛擬的當代性”,難免再次成為基于西方視角、忽視全球在地性藝術實踐、僅自洽于理論建模、在現實世界中往往缺乏真實效力的新的全球想象。
如果說丹托意義上的“當代藝術”和“當代性”同步發生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且在某種程度上陷入了反映論的同義反復,而阿甘本甚至并未將具體的“當代藝術”現象和“當代性”聯系起來,那么,相比之下,格羅伊斯則對二者進行了區分。格羅伊斯意義上的“當代藝術”和“當代性”均指向21世紀的新時代,但并不等價: 其“當代藝術”概念小于“當代性”概念,真正的“當代藝術”以“當代性”的實現為限定,即格羅伊斯所稱“只有表明自身的當代性”,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當代藝術”,而這一真正的“當代藝術”,又往往是反抗現行西方主流當代藝術范式的“反當代”(或“后當代”)藝術。與之相比,奧斯本意義上的“當代藝術”和“當代性”在時間上則更加明顯地區別開來,奧斯本將“當代藝術”界定于發端自20世紀60年代,而“當代性”概念則以20世紀90年代以后全球化當代藝術的興起為肇始,并依托于這一西方主流當代藝術范式完成了其全球當代藝術理論構想,亦即奧斯本所謂“虛擬的當代性”。
至此,我們檢視了歐美當代藝術領域具有代表性的三種探討“時間轉向”的三重“當代性”理論及其各自的問題。可以看到,歐美語境中對“當代性”的探討,不可避免地建基于其拉丁詞源“時間”,并以對這一“時間”的返觀、繞道或逃逸為基礎,指向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當下和未來,“將未來從它的現代角色中移除[……]為未來的重塑(re-imaging)留出空間”(Ross 6)。而無論是重審現代、抵抗進步,還是繞道過去、重塑未來,生發自拉丁詞根基礎上的“當代”和“當代性”,一脈相承的歷史文化既是其批判和反思的對象,也為打開未知可能性持續提供資源: 它們或復活一個與使徒同在的“彌賽亞時間”(阿甘本),或復活一個個有著當下在場和歷史語境的“靈韻”(格羅伊斯),或以復活多元文化和多重時間觀為名而重塑一個全球性的“虛擬統一體”(奧斯本),可以說,上述三種“當代性”理論均以反抗現代線性時間敘事為出發點,在不同程度上進行著基于西方人文藝術和理論資源的歷史性復魅。
最后,雖然三者分別試圖以引入超越西方正統基督教的時空觀(阿甘本)、引入代表最新人類文明成果的數碼科技(格羅伊斯)、引入全球在地實踐多元主體的方式(奧斯本),且均以全球化和普適性為導向,向著更多維度更廣闊時空的敞開,卻均不可避免地局限于各自的文化歷史和現實資源,或是陷入對傳統深厚的一神論宗教內部(猶太教、天主教、新教)分化的歷史現實復雜纏繞的情結(阿甘本),或是蘇聯“飛向太空”的爭霸雄心和對新科技迷戀的持續記憶(格羅伊斯),或是大英帝國曾經日不落的全球虛擬想象的當代復歸(奧斯本)。因而,三種“當代性”理論帶給我們的啟示還在于,既然身份和視角之于理論構建只能回避而不可避免,那么,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向無窮可能性敞開(而非封閉某種民族性)的愿景,依托于何種在地性實踐,以何種更具真實性的本土視角返觀或推進上述西方當代藝術場域中展開的諸種“時間轉向”,應當是身處本土文化藝術資源和中文語境的中國學者,可為當前國際學界持續探索中的“當代性”理論開啟更多可能性的有效路徑。
注釋[Notes]
① 早期關于“當代藝術”和“當代性”的理論著述以丹托最具代表性。20世紀90年代,丹托使用“當代性”一詞意指與“當代藝術”同步的、針對當下的歷史敏感性(Danto 5)。雖然丹托明確表示“當代性”與“現代性”有著本質區別,但并未進一步針對“當代性”進行理論闡述,造成丹托意義上的“當代性”難免與其“當代藝術”陷入彼此互證的“同義反復”(王志亮129)。
② 此處及下文譯文結合英譯參閱了王立秋《何為同時代?》和劉耀輝《何謂同時代人?》兩個版本。阿甘本“何為同時代?”,王立秋譯,《上海文化》4(2010): 4—10。阿甘本“何謂同時代人?”,劉耀輝譯(《裸體》18—35),(《論友愛》61—79)。

In
the
Flow
144)。⑤ 以丹托和謝弗(Jean-Marie Schaeffer)為例,奧斯本認為,前者“后歷史”的藝術是去歷史化、以哲學的方式抽空了藝術,造成一個只有“藝術界”的當代藝術,最終成了對當代藝術“當代性”本身的自反。而后者試圖以“美學”的方式拯救當代藝術,以全面收回形而上學傳統為代價,將藝術的純思辨理論作為當代藝術危機之所在,并將之追溯至浪漫主義時代藝術“神圣化”(sacralization)的錯誤,進而推導出繞開18世紀以來的西方哲學、強調感覺經驗以重返最初作為“感性學”的“美學”路徑。奧斯本還辯駁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同樣流行的現象學及其法國版本的回潮(Osborne 12—15)。
⑥ 這三個階段的分期圍繞著美國藝術國際霸權的興衰展開,分別對應戰后美國藝術在北美和西歐的興起、60年代以來全球更大范圍內(除北美、西歐之外,還包括南美、日本、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對藝術自律和藝術體制的反抗、1989年以后美國藝術霸權在全球范圍的全面勝利及陷入困境。具體地說,第一階段對應冷戰格局形成的戰后及50年代以來,主要指繼承戰前歐洲歷史前衛的戰后美國新藝術國際霸權的興起,以抽象表現主義、波普藝術、極簡主義、觀念藝術等主要在美國興起,進而波及歐洲,產生國際性影響的當代藝術形態為代表,這一“新前衛”的“新”是相對于歐洲歷史前衛的“老”而言的,以美國藝術體制持續收編歐洲歷史前衛,并沿著歷史前衛的線性邏輯進行持續的自律式演進為特征,奧斯本認為這一美國霸權意義上的“新前衛”至今仍是界定當代藝術最為泛化的一種指稱。第二階段以反藝術體制、反自律藝術的全球化開端為特征,主要指發生在60年代以來,以歐美為主導,試圖跳出媒介自律的線性演進邏輯,參與社會、政治、文化激進運動的“后觀念”藝術,它發端自北美,席卷西歐、南美、東南亞、日本(奧斯本認為,在蘇東地區和80年代后期以后的中國,雖然也出現了類似的藝術形態,卻并未作出結構性的貢獻)。第三階段始自1989年冷戰結束后的全球一體化進程,以上述歷史前衛、新前衛、后觀念藝術紛紛為市場經濟和新自由主義的全面勝利所收編以至于前衛的終結為特征,自此,當代藝術進入藝術與文化工業相結合、國際性當代藝術展覽既全面繁榮又面臨全面體制化困境的階段(Osborne 24—27)。
⑦ 奧斯本認為,“現代性是一種關于時間的文化[……]時間,作為19、20世紀歐洲哲學的難題,以其極不同于以前呈現為哲學問題的穩定特征的范例的方式,纏繞在歷史問題與死亡問題這種新的雙重形式中”(《時間的政治》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gamben, Giorgio. “What is the contemporary?”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 Trans. David Kishik.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阿甘本: 《裸體》,黃曉武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 - -.Nudities
. Trans. Huang Xiaow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 《論友愛》,劉耀輝、尉光吉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
[- - -.Che
cos
’èun
dispotitivo
,L
’amico
, andLa
Chiesa
e
il
Regno
. Trans. Liu Yaohui and Yu Guangj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 《剩余的時間》,錢立卿譯。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
[- - -.The
Time
That
Remains
. Trans. Qian Liqing.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6.]Balzer, David.Curationism
:How
Curating
Took
Over
the
Art
World
and
Everything
Else
. Toronto: Coach House Books, 2014.本雅明: 《啟迪: 本雅明文選》,張旭東、王斑譯。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Benjamin, Walter.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 Trans. Zhang Xudong and Wang B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Danto, Arthur.After
the
End
of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Erber, Pedro. “Contemporaneity and Its Discontents.”Diacritics
41.1 (2013): 28-48.Foster, Hal, et al. “Questionnaire on ‘The Contemporary’.”October
130 (2009): 3-124.Gao, Minglu. “Particular Time, Specific Space, My Truth: Total Modernity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Antinomies
of
Art
and
Culture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Contemporaneity
. Eds. Smith Terry, et al.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3-164.高名潞: 《西方藝術史觀念: 再現與藝術史轉向》。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 - -.Theory
of
Western
Art
History
:Representationalism
and
the
Turn
of
Art
History
.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Gillick, Liam.Industry
and
Intelligence
Contemporary
Art
Since
1820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Griffin, Tim. “Out of Time.”Artforum
50.1 (2011): 288-289.Groys, Boris.In
the
Flow
.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6.- - -. “Politics of Installation.”e
-flux
2 (2009): 1-8.- - -. “Comrades of Time.”e
-flux
11 (2009): 1-11.- - -. “A Genealogy of Participatory Art.”The
Art
of
Participation
:1950
to
Now
. Ed. Rudolf Frieling. San Francisco Museum of Modern Art; Thames & Hudson, 2009. 18-31.e-flux編: 《什么是當代藝術?》,陳佩華等譯。北京: 金城出版社,2012年。
[- - -, ed.What
is
Contemporary
Art
? Trans. Chen Peihua, et al. Beijing: Gold Wall Press, 2012.]McKee, Yates. “Debt: Occupy, Post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Aesthetics of Debt Resistance.”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2.4 (2013): 784-803.Osborne, Peter.Anywhere
or
Not
at
All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Art
.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3.彼得·奧斯本: 《時間的政治: 現代性與先鋒》,王志宏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7年。
[- - -.The
Politics
of
Time
:Modernity
and
Avant
-Garde
. Trans. Wang Zhih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Ross, Christine.The
Past
is
the
Present
;It
’s
the
Future
Too
:The
Temporal
Turn
in
Contemporary
Art
.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2012.盛葳:“當代性: 重建中國抽象藝術的歷史和理論”,《藝術工作》4(2018): 34—39。
[Sheng, Wei. “Contemporaneity: Rebuilding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hinese Abstract Art.”Art
Work
4 (2018): 34-39.]時勝勛:“中國當代藝術‘當代性’的話語構成與價值沉淀”,《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5(2018): 11—13。
[Shi, Shengxun. “The Discourse Structure and Value Deposit of ‘Contemporane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Art
) 5 (2018): 11-13.]Smith, Terry.Art
to
Come
:Histories
of
Contemporary
Art
.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王林: 《從中國經驗開始》。長沙: 湖南美術出版社,2005年。
[Wang, Lin.Starting
from
Chinese
Experiences
.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5.]王志亮:“當代藝術的當代性與前衛意識”,《文藝研究》10(2014): 127—136。
[Wang, Zhiliang. “Contemporaneity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the Spirit of Avant-garde.”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10 (2014): 127-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