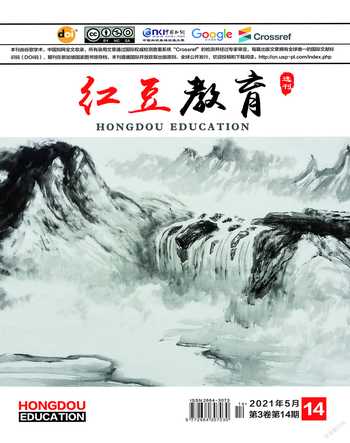國內外監管理論的研究進展
【摘要】文章改變了傳統的研究路徑,按照大學科領域視角對監管理論的研究成果進行整理和歸納,將研究視角分為經濟學領域視角與政治與行政學領域視角。經濟學領域視角下的監管理論,劃分為公共利益監管理論、利益集團監管理論、激勵性監管理論。政治與行政學領域視角下的監管理論,劃分為監管政治理論、制度主義監管理論、回應性監管理論。最后也對當前國內監管理論研究的重點方向做出了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監管理論;經濟學領域視角;政治與行政學領域視角;研究進展
一、監管理論的歷史背景
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西方學術界對當代監管領域問題的研究迅速興起,原因有二:首先,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西方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相繼掀起了放松監管的改革風氣。其次,自20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由于政府對社會領域的監管漠不關心,以及缺乏監督能力,一些西方國家在社會運動的影響下加強了對社會領域的監管。20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學術界對監管理論的研究從經濟學單學科角度逐漸擴展至法學、行政學、政治學等多學科角度。其中可以將監管理論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研究視角:一種可以分為經濟學研究視角,主要有公共利益監管理論、利益集團監管理論、激勵性監管理論這三種理論;另一種可以劃分為政治與行政學監管研究視角,主要有監管政治理論、制度主義監管理論、回應性監管理論這三種監管理論。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學界出現了“后設監管”概念,相對于傳統監管理論,后設監管更強調多元監管主體的共同參與。
二、國外監管理論的演進
(一)經濟學視角下的監管理論
1.公共利益監管理論
公共利益監管理論是監管理論中最早的經典理論。它是在資本主義市場失靈、凱恩斯主義和福利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種理論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獲得了許多學者的肯定,但是在該理論的起始階段,大家并沒有對其名稱進行統一的命名。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芝加哥學派的Domas[1]才將公共利益監管理論作為當時背景下該理論的統一名稱,以便在構建新理論時找到一個基準。具體而言,該理論認為,政府監管的首要出發點是糾正和規避市場中失靈現象,避免市場機制出現偏離公共利益的行為和可能性。也就是說,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應該站出來解決和規避市場失靈狀況中出現的資源分配不公及效率低下的情況。該理論忽視了利益集團和政治家對決策的影響,忽視了“多元化社會中的利益多樣性”[2]。這些缺陷進一步催生了以經濟學家斯蒂格勒為代表的“利益集團監管理論”。
2.利益集團監管理論
20世紀七十年代形成的利益集團監管理論與之前的公共利益理論有很大的差別。它強調政府所作出管制行為或者監督管理行為是為了迎合行業組織或者產業組織對市場主體進行監管的需求而衍生出來的。政府監管的本質是,一些行業利益集團通過相關的游說將監管機構和立法者控制或者影響起來。因此,政府監管立法總是有利于那些影響力更大、運作良好的利益集團,因為他們能夠更有效地提供政治支持。利益集團監管理論較好地解釋了不同社會經濟制度下的監管失靈現象,但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在面對利益集團時,政府作為一種行為主體存在一定的自主權和主動性,而該理論全完全忽略了;第二,政府并不是追求的單一層面利益,而是多層次的,將政府追求的利益等同于經濟利益并不具有說服力,存在以偏概全之嫌;第三,理論的解釋邏輯與實際發展存在明顯差異。20世紀七十年代前后,一些西方國家興起了放松監管化改革風潮,表明監管主體和監管對象都希望降低監管力度,這與理論上利益集團積極希望通過監管來滿足自身利益的觀點存在明顯的邏輯矛盾和沖突。
3.激勵性監管理論
西方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開展了放松監管和再監管運動,極大促進了人們對于如何提高政府監管效率領域的研究,為了更好的衡量監管政策優劣和提高監管結果的績效,學者們指出要用新的理論來激勵監管主體或相關監管機構從而提高整個監管過程的效率,降低相關部門的監管成本,進而增加監管收益與監管成本之間的差距,這些研究成果在20世紀70年代逐漸演化為一種具有代表性的監管理論即激勵性監管理論。這一理論首先吸取了博弈論的思想,認為監管主體和被監管對象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現象。因此,當監管過程中的其中一方利用這種信息不對稱以獲取私利時,監管的結果就可能會給社會帶來嚴重的效益成本。
通過分析以上理論,可以看出,公共利益監管理論指出政府的監管目標是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和社會公平正義等,分析了政府監管的動機;基于政府監管失靈的理論分析下的利益集團監管理論,修正了以政府的表現過于樂觀的公共利益監管理論;而激勵性監管理論在西方各國監管改革背景下應用而生。三種理論在各自的時代背景之下,有一定可取之處,但同時它們也有共同的不足之處:首先就是將監管主體狹義的限定為政府公共機構,被監管對象被限定為企業或者私人機構,忽視了監管主體的多元性,對非政府組織的監管研究沒有過多關注;其次是經濟學監管研究視角對于監管政策執行中會產生影響作用的制度、組織、文化等方面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些局限和不足為運用政治與行者學監管視角的知識來研究監管問題提供了契機。
(二)政治與行政學視角下的監管理論
1.監管政治理論
監管政治理論也有學者將其稱為政治俘虜理論,監管政治理論認為監管機構和官員具有主動性和獨立性,將監管作為一種工具,從而為自身謀求福利,而監管對象則是監管主體獲取利益的主要來源。監管政治理論與之前的三種監管理論相比,它強調監管互動主體的多元化,認為監管是公共利益、利益集團、政府本身利益之間多方博弈之間的一種平衡性結果。雖然監管政治理論有效地補充了經濟學視角下監管理論所沒有考慮到的監管互動主體多元化的因素,但是監管政治理論似乎并沒有清晰地闡述出,如何明確地界定和分析監管政治過程中公共利益、利益集團、政府本身利益之間多方博弈的平衡性結果。
2.制度主義監管理論
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制度主義逐漸興起。在監管的分析層面上制度主義主要從監管的決策過程、監管的變化形式以及監管的組織模式等角度來探討。它強調政府的規制不僅是為了服務于公共利益,同樣也不僅僅是政府與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的產物,它是特定制度下的特定產物。美國學者Eisner[3]從制度主義的角度分析了監管政策與監管制度之間的互動關系,認為制度對政策確立起著重要作用,而確立的政策也會反作用于制度。美國學者Larry Reynolds[4]認為制度監管主要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社會既定制度方面的監管,另一種是社會和利益相關體有意識地主動創建新的監管規則,以使監管對象遵循創建的規則。該理論在當時來說具有一定是啟發作用,將人們的研究視角和思維包拓寬到對各種行為主體背后的結構性因素層面,如外部宏觀制度環境,這豐富和拓展了監管理論的研究范疇。然而,該理論并沒有對單個組織或微觀制度機制納入分析范圍之內,使得它在解釋監管創新方面缺乏令人信服的論證。
3.回應性監管理論
為了解決強化政府監管與放松監管之間的爭論,Ayres和Braithwaite(1992)[5]提出了回應性監管理論,兩人分別從經濟博弈論角度和社會學的視角分析出大致相認同的推斷,認為僅僅使用政府監管或者單一使用市場調節并不能達到最佳的社會運行效果,而通過兩者監管手段的混合使用才能達到預期的最佳效果。該理論認為,監管者必須根據監管者激勵的具體情況選擇策略和手段。具體而言,這種混合監管模式的核心是“金字塔”模式,強調應從金字塔底部的非懲罰性措施開始,如企業或行業自律。在前一種策略失效后,再逐步提高監管力度。回應式監管理論的核心是基于監管主體、策略、手段的多樣化和統一性,旨在構建政府與非政府主體之間的合作監管模式。
三、國內監管理論的研究重點
學者劉鵬[6-7]、楊炳霖[8]、徐鳴[9]三位學者詳細梳理了西方監管理論體系,對國內學習監管理論起到了一定的引領作用。張秉福[10]、楊宏山[11]和曹永棟等[12]對發達國家監管改革以及監管理論進行分析,對國內監管改革具有一定借鑒意義。雖然目前國內對于政府監管的研究體量頗豐,但目前研究視角或領域還主要集中于環境監管[13-14]、金融監管[15-16]、食品安全監管[17-18]以及其他干預行為等領域的探討,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案例研究、定性規范研究和大樣本實證研究,以總結國外先進監管經驗、理念以解決國內現實問題為主。現階段研究拓展了我們的思維,啟發著我們對其他問題的探討:國家在監管過程中扮演什么角色?為什么同一個政府在不同領域的監管政策存在巨大差異?這些問題對研究監管的本質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Hantke-Domas M . 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 of Regulation: Non-Existence or Misinterpret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2003,15(2):165-194.
[2]Stephen J. Ceccoli. Pill Politics: Drugs and tht FDA[M].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4:340.
[3]Harris R A , Eisner M A . Regulatory Politics in Transition.[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94,88(2):468.
[4]Larry Reynolds.Foundations of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Regul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1981,15(3):641-656.
[5]Ayers.I.and.J.Braithwatie.Responsive Regulation:Transcending the Deregulation Debat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4-39.
[6]劉鵬,鐘光耀.比較公共行政視野下的市場監管模式比較及啟示:基于美德日三國的觀察[J].中國行政管理,2019(05):29-38;.
[7]劉鵬.西方監管理論:文獻綜述和理論清理[J].中國行政管理,2009(09):11-15.
[8]楊炳霖.回應性監管理論述評:精髓與問題[J].中國行政管理,2017(04):131-136.
[9]徐鳴.跨學科視角下西方監管理論的演變研究[J].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2019(05):78-86+99.
[10]張秉福.發達國家政府規制創新特點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經濟體制改革,2012(3):149-153.
[11]楊宏山.政府規制的理論發展述評[J].學術界,2009(4):248-253.
[12]曹永棟,陸躍祥.西方激勵性規制理論研究綜述[J].中國流通經濟,2010(1):33-36.
[13]李思慧,徐保昌.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來自中國地級市層面的經驗證據[J].現代經濟探討,2020(11):31-40.
[14]許瑞恒,林欣月.多元補償主體、環境規制與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J].經濟問題,2020(11):58-67.
[15]吳曼華,田秀娟.中國地方金融監管的現實困境、深層原因與政策建議[J].現代經濟探討,2020(10):120-125.
[16]沈偉,張焱.普惠金融視閾下的金融科技監管悖論及其克服進路[J].比較法研究,2020(05):188-200.
[17]黃新華,趙荷花.食品安全監管政策變遷的非線性解釋——基于間斷均衡理論的檢驗與修正[J].行政論壇,2020,27(05):59-68.
[18]向智才,金晉,張朝陽.我國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制度的法律規制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19):147-152.
作者簡介:李建國,男,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行政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