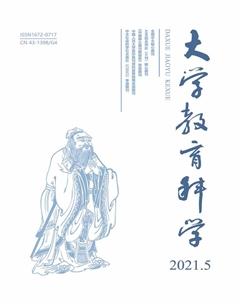人文性:中國高等教育學建構的價值向度
黃巨臣 李樂帆
摘要:“人文性問題”之所以成為高等教育學迫切需要重視和探討的主題,既是對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方向的反思所致,同時也是學科建設本身的內在邏輯使然。中國高等教育學的合法性危機由來已久,對此及其相關人文性問題的理解和探討,既是在歷史的、現實的高等教育實踐中進行,同時也關聯到新的時代要求和未來社會的發展可能。因此,需要在多重邏輯的視角中認識、明晰和闡述高等教育學的人文性問題,深化人文性與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之間的關系研究,并在不同邏輯層面予以呈現:在現實邏輯層面,其合法性危機產生的根源之一在于人文性的缺失;在理論邏輯層面,應從“實現人的發展、滿足人發展的需求、提供思想資源”的價值、功能、過程等多個維度來明晰人文性的內涵;在再造邏輯層面,提升“人文性”理念的價值引領、構建“人文性”導向的研究范式以及建構“人文主義”的話語體系是中國高等教育學實現以“人文性”為核心內涵的價值取向建構、夯實學科合法性基礎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高等教育學;人文性;建構;多重邏輯;價值向度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0717(2021)05-0024-08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潘懋元先生已提出要研究高等教育問題,構建高等教育學的體系和內容[1]。此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眾多專家學者從不同視角對學科的建設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既總結了高等教育學建立以來所取得的成就,也對學科的定位與研究領域關系[2]、高校教學與科研的關系[3]、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關系[4]、國際化和本土化的關系[5]等問題進行了反思,更為學科的未來描繪了不同藍圖。毋庸置疑,這些成果對于構建中國本土的高等教育學具有重要建設性意義,但上述研究關注的重點卻很少涉及“人文性”方面的內容。高等教育學的行動實踐和展開邏輯深植于本土的歷史文化傳統、政治經濟體制和治理模式之中,但當前的高等教育研究“往往只從經濟、政治的角度著眼……對于文化的作用卻忽視了”,尤其是在“文化傳統對于高等教育的影響是頑強的”認識層面[6]。更具體而言,在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語境下,這種“文化傳統”鮮明地指向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中的“人文性問題”。然而,當前這個問題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多數高等教育研究學人也未意識到學科發展的關鍵點之一是在于建構以人文性為基礎的價值向度。長久以來,人們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對“學科身份合法性危機問題”的外沿突圍,而對“人文性問題”的內在研究與反思嚴重不足,阻礙了學科的繁榮發展。事實上,“高等教育學科的合法性不在于有沒有獨特的研究對象、嚴謹的研究方法和邏輯一致的知識體系,在于是否形成了普遍認同的知識傳統和價值觀念”[7]。學科危機實質上觸及的是長久以來以人文價值精神為核心的“人文性”缺失。
因此,本文試圖通過一種兼具解釋性和批判性的研究視角,來理解、認識和建構“人文性”作為高等教育學的價值向度。解釋性的研究視角聚焦于高等教育的行動實踐,即高等教育研究者如何通過自身努力去揭示、描述和呈現“人文性”缺失的問題及其表現,進而明晰“人文性”的豐富內涵及其重要價值;批判性的研究視角,則致力于反思現今的理念、工具和方法,嘗試構建高等教育學的人文性價值向度,從而推動學科的建設。
一、現實邏輯:人文性缺失引發高等? ?教育學合法性危機
長期以來,在對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的合法性危機問題研究上,人們主要從學科制度、學科建制或學科建設等單一的某個角度切入,既無法全面地探討多重因素對學科發展的影響,也未注意將之與“人文性”價值及其精神的探尋和追問結合起來。因此,基于一個整合的視角,應遵循“學科建制—學科制度—學科建設”的現實展開邏輯,合乎規律地闡述和揭示其中存在的問題,以深化對該主題的認識和理解。
(一)學科建制中國家權力的管控與擴張
“我國的高等教育學科生存在一個以學科建制為基礎的時代”,但“也是因為學科建制,高等教育學的學科構建陷入了學科藩籬,始終糾結高等教育學科存在的‘獨立性”[8]。事實上,學科建制的背后暗含著國家行政權力的運作邏輯。與其他學科發展遵循的“先建構理論體系,后獲得學科建制”路徑不同,高等教育學是先獲得建制,其后才開始探尋和發展理論方法體系,這既是該學科發展的特殊性,也是行政權力主導學科發展的一種生動體現。中國教育管理體制強大的行政權力往往無意間導致“大學與學科”的關系被“行政與學科”的關系所覆蓋,并逐漸在日常實踐中模糊和削弱了學科的人文性及其精神。盡管以往關于高等教育學科發展的論述中發出過“學科取向”漸進自主發展的聲音,認為國家對學科的管控在教育領域“放管服”改革中有所弱化,高等教育學已經作為一個獨立的力量在運行,但這種論斷忽視了高等教育學的自主性仍嚴重依賴于行政基礎性制度權力所提供的各類資源和支持這個事實。在現實的學科治理架構下,行政力量的影響非但沒有減弱,反而在學科申報、學科評估等學科準入制度和等級制度方面不斷得到強化。進一步而言,“一種知識體系或類型要獲得學科的準入,必須滿足合教性、合人文性、合政治性、合認識性”等條件,而“在獲得學科身份后,學科又因學科的認知維度、組織維度和效用維度的差異而存在等級差異”[9]。從理想化的狀態看,高等教育學準入主要條件應該是合教性、合認識性和合人文性,但由于高等教育學科建制先天地與國家政治性密不可分,使得學科在后來的發展中難以擺脫對行政權力的過度依附,故在整個學科序列中政治性的等級靠前,人文性被置于最低序列乃至被遺忘,從而產生了合法性危機。需要指出的是,高等教育是“人的教育”,具有“對人的關注的特性”,“教育是人的一種實踐活動方式,是自我建構的實踐活動,具有主體性”[10]。這從本質上決定了學科的發展離不開對人發展價值的追求,即人文性是高等教育學的基本內涵。由于高等教育學科人文性精神及其內涵的缺失與學科建制中國家權力的管控與擴張互為因果、相互強化,國家日益傾向于把學科當做行政事務來處理,從而加深了學科發展的合法性危機。
(二)學科制度中研究范式的偏頗與迷失
學科制度中研究范式的形成、運用和發展過程表面上是社會中教育現象、問題和研究理念、工具相互促進的變化過程,是不以個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但實質上卻是學術共同體追求理想化學科“范式”價值的過程。換言之,所謂的研究范式不過是人們用以推動學科發展的形式。但隨著實證主義/科學主義進入到高等教育學領域后,以數據分析為主的定量研究逐漸“大行其道”。其實,這種研究范式導向有著很深的歷史背景與時代趨勢。近現代以來,尤其是21世紀以來的大部分人文社會科學都致力于將本門學科科學化,認為任何一門學科都可以用假設、數學和模型來復現和概括,由此確立了科學主義在學科發展中的正當地位[11]。具體到高等教育學,一些專家學者出現了對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盲從和迷信,都在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乃至貶低人文性質的思辨式研究范式。他們認為與定量研究方法相比較,思辨式研究不是科學(因為沒有大量的數據、模型和檢驗),故而轉向支持用數字來換算、衡量高等教育中的復雜現象和問題。且不少學者在開展研究時,進一步把廣義的實證方法窄化為狹隘的數據分析方法,試圖以數據化的模型來實現對高度復雜性的人及高等教育現象和問題的處理。但這顯然極為困難且也難以揭示出一般性的規律,最終催生出了研究工具越“科學”卻與人的發展越疏遠的悖論。在某種程度上,以龐大數據為支撐的量化研究正在以它程序化的方式削弱高等教育問題研究的價值內涵,把我們置于“唯方法至上”的境地。當一切現象和問題都得到了換算,深嵌于高等教育學科背后的“人”的主體價值就會被逐漸湮沒。正如一些學者所言:“教育研究離不開思想性與人文性,甚至它的實證與科學化也要以人文性為前提。人性的豐富與色彩斑斕,需要方法的多面體棱鏡來透射與折射。否則,過于倚重實證、量化、技術及其效率,教育研究過程就有可能淪陷于機械化的工具與程序,勢必偏離了以人的存在為目的的教育本身。”[12]此外,在高等教育實踐中人文性缺失的危害已經超出了學術層面研究范式的范圍。當前,盛行的各類學術或科研導向的評估指標、大學排行榜和量化評價管理制度等,奉科學理性和工具主義為圭臬,過度關注和追逐數據指標、排名提升,而忽視人才培養質量的切實提高。
(三)學科建設中話語體系的弱勢與失語
在社會事務日益復雜的今天,缺乏人文性內涵及其精神的高等教育學無論是作為一種思維方式,還是作為一種學科的話語體系,都難以有效解釋和解決諸多的現實問題,也無法提供足夠豐富的可以促進學科發展的新思想、新觀念、新命題和新術語。因此,對于高等教育學話語體系問題的探討,必須引入更為廣闊的人文性視野和思維。一個學科的話語體系與學科體系、學術體系有著天然的內在聯系,難以分割。當討論高等教育學的話語體系時,也一定會涉及到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雖然“學術體系是揭示本學科對象的本質和規律的成體系的理論和知識;話語體系是理論和知識的語詞表達,是學術體系的表現形式和語言載體”,二者存在一些差異,但“一個學科的學術體系只有通過自己的話語體系才能作為一種對象性的存在表達出來,為人們所知曉和理解”[13]。因此,這意味著在某程度上話語體系的構建過程,同樣也是一個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的構建過程。
然而,當前高等教育學的話語體系始終在西方化還是本土化、科研為重還是教學為先、工具主義取向還是人文價值取向等之間搖擺不定,這反映出了人文性話語在學科地位中的“本質性弱勢”和“邊緣性失語”[14]。在西方化與本土化關系問題上,高等教育學尚未完全突破套用西方理論思想的局面,對本土傳統文化的人文價值內涵挖掘不足[15],以至于出現了“無根和斷裂”[16];在科研為重還是教學為先問題上,高等教育學沒能解決“重科研而輕教學”的問題;在價值取向問題上,高等教育學的工具主義取向還是人文價值取向的張力始終存在,由于學科“在思想體系上,邊界還不夠清晰,框架還不夠明晰,內容還不夠豐富,核心觀點的論證還不夠充分”[17],致使人文性話語存在感極低。人文性話語“不僅僅關系到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概念、范疇,以及研究范式與理論框架,更是關乎中國高等教育的理論自信”[18]。當前,人文性話語的缺失無法為高等教育學提供更多的圍繞著“人的發展”所需公平、自由、責任等方面的價值涵養,也就無法構筑起從個人到學科的延展性聯動發展模式。上述觀點也再次表明,高等教育學的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標準、學術話語的構建需要注入人文性的價值精神內涵,而這項工作才剛剛開始。
二、理論邏輯:明晰人文性內涵是高等教育學建構的關鍵
從理論意義的層面看,“人文性”作為一種反映高等教育實踐活動的價值理念,它本應獲得與高等教育學發展相稱的、應有的理解,以及合乎學科變遷內涵的有效詮釋。而事實正好相反,盡管“人文性”這一概念早已出現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些著作論述之中,但在高等教育學領域中,特別是基于本學科視角情境下的解讀和理解尚處于模糊不清的狀態。因此,我們需要從“價值—功能—過程”多維的角度來對它進行解讀和表達。
(一)實現人的發展是人文性的價值維度
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全面發展的實現總是與高等教育問題的解決有關。我們之所以必須圍繞人的發展和高等教育問題來剖析人文性的價值內涵,一是因為不論是從個體成長的社會性視角還是從高等教育學發展的學科性視角,“人的發展”始終都是高等教育學所關注并需要回應的問題,而且其中暗含著學術共同體成長與學科自身建設相互交織影響的問題進路,由此決定了解讀和明晰“人文性”的價值內涵必須先要從本學科語境中出現的與人發展相關的高等教育問題著手。二是因為強調人的發展要在高等教育問題的解決中才能得以實現,乃是我們所處的現實所決定:高等教育學的發展存在偏離人發展的趨勢,人文性的價值理念遭到了漠視乃至否定。故此,我們不僅需要回答“人的發展”在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中如何體現的問題,還要最大限度解決人文性在學科發展中遭遇的價值式微和缺失難題。然而,今天所要闡釋的人文性的理論處境,已經不是是否需要在高等教育學中表達人文性的價值內涵,而是以何種視角和語言來更好地表達人文性的本質內涵。為此,厘定和認清高等教育學科發展中人文性所聚焦的“人的發展”的中心問題是必要且重要的。顯然,闡釋人文性價值內涵關鍵是要回答如何實現“人的發展”的問題,這也是高等教育學學科長期研究的重要領域。面對這一問題時,人們需要在出現于高等教育中的各類復雜交錯的關系之間維持相對平衡,諸如在學科專業結構與人才培養結構之間、在人才培養與人才評價之間、在大眾化教育與精英教育之間、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在均衡與非均衡之間等等。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走出人文性式微困局中常常遇到的相互對峙局面,才能對問題作出正確判斷和解答。“人的發展”問題是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問題中的重要內容,高等教育學也正是在解決“人的發展”問題中實現自身的進步,推動學科的內涵式發展,并以此來彰顯人文性的價值維度內涵。反過來,當所有關于“人的發展”問題均不需要借助高等教育學來探究、認識和解決的時候,高等教育學便失去了存在的重要價值基礎,當然人文性也就不復存在。由此可見,解決“人的發展”問題,保證將人才培養作為高等教育根本任務是高等教育學存在的根基,也是人文性內涵在價值層面的集中反映。
(二)滿足人發展的需求是人文性的功能維度
人文性作為一種代表著未來高等教育學發展演進的可能方向,就是基于“人的主體性”背景下的情境,以人的“主體性”和“實踐性”為對象,以發展意識和主體思維為工具,立足人的現實需求,致力于了解人的發展需求具體包括哪些內容,即高等教育學中人文性功能維度的基本指向是要清晰地確定“人發展的需要是什么”。通常而言,基于人本身及其實踐活動的復雜性考量,人的需要也呈現出多樣化、差異化的特征,但不論類別如何區分,要“滿足人發展的需求”就必須明確產生需求的對象和具體的需求內容:(1)明確產生需求的對象。有學者指出:“決定研究是否有價值的是論題,是特定的研究對象”[19]。研究對象及其內容主要是通過人的社會活動得以體現,在高等教育研究領域中,研究者日益關注教師、學生、管理者等主體的個體行為、價值選擇等方面。這也賦予了高等教育學以更濃厚的人文色彩。因此,研究者在探討“產生需求的對象”時,主要還是圍繞著與高等教育學相關的教師、學生、校領導、教育行政部門負責人以及社會中重要利益相關者來展開。基于“一個從更為廣泛的視角審視人類社會和本質的哲學”的學科視角[20],人們在人文性功能維度上的探尋能夠幫助高等教育研究者建立對研究對象需求本質的深層次把握,有助于形成更具人文主義的思維方式。(2)具體的需求內容。從人的社會意義上看,人首先是人,其次才充當其他角色。人在社會中的生存和發展,涉及到生存權、發展權、工作權、教育權等需求,而這些權利的實際獲得和充分實現又往往與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職能的實現密切相關。當然,這些需求只是人的基本需求,總是受到更高需求的統攝,且隨著社會的進步,原本只是用于維持生存的基本需求就變成用于促進個人更好發展的“過有尊嚴生活”的高層次需求,這是根植于人們生活和意識中的另一種本質的需求。所以,對當代社會的普遍成員而言,人發展的價值實現依然是不可或缺的。與其他學科一樣,高等教育學不可能窮盡其研究對象的需求,只能根據現有認識去做出甄別、判斷和“詮釋理解”[21]。總而言之,滿足人發展的需求不僅是人文性功能結果的呈現,也是高等教育學發展的題中之義。
(三)提供思想資源是人文性的過程維度
如果說在對人性的全面理解基礎上明確的“實現人的發展”是高等教育學之人文性的價值維度內涵,在此基礎上“滿足人發展的需求”能夠構成學科人文性的功能維度內容,那么“提供思想資源”則成為高等教育學人文性過程維度的要義。這是因為,只有在“提供思想資源”的人文性框架之內,人發展的需求才會得到回應和落實,而與人作為發展主體相適應,高等教育學以及高等教育學人則會成為致力于推動上述目標實現的倡導主體和實施主體。在這種類似于“權利—義務”的關系中,“實現人的發展”和“滿足人發展的需求”等目標成為關系框架的軸心,高等教育學及其建設者理應為目標的實現而服務,而服務的前提和保障是需要擁有豐富的“思想資源”。在過程層面,“提供思想資源”意味著人文性的內容及其內涵要有相應的來源和依據,具體包括:(1)傳統的歷史文化。就思考范式而言,基于歷史性的文化和文化性的實踐而凸顯出的人文性維度,可以塑造一個學科真正的認知意義和理解價值。這種文化的“人文性”,是關于人發展問題的哲學之思,也是高等教育學學科特色的哲學理念。因此,我們要吸納那些關涉人文價值以及精神的文化、傳統、慣習、規章、制度等作為高等教育學人文性的“思想資源”。在此基礎上,還需要汲取歷史所積累的知識智慧精華、獨特思想并與當代文化價值追求相結合,將之融合進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中,闡明新時代中國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的基本規律和正確道路,建設與學科發展的現代性、階段性、特殊性相統一的人文內涵。(2)現實的實踐活動。一方面,高等教育學中人文性“思想資源”來源于外部的力量。首先,在新時期,黨和國家關于學科發展建設的重大論斷和戰略方針為高等教育學的發展路徑提供了遵循,“以人為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高等教育學的人文性內涵深化提供了指導。其次,政府的體制改革與職能創新致使與“人才培養”相關的高等教育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諸如2019年《教育部關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意見》等政策文件的精神,既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強大動力,也為高等教育學提供了人文性的思想資源。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學對自身各類問題的發現、認識與反思的經驗,包括對民辦教育營利與非營利的判斷、學科評估中排名與“去排名”的認識、高等學校分類中類別與等級的澄清、人才培養中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關系的反思等,均源于眾多的高等教育實踐,并經由學術共同體的發現、探究、總結和提煉而形成,都在無形之中為高等教育學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想。
三、再造邏輯:以人文性為價值取向建構中國高等教育學
“人文性”是高等教育學建構的價值向度,是高等教育學探究關于人發展問題的起點和內核所在。當代中國高等教育學人文價值理念的表達和基于合法化、正當性價值基礎的建構,需要同時做出以下三個方面的努力:一是提升“人文性”理念的價值引領,彰顯人文精神及其內涵;二是構建“人文性”導向的研究范式,注入必要的“人文關懷”;三是建構“人文主義”的話語體系,增強思考的深度。
(一)提升“人文性”理念的價值引領
以往人們認為價值理念的作用只是在于幫助人們去看待和解釋世界的現象與問題,卻忽略了它的改造和影響能力。事實上,“運用人文性的價值理念去認識社會,就是從人的內在本性要求出發,運用人類所特有的思維力去認識和評價各種社會現象、歷史事件,去建構未來的理想社會”[22]。這意味著為人們更合理地改造所生活的社會提供“人文性”的價值目標和理想信念,而提供恰當的認知模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正是高等教育學應有的社會責任。在我國的具體現實語境下,高等教育學科的發展始終與家國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23],高等教育的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人才培養都要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作為一種規范性探討的人文性價值理念也必須要考慮到高等教育學科發展在中國體制和價值中的階段性和特殊性[24],人文性的價值引領必須以中國的制度背景和語言表達為基準展開。“人文性”作為一個理解高等教育學科建構的分析性概念,具有哲學意義上的抽象性和本體性特點。再從人性論和認識論的角度來考察人文性,就會產生另一種解釋,即人文性是思維能力和價值尺度的統一,它是人所特有的一種主體能力和價值標準。同時,我們也可以將之視為學科價值建構所需要的一種理念。這意味著,不論是高等教育學在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還是學術共同體所體會到的感受,事實上都可以借助“人文性”的概念來加以闡釋和解讀。高等教育學的發展始終沒有脫離過“人才培養”,高等教育學建構的價值向度也不可能脫離社會普遍個體成員的生活。更進一步而言,高等教育學需要一種“人文性”的價值引領。當然,也有學者認為,這種“人文性”的價值引領需要以先確定高等教育學的人性假設為前提。“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往往以一定的人性假設為‘公設”,并以此構建它的理論系統和價值體系[25]。所以,在高等教育學科的價值建構過程中“不可能在‘人性論上處于一種‘無立場狀態,而是必然會選擇某種人性論做為‘公設或‘公理”[26]。但不論是社會人、經濟人、理性人還是知性人等人性假設,都應以“人文性”為支撐,將人發展的主體性視角納入其中。此外,它更需要將分散于社會系統、文化系統、學術系統內的人文傳統和思想,轉化為價值層面的有效解釋力,用“人文性”作為探討高等教育學學科發展的價值基礎。
(二)構建“人文性”導向的研究范式
高等教育學是一門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它所面對的不是一個同質化的世界,而是充滿了不確定性的領域。更具體而言,“因為涉及主體和價值問題,大多很難或不可能依據循證原則進行嚴格的實驗研究”[27]。在實證主義從自然科學向人文社會科學滲透的進程中,大量的實證研究方法涌入高等教育學的研究領地。實證研究雖然也確實能構造出過程分析和結果呈現所需的精確框架,但往往卻缺少鮮活的“血肉”。“在這框架內部,我們感受不到或想象不到人的生活”,且“這種格外的精確與真實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28],已經脫離了人的主體價值追求。尤其是在探討高等教育現象中有關群體、階層的問題時,決不能“唯方法主義”,因為“人們必須研究處理集合在一起的眾多個體靈魂,這些方法與理論概括必須在考慮到這種多樣性的基礎上進行特殊設計”[29]。這表明高等教育研究面對的是活的變化著的人、教育和社會,研究的對象不僅不是一成不變的既定主體,而且與其他主體的邊界還常常模糊不清,甚至是重疊的,研究者要清晰呈現出其原來面目本身就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任務。可見,研究對象的不可測量和不確定性是高等教育研究過程中真實存在的一面。因此,相比較而言,人文取向的研究更能以研究主體的個人知識、情感、體悟乃至經驗來深刻洞察現象背后的本質,而這也使得高等教育學在探索“人發展的問題”上充滿了可能性和創造性。同時,高等教育學的“人文性”導向研究既關注自身學術領域的發展和繁榮,也關注如何解決教育問題、真正為人的發展而服務,即為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以及高質量的培養人才作出貢獻。其根本任務是堅持人本導向、圍繞以人為中心的學科專業建設、人才培養方案改革、學術成果評價優化、學校教學管理改進等的研究,突出那些關于人的發展的研究重點。高等教育學研究唯有在與社會發展、個人命運的緊密連接中,其時代性和主體性才能得到切實彰顯。此外,為避免“人文性”導向研究陷入碎片化、個體化的境地,我們有必要在研究過程中進行整體的批判性反思、吸納其他學科的知識視野[30],這樣才有可能為高等教育學的研究范式改進提供思路和可推廣經驗。
(三)建構“人文主義”的話語體系
構建當代高等教育學價值向度的關鍵之一是要建構“人文主義”的話語體系,這就需要對人文問題和人文知識傾注足夠的關注。而關注的重點,應當是能否形成一套目標明確的“人文主義”話語體系。如前文所述,從歷史文化傳統中汲取“養分”與人文知識增量的漸進性累積是建構“人文主義”話語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高等教育學界應深植本國社會現實,回應社會發展和人全面發展的需求,總結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文化、科學的“傳統”。“在理想狀態中,學科的傳統來自高等教育與大學的文化傳統的沉淀”,之所以還要囊括“科學傳統”,乃是因為“早期一切科學的傳統就是人的傳統,是充滿著人文情懷的精神傳遞過程”[31]。所以,借鑒并吸收一切有益的“傳統”思想資源無疑是明智選擇。此舉既是當代中國高等教育學觀念演變的邏輯必然,也是學科存在哲學內在“品性”的回歸和確立。
還需明確指出兩點:(1)當代高等教育學建構的“人文主義”話語體系并不排斥主張價值理性的科學。作為“人學”的高等教育學兼具人文性和科學性,二者非但不是對立關系,而是相輔相成、交互融合。業界今天所倡導的是在一個新的基點上對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進行深刻而全面的反思,以期形成一種帶有共識性意味的智慧。對“人文主義”的尋繹,要通過更為復雜的教育歷史實踐和教育科學批判,在多元文化傳統和多種理性觀念之間展開對話。其最終的目標是要將人文性與科學性統合到人文主義之中,將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相互融合,重新審視和發現人的價值,樹立技術只是手段或工具,而人的發展才是目的的理念,讓人文性作為高等教育學的重要價值屬性為科學育人明確方向,使科學性為更好地開展育人活動提供工具和方法,并以此為基“促使產生更具綜合性、整體性的學科知識”和話語體系[32]。(2)建構高等教育學“人文主義”話語體系的目標之一固然是要擺脫“依附西方”的狀態,扭轉學科話語建設中人文性的“弱勢”“失語”局面,體現“中國表達、中國實踐、中國經驗、中國文化”特征,彰顯學科影響力和話語權[33]。但更重要的目標在于,促進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實質性的轉變和突破,并為業已形成以及正在形成的人文問題研究和人文思考模式提供一種可供參考的價值取向和范式,以增強對人、學科、社會發展的深度理解。
四、結語
事實上,高等教育學所建構的人文性價值向度與普通教育學所追求的“人文品質”既有共性一面又存在一定區別。從育人的角度看,高等教育學與普通教育學均屬于“人學范疇”,即通過一定的途徑和手段來培養人才,使人能夠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的學科。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二者所建構的人文性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人的主體性”“人的成長性”以及“人發展的可能性”等這些人本價值理念始終受到關注,其存在和最終目的均指向“育人”。但在知識層面,高等教育學的人文性向度更多是基于高深知識而建構。與普通教育的一般性知識相比,高等教育的高深知識“更加復雜,更加深奧,更加專業,其水平、結構、形態都與普通知識不同,其‘量的變化和質的轉化比起普通知識更加活躍、復雜”[34],這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高等教育的人文性“是知識中相對高級和比較深奧的部分”,其內涵及內容構成來源于“比較深奧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相關技能”[35]。這是二者所呈現出的顯著區別。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學人還需要反躬自問,我們應該以一種怎樣的眼光和態度去看待高等教育學科在發展中所建構的“人文性”并理解其背后所蘊含著的對人類文明發展的本質理論關懷,怎樣才能使之成為一套完整富有建設性和指導性的邏輯概念、模式乃至理論體系,而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理論和實踐中進行不懈的努力探索和建設。
參考文獻
[1] 潘懋元.高等教育學的若干問題[J].高等教育研究,1983(01):4-26.
[2] 張應強.超越“學科論”和“研究領域論”之爭——對我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方向的思考[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1(04):49.
[3] 張楚廷.再論教學與科研關系[J].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03(04):34-38.
[4] 陳向明.從北大元培計劃看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系[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6(03):71.
[5] 李均.開拓中國高等教育學科自主創新之路——論潘懋元高等教育理論的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J].山東高等教育,2015(10):73.
[6] 潘懋元,鄔大光.文化傳統與高等教育的理論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1989(01):3-8.
[7] 周光禮.中國高等教育研究:過去、現在與未來[J].中國高教研究,2016(10):9.
[8] 鄔大光.論我國高等教育學體系的特殊性[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05):20.
[9] 周國平.學科準入與分等視野下學科的合法性危機探討[J].教育發展研究,2012(02):68.
[10] 荀振芳.論教育是人的自我建構性的實踐活動[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2):136-138.
[11] Raadschelders J.C. The Future of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Embedding Research Object and Methodology in 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1(06):916-924.
[12] 閻光才.如何理解中國當下教育實證研究取向[J].大學教育科學,2020(05):4-11.
[13] 田心銘.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科學內涵與相互關系[N].光明日報,2020-05-15(11).
[14] 李文.話語權力視角下中國高等教育話語體系的建構[J].江蘇高教,2019(05):16-21.
[15] 楊嶺.論當代中國高等教育學學術話語體系的自主建構[J].遼寧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6):81-83.
[16] 鄔大光.中國高等教育的根本在文化[EB/OL].(2020-09
-01)[2021-5-09].https://www.eol cn/e_html/
2018/40/wudg/.
[17] 羅云,郭霄鵬.構建中國特色高等教育話語體系:價值、難題與對策[J].江蘇高教,2019(05):11.
[18] 謝維和,文雯.中國高等教育的獨立自主性——中國特色高等教育研究話語體系的意義分析[J].中國高教研究,2015(08):1.
[19] 王建華.高等教育學的建構[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70.
[20] Malinowski,B.Ethnology and the Study of the Society[J].Economica,1922(06):219.
[21] [德]馬克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M].韓水法,等譯.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5.
[22] 歐陽康.合理性與當代人文社會科學[J].中國社會科學,2001(04):17.
[23] 鄭慶全,楊慷慨.中國共產黨發展高等教育的百年歷程、成就與展望[J].大學教育科學,2021(02):34.
[24] 張興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特殊性”——訪廈門大學副校長鄔大光教授[N].中國教育報,2014-11-17(11).
[25] 周敦耀.論人性假設[J].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06):1.
[26] 王建華.知性人:高等教育學的一種人性假設[J].大學教育科學,2009(04):18.
[27] 王建華.高等教育學的知識重建[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05):40.
[28] [英]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梁永佳,等譯.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13.
[29] Malinowski,B.Baloma:The Spirits of the Dead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J].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16(46):274.
[30] 黃巨臣.我國高等教育研究范式轉型及其突破路徑[J].教育科學,2019(03):51-60.
[31] 李海龍.高等教育學的常識、傳統與想象[J].高等教育研究,2017(10):43.
[32] Johnson R.B, Onwuegbuzie A.J,Turner L.A.
Toward a Definition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J].
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2007(02):
112-133.
[33] 宣小紅,史保杰,薛莉.教育學研究的熱點與重點——? 對2016年度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轉載論文的分析與展望[J].教育研究,2017(02):26-39.
[34] 張德祥.高等教育基本關系與高等教育學體系建設[J]. 高等教育研究,2020(10):46-54.
[35] [美]伯頓·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M].王承緒,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13-17.
Humanity: Value Dimens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HUANG Ju-chen? ? LI Le-fan
Abstract: The humanity problem has become an urgent topic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needs more attachment and discussion on the requirement of current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on its inherent logic necessity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The understanding and discussion of this and its related humanistic issues are not only carried out in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practice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and the possibility of future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clarify and elaborate the humanistic problems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logic,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sm and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present it at different logical levels. In the view of practical logic, one of the root causes of legitimacy crisis lies in the lack of huma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the connotation of humanism should be clarified from the value, function and process of realizing human development, meeting the needs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ideological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producing logic, improving the value guidance of concept of humanity, construct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humanity, direction and building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humanism, are possible ways to achieve value dimension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with humanity as its core connotation, and eliminate legitimacy crisis of discipline identit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humanity; construction; multiple logic; value dimension
(責任編輯? 黃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