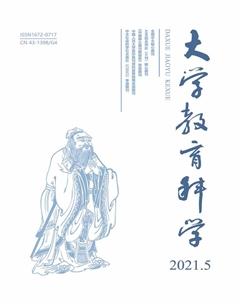建章立制,立德樹人:岳麓書院學規章程及其創造性轉化
鄧洪波
書院一般都會制定學規、章程,規范教學,導引師生。學規的內容,因時因地因院而各不相同,包羅甚廣,約略而言,則有三端。一是確立辦學、講會之宗旨,宣示書院教育的方針,為諸生樹立鵠的,為同仁確立目標,意期立志高遠,養成正確的人生理想。二是規定進德立品、修身養性的程序和方法,為學者提供更多的至善達德的幫助。三是指示讀書、治學的門徑和方法,是書院教育實踐經驗的理論結晶。章程不同于學規的遠大追求,強調細密的做法和可操作性,內容多是山長的擇聘、待遇、責任;生徒的甄別、錄取、分級、考課,以及考課的日期、內容、獎罰;教材的選擇,教學組織,課程設計,課時安排;講會的組織、程序、儀式、日期,以及會講的內容;經費的籌措、管理與開支;圖書的征集、整理、編目、借閱;員工的配備、責任、工食;書板的校刊、刷印等等,皆是具體而硬性的規定,意在從各個側面去維系書院的正常運作。把握書院的學規、章程,即可把握書院的精神,把握書院教育制度的本質。
清代以前,岳麓書院見于文字的規章很少。宋代,張栻的《岳麓書院記》主要強調其成就人才、傳道以濟斯民的教育方針。第一個正式學規是《朱子教條》,即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明代,除將《朱子教條》改名《晦庵先生教條》,尊為“文公學范”之外,尚有規范士人視聽言動的“程子四箴”及世宗的《敬一箴》。這些大多側重思想修養,很少具體條款規定,反映了書院注重“無形規范”的特點。到清代,特別是康乾之世,岳麓書院地位再次被抬到全國首列之后,其規章不斷增加,對修身養性、為德治學,以致日常生活行動之種種規定,日臻嚴密具體。據統計,清代岳麓有學規、學約、學箴、戒條、條約、規條、章程、佃約、示、諭、課程等二十余種,近二百條,數量之多,是岳麓書院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在全國也屬罕見[6](P397)。其建章立制的規范性管理于此可見一斑。
岳麓書院的學規與章程,大致可以分成進德、修業、考課幾大類型,而論其規章建設,有以下幾個特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進德成人必先于修業成才。岳麓書院歷來強調,修業必先進德,成才必先成人。王文清《岳麓書院學規》十八條[5](P1041-1042),前十條講忠、孝、莊、儉、和、悌、義等道德規范,意在進德成人。楊錫紱《岳麓書院學規》四條[5](P1039-1041),分立志、求仁、變化氣質、正文體,前三條皆是進德之規。曠敏本擬有《六有箴》: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從晝夜、瞬息、言行各方面規矩諸生[5](P1043-1044)。歐陽正煥則大書“整齊嚴肅”四字作為岳麓院訓,并作《書整齊嚴肅四字因示諸生》詩,以“涵養在主敬”“制外以養中,主靜以定性”“力行我為政”等訓示學子[5](P1044)。長沙府知府李拔也發表《岳麓書院辨志說》,并為院中存誠、主敬、居仁、由義、崇德、廣業六齋各作銘訓戒諸生[5](P1049-1050)。凡此種種,表明書院學以倫常為本、學以器識為本、學以修省為本,即“教學者以堅定德性”成為常態。正因為如此,才有岳麓書院在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頭建功立業,人才輩出,揮寫“惟楚有材,于斯為盛”的空前盛況。
第二,繼承發揚朱張理學傳統,高揚學術大旗。康熙五十六年(1717),山長李文炤參考《白鹿洞書院揭示》,制訂《岳麓書院學規》八條[7](P66),尊濂洛關閩之緒,而一以朱子為宗,進德“注重于立身、敦品、養性,治業則注重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力行”,主講悉以修己治人為訓,強調《四書》,由《四書集注》到《四書或問》,再到《朱子語類》,多所講究,其他則《太極》《通書》《西銘》《正蒙》皆理學名著,凡“學問思辨,必以力行為歸也”,具有濃厚的理學特色。乾隆十年(1745),楊錫紱首任湖南巡撫,“下車旬日,即詣書院展謁朱子、張南軒先生祠”,制訂《岳麓書院學規》四條,由立志、求仁到變化氣質,規范諸生,遵循的仍是正宗理學的路數,其精神實與乾隆皇帝所賜之“道南正脈”匾相契合。他認為“書院之設,所以講明正學,造就人材,處則望重鄉邦,出則澤施天下,非僅為工文藻、取科名、揚聲譽已也”,這與張栻提出的教育方針如出一轍,而其求仁之旨也與張栻所提倡的完全相同。歐陽厚均主院二十七年,刊立朱子“忠孝廉節”碑,用“有體有用之學”訓士,這些都反映出朱張傳統在岳麓書院的延續。
第三,注重經史,強調考時勢,通世務。經史乃為學根底,歷代都十分重視。李文炤稱“圣門立教,務在身通六籍”,而“學者欲通世務,必需看史”。王文清首任山長制定《岳麓書院學規》,規定“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目》數頁”,將經史定為每日必修課程,并且專門制定《讀經六法》《讀史六法》[5](P1042)用以具體指導經史學習。而其《岳麓書院學箴九首》[5](P1048-1049),更有“日月不滅,萬古六經。囊括萬有,韜孕經綸。史書廿二,綱目星陳。如何不學,長夜迷津”之說,將經史比作萬古日月、長夜明燈。他的《讀書法九則》[5](P1119),也有“讀書最要窮經、讀書要看史鑒”兩條。陳宏謀《申明書院條規以勵實學示》[5](P1044-1048)“限定功課”,要求“每日每月皆不離經史工夫”。而經史基礎之外,“禮樂兵農,經天緯地,錯節盤根,用無不利”,還要廣采博覽,以求多聞廣識,必如此,方能“考時勢”“通世務”“通曉時務物理”,真正做到“經世致用”。
第四,質證、辨難以求至是,追求學術真理。李文炤學規規定,每日講經書要“端坐辨難”“反覆推詳”,“共相質證,不可蓄疑于胸中”;每月作文,學生可以“攜原卷相商,以求至是”;平時讀書,“諸君倘有疑處,即與之以相商焉”、“有相質證者,不敢隱焉”,可謂將質疑辨難、訓練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貫穿到了教學的各個環節。陳宏謀條規規定“上堂講書,不拘四書、五經、諸史,諸生有獨得心解者,錄出送掌教就正;有疑者,不時登堂質問”。王文清學規直言“疑誤定要力爭”,而僅“正義、通義、余義、疑義、異議、辨義”十二字的《讀經六法》和“記事實、玩書法、原治亂、考時勢、論心術、取議論”十八字的《讀史六法》更是這種訓練的高度濃縮與總結。它所體現的敢于懷疑經典,不迷信權威,追求學術自由的精神,在當年極為先進,即使在今天,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也不落后。
第五,以考課促進教學。教學少不了考試、考核,但方式方法容有差異。李文炤規定每月三會,各作書二篇、經一篇,有余力者作性理論、小學論一篇,批改“止憑臆見丹黃,倘或未當,即攜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不給名次,而又師生相商以求至是,意在防止學生“月使之爭”,而傷及“教養之道”。與李文炤不同,陳宏謀則排名次并加獎懲,其條規規定,“諸生各立功課簿一本”,每日按清晨、午間、燈下三段,“據實登填”經史、古文、詩、臨帖等功課,“聽掌教不時抽閱叩問”,“有捏填者,自欺欺人,甘心暴棄,以犯規扶出”。每月課文兩次,“每課四書文一篇,或經文、或策、或論一篇,詩一首。策則古事、時務,論則論列史事古人,或《小學》《性理》《孝經》……間于四書文一首之外,出經解一首,或長章幾節,或經中疑義,每首約三百字以上”。每次考試,“不完卷者不閱,雷同者不錄,兩次不完卷者扶出”。考完之后,按名次“出榜給賞”,獎銀最高可達八錢,接近每月一兩的膏火數額。每次課卷發下,則“令諸生轉相閱看……名次列后者,閱前列之佳卷批點,即以廣自己之識解,不可生忌刻之心,而以為不欲看也。前列者,亦應閱落后之卷,以知此題文原易有此疵病”。這種方法,符合“孔子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無往非師之道。三人行且然,況同學至數十人,其師資不更廣乎?”這樣一來,“師資”就由少數幾位老師擴大到了數十位同學,此則正是以考課促進教學的又一意涵。
綜上所述,堅定德性,能夠保證岳麓書院不迷失于紛繁現世;高揚朱張學術大旗,可以保持其學術特色;養成質證以求至是的批判性思維的傳統,是其保持學術創造力的文化密碼;強調經史基礎而又通曉時務,經世致用,更是千年學府永葆青春活力的文化底蘊;以考課促進教學,使得教養相資、教學相長的理念可以更加靈動活化。而所有這些,若能夠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都是今日大學教育可以利用的文化資源。
首先,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先培德后育才、德業與學業并重是通用的原則,修身養性、擴充見識、養德成器則是堅定德性的不二法門。至于如何立德,就要有今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特色了。如此,則“傳道以濟斯民”的堅守,在新時代必能由古開新,結出碩果。這是古代書院進德之規的傳承與創新。
其次,學術傳統的傳承與創新。朱張學統一直是千年學府的學術傳統,也是歷代學規高揚的旗幟。傳承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其被寫入湖南大學校歌,“承朱張之緒,取歐美之長”,傳唱至今,可謂與時俱進的絕妙強音。傳統和現代融合,可以讓我們的學術精神既有悠久歷史的厚度,又有現代世界的鮮活。具備上述崇尚自由、不迷權威、實事求是、質證辨難、追求真理等學術精神的千年學府,其屹立今日世界大學之林而日新又新,自是題中之義。這是古代書院修業之規的傳承與創新。
其三,重經史,強基礎,而又考時勢、通世務,由通經致用接引,可以創造性轉化,完成今日大學服務社會、引領社會的時代使命。以袁名曜為例,他“與歐人過從”而通西學,居院講學,要求學生“穿穴經史”“先器識而后文藝”,故而學生魏源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能夠喊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時代強音[6](P493-496)。沿此路徑,依托扎實的學業基礎,深入社會,了解社會,考察時勢,必能創新學術,建功立業,造福人類,引領社會的進步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