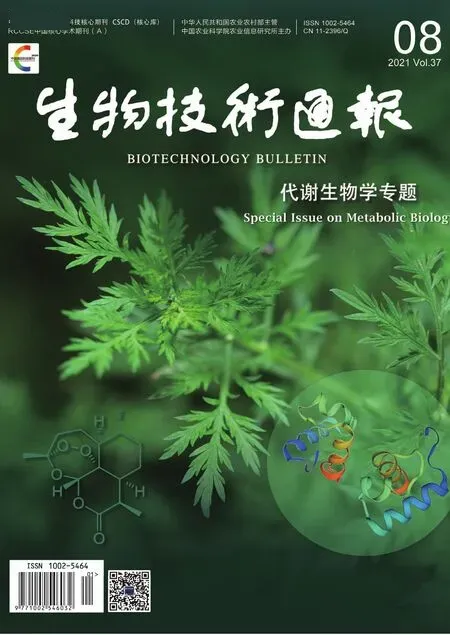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差異代謝物和細(xì)菌群落結(jié)構(gòu) 分析
劉傳和 賀涵 何秀古 劉開(kāi) 邵雪花 賴多 匡石滋 肖維強(qiáng)
(1. 廣東省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果樹(shù)研究所/ 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部南亞熱帶果樹(shù)生物學(xué)與遺傳資源利用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 廣東省熱帶亞熱帶果樹(shù)研究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 廣州 510640;2. 廣東省農(nóng)業(yè)科學(xué)院,廣州 510640)
連作障礙制約著果樹(shù)產(chǎn)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化感自毒作用是引起果樹(shù)連作障礙的主要原因之一[1]。有機(jī)酸、直鏈醇、酚酸、萜類(lèi)和生物堿等代謝物多數(shù)屬于自毒物質(zhì)[2],其中萜類(lèi)和酚酸類(lèi)物質(zhì)是導(dǎo)致土壤化感自毒作用的關(guān)鍵代謝物[3]。作物長(zhǎng)期連作后根際分泌的苯甲酸、羥基苯甲酸和肉桂酸等酚酸類(lèi)代謝物通過(guò)與土壤根際微生物互作而不斷積累,阻礙土壤有機(jī)質(zhì)的分解和礦化,妨礙了根系對(duì)土壤養(yǎng)分的吸收[4-7],導(dǎo)致自毒作用加劇。
土壤細(xì)菌群落作為土壤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重要組成部分[8],其群落結(jié)構(gòu)的變化與連作密切相關(guān)。在大豆、煙草、茶樹(shù)、香榧等作物連作后土壤研究表明,連作后以糖類(lèi)、氨基酸類(lèi)碳源利用為主的細(xì)菌數(shù)量顯著減少,根際土壤細(xì)菌碳源利用率下降[9]。連作導(dǎo)致土壤中細(xì)菌種類(lèi)減少、細(xì)菌多樣性降低,土壤細(xì)菌群落多樣性和豐富度指數(shù)下降,土壤微生物類(lèi)型逐漸由“細(xì)菌型”向“真菌型”轉(zhuǎn)變,土壤微生物出現(xiàn)失衡[8,10-14]。在門(mén)水平上分析表明連作后土壤的優(yōu)勢(shì)菌門(mén)厚壁菌門(mén)(Firmicutes),以及有益菌門(mén)變形菌門(mén)(Proteobacteria)、擬桿菌門(mén)(Bacteroidetes)和放線菌門(mén)(Actinobacteria)等所占比例逐漸下降[12,15]。土壤細(xì)菌根瘤菌目和酸微菌目的相對(duì)豐度,以及分枝桿菌屬(Mycobacterium)、藤黃單胞菌屬(Luteimonas)、芽單胞菌屬(Gemmatimonas)、浮霉菌屬(Planctomyces)細(xì)菌的多樣性因連作而減少[13-14]。
菠蘿(Ananas comosus(L.)Merr.)又稱(chēng)鳳梨,是著名的熱帶水果。據(jù)統(tǒng)計(jì),我國(guó)現(xiàn)有菠蘿種植約97.1萬(wàn)畝,產(chǎn)量約173.3萬(wàn)t[16]。我國(guó)菠蘿消費(fèi)量約以年均7.5%速度在增長(zhǎng),市場(chǎng)需求量大,菠蘿產(chǎn)業(yè)為我國(guó)熱區(qū)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菠蘿連作在我國(guó)各產(chǎn)區(qū)十分普遍。果農(nóng)在菠蘿果實(shí)收獲后,將莖葉粉碎還田翻松土壤后再種植菠蘿[17-18],并施用大量化肥,循環(huán)往復(fù),常連續(xù)種植10余年甚至更長(zhǎng)。隨著連作年限的增加,菠蘿果實(shí)產(chǎn)量、品質(zhì)明顯降低,產(chǎn)業(yè)發(fā)展受到影響。有關(guān)菠蘿連作對(duì)土壤代謝物及細(xì)菌群落結(jié)構(gòu)的影響變化等仍不清楚。
本研究基于非靶向代謝組學(xué)及16S rDNA高通量測(cè)序技術(shù),以菠蘿園邊角地未耕作過(guò)的土壤為對(duì)照,對(duì)連續(xù)種植5 a和15 a菠蘿的土壤代謝物和土壤細(xì)菌群落結(jié)構(gòu)進(jìn)行比較分析,篩選出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中的差異代謝物及代謝通路,分析細(xì)菌群落組成及豐度變化。本研究旨在探討菠蘿園土壤代謝物及細(xì)菌群落結(jié)構(gòu)的變化與菠蘿連作年限的關(guān)系,為菠蘿連作相關(guān)研究奠定基礎(chǔ),也為菠蘿的田間管理、土壤環(huán)境保護(hù)等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本研究取樣區(qū)域選擇在我國(guó)最大的菠蘿主產(chǎn)區(qū)廣東省湛江市徐聞縣。本次采集的土壤樣品來(lái)自徐聞縣菠蘿的主要種植區(qū)曲界鎮(zhèn),土壤類(lèi)型為磚紅壤。
選擇連續(xù)種植了菠蘿5 a、15 a的菠蘿園土壤(分別簡(jiǎn)寫(xiě)成T5、T15)及菠蘿園邊角地未耕作過(guò)的土壤(T0,對(duì)照)作為研究對(duì)象。菠蘿種植園每造均用吸芽苗種植,種植品種為“巴厘”,畝植4 000棵,果實(shí)收獲后菠蘿莖葉粉碎還田。每造菠蘿畝施尿素100 kg、復(fù)合肥(N15-P2O515-K2O15)150 kg,分別于種植后的第4個(gè)月(尿素50 kg、復(fù)合肥50 kg)和第8個(gè)月(尿素50 kg、復(fù)合肥100 kg)分兩次施完。
本研究土壤取樣于2020年3月中旬進(jìn)行。每個(gè)種植年限選擇3個(gè)園區(qū)(園區(qū)間隔 100 m 以上)。所有種植菠蘿的園區(qū)坡向、坡度和管理措施基本一致。取樣時(shí)菠蘿種植園當(dāng)造菠蘿未施首次大肥,每個(gè)園區(qū)隨機(jī)選擇東部、西部2個(gè)位置作為取樣對(duì)象。每個(gè)位置隨機(jī)選取兩個(gè)取樣點(diǎn)(相距5 m)。取樣時(shí)先除去地表5 cm厚的表層土壤,采用內(nèi)徑為5 cm土鉆采集0-20 cm土層樣品,每個(gè)取樣點(diǎn)平行鉆取2鉆;兩個(gè)取樣點(diǎn)的土樣混為1個(gè)樣品,共18個(gè)樣品,每處理6次重復(fù)。取樣后用離心管裝好立即置于液氮中速凍2 h后在-70℃超低溫冰箱中暫存。
1.2 方法
1.2.1 土壤代謝物的測(cè)定
1.2.1.1 土壤代謝物的提取 (1)取樣本1 000 mg于5 mL EP管中,加入1 000 μL提取液(甲醇∶水=3∶1,V/V),再加入1 000 μL乙酸乙酯及5 μL 核糖醇,渦旋30 s;(2)加入鋼珠,35 Hz研磨儀研磨4 min,超聲5 min(冰水浴);(3)將樣本于4℃離心,10 000 r/min離心15 min;(4)移取上清液于5 mL EP管中,再加入1 000 μL提取液(甲醇∶水=3∶1,V/V)和1 000 μL乙酸乙酯,重復(fù)以上2、3步驟,合并所有上清液;(5)在真空濃縮器中干燥提取物;(6)向干燥后的代謝物中加入20 μL甲氧胺鹽試劑(甲氧胺鹽酸鹽,溶于吡啶20 mg/mL),輕輕混勻后,放入80℃烘箱中孵育30 min;(7)向每個(gè)樣品中加入30 μL BSTFA(含有1% TMCS,V/V),將混合物在70℃孵育1.5 h;(8)冷卻至室溫,向混合的樣本中加入5 μL FAMEs(溶于氯仿);(9)上機(jī)檢測(cè)。
1.2.1.2 代謝物GC-TOF-MS檢測(cè) Agilent 7890氣相色譜-飛行時(shí)間質(zhì)譜聯(lián)用儀配有Agilent DB-5MS毛細(xì) 管 柱(30 m×250 μm×0.25 μm,J&W Scientific,F(xiàn)olsom,CA,USA),GC-TOF-MS具體分析條件如表1。
1.2.1.3 代謝物測(cè)定數(shù)據(jù)處理與分析 使用ChromaTOF軟件(V4.3x,LECO)對(duì)質(zhì)譜數(shù)據(jù)進(jìn)行處理[19],使用LECO-Fiehn Rtx5數(shù)據(jù)庫(kù),將質(zhì)控(Quality Control)樣本中檢出率50%以下或RSD>30%的峰去除[20]后的有效數(shù)據(jù)用于后續(xù)實(shí)驗(yàn)分析。
采用R(3.3.2)包ropls進(jìn)行正交偏最小二乘法-判別分析(orthogonal projections to latent structures- discriminant analysis,OPLS-DA)模型計(jì)算,獲取更可靠的代謝物的組間差異信息;采取將差異倍數(shù)(fold change)、t檢驗(yàn)的P值(P value<0.05)和OPLS-DA模型的VIP值(variable importance in the projection,VIP>1)——變量投影重要度相結(jié)合的方法篩選差異代謝物;采用單因素方差(ANOVA)分析繪制的火山圖(volcano plot)統(tǒng)計(jì)差異代謝物在T0-T5和T0-T15比較組中的表達(dá)水平;采用KEGG(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對(duì)差異代謝物進(jìn)行通路富集分析。
1.2.2 微生物16S rDNA測(cè)序分析 微生物16S rDNA的擴(kuò)增及測(cè)序委托北京百邁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完成。PCR擴(kuò)增引物為:(16SF)AGRGTTTGATYNTGGCTCAG,(16S-R)TASGGHTACCTTGTTASGACTT;PCR擴(kuò) 增 程 序:95℃預(yù)變性5 min;95℃變性30 s,55℃退火30 s,72℃延伸90 s,30個(gè)循環(huán);72℃延伸7 min,4℃保存。
采 用PacBio測(cè) 序 平 臺(tái),對(duì)CCS(Circular Consensus Sequencing)序列進(jìn)行Barcode識(shí)別和長(zhǎng)度過(guò)濾,得到Optimization-CCS,使用Usearch軟件[21]對(duì)Tags在97%的相似度水平下進(jìn)行聚類(lèi)并劃分OTU,根據(jù)OTU的序列組成得到其物種分類(lèi),基于OTU分析結(jié)果,對(duì)樣品在各個(gè)分類(lèi)水平上進(jìn)行分類(lèi)學(xué)分析,獲得各樣品在門(mén)、屬分類(lèi)學(xué)水平上的物種分布圖與在目水平上的物種聚類(lèi)熱圖。稀釋性曲線(dilution curve)用于檢驗(yàn)測(cè)序數(shù)據(jù)量[22];ACE、Chao1、Shannon及Simpson指數(shù)用于分析細(xì)菌菌群的多樣性及豐度;非度量多維標(biāo)定法(Non-MetricMulti-Dimensional Scaling,NMDS)[23]分析細(xì)菌菌群結(jié)構(gòu)差異;斯皮爾曼(Spearman)相關(guān)性分析物種在環(huán)境樣本中的共存關(guān)系。通過(guò)典范對(duì)應(yīng)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CCA)[24]在屬水平細(xì)菌菌群和pH等理化指標(biāo)之間的相關(guān)性,樣品射線與pH射線成銳角即為正相關(guān),成鈍角為負(fù)相關(guān)。
2 結(jié)果
2.1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樣本OPLS-DA法判別分析
圖1顯示,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微生物代謝物模型參數(shù)中R2X=0.776,R2Y=0.979,Q2Y=0.888,說(shuō)明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代謝模型對(duì)自變量X的解釋程度為77.6%;對(duì)分類(lèi)變量Y的解釋程度為97.9%,對(duì)樣本變量的預(yù)測(cè)程度為88.8%,該模型R2Y非常接近1,表明OPLS-DA模型為有效模型,樣本數(shù)據(jù)真實(shí)可靠度較高、穩(wěn)定性和預(yù)測(cè)能力較強(qiáng)。

圖1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土壤所有樣本OPLS-DA得分圖Fig.1 OPLS-DA scores of all soil samples from the pineapple orchard in different continuous-cropping years
OPLS-DA模型能直觀的展示出組間的分離情況,18個(gè)樣本均處于95%置信區(qū)間內(nèi),T5、T15組間接近且有部分重疊但與對(duì)照明顯分開(kāi),表明T5和T15組間代謝模式接近,但均與對(duì)照存在顯著差異。組內(nèi)各樣本聚集,分散程度較小。
2.2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差異代謝物火山圖分析
圖2分別顯示了T5組、T15組與對(duì)照組(T0)間的差異代謝產(chǎn)物分布情況。由火山圖可知,T5組與T0組土壤間有120個(gè)差異代謝物,其中顯著增加(P<0.05)的有119個(gè),顯著降低(P<0.05)的有1個(gè);T15組與T0組土壤微生物中有80個(gè)差異代謝物,其中顯著增加(P<0.05)的有60個(gè),顯著降低(P<0.05)的有20個(gè)。

圖2 差異代謝物火山圖Fig.2 Volcano plot of differential metabolites
2.3 顯著差異代謝物篩選
運(yùn)用OPLS-DA模型的分析方法,將差異倍數(shù)(FC>2)、t檢驗(yàn)P值(P value <0.05)和VIP值(VIP >1)相結(jié)合的標(biāo)椎對(duì)T0-T5比較組和T0-T15比較組差異代謝物進(jìn)行篩選,共篩選出11個(gè)具有顯著性差異(P <0.05)的代謝物(表2)。其中,有機(jī)酸4種,氨基酸及其衍生物2種,糖類(lèi)3種,醇類(lèi)2種。
據(jù)表2可知,T0-T5比較組和T0-T15比較組差異代謝物的組分含量存在差異。與T0相比,T5中的有機(jī)酸類(lèi)代謝物(2R,3S)-2-羥基-3-異丙基丁二酸、4-羥基苯甲酸、4-羥基-3-甲氧基苯甲酸、3,4-二羥基苯甲酸的表達(dá)分別升高了1.924倍、1.538倍、1.569倍和1.740倍;而在T15中,與T0相比這4種代謝物的表達(dá)分別提高了2.099倍、2.191倍、1.879倍和1.746倍。類(lèi)似地,T5中N-乙酰基-β-丙氨酸、N-氨基甲酰谷氨酸的表達(dá)分別較T0升高了2.211倍和2.327倍;而在T15中N-乙酰基-β-丙氨酸、N-氨基甲酰谷氨酸的表達(dá)分別較T0升高了3.186倍和3.440倍。

表2 不同比較組間差異代謝物Table 2 Differential metabolites among the comparison groups
與T0比較,T5中的糖類(lèi)、醇類(lèi)代謝物表達(dá)提高的倍數(shù)高于T15中糖類(lèi)、醇類(lèi)代謝物含量提高的倍數(shù)。T5中的葡萄糖、槐糖、松三糖的含量水平分別比T0升高了4.878倍、4.201 倍和1.292倍;而在T15中葡萄糖的含量水平比T0提高了1.580倍,槐糖、松三糖的含量則分別降低了3.892倍和1.386倍。類(lèi)似地,與T0相比,T5中的醇類(lèi)代謝物(3β,5α,6β)-膽固醇3,5,6-三醇、山梨糖醇含量提高了3.071倍和2.244倍;而T15中這2種代謝物的含量水平分別提高了1.568倍和1.901倍。
2.4 差異代謝物KEGG富集分析
2.4.1 基于HMDB數(shù)據(jù)庫(kù)的差異代謝物統(tǒng)計(jì) 如圖3所示,T0-T5比較組在HMDB數(shù)據(jù)庫(kù)檢索到的差異代謝物種類(lèi)有8種,T0-T15比較組檢索到的差異代謝物種類(lèi)有6種。在T0-T5比較組和T0-T15比較組中同時(shí)檢索到的差異代謝物有5種,分別為脂肪酰基、苯及其取代衍生物、有機(jī)氧化合物、類(lèi)固醇和類(lèi)固醇衍生物、肉桂酸及其衍生物。其中,苯及其取代衍生物、肉桂酸及其衍生物、類(lèi)固醇和類(lèi)固醇衍生物在T0-T5比較組和T0-T15比較組所占比例相同。在T0-T5組檢索到的有機(jī)氧化合物類(lèi)代謝物有3個(gè),在T0-T15組有2個(gè);T0-T5組檢索到的脂肪酰基類(lèi)代謝物有8個(gè),在T0-T15組有3個(gè)。此外,僅在T0-T5組中檢索到的差異代謝物有3種,分別為吡啶及其衍生物、非金屬氧陰離子化合物和羧酸及其衍生物;僅在T0-T15組中檢索到的差異代謝物有1種,為二嗪類(lèi)代謝物。

圖3 T0-T5比較組和T0-T15比較組差異代謝物HMDB分類(lèi)圖Fig.3 HMDB classification map of differential metabolites from the comparison groups of T0-T5 and T0- T15
2.4.2 差異代謝物代謝通路分析 KEGG通路富集分析表明,顯著差異代謝物主要富集在11條代謝通路上(表3),分別為果糖和甘露糖代謝、類(lèi)固醇生物合成、苯丙烷生物合成、泛醌和其他萜類(lèi)醌的生物合成、酪氨酸代謝、苯丙氨酸代謝、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亞油酸代謝、葉酸生物合成、異喹啉生物堿的生物合成和不飽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
表3結(jié)果顯示,這11條通路所對(duì)應(yīng)的代謝物有8個(gè)。3,4-二羥基苯甲酸主要參與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4-羥基苯甲酸和4-羥基肉桂酸共同參與苯丙氨酸代謝和泛醌及其他萜類(lèi)醌的生物合成途徑;并且,4-羥基苯甲酸還參與葉酸生物合成途徑;而4-羥基肉桂酸參與苯丙烷和異喹啉生物堿的生物合成途徑,此外,4-羥基肉桂酸還可單獨(dú)參與酪氨酸的代謝過(guò)程。山梨糖醇主要參與果糖和甘露糖代謝過(guò)程,膽固醇主要參與類(lèi)固醇生物合成途徑;亞油酸既可單獨(dú)參與亞油酸代謝途徑,又可與山崳酸和木質(zhì)酸一起共同參與不飽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途徑。

表3 差異代謝物代謝通路分析Table 3 Metabolic pathway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ial metabolites
2.4.3 KEGG富集網(wǎng)絡(luò)圖 KEGG富集網(wǎng)絡(luò)圖(圖4)更直觀顯示了T5、T15差異代謝物所參與的關(guān)鍵代謝通路,且每條關(guān)鍵通路多為一種以上的代謝物所共同參與的,同一條通路的代謝物組成有明顯差異。由圖4可知,不飽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途徑在T5、T15代謝中的影響均最大,但參與不飽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的代謝物有差異,在T5中受到油酸、山崳酸、花生酸、亞油酸和木質(zhì)酸共同的影響,而在T15中主要受到亞油酸、木質(zhì)酸和山崳酸的影響;其次,苯丙氨酸代謝途徑在T5中的影響較大,泛醌及其他萜類(lèi)醌的生物合成途徑在T15中的影響較大,而這兩種代謝途徑均是由4-羥基苯甲酸和4-羥基肉桂酸所共同參與的。此外,圖4-A顯示T5對(duì)氧化磷酸化途徑的代謝影響較大;圖4-B顯示T15對(duì)β-丙氨酸代謝、苯丙氨酸、酪氨酸、色氨酸的生物合成和亞油酸代謝的影響較大。以上結(jié)果表明,T5、T15代謝水平存在一定的差異,顯著差異代謝物在T5、T15同一條代謝通路中的影響也有所不同。

圖4 差異代謝物KEGG富集網(wǎng)絡(luò)圖Fig. 4 KEGG pathway enrichment map of differential metabolites
2.5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細(xì)菌16S測(cè)序數(shù)據(jù)
對(duì)T0及T5、T15土壤進(jìn)行16S全長(zhǎng)測(cè)序(6次重復(fù)),分析了細(xì)菌群落的多樣性。通過(guò)Barcode識(shí)別后共獲得122 534條CCS序列,每個(gè)樣品至少產(chǎn)生3 889條CCS序列,平均產(chǎn)生6 807條CCS序列,過(guò)濾后共獲得121 795條(99.47%)有效CCS序列用于后續(xù)實(shí)驗(yàn)分析,樣品平均序列長(zhǎng)度為1 447 bp,在97%的相似水平下進(jìn)行聚類(lèi)分析,共獲得OUT 9582個(gè)。由圖5可知,當(dāng)測(cè)序量接近5 000讀長(zhǎng)時(shí),稀釋性曲線(dilution curve)逐漸趨于平緩,表明本試驗(yàn)樣品序列充足,取樣能夠真實(shí)地反映菠蘿地土壤中的細(xì)菌群落結(jié)構(gòu)多樣性。

圖5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樣品的稀釋性曲線Fig. 5 Dilution curve of soil samples in the different continuous-cropping years of the pineapple orchard
如圖6,細(xì)菌在OTU水平上的NMDS分析結(jié)果顯示,T5、T15土壤細(xì)菌群落分布比T0更集中,且T5、T15之間細(xì)菌群落明顯分開(kāi),說(shuō)明不同種植年限菠蘿地土壤細(xì)菌群落結(jié)構(gòu)存在顯著差異。

圖6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細(xì)菌群落N(xiāo)MDS分析Fig. 6 NMDS analysis of different soil bacterial community in the different continuous-cropping years of the pineapple orchard
2.6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細(xì)菌群落多樣性和相對(duì)豐度變化
在門(mén)水平上對(duì)細(xì)菌群落相對(duì)豐度進(jìn)行分析,如圖7-A所示,從土壤中鑒定到的細(xì)菌主要來(lái)自6個(gè)門(mén),約占細(xì)菌總數(shù)的67.72%,分屬放線菌門(mén)(Actinobacteriota)、變形細(xì)菌門(mén)(Proteobacteria)、綠彎菌門(mén)(Chloroflexi)、酸桿菌門(mén)(Acidobacteriota)、浮霉菌門(mén)(Planctomycetota)、厚壁菌門(mén)(Firmicutes)。其中放線菌門(mén)(Actinobacteriota)、變形細(xì)菌門(mén)(Proteobacteria)、綠彎菌門(mén)(Chloroflexi)、酸桿菌門(mén)(Acidobacteriota)、浮霉菌門(mén)(Planctomycetota)為菠蘿地土壤的優(yōu)勢(shì)菌群,這些菌在T5、T15土壤中分別占細(xì)菌總數(shù)的70.51%和89.82%。圖7-A顯示,T5、T15土壤中厚壁菌門(mén)(Firmicutes)所占比例較T0明顯減少,放線菌門(mén)(Actinobacteriota)、綠彎菌門(mén)(Chloroflexi)和浮霉菌門(mén)(Planctomycetota)所占比例顯著增加。變形細(xì)菌門(mén)(Proteobacteria)和酸桿菌門(mén)(Acidobacteriota)在T5土壤中所占比例最高,但在T15土壤中比例降低,低于T0。
圖7-B表明,從屬水平上分析T5、T15土壤細(xì)菌群落的相對(duì)豐度明顯高于T0。與T0相比,T5土壤在屬水平上相對(duì)豐度顯著增加的細(xì)菌群落主要有伍氏束縛菌(Conexibacter)、Thermosporothrix、Aciditerrimonas、Acidibacter、Fimbriiglobus、Actinoallomurus;T15土壤顯著增加的屬有分枝桿菌屬(Mycobacterium)、中華單胞菌屬(Sinomonas)、Conexibacter、Thermosporothrix、Aciditerrimonas、Fimbriiglobus、Actinoallomurus。但T5、T15土壤伯克氏菌屬(Burkholderia)的相對(duì)豐度較T0明顯降低。
圖7-C所示為在目水平上T0與T5、T15土壤細(xì)菌群落相對(duì)豐度的差異。與T0相比,T5土壤中顯著增加的細(xì)菌目有Azospirillales、黃色單胞菌目(Xanthomonadales)、Polyangiales、Pedosphaerales、Isosphaerales、Solibacterales、酸桿菌目(Acidobacteriales)、芽單胞菌目(Gemmatimonadales)、Gammaproteobacteria-Incertae-Sedis、細(xì)鏈孢菌目(Catenulisporales);顯著減少的細(xì)菌目有鏈霉菌目(Streptomycetales)、假諾卡式菌目(Pseudonocardiales)。而T15土壤相對(duì)豐度顯著增加的細(xì)菌目有乳桿菌目(Lactobacillales)、弗 蘭 克 氏 菌 目(Frankiales)、土壤紅桿菌目(Solirubrobacterales)、黏 球 菌 目(Micrococcales)、酸 微 菌 目(Acidimicrobiales)、Streptosporangiales、芽孢桿菌目(Bacillales)、棒桿菌亞目(Corynebacteriales)、Gaiellales;顯著減少的細(xì)菌目有根瘤菌目(Rhizobiales)、鏈霉菌目(Streptomycetales)、假諾卡式菌目(Pseudonocardiales)。T5、T15相對(duì)豐度均顯著減少的細(xì)菌目有鏈霉菌目(Streptomycetales)和假諾卡式菌目(Pseudonocardiales)。

圖7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細(xì)菌群落在門(mén)、屬、目水平上的相對(duì)豐度Fig. 7 Relative abundance of different soil bacterial community at phyla,genus and order level in the different continuouscropping years of the pineapple orchard
2.7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細(xì)菌群落多樣性 分析
表4所示,T5土壤的ACE和Chao1指數(shù)均顯著高于T15和T0;而T15土壤的ACE和Chao1指數(shù)均低于T5和T0。結(jié)果表明T5土壤細(xì)菌相對(duì)豐度升高,T15細(xì)菌群落相對(duì)豐度下降。如表4所示,T5、T15的Simpson指數(shù)分別為0.01和0.04,顯著低于T0(0.12);而T5、T15的Shannon指數(shù)分別為5.39、4.66,顯著高于T0(3.90)。結(jié)果表明T5、T15土壤中細(xì)菌群落多樣性增加,且以T5土壤中細(xì)菌群落多樣性相對(duì)更高。

表4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細(xì)菌豐度與多樣性Table 4 Diversity of relative abundance of different bacterial of soil under different continuous-cropping years of the pineapple orachard
2.8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地土壤細(xì)菌群落與土壤pH的相關(guān)性
由圖8可知,連作年限與土壤pH成負(fù)相關(guān);細(xì)菌屬(Aciditerrimonas)、Acidibacter、Actinoallomu- rus、Paraburkholderia與pH成正相關(guān),分枝桿菌屬 (Mycobacterium)、Gaiella、中 華 單 胞 菌 屬(Sino- mo-nas)、Conexibacter、Thermosporothrix與pH成 負(fù) 相關(guān)。

圖8 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園土壤中細(xì)菌群落與pH值的相關(guān)性CCA分析Fig. 8 CCA analysis correlating bacterial community to pH value of soil under different continuous-cropping years of the pineapple orchard
3 討論
糖類(lèi)作為微生物的主要碳源,為微生物正常代謝提供所需要的能量。已有研究表明,大豆連作導(dǎo)致葡萄糖的組分含量下降,同時(shí),隨連作時(shí)間的延長(zhǎng),土壤多糖含量逐漸降低,影響土壤有機(jī)質(zhì)的組成及植株的生長(zhǎng)發(fā)育[25-26]。這與本研究中,連續(xù)種植了15年菠蘿的土壤中槐糖、松三糖的表達(dá)水平降低的結(jié)果相似。
酚酸類(lèi)代謝物是多數(shù)作物的主要化感物質(zhì),其自毒潛力隨種植年限的增加而有上升的趨勢(shì)[3,27]。本研究表明,菠蘿連作后土壤中的4種有機(jī)酸類(lèi)代謝物的表達(dá)水平均升高,尤其是在菠蘿連作15年的土壤中酸類(lèi)代謝物的表達(dá)升高幅度更大。由于長(zhǎng)期連作,施肥量大,有機(jī)酸類(lèi)物質(zhì)增加,造成土壤逐漸酸化,不僅容易滋生出大量好酸性微生物,也加劇了土壤的自毒作用[27-32]。菠蘿連作5年、15年后土壤中4-羥基苯甲酸等酚酸類(lèi)物質(zhì)的含量水平均提高,且連作15年提高的幅度更大,表明菠蘿長(zhǎng)期連作對(duì)土壤環(huán)境產(chǎn)生了不利影響。在蠶豆、花生等的連作障礙研究中發(fā)現(xiàn),肉桂酸、苯甲酸和對(duì)羥基苯甲酸等自毒物質(zhì)是導(dǎo)致連作障礙的重要影響因 子[3,30]。茄子連作障礙的研究也表明,連作后土壤中的肉桂酸濃度增加,加劇了茄子的自毒作用[33]。連作后土壤中的對(duì)羥基苯甲酸含量增加影響了土壤微生物活性與多樣性,導(dǎo)致土壤中的細(xì)菌、放線菌數(shù)量減少,真菌數(shù)量增加[34],土壤中有益生物減少、有害生物增加,最終導(dǎo)致連作障礙的發(fā)生[35]。
KEGG代謝通路分析表明,不同連作年限菠蘿地土壤差異代謝物主要富集在不飽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途徑等11條代謝通路中,并且每條關(guān)鍵通路多為一種以上的代謝物所共同參與的。不飽和脂肪酸的生物合成途徑對(duì)連作5年、15年菠蘿土壤代謝的影響均最大,該途徑是由亞油酸、山崳酸和木質(zhì)酸等有機(jī)酸共同參與的代謝途徑,這可能與連作導(dǎo)致土壤酸化,有機(jī)酸參與的代謝活動(dòng)增強(qiáng)有關(guān)[36-37]。
土壤細(xì)菌代謝旺盛、繁殖快,種類(lèi)多、數(shù)量大,是土壤微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對(duì)作物的生長(zhǎng)有著重要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細(xì)菌群落的變化與連作障礙關(guān)系密切[12,38]。本研究通過(guò)微生物16S測(cè)序?qū)?xì)菌群落結(jié)構(gòu)分析結(jié)果表明,與對(duì)照相比,連續(xù)種植菠蘿5年和15年的土壤細(xì)菌群落多樣性提高,但連續(xù)種植菠蘿15年的土壤細(xì)菌群落的相對(duì)豐度降低,這與其他作物連作相關(guān)研究結(jié)果相 似[12,39]。土壤pH值在細(xì)菌群落結(jié)構(gòu)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是決定細(xì)菌群落結(jié)構(gòu)演替與群落結(jié)構(gòu)發(fā)生分異的主要驅(qū)動(dòng)因子,土壤pH與土壤細(xì)菌群落的相關(guān)性最高[38,40-41]。基于CCA分析結(jié)果表明,土壤pH與菠蘿連作年限呈負(fù)相關(guān),這不僅為菠蘿長(zhǎng)期連作后導(dǎo)致土壤酸化做出了解釋?zhuān)矠椴ぬ}連作后導(dǎo)致土壤細(xì)菌群落減少,土壤pH變化在調(diào)節(jié)細(xì)菌群落發(fā)生分異中的作用提供了有利的證明。長(zhǎng)期種植單一作物導(dǎo)致土壤微生物多樣性出現(xiàn)不同程度的下降,根際微生態(tài)環(huán)境受到破壞[14],需要采取減施化肥、輪作、休耕等措施控制土壤的酸化與鹽分積累,提高微生物群落尤其是細(xì)菌群落的多樣性,提高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穩(wěn)定性[42-43]。
4 結(jié)論
菠蘿連作后土壤中的酸類(lèi)代謝物表達(dá)水平升高。連續(xù)種植5年菠蘿的土壤中葡萄糖、槐糖、松三糖等糖類(lèi)代謝物的表達(dá)水平升高。連續(xù)種植了15年菠蘿的土壤中槐糖、松三糖的表達(dá)水平降低;葡萄糖的表達(dá)水平雖高于菠蘿園邊角地未耕作過(guò)的土壤,但低于連續(xù)種植5年菠蘿的土壤中葡萄糖的表達(dá)水平。細(xì)菌16S測(cè)序表明,連續(xù)種植菠蘿5 年和15 年的土壤細(xì)菌群落結(jié)構(gòu)存在明顯差異;連作5年、15年土壤細(xì)菌群落多樣性提高,但連作15年的土壤細(xì)菌群落相對(duì)豐度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