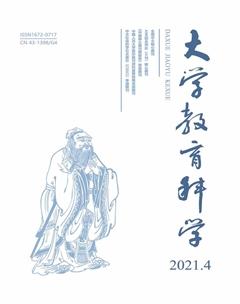教育文化史:新文化史視域下的教育史學新范式
楊偉東 胡金平
摘要: 20世紀末,西方史學發生了“文化轉向”,新文化史成為史學主流,對歷史學及其相關學科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教育史作為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在新文化史學的影響下逐漸生成一種新的教育史學范式——教育文化史。教育文化史秉持人文主義教育史觀,以教育歷史中的“文化”為研究對象,積極借鑒人類學、語言學、文化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通過微觀視角、底層視角和文化視角來審視歷史,視史料為文本,以敘事的方式呈現學術成果。教育文化史的提出,一方面促進了教育史學觀念的更新、教育史學研究范圍的擴展和教育史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另一方面,教育文化史在強調教育的文化解釋的同時忽視了教育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解釋,對教育歷史客觀性的懷疑可能會引起主觀主義的盛行,無所不包而又缺乏中心的做法可能會導致教育史的碎片化。
關鍵詞:文化轉向;新文化史;教育文化史;范式
中圖分類號:G519 ?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0717(2021)04-105-08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史學發生了從社會史學到文化史學的“文化轉向”,產生了一種新的史學范式,人們稱之為“新文化史”。史學范式的轉變對歷史學及其相關學科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教育史學在這一轉變的影響下也發生了一些變化。一些學者對教育史學的這些變化進行了初步研究,探討了新文化史影響下的教育史學在研究視角、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史料來源、表達方式等方面的變化[1-7]。可以看出,現有研究從注重借鑒新文化史的研究視角,到較為全面地梳理新文化史的方法論,再到嘗試建構新文化史學影響下的教育史學方法論,逐漸顯現出一種新的教育史學范式。然而,現有研究還未能從“范式”的角度系統而深入地闡釋這些變化,也未能充分揭示這些變化對教育史學發展的意義及其局限。有鑒于此,本文在分析新文化史學范式的基礎上,提出“教育文化史”這一概念以指代在新文化史學影響下產生的教育史學新范式,并嘗試著去分析教育文化史的內涵,探討教育文化史對教育史學的意義及其局限。
一、文化轉向與新文化史學
1989年,美國學者林·亨特主編的《新文化史》出版,“明確打出了新文化史的大旗,確定了歷史學主流之‘文化轉向的事實”[8](P4),標志著“新文化史”作為一種新的史學范式的確立。庫恩認為“范式……代表著一個特定共同體的成員所共有的信念、價值、技術等等構成的整體。”[9]“范式”大體上可以理解為某一學術共同體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進行學術研究時所共同遵守的前提、準則和方法等。具體到史學領域,史學范式一般包括史學觀念、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寫作方式、解釋模式等方面。以下本文即按此框架對歷史研究的“文化轉向”進行分析。
歷史研究的“文化轉向”首先是史學觀念的轉向。“史學觀念是指對歷史知識性質的根本看法。這里涉及歷史學家對歷史的態度,對史料的看法,對現在和過去關系的認識,對自身在研究實踐過程(也就是歷史認識過程)中所起作用的考慮。顯而易見,不同的史學觀念會產生特點迥異的研究成果。”[10](P5)史學觀念是歷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礎,有什么樣的史學觀念就會有什么樣的史學研究,因此史學范式的轉變往往是從史學觀念的轉變開始的。新文化史學的“新文化史觀”起源于人們對新史學“社會史觀”的批判和調整。新史學繼承并發展了19世紀以來形成的實證主義史學觀念,認為歷史研究雖然是歷史學家對過去進行建構的過程,但這種建構并非主觀臆造,而是在一定客觀坐標系內的建構,因此并不否認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和科學性。新史學家推崇“問題史學”,提倡從問題出發搜集史料,認為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主張對社會歷史的綜合研究,提出“總體史”,打破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隔閡,倡導跨學科的研究,特別是對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等社會學科的借鑒,并致力于尋求社會歷史的結構及其發展規律。到20世紀60年代末,新史學正如日中天的時候,其內部逐漸出現了一些批評的聲音。一些歷史學家不滿于新史學過分強調經濟、社會、人口的研究取向,認為這種研究取向在強調歷史的社會經濟基礎、社會歷史的結構及其發展規律的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經濟決定論和漠視人的弊端,于是轉而強調政治、文化、心態等上層建筑,主張將文化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一視同仁。與此同時,以“語言學轉向”為特征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對新史學的理論基石產生了巨大沖擊。周愚文在總結其他學者相關論述的基礎上歸納出后現代主義史學的九項主要論點:“反對歷史的大敘事,后設敘事;反對歷史的因果解釋;否認歷史的連續性,而強調間斷性;否認歷史知識的客觀真實性與一慣性,且其具權力性質;反對中心主義與統一史,主張多元解釋;歷史書寫只是敘述文本的論述,不涉及真理;歷史文本即是歷史實在,其有多種形式,文本是建構的,不涉及之外的世界;歷史敘事無法再現歷史實在;歷史敘事是文學修辭,甚至與虛構類同。”[11]在史學內部的反思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批判下,新的史學觀念——“新文化史觀”逐漸形成。“新文化史觀”反對“一切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歷史決定論,強調文化的重要性及其對社會的能動作用,否認歷史知識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認為歷史知識只不過是文本和敘事。“新文化史觀”認為,史料并不是對歷史事實的客觀記錄,而是主觀建構的文本,其背后隱含著記錄者的主觀意識和當時的時代精神,他們質疑歷史研究的科學性和普遍性,強調歷史的人文性和特殊性。在新的史學觀念的指引下,歷史學發生了重大變革,新的史學范式也因此逐漸成型。
史學觀念的轉變引發了歷史研究對象的轉變。在新文化史的視域中,“文化”的地位被空前提高,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要對象。新文化史學家眼中的“文化”不同于傳統文化史學家所說的“文化”,卻是更接近于人類學家對文化的看法。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將文化史的發展歷程概括為四個階段:一是“經典”階段,此時的文化史學家關注的是經典作品(也就是藝術、文學、哲學、科學等學科中杰出作品的“典范”)的歷史;二是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藝術的社會史”階段,是對經典文化史的反動,強調文化的經濟和社會基礎[12];三是20世紀60年代大眾文化史的發現階段;四是“新文化史”階段[13](P7)。他認為新文化史的“文化”觀念更接近人類學家對文化的看法。“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歷史學家對‘文化一詞的使用逐漸發生了變化。這個用詞以前是用來指稱上層文化,但現在把日常文化也包含在內,包括習俗、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換句話說,歷史學家越來越接近人類學家對文化的看法。”[13](P37)事實上,新文化史學家的“文化”觀念主要借鑒自人類學對文化的定義,特別是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對文化的經典定義。格爾茨批判以往的文化定義過于多義和模糊,進而提出了一個簡潔而明確的文化概念。“我所堅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重所指的,也不是含糊不清的:它表示的是從歷史上留下來的存在于符號中的意義模式,是以符號形式表達的前后相襲的概念系統,借此人們交流、保存和發展對生命的知識和態度。”[14](P95)這一概念不僅指明了文化的內涵,也暗示了文化研究的路徑,即文化研究是一種解釋意義的研究。正如格爾茨所說:“我主張的文化概念實質上是一個符號學的概念。馬克斯·韋伯提出,人是懸在由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觀點。于是,我以為所謂文化就是這樣一些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因此,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14](P5)新文化史學家林·亨特對文化的理解與格爾茨有異曲同工之處,她認為:“新的歷史探討方向的焦點是人類心智,把它看作是社會傳統的儲藏處,是認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語言處理事實的地方。文化就駐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義為解釋機制與價值系統的社會貯藏所。”[15]無論是將“文化”定義為“存在于符號中的意義模式”,或者“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抑或是“解釋機制與價值系統的社會貯藏所”,這里的“文化”都不僅僅是傳統文化史所說的社會表層的文化現象,而更側重于表層文化現象背后所蘊藏的“意義模式”與“價值系統”。簡而言之,新文化史學家所說的“文化”大體上是指某一特定人群所共有的深層價值觀念及其表層象征。這一特點使得新文化史的研究旨趣發生轉變,即從傳統文化史注重對文化現象的客觀描述和因果解釋轉向對文化現象背后的“意義模式”和“價值系統”的揭示。
當代史學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征即跨學科的方法借鑒。當然,不同的史學研究取向所跨的學科并不相同,對研究方法的偏好也隨之而變。新史學將研究重點放在社會、經濟、人口等方面,這一研究對象決定了新史學在研究方法上傾向于借鑒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等社會學科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對計量方法的偏好,包括運用計算機進行統計分析,建立數據庫和數學模型等。新文化史將研究對象轉移到文化方面,關注的焦點是表層文化現象背后的意義模式,相應的研究方法也從借鑒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等學科轉向借鑒人類學、語言學、文化學等學科。正如張廣智所言,新文化史“從人類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那里獲得了文化的概念、研究的視野和解釋的手段,從文學理論、語言學和符號學那里得到了分析的武器,又從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等后現代思潮中學會了批判的態度。”[16]新文化史在研究視角上深受文化人類學的啟發,偏于微觀視角、底層視角和文化視角,所選取的課題往往小而貼近生活,隱含豐富的文化意蘊,擅長做以小見大的研究。這一特點從許多新文化史著作的名稱上即可看出,如夢娜·沃祖芙的《節慶與法國大革命》,阿蘭·科爾賓的《嗅覺與法國社會想象》,羅伯特·達恩頓的《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等。正如呂建忠在《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的譯序中所說的:“如果把一個國家的文化比喻為一個有機體,本書可以說是從法國文化史取下一個組織切片,然后拿來做斷層掃描。”[17](P1)事實上,新文化史的大部分著作都符合這一隱喻。在研究的具體方法上,最能體現新文化史學特色的當屬話語分析和“深描”。“話語分析”原本是一個語言學概念,包括兩層含義,一是對比單句更長的語言單位結構的靜態分析,二是對交際過程意義傳遞的動態分析[18]。新文化史學家的話語分析更側重后者,他們將歷史文本看做話語實踐的結果,著力分析歷史文本意義建構的過程,揭示這一隱秘過程中的權力運作機制。1990年出版的《發明法國大革命:18世紀法國政治文化隨筆集》一書,巴克運用話語分析的方法,把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視為一套話語體系及其被制造、被宣傳的過程。作者認為法國大革命并非單純的社會歷史實在,而是語言建構的結果。“革命實際上就是一場發明,大革命的激進特征、話語、思想體系和行為等無不是人類的發明,而非歷史突變的產物。”[10](P506)“深描”則是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發明的一種研究方法,但他并未給出確切的定義,而是通過“眨眼”的例子來說明“深描”:一般的眨眼和有意的擠眉弄眼在動作上可能相同,但兩者的意義卻是不同的,如果只是“現象主義”式地觀察它們,就是“淺描”,而如果理解并揭示出“擠眉弄眼”這一信號密碼背后的意義生成機制則是“深描”[14](P6-7)。達恩頓的《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是以“深描”研究文化史的典型。該書的重點并不是描述法國社會表層的文化現象,而是挖掘表層文化現象背后的意義模式,揭示當時的法國人思考世界的方式。作者在該書序言中說:“本書探討18世紀法國的思考方式。書中試圖陳明的不只是人們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們怎么思考——也就是他們如何闡明這個世界,賦予意義,并且注入感情。”[17](P1)
歷史研究的成果最終需要以文本的形式呈現出來,不同的史學范式決定了不同的文本寫作方式。新史學對社會結構的重視,對計量方法的偏好,對歷史規律的追求等特點使得新史學的寫作方式偏于結構分析和數理統計,導致新史學文本晦澀難懂,受眾狹窄。“新史學家的作品,或成百頁的論文或數千頁的宏著,他們非常喜好附有大量圖表,充滿數理公式,以致一般讀者無法讀懂,在專業學者群中也鮮有反應,失卻了歷史學所應負有的社會功能。”[19]針對這些弊端,一些史學家提出“歷史敘事的復興”來糾偏。1979年勞倫斯·斯通發表了《歷史敘述的復興:對一種新的老歷史的反省》一文,提出歷史寫作的“敘述(敘事的另一種翻譯,筆者注)的復興”。“‘敘述是指將歷史材料以時間順序組織起來,并將內容組成一前后呼應的故事,當然也不妨有一些次要的情節點綴其間。這種敘述歷史與‘結構型歷史有兩點不同:一是其安排是以‘敘述而非以‘分析為主;一是其注意的重點在于‘人物而非‘環境。這種歷史是處理‘特殊和‘具體,而不是‘集體和‘數值的情況。”[20](P8-9)歷史敘事的復興并不是要完全恢復傳統的歷史敘事方式,而是在新文化史學范式的影響下對傳統敘事方法的改革。新文化史的歷史敘事不僅重視對歷史事件的情節編排和文學性表達,更注重對歷史事件的文化解釋。新文化史批判了傳統史學的因果解釋,認為這種解釋模式是在傳統史學“后設敘事”的敘事框架下形成的“直線史觀”的解釋模式,將歷史視為統一的、連續的發展過程,忽視了歷史的多元性和斷裂性。新文化史認為歷史解釋機制應當從因果分析轉向意義闡釋,通過對符號及其背后隱喻的詮釋來理解其中隱含的價值和意義。
綜上所述,新文化史在史學觀念、研究對象、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寫作方式、解釋模式等方面均與新史學有很大不同,形成了一種全新的史學范式。當然,任何概括都有簡單化的危險,新文化史的史學實踐多種多樣,上述概括只是為了學理分析和論述的方便在最基本意義上的概括。
二、教育文化史的提出及其內涵
歷史學是教育史學的“母學科”,兩者存在天然的血緣關系,教育史學的發展離不開歷史學母乳的滋養。然而,在我國的學科體系里,教育史屬于教育學的分支學科,與歷史學幾乎沒有關系。這樣的學科設置使得我國的教育史學缺乏歷史學的理論基礎,教育史研究因此淪為一種描述性研究,缺乏應有的學術深度,進而導致了教育史學的“學術危機”。張斌賢對教育史學的“學術危機”有過深刻論述:“所謂‘學術危機,主要是指由于教育史學界對教育史學科的對象、性質以及方法論等基本問題的嚴重的認識偏差以及由于這些偏差而造成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種種不規范乃至非學術化的問題。”并認為“阻礙教育史學科成為一個成熟學科的基本原因主要在于,缺乏包括獨特對象、概念、范疇、原理、方法論和方法在內的相對獨立和完整的學科體系。”[21]因此,要擺脫教育史學的“學術危機”,需要積極借鑒歷史學的理論成果,完善教育史學的理論體系。新文化史學作為一種新的史學范式對傳統教育史學造成一定的沖擊,并逐漸催生出一種新的教育史學范式,這里稱之為“教育文化史”。
教育文化史秉持“人文主義”的教育史觀。我國的教育史學研究具有一定的滯后性,當歷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發生轉變的時候,教育史學卻仍然抱守實證主義史學觀念:強調教育史的客觀性和教育史研究的科學性,認為史料是教育史實的忠實記錄,致力于發掘教育歷史發展的規律。事實上,不僅在“一切都是文化”的新文化史學視域里,教育是一種文化現象,即使在傳統史家眼里,教育也是屬于文化范疇的人類活動。教育歷史具有很強的人文性,而我們長期以來卻以“實證主義”的觀念對待這一飽含人文性的歷史文化現象,無異于緣木求魚。因此,有必要吸收新文化史觀的合理因素對實證主義的教育史學觀進行批判和革新,借鑒新文化史的人文主義史學取向,將學術追求從客觀教育規律的科學主義轉向教育歷史的人文主義。在新文化史學的視域里,教育是一種文化現象,教育史研究并不是要發現或許根本就不存在的教育“史實”及其發展的“規律”,而在于對教育歷史作出文化學的解釋,將教育歷史視為人“創造”的歷史,挖掘人的個體經驗和價值觀念等對教育的塑造作用,即歷史上的人是如何認識和建構他們的教育的。教育文化史秉持人文主義教育史觀,具體而言有以下三方面內涵:第一,辯證對待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歷史決定論,認識到教育的獨立性、能動性及其對社會歷史的塑造作用。第二,改變傳統的客觀主義史料觀,認識到史料的文本屬性,注意對史料的選擇、甄別和解讀,挖掘隱藏在史料背后的主觀意志和時代精神。第三,擺脫“尋找教育歷史發展規律”的研究目的論和“教育史研究服務于當下教育”的研究功能論的束縛,著力發掘教育歷史自身獨特的人文價值。
確定研究對象是任何一項學術研究的首要問題。近年來,關于教育史研究對象的討論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以杜成憲為代表的“二分”教育史研究對象觀,即將教育史研究對象劃分為“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兩個方面。杜成憲認為:“從實質內容方面考察,中國教育史實包含中國教育制度史和中國教育思想史兩大部類。從純粹的教育研究的角度而言,中國教育史研究實難出中國教育制度史和中國教育思想史之范圍。”[22]另一種是以周洪宇為代表的“三分”教育史研究對象觀,即將教育史研究對象劃分為“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活動史”三個方面。周洪宇認為,教育活動史“既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起源,又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存在的前提和基礎,還是連接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中介和橋梁。教育活動史與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構成一種倒三角關系,教育活動史是起源、前提和基礎,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是派生物和結果。沒有教育活動史,就沒有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三者相輔相成,三足鼎立,缺一不可。”[23]“教育活動史”的提出既拓寬了教育史學研究范圍,又提供了一種新的教育史研究范式,是對教育史學的重要貢獻。然而,隨著教育史學觀念的轉變,教育史研究范圍進一步擴大,原有的“三分”教育史研究對象觀已經不能完整地涵蓋教育史的研究對象了。在新文化史的視域下,“教育文化史”成為“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教育活動史”三者之外的教育史研究的新領域,四者共同構成“四分”教育史研究對象觀。作為教育史研究對象的“教育文化史”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教育中的文化現象或文化因素的歷史。如書籍史、教材史、教具史、玩具史、游戲史、兒童史、私塾史、教育技術史、教育空間史、教育語言史、教育符號史、教育隱喻史等等。這些方面因為種種原因被以往的教育史研究所忽略,但卻是教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理應納入教育史研究范圍。二是指教育文化現象背后所隱含的時代教育精神的歷史。以新文化史的觀念和方法來研究教育史,不僅重視對教育文化現象的歷史研究,更注重對教育文化現象背后所隱含的時代教育精神的挖掘,這一點正是傳統教育史學的短板。如對“白話文運動”的研究,教育文化史一方面考察白話文在教育領域的推廣所引起的課程設置、教材編纂、教學方法等“現象”層面的教育變革,另一方面也注重探討白話文與文言文博弈背后所隱含的語言觀念、價值選擇、時代風氣等“意義”層面的文化沖突。“教育文化史”不僅在“現象”層面擴大了教育史學的研究范圍,也在“意義”層面深化了教育史學的研究深度,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拓展了教育史學研究對象。
傳統教育史學在方法論上深受實證主義史學思想的影響,重視史料考證在歷史研究中的價值,甚至將史料考證視為教育史研究的唯一方法。在這一思想的束縛下,傳統教育史學一直存在方法論薄弱的不足,教育史研究也局限于對教育史料的整理和編排的淺表層次。史料誠然是歷史研究的基礎,但史料并不是歷史存在的客觀記錄,其背后隱含著記錄者的主觀意志及其所處時代的時代精神。因此,對史料的解讀不能僅僅局限于傳統史學的考證法,而應將史料視為文本和話語,積極借鑒人類學、語言學、文化學等學科的“深描”、文本分析和話語分析等研究方法,致力于挖掘史料背后的文化因素及其權力運作機制。例如劉云杉的《帝國權力實踐下的教師生活形態:一個私塾教師的生活史研究》,以清末塾師劉大鵬為個案,以其日記《退想齋日記》為主要史料進行文本分析,揭示了科舉制廢除前后中國底層塾師的精神世界,反映出作為制度權力的科舉制與作為文化權力的士紳慣習是如何規訓教師的精神世界的[24]。又如司宏昌的《嵌入村莊的學校:仁村教育的歷史人類學探究》,以一個普通村莊百余年的教育變遷為研究對象,以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和口述史為研究方法,不僅在現象層次勾畫出村落里的教育和學校變遷的微觀個案圖景,更在深層次上回答了教育是如何塑造人的這一“社會公共問題”。“村落之中的兒童是如何變成他們自己的?這是涉及一個龐大群體的疑問。實際上,我不僅想嘗試回答個人精神和理論的困擾,也試圖回答與我有同樣文化和生活經歷的一個群體的生存困擾:他們是如何變成他們自己的,學校和教育在他們的人格、精神和情感的深處究竟留下了什么樣的印跡?這是一個事關數以億計的個體的社會公共問題。”[25]
研究方法不是單純的操作程序,一定的研究方法總是帶有各自獨特的使用原則和操作規范等,因此在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時也要注意相應的使用原則和操作規范等。教育文化史傾向于借鑒人類學、語言學、文化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同時在研究視角、解釋模式等方面也帶有這些學科的特點。在研究視角上,教育文化史主張微觀視角、底層視角和文化視角。微觀視角和底層視角已有學者做過較為充分的論述,此處不再重復。文化視角指從文化學角度解釋教育歷史,即將教育視為一種文化觀念的象征和符號,對于教育史的解釋不再停留于教育表象的描述,而是著重挖掘這一表象所象征的觀念、規范、習俗等價值層面的內涵。如果說微觀視角將教育史學的研究規模從宏觀分析轉向微觀考察,底層視角將教育史學的研究重點從精英人物轉向普通百姓,那么文化視角則是將教育史學的研究取向從現象描述轉向價值探討,這是教育文化史與傳統教育史學的最大不同。在解釋模式上,教育文化史主張意義闡釋。傳統的教育史研究擅長于用線性歷史觀看待教育史,追求教育歷史運動的因果分析,這樣的解釋機制無法解釋教育現象背后的文化內涵。教育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其中的文本、話語、象征、符號等等幾乎無處不在,而其內涵難以用機械的因果關系解釋清楚,必須訴諸于詮釋學的意義闡釋,通過對符號及其背后的隱喻的詮釋來理解其中隱含的價值和意義。
教育文化史的表現方式從實證主義的分析話語轉變為人文主義的敘事話語。學術研究的成果最終要以文本的形式呈現出來,文本的呈現方式并不是隨意的,而是由研究范式決定的。傳統教育史學秉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教育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其發展有一定的規律可循,因此傳統教育史研究的話語方式就在于考證教育歷史事實和證明教育歷史規律,其表現形式也就成了實證主義式的分析論證。這種話語方式預設了一元史觀和后設敘事,將歷史發展過程視為一條有跡可循的因果鏈,強調歷史的必然性和統一性,否定歷史的多樣性,忽視個案和特例的價值。教育文化史質疑了傳統教育史學對教育史的客觀性和統一性的盲從,認為教育史只是文本建構的結果,并不存在客觀的教育史,也沒有一條一以貫之的發展線索,原生態的教育是多元的、地方性的、實踐的,因此教育史的話語方式不再是試圖證實某種一元的假設,而是描述教育歷史的多種樣態并闡釋其特殊的文化意義。“地點、時間及人群組合的特殊性、差異性、偶然性、多元性成了常態,對各種文化體系的解讀也就代替了對前因后果的解釋。”[8](P6)教育文化史在敘事方式上應積極借鑒已比較成熟的新文化史敘事。新文化史的經典敘事作品盡管各具特色,但在敘事方式上也有一些相似之處:以社會下層的日常生活為研究對象;以微觀視角進行小規模考察;豐富詳實的史料和細致入微的分析;深入挖掘各種符號、象征、表象背后的隱喻意義;故事般的情節和文學性的語言等等。以敘事話語進行教育史寫作有其獨特的價值:其一,展現教育歷史的多樣性;其二,貼近實際的教育生活;其三,挖掘教育現象背后的文化意義,加強教育史研究的學術性;其四,敘事語言通俗易懂,可讀性強,有利于擴大教育史受眾。
三、教育文化史的學術價值及其局限
我國史學界在接受西方史學新思想方面向來滯后,教育史學界對西方史學變革的反應更加遲鈍。從1989年林·亨特首次舉起新文化史的大旗到今天已經過去了30多年,新文化史作為一種史學潮流已漸漸退出史學主流地位,但新文化史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史學范式對我國教育史學仍有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它對傳統史學的批判和對新的史學范式的建構啟發了我國教育史學擺脫束縛、開拓創新的路徑。盡管新文化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從一開始人們對它的批判就從未停止過,這些批判促使我們更加客觀地看待新文化史,也為我們合理評價教育文化史提供了參照。
一方面,教育文化史的提出促進了教育史學觀念的更新、教育史學研究范圍的擴展和教育史學理論體系的完善。首先,教育文化史打破了傳統教育史學實證主義史觀一統學界的局面,提出了人文主義的教育史觀,啟發人們重新思考教育歷史的客觀性、史料的真實性、教育歷史與現實的關系、研究主體的主觀性等教育史學基本問題,改變了人們對教育歷史的根本看法。教育史學者都是在一定的教育史學觀念的主導下選擇研究領域、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教育史學觀念的改變從根本上改變了教育史學的學術面貌。其次,教育文化史的提出擴展了教育史學的研究范圍。長期以來我國的教育史學研究局限于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范圍狹隘,內容僵化。近年來雖然出現了教育活動史、教育生活史、教育身體史、教育情感史、教育記憶史等教育史學新領域,但相對于幾乎無所不包的“新文化史”來說仍顯狹隘,況且在西方史學界,身體史、情感史、記憶史本就屬于新文化史的領地。文化的范圍之廣,以至于“要把什么東西說成不是‘文化,反倒變得愈來愈困難了。”[13](P3)在教育文化史的視域里,不僅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活動等是教育文化的一部分,與教育相關的一切符號、象征、表象、記憶、情感等無不是教育文化。在這些教育現象之下,教育文化史還發現了隱藏的教育的時代精神、權力機制、風俗習慣、民間觀念等等,教育史的研究范圍不僅在橫向上得到拓展,在縱向上也得到了加深。最后,教育文化史提供了一種新的教育史學范式,完善了教育史學理論體系。一門學科的理論體系包括對該學科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價值等方面的系統性觀點。傳統教育史學在學科理論體系方面雖然也有一套成熟的觀點,但缺乏對自身理論體系的獨立思考。“長期以來,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一樣,歷史唯物主義取代了對學科自身方法論的思考。……在這種情況下,教育史的研究或者成為用抽象的概念剪裁史實,或者成為對宏觀歷史觀念的注解,或者成為史料的堆砌羅列和史實的陳述。其結果是諸多論著‘千人一面、了無新意。”[21]教育文化史突破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束縛,嘗試性地建構起一套新的教育史學范式,對教育史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價值等都形成自己獨特的看法,對進一步完善教育史學理論體系有一定的貢獻。
另一方面,教育文化史在強調對教育歷史的文化解釋的同時卻忽視了對教育歷史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解釋。這種對教育歷史客觀性的懷疑可能會引起主觀主義的盛行,無所不包而又缺乏中心的研究方法可能會導致教育史的碎片化。首先,教育文化史主張對教育歷史進行文化解釋,忽視了教育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解釋。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能動性,可以對社會、經濟、政治等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教育并不是完全獨立的,不可能脫離一定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而存在,兩者相互依存相互影響。教育文化史在強調教育的文化解釋的同時走向了極端,忽視了教育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解釋。事實上,新文化史學者強調文化的重要性只是一種學術爭論的策略,在他們的學術實踐中社會與文化一直是并重的,甚至很多新文化史學家是以社會史開啟其學術生涯的[26]。因此,教育文化史研究在注重教育史的文化解釋的同時也要兼顧教育史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解釋,不能顧此失彼,陷于片面。其次,教育文化史對教育歷史客觀性的懷疑可能會引起主觀主義的盛行。教育文化史繼承了新文化史對歷史知識性質的看法,否認歷史知識的真實性以及對歷史事實的追尋,認為史料是文本,其背后隱含著權力運作,歷史知識只是一種敘事,歷史與文學沒有本質區別。這種看法有助于我們反思教育史研究中的主觀性問題,但片面強調歷史研究的主觀性而忽視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可能會導致主觀主義的盛行,最終侵蝕歷史學科存在的基礎。史料本身的文本屬性和史料意義闡釋的主觀性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毫無根據地想象和建構歷史。如何平衡歷史研究中的主觀性與客觀性值得我們深思。最后,教育文化史在反對一元史觀的同時可能會導致教育歷史的碎片化。教育文化史反對傳統教育史學的一元史觀和后設敘事,反對將教育歷史的發展軌跡視為一條有跡可循的因果關系鏈,認為教育歷史是多元的、差異的,重視個案和地方性教育經驗的價值。這一觀點有助于教育史研究的多樣化,但過分強調個案和特例的價值而忽視對普遍性教育經驗的總結也有可能引起教育史的碎片化。有價值的學術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個案的細致分析上,還要能以小見大,這就需要在微觀的實例與宏觀的趨勢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單純地強調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
參考文獻
[1] 黃寶權.新文化史視域下教育活動史研究的“三個轉向”[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3):102-105.
[2] 劉京京.教育史學研究的路徑轉向——基于新文化史學的研究視角[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4(19):13-16.
[3] 陳桂香.新文化史學視角下的教育史研究[J].教育評論,2016(03):150-152.
[4] 周采.新文化史與教育史研究[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6(04):12-15.
[5] 曹彥杰.文化轉向:新文化史學對教育史學的方法論啟示[J].大學教育科學,2017(02):104-111.
[6] 郭航.新文化史視域下教育史研究路徑探析[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7(31):15-18.
[7] 諸園.新文化史視角下教育史課程建設[J].安慶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05):121-125.
[8] [美]林·亨特.新文化史[M].姜進,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9] [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M].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47.
[10] 徐浩,侯建新.當代西方史學流派(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11] 周愚文.教育史學研究[M].臺北:國立臺灣師范大學出版中心,2014:153-154.
[12] 楊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學的興起——與劍橋大學彼得.伯克教授座談側記[J].史學理論研究,2001(01):143-151.
[13] [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M].蔡玉輝,譯.楊豫,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4] [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M].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15] [美]喬伊斯·阿普爾比,林恩·亨特,瑪格麗特·雅各布.歷史的真相[M].劉北成,薛絢,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198.
[16 ] 張廣智.西方史學史(第四版)[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407.
[17] [美]達恩頓.屠貓記·法國文化史鉤沉[M].呂健忠,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8] 李悅娥,范宏雅.話語分析[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5.
[19] 張廣智,張廣勇.史學:文化中的文化——西方史學文化的歷程[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344.
[20] [英]勞倫斯·斯通.歷史敘述的復興:對一種新的老歷史的反省[A].古偉瀛,譯.陳恒,耿相新,編.新史學·第4輯·新文化史[C].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21] 張斌賢.教育史研究:“學科危機”抑或“學術危機”[J].教育研究,2012(12):12-17.
[22] 杜成憲.中國教育史學科體系試構[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1997(01):19-26.
[23] 周洪宇.對教育史學若干基本問題的看法[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9(01):5-16.
[24] 劉云杉.帝國權力實踐下的教師生活形態:一個私塾教師的生活史研究[A].丁鋼,主編.中國教育:研究與評論(第3輯)[C].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143-173.
[25] 司洪昌.嵌入村莊的學校:仁村教育的歷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9:03.
[26] 周兵.新文化史:歷史學的“文化轉向”[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257.
Educational Cultural History: A New Paradigm of Educ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ltural History
YANG Wei-dong HU Jin-ping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western historiography had experienced a cultural turn, an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history, which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history and its related subjects. As a branch of history,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cultural history, educational history has gradually formed a new paradigm of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educational cultural history.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culture adheres to the humanistic view of educational history, takes the culture in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tively draws lessons from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anthropology, linguistics, culture and other disciplines, examines history through multi-level perspectives that takes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text and pres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narrative way.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culture history has promoted the renewal of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concept, the expansion of the research scope of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the perfection of educational history theory system. However,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education also emphasized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education while neglecting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education. The uncertainty about the objectivity of educational history may lead to the prevalence of subjectivism, and the collective but lack of central approach may lead to the further division of the educational history.
Key words: cultural turn; new cultural history; educational cultural history; paradigm
(責任編輯 ?陳劍光)
收稿日期:2020-12-24
作者簡介:楊偉東(1991-),男,陜西咸陽人,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教育史研究;胡金平,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21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