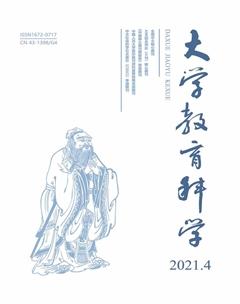教育主體 “成人”的功德
張傳燧
每個人的生活至少會顯現出三個層級,即“前活著”、“活著”和“活著之上”。人,首先是處于最底層的“前活著”階段。在此階段,人處于無意識狀態,是一種僅有植物神經感覺的 “自然律動”,主體只是無意識地調節著各項身體機能,如心率、消化等。生活中,大多數人1/3乃至1/2的時間都是在無意識狀態中度過的,這盡管與動物沒有多少區別,但我們也得視其為人。在這“前活著”時期,不管怎樣,他也應該有自己的權利,更應當受到尊重。其次,才是“活著”的人。“活著”的前提是“謀生”,人們追求個人吃喝拉撒睡的基本要求,以滿足個體的基本需要及生存為最終落腳點,目標就在于簡單的生物性生存。再次,是“活著之上”的人。人不可能僅停留于“謀生”和滿足于“活著”,大多數人會向更高層面靠近。因此,個體都會去主動追求有意義和價值的生活目標,追求自我的幸福生活與發展而成為“活著之上”的人。上述三個階段是順勢順意連接的,有時也有交叉,可以看作是從低到高的三種不同人生境界。與此相應,每個人的主觀感受也可分為三個階段:快樂、愉悅和幸福。初級的快樂是肉體的感覺需求,那是飽、暖、物、欲;愉悅是精神的追求,那是親情、愛情、友情,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以及游走天下;幸福歸于靈魂的享受,那是“活著之上”的信仰,是付出、奉獻、為社會發光發熱,讓他人因為“我”的存在而歡欣。
教育不僅僅是訓練其外在的糊口謀生技能,更重要的是賦予人內在生命的發展力量,讓個體因受過教育而更明了通透,更審慎堅定,更有追尋自由的眼光、思想和能力,從而構筑起自己的生命,創造出一條獨特發展的道路。事實上,受過教育的人既應當是勞動謀生的中堅,還要成為社會道德的種子,更應成為理性思考的精英。對于一個健全社會來講,讓受過教育的人養成高尚的品質且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更為重要。因此,早在2010年,胡弼成教授就在《科學時報》上呼吁“盡快為高校學生開設思維課程”,讓思考能力與積極品質在個體身上獲得培養。
“活著”和“活著之上”的人,兩者之間的“一念之差”是鏈接點。這一念,處在有意與無意、是與否、善與惡、好與壞,言與行、虛與實,乃至幸福與不幸福之間,是人性的流露和文化“成人”的力量,更是人內在精神轉化成外爍行為的中介。教育主體的角色任務就在于將這“一念”的積極正面引導、傳承、傳遞給下一代,使學生主體從人生的一個臺階漸次上升至另一個臺階,將個體縱深的發展性變化貫穿于整個生命各階段不同的歷程。同時,教育主體需要有“德”且“格”,這是愛的表現。人始于愛心、終于良心,教育之愛心、良心須臾不可分離和缺少。教育之“德”緣于愛心,教育之“格”源于良心。愛心是責任感驅使的,良心則是悲憫與正義的結果,它們都不是強制而來的,但都是個體的主動修為(Educating man)。正如胡弼成教授在《城市處境不利者社會流動:教育歸因及補償機制》(中南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第一版)著作中所強調,教育應更多地關注處境不利人群的內在,重視主體的有意義的最佳體現,著力培養以韌性特質為核心的積極品質,賦予其自我實現的心智和能量。
在生存、生活與發展中,教育主體一刻也不能離開且受制于外在大環境的影響,而且,社會環境中的因素是會濡染每個人的,不管是積極因素還是消極因素。因此,教育主體須將積極的元素注入環境,教育才會生成積極的理論與實踐,人類才會生活得更加幸福和有意義。當然,每個人很多時候并不都是幸福的,但教育主體就是要學會“咬定青山不放松”,讓人超越“活著”,去追求“活著之上”、尋找“靈魂安放”的意義與價值。這就是教育主體積極“活著”的價值所在,也是胡弼成教授所傳遞的“成人”之功德所在。
終讀《城市處境不利者社會流動:教育歸因及補償機制》全書,掩卷而思,似懂非懂,恍然喟然,五味雜陳如下:
生命是連續不斷的過程,正如宇宙是過程和聯系的集合體一樣,教育要適應不同生活境遇與生計可能性下的生命成長和一刻也不能終斷的各層級各類發展的需要;人活著必須勇敢地面對世間的一切,哪怕在世事和生活遇到挫折的時候,教育(尤其課程)都要善意地去對待和處置“我和他”的關系,設計好和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教育發展以個體生命為第一前提,不管是什么教育及其管理都必須聚焦人性基礎上人的普遍需要和人類的文明走向;以大教育觀之,教育內各子系統(包括并不限于社區、家庭和學校)相互作用,均需為人發展的各層級服務,其核心內容已然涵蓋教育愛、個體的獨特性以及人性的普遍性;教育主體需要發掘教育的幸福功能,“我活也要讓別人活”,一切為了自己的幸福以及周邊人幸福的未來,乃至全社會的福祉;在每一個社會尤其在教育中,創造條件讓人學會思考、學會腦力勞動、尊重人的個性和發展是社會福祉的開端。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