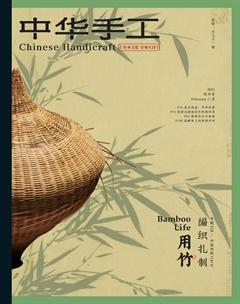戛玉鳴金,聲聲有意
彭一



顧名思義,“金工”,就是“金屬工藝”。
小錘聲聲,鏨刻之間,回響了千年。這門承古融今的技藝,一直是我國手工藝行業中的“重頭戲”。造型飽滿、肌理分明、工藝精細的金工作品熔鑄著金工師的妙心巧思。
而在許多眼里,金屬是冰冷的,只有金工師深知它們柔軟且靈動的另一面。
本次我們聚焦幾位“80后”“90后”金工人,從工藝技法、創作思路、行業理解等維度,展現當代金工創作者的新思路與新視野,傳遞金工技藝的深刻內涵與人文價值。
木紋之金
Q:木紋金是什么?它的工藝有哪些特別的講究?
A:木紋金,是指把顏色不同的金屬錯層累積疊加在一起的金屬材料,通過熔接、鍛打、雕刻、壓片、鍛造等工藝,制作出美麗花紋的金屬工藝技術,最初的成型圖案類似木頭的紋理,所以簡稱為“木紋金”。
木紋金的工藝極其復雜,技術難度較高,是目前最難的金屬工藝之一。如今在中國,只有少數人能熟練掌握。對于木紋金的創造來說,由于金屬的堅硬質地,想讓其融合相交無比困難。每次的制作過程,都好似一場激戰,需要持久的耐心與毅力,而這份執著,正是一位匠人匠心的最好體現。
木紋金的工藝繁復且精細,有著熔料、鍛打、退火、壓片、裁切、找平、粗磨、精磨、熔融、鍛壓、刻花、壓片、裁料、打磨、焊接、著色等20個步驟。每一步都必須準確精細,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一步有差將前功盡棄。
堅硬質地的金屬如最不易馴服的烈馬,想要讓其融合、相交,需要的是千百倍的耐心與毅力。我不停地與這些頑固的金屬們對話、交戰,哪怕是20天、30天只能制一件器物,也依然享受這種潛心制物的過程。
Q:木紋金(或是金工)歷經了哪些歷史演變,具體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
A:關于木紋金的歷史,現在最有力的說法是在日本江戶時代初期(公元1600年左右),經過遣唐使的交流學習,日本秋田縣的鈴木重吉制作的俱利雕刻開啟了木紋金的歷史。
俱利雕刻是參考中國的雕漆工藝中具有代表性的雕刻作品《屈輪·堆朱》(堆朱:中國稱為剔紅工藝)制作的金工作品。中國的《屈輪·堆朱》主要是黑漆和紅漆2種漆的多層交替與重疊,在其表面雕刻出旋渦花紋等錯綜復雜的紋理。
堆朱作品及工藝技術約在公元1192年的日本鐮倉時代傳到了日本。日本工匠在接受并繼承堆朱技巧的同時,由于堆朱作品層次變化的美感使日本工匠們用同樣的工藝方法在金屬材料上得到相近卻又不同的工藝作品,被稱為“木紋金”。
此后,這種工藝在鈴木重吉的發展和傳授下在日本蓬勃發展。但這項工藝技術也并非一般工匠能夠達到,所以流傳下來的金工作品也并不多。
直到18世紀后期,一些木紋金作品以藝術品的形式流傳到歐洲和美洲,木紋金開始被世界所認識。于是,歐洲和美洲對木紋金這種工藝形態的藝術品的需求也隨之增加。而在當時的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武士是禁止佩戴刀的,進而促使一些本土的木紋金工匠受雇于國外的藝術品需求方。而對于國外的很多工匠們來說,這種獨特藝術形式背后的金屬工藝更令他們著迷。
Q:您覺得當代的木紋金作品與傳統的木紋金有哪些根本區別?
A:傳統的木紋金是基礎,現當代的木紋金是創造。
傳統的木紋金作品由于設備和原材料的限制,并沒有多元化的制作和高難度的作品。隨著科技與時代的發展,讓我們擁有了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通過這些載體和新材料能更好地將傳統的木紋金和金屬工藝技術無限地創新與發展。
有了機器的輔助,能讓作品的形制變得更多樣化。機械的輔助可以讓手工藝達不到的精細之處有更好、更完美地體現。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執著”地認為,只有完全的手工制作才稱得上是上乘之作。事實上,能熟練地掌握各項機械操作,并與精湛的手工藝相結合,才是現代手工藝傳承與發展的大方向。
很少人知道,通過上百小時的錘煉,才會誕生一件花紋獨特、造型雅致的木紋金作品。比如一塊1 000克左右的銀磚,經過12萬次以上的錘打之后,才能成為一把銀壺。
如今的生活越來越趨向于快節奏,很少有人愿意花漫長的時間去打造一件器物,越是如此,人們的精神世界會越匱乏。只有讓越來越多的人了解手工制作金屬的過程,知道其中的繁瑣與艱難,才會理解其中的價值。
Q:“姜造”是一個怎樣的品牌?
A:姜造,是一個售賣“藝術生活態度”的品牌。在我的理解中,藝術品的價值不只是供觀賞的物品,它是天、地、人、情交流后的創作。
品牌始于2006年,創始人姜炤和團隊的伙伴們用盡一切氣力,想要傳達金屬工藝的真正價值,以及呈現東方人的生活風格和東方的風土條件。
“姜造”,也是一句呼喚和祝福,是創始人對器物以及其使用者的承諾,希望讓藝術回歸生活,讓好器物相伴人們的一生。
品牌將作品的實用與審美融合于一體,讓器物擁有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屬性,同時也將制造者的內心以及對于藝術的感悟,通過雙手呈現在器物之上,讓每一件作品都自帶溫度。
器說新語
Q:用一件作品來展現您的創作風格,您會推薦什么?
A:我會推薦我早期的金工壺作品——《開源》,作品的靈感源于宋代詩人魏良臣《棲賢山訪戴叔倫隱處》中的“流水自潺潺”。為了更好地表達流水靈動的意境,我運用木紋金的傳統工藝來呈現流水的自然形態。壺身的流水紋路緩慢匯集于壺嘴,用木紋金的特性將銀雕刻成潺潺流水的形狀,銅則是對壺身的“陸地”進行表達。壺蓋上的紋理則用木紋金雕刻出細密的花紋,形如天空,與壺身進行區分。壺鈕用黑白相間的紋理與壺把的黑色、壺嘴的白色進行呼應。整個作品彰顯出自然的肌理,使作品有了一定的生命力。
Q:您認為什么樣的金工作品是受市場青睞的?
A:金工作品大多是面向生活的,比如一把金工壺,我們首先應確保它的基本功能,才能進一步研究其美學呈現。在優先位置的選擇方面,我認為作品的功能性優先于藝術性,而如果作為裝飾的作品,我會把藝術性放在第一位。換言之,作品服務于使用者,而藝術是創作者的一種表達。
兼顧作品功能性與藝術性的同時,還應考慮市場的反饋。市場所青睞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作品的自身定位,當然也包括受眾的年齡、消費水平等諸多因素。如今的時代,是年輕的時代,能打動年輕人的作品,一定是有競爭力的,特別是為“90后”“00后”這一龐大群體。若將作品的趣味性、實用性與藝術性相互協調,或許能得到很好的反饋。
Q:您如何理解“傳統與創新”的內在聯系?
A:傳統,是“制度”;標準,是“習慣”,更是數千年來無數工匠用實踐摸索出來的流程與沉淀下來的經驗。當下,人類工業水平不斷攀升,讓我們的工具有了巨大的發展,工具的創新促使我們的作品得以更好地完成。比如,在金屬器物上鑲嵌寶石,這是金工常見的制作工藝,而通過顯微鏡或其他工具的輔助,作品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傳統金屬工藝就像一根樹干,是創作之根;而創新創作,是不斷萌生的新芽,當然,兩者需相輔相成。
經文生藝
Q:是什么原因讓您選擇金工創作,與“經文”相關的作品又是出于何種想法?
A:繪圖、選料、塑形、鍛造、養色,金工有著它獨特的工藝流程與魅力,因為熱愛,我鉆進了這個領域。手工藝算是一個“魔性的場域”,會讓人陷入其中就無法自拔,有太多可研究與探討的方向。我生活在孔子故里,山東濟寧的曲阜,受當地傳統文化的熏陶,我的金工創作多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靈感。
縱觀我近年來的作品,大多與經文相關。之所以如此,其實是一次在與好友的交流中突發奇想:中國書法是否只能于宣紙上創作?能否有更多的表達形式?金工作品上的經文由此誕生。創作初期,自己喜愛形式感強烈的康熙字典體,后改用行書。在“粗獷”的金屬器物表面“行文”,文字的深刻能更好地表現。
在不斷創作與嘗試中,我感受到文字符號所帶來的獨特情感,以金刻字,同時也是刀筆之下對自身的磨煉。經文的每字每句,皆采用金屬拉花鋸手工制成,僅幾段經文,就需花費半個月的時間,其過程需要創作者具備足夠的耐心與毅力。
Q:在美學方面,您的創作是否有自己的邏輯和原則?
A:創作邏輯的建立,應該是在長期創作過程中思考與復盤中總結出來的,我出生在魯西北的平原之上,四季分明、酷暑寒冬的生活環境造就了北方人粗獷的性格。創作的金工作品,受眾以北方的茶友居多,多合北方茶友的口味,所以也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創作的地域性特征。
而創作的結果,需要美好事物的輸出,在美學的樹立方面,我一直注重內心的感受,以所聞所見形成自己對作品的理解,此外,器物使用者的感受是創作的重點,換句話說,則是“成人達己則為美”。
Q:您對自己未來的創作有哪些期待?
A:我希望能打開創作的思路,多嘗試不同題材的金工作品,讓自己的設計理念更新迭代。因為我所生活的地方是東方圣城,運河之都,這里的儒家文化、運河文化、佛教文化等值得被探索與研究,所以從中汲取創作靈感,是我未來創作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