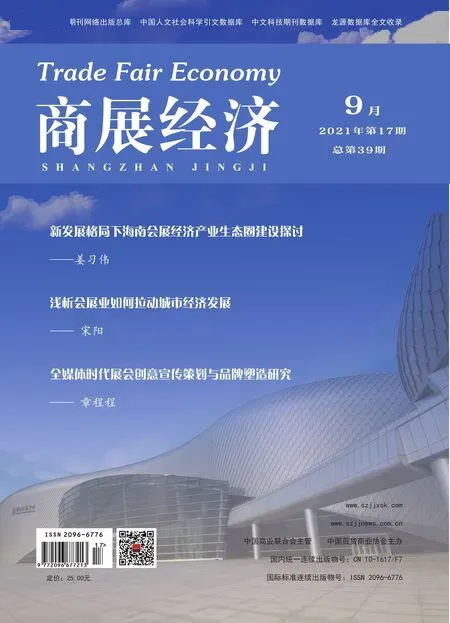全球價值鏈視角下反跨境避稅研究
——基于A跨境企業的案例研究
廣西財經學院 謝建 毛竟宇
跨境企業在全球經濟、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得到了快速發展,成為當前推進世界整體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跨國公司在助力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在積極籌劃全球繳納稅收的最小化[1]。近年來,世界一些著名跨境企業,如谷歌、星巴克、亞馬遜、微軟、蘋果等,依托全球價值鏈策略進行避稅。我國處在全球價值鏈的生產制造環節,且我國針對高新行業的稅率較低,跨境企業在華子公司成為調節各價值環節利潤的“中轉站”,利用無形資產轉讓定價進行利潤分配,并將利潤轉移到低稅率子公司,使得全球稅負最小化,對我國稅收利益造成了嚴重損害[2]。在國際上,BEPS行動計劃基于防止利潤轉移導致稅基侵蝕而制定,強調各主權國家的稅收公平。我國反避稅稅制制定較晚,反避稅制度體系還不夠完善,從制度設計方面到稅收征管方面仍存在較多不足,沒有完全融入國際反避稅原則之中。因此,深入探討我國反跨境避稅實際工作的案例,結合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定位,分析我國稅制層面和征管層面存在的問題,為提升反避稅工作水平與效率,提出征管建議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于全球價值鏈的研究以產業升級為主。陳藝毛等(2019)通過實證方法測算了我國在價值鏈中的地位及趨勢,認為我國由于核心技術的欠缺,處于價值鏈低端環節,出口獲利能力有待提高[3]。由此延伸出的新觀點是在區域內我國要成為全球價值鏈的構建者,控制我國在區域內的貿易地位。余海燕、沈桂龍(2020)認為發達國家通過其在全球的資源配置并結合自身優勢,成為價值鏈的締造者[4]。我國正在積極推動區域內合作,“一帶一路”倡議到中國加入RCEP,可以預期未來我國的全球化進程會進一步加快,各國貿易會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李小平等(2021)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10年的面板數據,檢驗了產業鏈聚集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影響[5]。
基于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國際反跨境企業避稅相關研究也日益增多。國家稅務局課題組(2019)提出價值鏈的復雜多樣導致跨境企業避稅手段豐富多樣,價值鏈管理層面的避稅成為新趨勢[6]。簽訂稅收協定無疑是反避稅的最佳手段。李茂、劉思海(2020)提出中國在未來簽訂修正雙邊稅收協定時,應同時注重來源地和居民的稅收管轄權,做到兩者兼顧[7],使得稅收協定更具有普遍約束力。曾昭孔等(2020)從反避稅的調查、服務與管理形成“三位一體”的格局對完善當下反避稅規則提出建議[8]。
近期反跨境企業避稅研究發展迅速,但仍存在一些問題。研究方向集中在避稅形成原因及經濟效應分析,純理論研究較多但脫離實際,研究發達國家反避稅經驗與我國難以契合。因此反避稅研究不應局限于以單一避稅方式為研究起點,應與全球價值鏈管理模式相結合,從根本上剖析跨境企業避稅問題。
1 全球價值鏈視角下反跨境企業避稅案例分析
1.1 案例簡介
A成立于2002年5月,是世界500強美國A(U.S.)公司的控股公司。2012年5月后成為A(U.S.)間接全資控股,S全資控股(股權結構如下圖1)。截至2012年,A(U.S)公司已在中國大陸建立了40多家獨資及合資企業(其中獨資公司21家),擁有員工6000人,在中國大陸的總投資額逾8億美元,涉及多個行業。

圖1 公司股權結構示意圖
1.2 A公司全球價值鏈避稅手段分析
1.2.1 通過關聯交易轉移利潤
A公司境外關聯銷售對象主要為I和R,累計外關聯銷售金額占關聯銷售總額的85.4%,占公司總交易金額的12.55%。境外關聯銷售金額自2011年度開始逐年增加。但是,隨著境外關聯交易金額的增加,公司獲利能力卻出現了下降趨勢。尤其是2012年是企業享受稅收優惠的最后一年,企業關聯購銷金額猛增,外關聯達到8000余萬元、內關聯達到16000余萬元,在營業收入比2011年增長12.33%的情況下,企業盈利水平卻從2011年的6400多萬元陡降為160多萬元。2013年企業營業收入52594萬元,外關聯銷售金額達到15220萬元,企業盈利水平卻巨虧2474萬元。從2008年享受優惠政策開始,關聯交易額占總交易額的比例明顯增加,從13.6%升至81.38%。調查還發現,公司部分主要產品既有關聯銷售又有非關聯銷售,但非關聯銷售毛利遠遠大于關聯銷售毛利。由此說明A公司與處在銷售環節的I、R公司進行內部關聯交易,將低附加值環節利潤轉移至高附加值環節,以規避稅收。
1.2.2 通過支付高額特許權使用費轉移利潤
根據合同規定,A公司每年要向S支付9.5%的特許權使用費。首先,該企業作為外商獨資企業且處在生產制造環節,向處在研發設計環節的S支付高金額技術使用費,可以達到在所得稅前列支、少繳境內所得稅的目的;其次,未被美國S完全控制的其他兩家合資公司,相對而言獨立性稍強,提取的技術使用費標準分別為2.98%、1%,可作為參照標準,說明其特許權使用費明顯過高;最后,根據稅務部門調查了解,同樣是食品加工業的麥當勞、肯德基、德克士等名牌店提取的特許權使用費均不超5%,日產汽車向日本提取的技術使用費也未超3%。
通過上述價值鏈安排,A公司僅具有生產制造等低附加值能力,集團擁有核心技術及高附加值環節匹配功能的實際掌控權。集團低價采購子公司的產品,并向A公司收取特許權使用費的方式,使高額利潤留在集團內部。
2 我國現行反避稅制度存在問題
2.1 避稅成本過低與處罰力度不足
A公司在被稅務機關立案調查后,實際補繳稅款只占應補繳稅款的30%左右。由此反映出我國現行稅制的不完善致使跨境企業鉆了空擋,在不違反國內法律的情況下選擇避稅而非遵從納稅形式降低成本。處罰成本與惡意避稅成本相差甚遠,給跨境企業帶來充足的避稅動機。
2.2 反避稅效率較低
A公司有充分的避稅嫌疑但在落實中始終給予不了處罰,該案拖了5年之久才結案。現行反避稅主要包括選案、稽查、審理與執行四大環節。首先,現行反避稅征管對稽查工作的體系構成并不理想,稅法的強制性措施在實際執法過程中不能得到很好的展現。其次,我國反避稅工作小組人才缺乏,工作效率難免受到制約。最后,監管方法一般只對事后采取調查措施,對正在經營狀態下的企業缺少動態信息捕獲,預測能力較差,使得反避稅工作脫節,從而對稅務機關反避稅效率產生直接影響。
2.3 稅務機關與跨境企業之間信息不對稱
本案例中稅務機關向美國申請情報交換,但一直沒有收到回復。為了給予A公司充分理由確認不合理避稅行為,稅務機關與多個資源數據庫對比,由于A公司處于高壟斷行業,無相關可比企業,只能在集團內部與相對獨立企業作比較,嚴重影響了反避稅工作的執行。綜合而言,稅務機關對跨境企業的信息不對稱主要源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跨境企業組織結構各不相同,稅務機關無法用某一個標準去度量所有跨境企業的經營狀況;二是跨境企業提供納稅申報資料中的有效信息數量較少,稅務機關無法對跨境企業的所有涉稅信息進行展開調查;三是在當前的征管模式下,稅務工作人員與跨境企業之間沒有形成相對應的合作關系,使得在稅務系統內缺乏對跨境企業的深刻認識及充分了解。
3 關于完善全球價值鏈視角下反避稅制度的建議
3.1 完善反避稅法律
現有國內反避稅法律條文之間聯系不緊密,且對概念定義有所差別。所以亟需一套專門反避稅的法律去統一反避稅工作的各環節執行辦法。在日后反避稅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與修訂中,我國應時刻關注國際反避稅規則走向,立足于我國國情和價值鏈定位,借鑒BEPS行動計劃以實例解釋概念的方式,對具體資產進行分類,明確勞務明細,更好地實現其在我國的立足。
3.2 提高反避稅工作效率
建設反避稅人才庫并設立專門的反避稅機構部門。反避稅工作人員素質直接決定了反避稅工作成效。現有統計表明稅務人員中研究生數量僅占4%,本科生數量僅占13%,招募更多的優秀畢業生并進行專業培訓是建設高素質人才庫的關鍵。同時借鑒發達國家為提高反避稅效率設立反避稅獨立機構,并賦予稽查權利,根據經驗表明,建立獨立部門后的稽查效果有了顯著提升。我國現有的反避稅處不能專精與反避稅稽查工作,且各部門之間人員借調現象嚴重影響了反避稅工作效率。
3.3 積極簽訂稅收情報交換協定
稅收情報交換協定是反BEPS行為的秘鑰。我國目前已與十個國家與地區簽署了稅收情報交換協定,但就目前我國開放程度而言,數量遠遠不足。我國加入BEPS行動計劃,彰顯了我國反跨境避稅的決心,但仍存在稅企信息不對稱問題導致稅基被侵蝕。積極與貿易伙伴簽訂稅收情報交換協定可以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有利于構建公平的稅收環境,從而保護我國稅基。
3.4 構建全球價值鏈反避稅體系
全球價值鏈反避稅體系擁有風險與價值相匹配原則。目前我國價值鏈定位在中低端,特征是跨境企業在我國設立以采購生產制造為主的子公司,且在華子公司呈現出不盈利或微利的局面,利潤被轉移至集團內其他環節子公司。首先,稅務機關不應只關注某一家子公司,應將跨境企業各環節作為一個整體,利用風險與功能價值分析,明確集團內各個環節子公司的功能定位,進一步實行經濟實質審驗;其次,需要對審查價值鏈上各經濟實體的定位是否與事實相符的問題進行具體核實,各環節的利潤與價值是否匹配,避免“導管公司”的出現;最后,要堅持獨立交易原則,審查關聯交易的真實性與合理性,將預約定價安排固定到跨境企業征管體系中,增加我國稅收的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