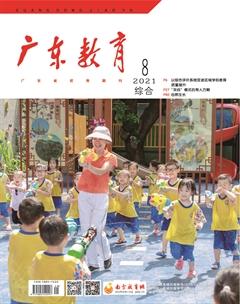教師何以“人微言輕”
謝良梅
教師群體常常會自嘲“人微言輕”,其“潛臺詞”是教師話語權的式微,放置在教育領域觀察,就是教師缺失了對教育實踐活動中的現實、問題以及思考做出真實而具體的表達,并且在表達中反映自己在教育方面的思想、態度、價值觀念等的權力。這本應是教師立身處命的根本,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向。話語權的式微一方面固化了社會大眾對教師日常工作“簡單、機械、無趣、缺乏技術含量”的認知,也降低了一大批優秀人才從事教師行業的意愿;另一方面,教師的形象還呆板地停留在“被道德化”的群體雕刻塑造,一旦有違反了社會對教師的道德預設,就很容易被道德綁架。
造成教師話語困境的原因,其一,是由于學校層級分明的行政化管理模式,讓作為教學主體的教師更多地局限在“參與”的層面,而對于學校內部教學事務的任何方面都沒有最終的決策權,長此以往,教師就習慣于被管理的地位而沒有過多的發言權,教師難免就對學校的管理持冷漠和觀望的態度,看他人表演的“吃瓜”心態造成學校行政與普通教師違和狀態;其二,以分數、獎狀等外在化的評價機制對教師的教學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制約和影響。通過“匯報課”“展示課”“觀摩課”“比賽課”,及其“檢查”“評比”等程序,對教師的教學進行監控和評價,在此過程中,行政管理層甚至引入多重外圍評價,例如學生對教師的表格化的打分來貫徹管理者意志,從而操控教師的教學行為;其三,基于教材教學、學習培訓、職稱評定、考試命題、評優評先等平臺的專家話語霸權高度介入,導致教師再次“被動失聲”。教師逐漸淪為一個只是從事機械性、重復性勞動的平庸者以及被高度體制化的附庸與產物,教師職務的幸福感與使命感不斷下降。其結果是,教育管理者只能迷信行政管理效能,強化各種檢查與評價,以及通過切割“利益蛋糕”的方式來刺激教師的動能。這也就不難理解,頻繁課改中,本是課改主導力量的教師群體,在一次次被邊緣化過程中,喪失了課改的興趣與動力,導致課改效果差強人意,課改難免就淪為文字游戲而落不到實處,最后又只能以考試評價的方式來強硬推行,如此又違背了課改初心。
然而,我們也應看到,教師話語權式微也與其自身主體意識的“覺醒”不足有關,當教師習慣于唯教材是舉、依賴市場上的資料上課、濫用網上下載課件、盲目拿套題訓練,以及用一成不變的眼光看待一屆又一屆學生的時候,教師的教學思想逐步流失,研究能力逐步下降,職業高度與寬度逐步窄化。隨著網絡信息的發展,教師會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駕馭課堂,最后只能訴諸話語暴力達到強硬灌輸、樹立自身職業尊嚴的目的。這無疑加劇了教學沖突、師生對立。或許,對于一些教師而言,話語權的式微并非是致命性的職業漏洞,只要有考試與分數這個工具在,簡單機械毫無創意的教學工作就有市場,這是一種可怕的認知。
因此,要做好教育、做清醒的教育就應切實地發揮教師動能,注重教師話語權的回歸與重塑。首先,尊重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的主導地位,充分信任教師在教育教學中的主體性。值得注意的是管理思維在教育管理中的過度滲透,管理思維強調影響力與控制力,教育思維則著重于尊重差異、強調多元、追求合適教育,兩者有著天然差別。然而,教育管理者若在上媒體頭條、圈粉造粉、借位借勢、人脈營造上“用力過猛”,在強化學校管理的維穩上過度,在依賴行政手段解決一切教育問題上過分,教育中的問題難免會放大。因此,“簡政放權”應作為學校教學改革的重大舉措,真正實現“行政的歸行政,教學的歸教學”,理清各自的責任與義務,行政管理者不能過度扮演教書育人權威者與評判者,而應讓教師真正擁有獨立的話語權,自由地表達自己內心真實的聲音。其次,專家學者應與教師平等對話。現在有些專家與教育教學第一線相距甚遠,卻偏好利用體制給予的“地位”,居高臨下地強勢推行自己的話語,單線傳輸并不見得能“以理服人”,在某種程度上說,專家與一線教師應該是專業成長的共同體。再者,教師要有職業信仰,秉持正確教育價值理念,主動去建構屬于自己的話語體系,并利用各種平臺發出自己的聲音,在此過程中,多學習、多研究、多思考、多寫作應是教師教學的常態,在課堂上,教師要摒棄權威化、絕對化、單線性的粗暴話語,主動與學生搭建一個平等協商并富有邏輯力、生命力的對話平臺,與學生共同成長,構建屬于自己的教與學共同體,共同營造教育教學中的良性生態鏈。
本欄責任編輯?黃博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