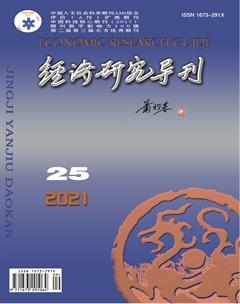“一帶一路”背景下重慶與東盟經貿合作路徑研究
張燦
摘 要:近年來,重慶與東盟雙邊貿易與投資合作增長迅速,“一帶一路”背景下“中新互聯互通項目”“陸海貿易新通道”、沿線基礎設施建設為雙邊經貿合作帶來了全新機遇,但當前仍存在雙邊經貿合作仍面臨競爭突出,合作區域不平衡、通道運輸瓶頸制約、通關效率低、周邊省份競爭激烈等諸多挑戰。要充分利用“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新機遇,應從擴大貿易規模、拓寬產業合作領域、深化產業合作層次、加快完善物流通道建設等方面,促進重慶與東盟經貿合作的提質升級。
關鍵詞:“一帶一路”;重慶;東盟;經貿合作
中圖分類號:F114?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1)25-0133-03
一、“一帶一路”背景下重慶與東盟經貿合作現狀
(一)雙邊貿易呈波動式增長趨勢
重慶與東盟的雙邊貿易在2010年自貿區全面建成后迅速增長,2010年重慶與東盟雙邊進出口貿易總額14.59億美元,同比增長70.47%,2011年雙邊貿易45.88億美元,同比增長214.39%,此后持續保持增長并在2014年出現最大值,達189.55億美元,約為自貿區建成之初的13倍,東盟首次超過歐盟,成為重慶第一大貿易伙伴。在2015—2018年間雙邊貿易有所回落,呈現波動式變化,但整體呈現增長態勢。2019年東盟取代歐盟成為重慶第一大外貿合作伙伴,雙邊貿易額達157.53億美元,同比增長43.2.1%,占重慶對外貿易總值約19%,在重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外貿總值中占比達68.1%。
(二)貿易伙伴、商品結構相對集中
重慶與東盟國家在貿易地理結構上相對集中,2019年重慶與東盟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為越南(占比約30.22%)、馬來西亞(占比約28.22%)、泰國(占比約15.12%)、新加坡(占比約9.52%)、印度尼西亞(占比約6.98%),前五大伙伴的進出口總值約占了重慶與東盟進出口總值的90%,而與老撾、文萊的雙邊貿易交往甚少。同時,雙邊進出口商品較集中于制成品領域,重慶對東盟出口主要有電子信息產品、金屬制品、塑料制品等,重慶從東盟進口的產品主要有集成電路、計算機硬盤驅動器、儀器儀表、天然橡膠與合成橡膠混合物等。
(三)雙邊互動投資,重點國別深入合作
截至2019年年底,重慶實際利用東盟國家外資累計達到118.62億美元,對東盟國家累計備案投資企業113家,投資主要流向新加坡、越南,涉及汽車制造、工程技術等行業領域;同期承接東盟國家服務外包業務執行額2.68億美元。依托中新互聯互通項目,重慶與東盟重點國家新加坡展開深入合作,如在重點合作領域金融服務方面,通過中新示范項目實現的跨境融資逾42億美元,融資成本低于國內約1.4個百分點,為西部企業解決融資難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渠道,雙方通過合作創新推出多項銀行、保險業跨境金融產品。
二、“一帶一路”背景下重慶與東盟經貿合作的機遇
(一)“中新互聯互通項目”助力經貿合作提質升級
2015年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范項目(簡稱“中新互聯互通項目”)落戶重慶,重慶與新加坡重點推進在金融服務、航空產業、交通物流、信息通信等現代服務經濟領域的合作。目前在融資項目、航空合作、智慧物流、大數據通道、醫療合作等方面已取得顯著成效。依托中新互聯互通項目,重慶將進一步探索與東盟其他國家的經貿合作機遇,提升經貿合作水平。
(二)“陸海貿易新通道”凸顯物流中樞地位
“陸海貿易新通道”的建設與發展誕生了更加經濟、便捷的南向出海通道,重慶至東盟國家主要港口的貨物運輸時間從傳統江海聯運的30天左右,縮短至7—10天,全程提速15—20天,國內段的運輸時間可節約10—13天,極大地降低了交易的經濟成本。除鐵海聯運外,依托與東南亞國家的公路干線、鐵路干線形成了跨境公路運輸、國際鐵路聯運多種物流組織形式,為重慶與東盟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投資、旅游等合作提供了便捷的物流支撐。
(三)基礎設施建設助推經貿合作空間升級
《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提出將基礎設施建設、交通物流等領域作為優先發展目標,這與當前西部省份共同參與加快推進“陸海新通道”建設高度契合。東盟國家基礎設施水平差異巨大,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的基礎設施較為發達,而其他國家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老撾、柬埔寨鐵路匱乏,交通狀況亟須改善,越南、老撾電力能源供給不足,供給設施落后,部分國家通訊能力也亟須提升。重慶可充分發揮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產能優勢,與東盟國家積極主動地開展基礎設施產業方面的合作,深化經貿合作層次。
三、“一帶一路”背景下重慶與東盟經貿合作面臨的問題
(一)雙邊貿易競爭突出,合作區域凸顯不平衡
基于類似資源稟賦及工業化演進路徑,重慶與東盟國家的出口貿易結構競爭性突出,機電產品、賤金屬及制品、化工產品、機械設備及零部件、運輸設備等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產品均是雙方出口第三方市場的主要商品,且出口地理方向均以美國、歐盟、東盟等國家或地區為主,雙邊貿易存在同質競爭現象,出口結構的類似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雙邊經貿合作空間的拓展。同時,重慶與東盟國家的雙邊貿易中也凸顯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貿易主要集中在馬來西亞、泰國、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五國,2019年的占比接近東盟十國的90%,而與老撾、文萊幾乎無貿易往來。
(二)通道運輸瓶頸制約,通關便利化有待提升
“陸海貿易新通道”自正式運營以來,運行班列不斷增加,輻射帶動效應也不斷擴大。但其龐大性、系統性、復雜性也逐漸凸顯出諸多的困境與不足。一是沿線基礎設施薄弱,國內段南昆、南防、欽北等西南鐵路由于修建年限較早,運能不足,不能滿足通道運行后迅速增長的貨物運輸需求;主要出海港口欽州港航線較少、物流成本偏高,有效產業支撐不足,導致綜合競爭能力不強;國外段東南亞國家鐵路軌道普遍采用窄軌,出境貨物需要在邊境卸車或通過變軌來實現,無形中增加了貨物的運輸成本。二是沿線統籌協調困難,省際合作不暢,各國海關制度不一,便利化水平亟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