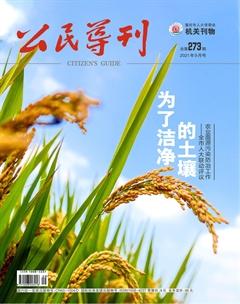新中國民族法制建設歷程
劉玲
2021年8月27日至28日,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回顧黨的百年歷程,黨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回顧走過的歷程,在我國民族地區經濟社會蓬勃發展的進程中,民族法制建設也大踏步前進,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這棵參天大樹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民族法制建設伴隨著我國民族事務治理的法治化進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承載著不同的歷史任務,在新時期更展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梳理民族法制建設的歷史進程,展現成就、展望未來,有利于在法制框架下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障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權,依法保障少數民族平等權利與合法權益,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務能力。
民族法制建設的初步創立時期(1949-1953年)
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正式確立于1954年,在之前,由全國政協代行國家權力。這一時期的立法,從中央到地方的多級主體均或多或少享有立法權。中央一級,享有立法權的主體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政務院。地方一級,享有地方立法權的主體包括大行政區的人民政府委員會、省人民政府、直轄市、大行政區轄市和省轄市的人民政府、縣人民政府,以及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
這一時期,關于民族方面的立法首先是1949年制定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共同綱領》規定了新中國在成立初期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民族、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在僅有的七章篇幅中,單列“民族政策”一章,并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這是憲法性法律文件對民族區域自治的最初確認,構成了新中國民族立法的法律基礎。
其次,這一時期還出現了關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專門法律。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準了政務院125次政務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以下簡稱《實施綱要》)。《實施綱要》是對《共同綱領》原則規定的具體化,對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做出了具體而全面的規定。
此外,這一時期由政務院出臺的一系列的指示、決定和命令,對于民族工作的法制化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相關的規范性文件有:1950年11月24日通過的《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試行方案》和《籌辦中央民族學院試行方案》、1951年2月5日《關于民族事務的幾項決定》、1951年5月16日《關于處理帶有歧視或侮辱少數民族性質的稱謂、地名、碑碣、匾聯的指示》、1952年2月22日《關于地方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實施辦法的決定》和《關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數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權利的決定》、1952年2月23日《各級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試行組織通則》、1952年4月16日《關于建立民族教育行政機構的決定》等。
在地方,也普遍存在著立法實踐。這一階段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多集中于民族自治地方成立時通過的組織條例和施政綱領,還有個別變通執行法律的規定。
總之,這一階段的民族法制建設以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這一重要政策與政治制度,為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奠定法制基礎;確認了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權利和自治權利,充分保障少數民族當家做主的權利;著重改善民族關系,為消除隔閡與加強團結提供法制保障。
民族法制建設的曲折發展時期(1954-1978年)
從1954年憲法(以下簡稱“五四憲法”)頒布到1979年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前,立法權基本集中在全國人大,除民族自治地方外,國家行政機關和其他地方權力機關均不享有立法職權。
在國家立法層面,“五四憲法”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規定,進一步明確了這一制度的基本內容,對自治機關的自治權進行了具體規定。
就地方立法而言,“五四憲法”取消了一般地方的法令、條例或單行法規擬定權,僅保留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立法權,因此這一階段的地方立法實踐實際上成為了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實踐。
這一時期的立法雖然經歷了一些曲折,但是既有五四憲法的奠基之作,又有民族自治地方組織立法與選舉立法的補充舉措,前者成為1982年憲法的重要基礎,后者有力地促進了民族自治地方各級國家機關的組織制度化,而且為后期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積累了寶貴經驗。
民族法制建設的加速發展時期(1979-2011年)
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以下簡稱《地方組織法》),明確規定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享有地方性法規制定權。1982年憲法(以下簡稱“八二憲法”)奠定了中央與地方分享立法權限的根本法基礎,確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共同行使國家立法權,國務院行使行政法規制定權,并確定了國家立法權、行政法規制定權、地方性法規制定權、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制定權的劃分、歸屬及其相互關系。1986年修改的《地方組織法》,將地方性法規制定權擴大到省級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2000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對我國的立法體制進行了確認。
自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加強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制建設”的要求之后,我國民族法制建設進入了快車道。這一時期的國家立法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憲法關于民族問題的規定更加健全與完善。“八二憲法”重申了“五四憲法”的民族平等與民族團結的重要原則,明確了民族區域自治的內涵,擴大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機關自治權的范圍,將各民族共同繁榮和發展民族自治地方經濟文化事業擺在突出位置,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關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專門法律法規積極應對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數民族的發展訴求。1984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以下簡稱《民族區域自治法》)是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制度的基本法律,以憲法為依據,對民族區域自治進行了全面的規定,正確規定了民族自治地方與國家的關系、民族自治地方內的民族關系、自治機關的自治權,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更加趨于完善。2001年修改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進一步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重大舉措。這次修改著眼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實際,對于加大對民族自治地方的投入、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發展做出了新規定。2005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以規范上級國家機關對民族自治地方的幫助扶持責任為重要著力點,旨在幫助民族自治地方解決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從地方立法來看,由于立法主體范圍的擴大,各個行政層級的立法出現井噴現象。其中對民族區域自治法律法規的實施性立法較為集中,有13個省市發布了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若干規定,14個省市發布了散居少數民族工作條例(民族鄉工作條例或城市民族工作條例),還有一些省市發布了清真食品管理條例或規定。
民族法制建設的創新發展時期(2012年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民族事務治理的法制化,更加強調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推進民族工作,在創新推進民族工作的同時,民族法制建設也呈現出創新發展的特點。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行戰略部署,并將“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法治化”的重要保障之一,從而將中國的民族法制建設推進到新的歷史階段。
2015年3月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自治州的人大和政府可以行使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的制定權。這不僅意味著民族自治州可以享有地方立法權,也為城市少數民族權益保障以及城市民族行政建構(如民族鎮、城市民族區)和社會結構(如城市互嵌型社區等)的建設和完善提供充足的法治空間。
2015年6月,國家民委、公安部聯合發布《中國公民民族成份登記管理辦法》,這是我國第一個專門規范公民民族成份登記管理的部門規章,是民族事務法治化取得的新成果。其他民族方面的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也大量出臺,民族事務治理體系日益完善,治理能力日益提高。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2010年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和國家民委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的意見》之后,為創新民族團結工作,國家民委于2014年制發了《關于推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進機關、企業、社區、鄉鎮、學校、寺廟的實施意見》,為有效發揮創建活動“主陣地、主渠道”的作用提供了直接的指導。在這之前,2009年和2010年新疆和云南迪慶州分別制定《民族團結教育條例》和《民族團結進步條例》,開民族團結地方立法先河。2012年以來,以民族團結命名的立法共12件,這些立法實踐是應對統一多民族國家建設的需要,用法律來保障民族團結,建立常態化、法治化的民族團結工作機制,成為新時代民族法制建設的一大亮點。
2018年3月11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更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寫入憲法,為新時代維護祖國統一、促進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憲法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