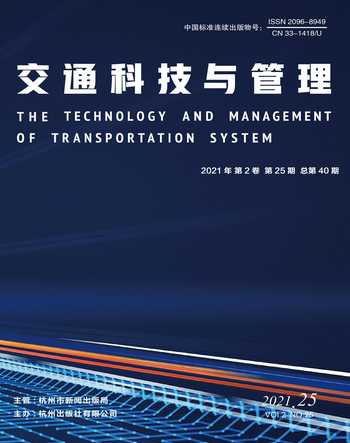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中的應用研究
高進

摘 要:處于我國市場經濟穩定增收的良好時代大背景中,受我國科技領域健康發展的有效助推,“智能船舶”這一先進性產物應運而生。將智能船舶深度融合于我國海事監管作業中,其則可根據指令任務自主規劃出契合時下船舶安全運行、環保、節能等要求的最佳工作方案,為控制人員提供決策參考。為最大化彰顯智能船舶的實際應用價值,領域工作人員應立足當前智能船舶發展實況,深挖智能船舶應用在海事監管作業中的深遠影響,策劃出強化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中應用實效的可行性措施方法。促進智能船舶日趨完善成熟,保證我國海事監管作業落實質量能夠高度契合預期設想。
關鍵詞:智能船舶;海事監管;應用
“海事監管”的實質屬性簡單來講就是海事機構遵照國家出臺的統一性法律規定,對船舶及其運行實況能否符合有關條例的檢查管理作業,其突出性特征為“人為干預”。能夠預見,處于智能航運這一航海領域發展主流浪潮中,智能船舶與監管作業的密切融合性將逐漸升高,船舶特有的優點功能、性能的表現將日益全面。對此,我國海事監管領域將智能船舶合理引用于日常作業中,可通過充分發揮其自身持有的眾多積極性應用價值跨越加強監管作業落實的綜合成效。確保航運中現存的各類不良問題可得到實時捕捉、高效處理,助力我國海事監管領域在智能航運大環境中可穩步發展。
1 智能船舶的發展
1.1 智能船舶的概念定義
2015年,我國船級社通過《智能船舶規范》明確規范了“智能船舶”的概念定義,即將遠程傳感、移動通訊、物聯網、物聯網、云端等前沿性信息技術科學整合于傳統船舶,增設其自動感知能力保障船舶的本體運行、海洋環境、港口等多項方面的信息數據能夠及時、精準的采集獲取。并利用計算機設備裝置及程序技術、自動控制及大數據技術實現對現有數據資源的客觀分析,將船舶安全運行、航行管理、運檢養護等工作實現智能化控制的先進性船舶。另外,《智能船舶規范》同樣將智能船舶獨有的功能清晰劃定為智能船體、智能運行、智能船艙、智能能效控制、智能集成系統等細化內容。為將這些功能切實實現以及不斷完善優化,智能船舶合理運用了信息感知、通信導航、能效管理、航線策劃、運行狀態動態監測、故障自檢診斷、應急預警救助、自主航行等當今較為先進的實用性技術。
1.2 智能船舶的發展現況
“IMO”海上委員會這一官方組織在專屬會議中,通過多方集中討論將智能船舶細化定義為“配有自動系統與智能輔助決策的現代化船舶”、“具有在船船員的遠程遙控船舶”、“無船員在船的遠程遙控船舶”以及“完全自主化的船舶”這四個不同等級。現階段,智能船舶仍處于起步的全面探索階段中,并以西方提出的研究論點為代表。2014年,英國“羅羅公司”正式牽頭發起“AAWA”智能船舶實踐應用項目,此項目將“船舶的無人駕駛”設定為核心目標,計劃發展到2020年基本實現遠程船舶操控從而減少所需要的船員數量,2025年初步實現近程航海區域內船舶的遠程操控,2030年將遠海航區的遠程控制船舶任務全面實現,2035年則徹底實現無人船舶。同時,歐盟也跟進了“MUNIN”計劃。旨在實驗佐證智能船舶自動航行及“無人船”應用的可能性,以及分析與其有關的現代技術引用標準,為法規條例的完善修正提供科學依據。計劃于2034年前,逐一達成無人船創新研制、優化與自主運行可行性的研究目標[1]。
歐盟推出的“Autonomous”自主集裝箱船的遠程操控及自主運行這一試點項目,整合了全自主、自動的離泊與裝卸功能。如圖1所示。
如今,我國針對智能船舶的深度研究也駛進了快車道。2017年年末,在我國承辦的國際海事會展中,展出了凈重38 800噸的全球第一艘智能商船“iDolphin”散貨船“大智”。此船也是以我國“CCS”船級社所設計的建造標準為主的首艘智能船舶,并已申請“CCS”符號“I-SHIP(N、M、I、E)”的智能船舶[2]。2018年年初,上海正式成立了無人貨船專屬開發的聯盟組織。據同年2月份《廣州日報》的新聞報道,珠海萬山建設了總面積225平方海里左右的無人船實踐實驗場,專用于智能船舶的全自動駕駛與應急避障等多樣海事技術的測試。此試驗場由珠海政府部門、我國“CCS”船級社、云州科技與武漢理工這兩所高校協同開發設立,為我國無人航運指明了持續發展的科學道路。
據上述分析,當前各國針對智能船舶的分析研究正處于“配置自動系統與智能輔助決策的海運船舶”向“持有少量船員的遠程遙感船舶”的過渡邁進階段,創新研制著小型智能貨船與特殊專用的“艇”的“可遠程操控且無需船員在船”的形式體系。但智能船舶的商業化用途還需依賴于我國智能航路的規劃發展與岸基控制基地的健全建設。然而,海事監管領域工作人員可將智能船舶應用于日常監管任務執行中,有益于海事監管綜合成效的穩步增長。
2 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中的影響
智能船舶實質屬性為高度自動、智能化,能夠對海事監管工作執行自主決策。科學應用智能船舶的多樣功能、性能,將對我國海事監管領域的長足進步起到深遠影響。
2.1 船舶配員
船舶在新時代下的智能化發展,將驅動船舶需配置的船員資源實現大幅減少,一些智能船舶甚至無需船員在船即可自動執行指令任務。此外,由于智能船舶持有的自動、自主化特性,“在船船員”同樣并非為傳統理念中的實際人員,而是航海與電氣機電的技能操作,備于應急使用,以及由現代互聯網、人工智能操控的前沿技能。而為了確保船舶能夠正常履行海事監管職責責任,科學、及時的處置船舶行進中的突發事項,則需加強岸基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性及操控人員的綜合素養。對此,智能船舶的控制對象應由以往船舶本體運行現況轉變為遠程操控的執行與保障性岸基設施、人員的現有情況,需優化調整船舶配員基本準則及與“船——岸”人員的根本適任要求。
2.2 設備監管
智能船舶內設配有可靠、智能的推動裝置與互相配套的輔助裝置、智能駕駛及制動系統等,因此其整體安全性能可明顯高出普通船舶,且污染排放量及運行所需的能源資源更少,應用價值更高。然而因智能船舶引用的大數據、移動通信、智能遙感、自動控制等先進性技術較為多元,所以其需承受較高的遭遇黑客攻擊的隱患風險,且這些后果嚴重。對此,智能船舶信息化裝置的安全運行監管將至關重要。不僅需嚴格管控設備、裝置等硬件設施,還應對數據資源、網絡安全等軟件程序、裝置加以著重管理。
2.3 防污染監管
因智能船舶并不需要過多的人為操作,且承載了“LNG”與電力等新型能源。所以,即使沿用傳統能源驅動智能船舶運行,但隨其衍生出的含油污水、排放尾氣等污染物皆通過了先進性處理系統完成了廢棄垃圾物的充分收集與高效處理。將這些系統注重維持于穩定運行中,則可將智能船舶的污染物排放精準控制在標準范圍內[3]。而對于需持有部分船員的智能船舶來講,船員日常產出的生活垃圾同樣可施以在船處理,或在統一收集后運往港岸處理。因此,針對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作業中的污染問題,僅需單一性的對其處理污染物的系統設施加以遠程監控,當其突發運行故障后則可采用智能應急處理。
2.4 監管人員適任能力
因智能船舶的設計、制造深度運用了各類專業學科及領域行業的最新型科研成果,如精密、高強度、耐磨損、耐腐蝕的機械及云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促進船舶內部各設備裝置均持有先進、復雜、現代化等特點,且這些設備裝置能夠搭載物聯網技術實現“互通互聯”,可將船舶有機構建為完整性較強的整體,并與岸基控制基地、附近環境展開實時互動。對此,僅將船舶安檢人員的適任能力設定為職業素養評價標準,將難以對智能船舶統籌開展科學性的安全檢查。
2.5 通航保障及海上搜救
因操控智能船舶需在深度分析、客觀判斷其智能化的基礎上,高度依賴與其配套成立的岸基控制中心。所以,在“無人”或“有人”這兩種船舶形式共同兼具的通航大環境中,以往主管機關慣于使用的通航保障策略措施將難以契合使用。尤其是智能船舶實行試航作業時,為其創設出怎樣的海上通航環境與突發意外的應急處置方法,均需重新定位考量。
3 加強海事監管中智能船舶應用的對策建議
智能船舶在新時期中的研制誕生與興起發展,對我國海事監管領域的長遠發展帶來了有力驅動。為保證智能船舶在日常海事監管作業中的正當性、合理性,充分迎合智能航運時代的到來,海事監管領域可參考以下幾點作業方法。
3.1 密切跟蹤——積極參與
海事監管機構應重點聚焦領域內對智能船舶應用明確提出的前沿性理論指導,有機整合領域信息與監管作業現實需要,積極參加“IMO”這一權威層次的智能船舶應用準則、規定的制定優化。發出中國聲音,實現智能航運日后發展方向、趨勢的主導引領[4]。
現行的“船舶安全準則”與“海上防污染公約”在統一制定中,均特設了“等效替代”的條款規定。然而怎樣具體踐行等效代替,還需主管機關進行細則策劃與貫徹實施。例如“SOLAS”公約與“MARPOL”公約的第五條約定等。因此,海事機構應帶頭開展智能船舶應用所需打破的公約條例,將等效事項或等效規定實現明確規劃。如智能船舶的應急避碰需依托通信設備、無線電遙感等裝置,但其避碰使用的號型、號燈等怎樣加以等效替代;對于船員較少的智能船舶來講,怎樣利用救生衣等個人救生設施對應等效救生艇等大型集體救生裝置等。主管機關應對這類替代性部署及設計,在系統程序、機制制度等多方面予以特殊保障,以前瞻視域完成超前設置,并注重規定規則的合規性、可行性。
站在智能船舶培元角度考量,應嘗試摸索突破“最低配員”約束的科學路徑,重新定義在船船員的崗位職務與適任要求。例如通過“雙證培訓”的定期開展,確保智能船舶船長、駕駛員均可持有豐厚的機電常識儲備。其中,船員職務可分為船長及助理船長,期間過渡可設置機電長與助理機電長等崗位。并以安全等效作為資源合規配置的根本落腳點,增設岸基控制人員的行為準則、適任標準與配置規定。例如一等、二等操控員等。且應保證這些岸基控制人員中擁有遠洋船長,至少也應有等效資歷。
3.2 專家護航——保證安全
因智能船舶具備的復雜化特點與“船——岸”一體化的作業模式,普通海事監管人員在依靠智能船舶開展日常監管作業時,通常難以精準鑒定船舶現存的運行安全及污染排放方面的問題隱患,導致常規的船舶按鍵作業難以充分發揮價值作用。對此,為保證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工作中的安全監督合法性職責能夠正當履行,應考慮將領域專家推出的評估制度引進其中,對船舶的設備裝置、系統程序的運轉可靠性與信息網絡的安全性進行專業評估,出示測評報告。并將這一報告結果設定為優化船舶運行效果的科學憑據[5]。此外,因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作業中需承擔起的職能義務與普通船舶的作業要求差異性較大。為彰顯智能船舶在監管作業中的積極性優勢,領域人員應在在船人員等級分類的前提下,挑選出部分高素質人員加以智能船舶的操作技能、運行維護等核心主題的專業培訓,保障其可純熟掌握實效性船舶控制技巧,高質履行監管職務權利。
3.3 開放兼容——支持發展
智能船舶需承載大數據、互聯網、移動通訊等前沿性信息技術的有力輔佐實現穩定發展。對此,應圍繞智能船舶設計規劃出標準統一的數據技術、信息交換等作業指標,不斷強化信息資源數據的總統安全性。另外,由于海事監管作業是智能船舶日常運行的重點項目之一。因此,需站在當下智能航運的發展大趨勢的制高點展開系列合規性監管工作。在推進智能海事統籌建設進程中,應以嚴謹、開放、合法等關鍵要素為著力點,科學策劃出智能船舶、在船船員、岸基控制人員等因子的靜態、動態兩種的數據標準與監管指標,確保數據資源的統一收集、安全儲備與實時共享傳輸,保證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領域中的健康發展與我國智能海事的健全建設可構建出相得益彰、相互促進的良好格局。
3.4 尋找支點——展示作為
由于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作業中的自動化、自主性特點較為突出,能夠實現“少人化”或是“無人化”發展,其設備裝置、系統程序的安全運轉狀態需依靠岸基設施完成遠程感知與及時交互。傳統管理模式無法匹配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中的作業狀態,使得現有海事監管機制的實效性正逐步淡化。對此,可圍繞現行的“VST”主導的智能海事管理規程展開智能船舶及其配套岸基控制基地新型監管體系的規劃制定,確保二者信息傳遞共享的及時性,驅動控制基地能夠接收到時下智能船舶的多項技術數值參數與運行情況。保證船舶突發異常事件或控制基提出命令請求后,能夠及時提供正確性海事協助或海上搜救,助力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領域內的穩定發展,切實體現出海事作為。
3.5 放眼未來——制度保障
智能船舶內含的大量先進技術,實現了對以往“船”、“船員”為核心的監管機制的深刻改變,需重新以高自主化、智能化、“船——岸”一體化的新型船舶體系為管理對象[6]。因此,為保證智能船舶在日常海事監管作業中可充分發揮自身實際效用。需成立智能船舶專屬管理小組,實時追蹤國內、外智能船舶目前的綜合發展實況,創新智能船舶專項“船與岸”的運行安全與污染排放方面的規范性標準,不斷拓展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中的服務功能與提高服務品質。
4 結語
綜上所述,基于我國社會發展良好新形勢下,智能船舶在我國科技領域創新發展的驅動下得到了設計誕生與健康發展。雖然我國智能船舶在海事監管領域的引用時間不長,仍處于最佳應用路徑的科學探尋狀態中。但因智能船舶近年來發展勢頭的日趨迅猛,海事領域應深層次介入其中,全方位探尋其高度契合我國海事監管現況的實效性船舶應用方法,高效完成頂層設計工作。確保我國海事部門能夠在智能航運時代中多角度發揮自身職能義務,助力我國海事監管領域能夠早入收獲發展新成就,提升我國在國際層面中的核心競爭實力,促進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
參考文獻:
[1]何淼,賀益雄,賈相閣,等.新規則下適應復雜形勢的航海技術專業改革[J].交通企業管理,2021(3):98-100.
[2]吳恭興,王凌超,鄭劍,等.考慮復雜氣象變化的智能船舶動態航線規劃方法[J].上海海事大學學報,2021(1):1-6+12.
[3]張笛,趙銀祥,崔一帆,等.智能船舶的研究現狀可視化分析與發展趨勢[J].交通信息與安全,2021(1):7-16+34.
[4]王遠淵,劉佳侖,馬楓,等.智能船舶遠程駕駛控制技術研究現狀與趨勢[J].中國艦船研究,2021(1):18-31.
[5]呂紅光,裴天琪,尹勇,等.智能船舶背景下《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的修正[J].上海海事大學學報,2020(4):117-124.
[6]許凱瑋,張海華,顏開,等.智能船舶海上試驗場建設現狀及發展趨勢[J].艦船科學技術,2020(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