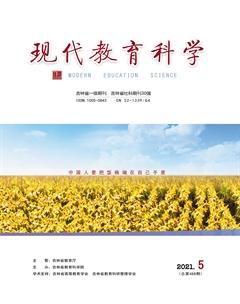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的構建與實踐探索
王利鋒 楊振明 丁洪浩 梅士偉 馬利凱
[摘 要]涉農綜合性大學是高等農業教育發展和高層次農業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國家啟動新農科建設后,綜合性大學如何推進新農科建設,需要理論層面的思考與實踐層面的探索。在理論層面,組織運行機制、結構優化機制與綜合保障機制構成新農科建設機制的主體框架,學科發展理論、機制設計理論、定位理論為新農科建設機制構建提供了理論支撐,國家“四新”建設與新農科建設“三部曲”為新農科建設機制構建提供了政策依據。本文以吉林大學為例,在深入分析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面臨的挑戰與優勢基礎上,從頂層設計、學科交叉、專業優化、科教融合、協同育人、綜合保障等六個方面探索了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的實踐路徑。
[關鍵詞]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構建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21)05-0020-07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1.05.004
2019年6月教育部啟動新農科建設后,隨著“安吉共識”“北大倉行動”“北京指南”的接續發布與實施,新農科建設逐漸從理念引領深入到體系構建和機制創設上來,并引導廣大涉農高校全面發力。涉農綜合性大學作為高等農業教育發展和農業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在新農科建設背景下,如何發揮學科綜合和基礎科學研究的資源稟賦,協同推進服務國家重大戰略能力提升、“雙一流”建設和新農科建設機制構建,成為當前涉農綜合性大學推動農科教育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1]。
一、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的理論解析
綜合性大學是現代大學發展到高級階段后出現的一種組織產物,多學科性、科學研究性、基礎性是其核心特征。在本文中,綜合性大學是指我國含有或涉及農學學科專業的綜合性高校。為適應全球變化的需要、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需要和高等農業教育改革的需要,新農科建設要走融合發展之路、多元發展之路、協同發展之路(簡稱“三大發展”),需要農工結合、農理結合、農醫結合、農文結合(簡稱“四個結合”)[2]。“機制”的基本含義包括結構、功能和作用三個方面,也可以說是一套結構化的規則,是“帶規律性的模式”[3]。機制的運行規則都是人為設定的,其建立離不開制度與體制,同時又有助于制度與體制的運行和實施[4]。因而,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的構建過程,就是明確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的理論支撐、管理運行機制和保障體系,從而為前述“三大發展”“四個結合”提供具體的運行基礎。
(一)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的分析框架
1.新農科組織運行機制。主要包括新農科層級管理、新農科建設工作組織架構、新農科建設規劃、新農科建設項目立項與實施等體系與子機制。與高等農業院校采取的新農科建設專項推進形式不同,綜合性大學主要采取統籌推進的方式。其中,最為常見的是“四新”整體推進模式,即在學校層面成立“四新”建設工作領導小組,下設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四個工作組,分類推進;該模式綜合化程度高,適應綜合性大學大規模辦學實際。此外,一些綜合性大學還采取了“新農科+新X科”融合推進的模式,如新農科與新工科融合建設。
2.新農科結構優化機制。結構優化是新農科建設建強出新的關鍵。一方面,通過結構調整“推陳出新”,即破除原有農學學科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內生發展動力,揚棄原有不適合綜合性大學發展和新農科趨勢的弱勢專業,用新技術改造傳統農學學科專業,實現從“有”到“優”。另一方面,需要通過結構重組“交叉創新”,充分利用學校綜合性學術資源推動交叉學科研究,瞄準世界科技前沿、關鍵領域和解決“卡脖子”問題,建立跨學科組織,開展協同創新和交叉融合研究,適時設立新的學科專業,布局重點、急需、未來學科建設,推動原始創新能力提升。
3.新農科綜合保障機制。新農科綜合保障機制主要涉及資源配置保障和建設評價,總的職責是保障人、財、物的正常供給和內外交流,保障教育教學工作的正常運行。其中,資源配置保障主要包括人才資源保障、投入保障和制度保障三大維度,人才資源保障是核心,投入保障是支撐,制度保障是基礎,評價是高校辦學和學科建設的指揮棒。對綜合性大學而言,需要在以教學、科研為主要評價機制的基礎上,構建一種能夠充分調動學校、學科、教師參與新農科建設的新型評價方式,把新農科建設納入一流大學建設的重要指標。針對農學學科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研究工作周期相對較長、成果呈現形式多樣等特點,建立和推動適合學科發展的分類評價機制,不斷激發各類人才的創新創造潛力,引導教師“把論文寫在大地上”。
(二)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構建的理論基礎
1.學科發展理論。從學科發展理論來看,學科交叉是大學學科資源整合和優化的主要途徑,新的科技領域的產生往往通過學科交叉實現;基于學科發展中的不平衡性,通常需要集中投資優先選擇和保證關鍵學科,形成“頭部效應”[5]。這些是典型的學科“非對稱發展觀點”“非均衡發展觀點”。近年來,學科發展中的“生態主義發展觀點”等觀點也開始對學科發展戰略制定、學科建設舉措選擇及總體建設成效產生影響[6]。因而,考慮到綜合性大學學科的多元性,需要學校根據學科發展的歷史方位、階段目標、學科結構、資源稟賦做出科學規劃,在生態主義學科觀整體觀照下,實施農學學科非對稱發展策略。
2.機制設計理論。機制設計理論主要解決社會機制建設中的資源配置、信息效率、激勵相容三個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機制設計理論系統論證了基于既定目標,設計出相應執行機制的必要性與可行性[7]。從已有研究和應用實踐來看,它既可用來研究大到整個國家制度層面上的頂層設計問題,也可用來研究社會中觀或微觀系統的機制設計問題。新農科建設正處于改革和發展關鍵期,資源約束、信息不對稱、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不相容的現象普遍。機制設計理論的引入,對于新農科建設機制構建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3.定位理論。定位理論主要詮釋了現代市場中產品的核心競爭力、品牌穩定性、品牌認知等問題。理解高校定位的內涵有利于讓學校與眾不同,形成核心競爭力,鮮明地建立學校品牌[8]。就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而言,同樣需要對自身的深刻認知,從而明確發展定位和發展策略,以實現涉農綜合性大學之間、綜合性大學與高等農業院校之間的差異化和特色化發展,凸顯各自的核心優勢。
(三)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構建的政策依據
1.“四新”建設的戰略要求。2018年6月,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的召開,拉開了我國新一輪高等學校教育教學改革的大幕。2019年4月,教育部、科技部等13個部委聯合召開“六卓越一拔尖”計劃2.0啟動大會,全面推進新工科、新農科、新醫科、新文科建設。這是我國高等學校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改革又一重大戰略舉措。“四新”建設要求高校將“以本為本、四個回歸”確立為教育教學的根本,主動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發展形勢,著力調整學科專業建設,強化協同育人和實踐教學機制建設,形成以人才培養為核心的質量文化,全面提高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綜合性大學是高等教育體系的“龍頭”,需要在“四新”建設上走在前列。
2.新農科建設“三部曲”的現實要求。2019年6月,教育部啟動新農科建設,發布“安吉共識”,提出“四個面向”新理念,擘畫了新農科建設的總要求。9月,發布“北大倉行動”,推出“八大行動”新舉措,繪就了新農科建設的路線圖。12月,發布“北京指南”,推出“百校千項”新項目,明確了新農科建設的發力點。新農科建設要求涉農高校利用現代生物技術、工程技術、信息技術等手段,改造升級傳統涉農專業,助力打造天藍水凈、食品安全、生活恬靜的美麗中國,服務百姓幸福生活,提高生態成長力,為國家戰略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這也是對涉農綜合性大學的新要求。
(四)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構建的主要原則
1.特色化。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的“特色化”要從“科研方向特色定位”和“育人理念特色推進”入手。相較于同層次高等農業院校,綜合性大學農學學科的學科專業規模、教師和學生數量、科研梯隊建設以及經費保障等都處于相對弱勢。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尋求特色化建設成為定位與發展的首要問題。在科研上,充分利用已有的穩定研究方向,求精求細,打造特色平臺,培植領軍人才,在業內汲取更多的榮譽和資源。而從育人來看,可以調動多學科資源和師資優勢,著力構建大思政格局,把“鄉村振興”“生態文明建設”“健康中國”等涉農重大戰略內容一體化融入專業課教學與思想政治理論課、通識課教學,厚植學生成才基礎[9]。
2.在地化。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的“在地化”表現在科研布局和人才培養上要圍繞當地的農業產業鏈部署展開,實現學科建設與當地農業產業布局有效對接。農業科學知識體系本身的實踐性和地域性較強,其發展歷史表明,學科組織與當地特色農業產業之間存在共同演化與互構的關系。新農科范式的形成與發展也依賴于高校科技成果、人才資源與當地產業資源的系統整合。高校知識創新鏈催生出先進的農業科技,這些資源與當地產業交互、 整合與共享,可以有效提升農科知識研究成果的轉化率,增強屬地產業的發展動力。在此基礎上,通過大學創新體系與產業結合,實現從“大學城”向“科學城”轉變[10]。如世界著名的荷蘭瓦赫寧根“食品谷”,便是瓦赫寧根大學與當地產業融合發展而形成的引領行業發展的世界級農業“硅谷”。
3.協同化。與傳統農科相比,新農科的“新”字,首先體現在打破傳統農科建設的路徑依賴,協同醫學、信息科學、社會科學、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學及工程技術,形成農工、農理、農醫、農管多元協同創新的新型發展策略,從而增強農學學科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進一步激活多學科協同育人和社會服務的生命活力[11]。農業學科生態的復雜性還要求綜合性大學在新農科建設過程中,增強學科組織的開放性,推進涉農學科集群的國內和國際交流合作,達到多機構的協同效應,形成一個共生而有序的新農科創新生態網絡。
二、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面臨的挑戰與優勢
(一)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
1.在組織運行層面,新農科建設的新體制和新機制需要進一步完善。受綜合性大學學科發展歷史和現實影響,新農科建設的頂層設計和組織領導體系、學科建設規劃和發展路徑尚未完全成型,農學學科發展潛力沒有充分挖掘、學科發展活力沒有充分激發。從國內高校來看,涉農綜合性大學大多是由單科性高等農業院校或科研院所合并進入或組建綜合性大學,由于綜合性大學一般學科眾多,學校組織機構、學科傳統、校園文化等方面的融合并非朝夕之功,加之傳統學科劃分過細,學科建設與發展的路徑依賴、學科壁壘現象明顯,這就會對新農科“交叉”“協同”“創新”等理想機制構建造成嚴重的遲滯效應。
2.在結構優化層面,新農科建設的新學科和新專業需要進一步彰顯。整體上看,綜合性大學農學學科結構布局和生態需要進一步優化調整,部分學科實力弱、發展乏力、投入產出效益低、資源消耗較重,具有前瞻性、前沿性和發展潛力的新興一流學科和專業尚未大量呈現。這主要是因為綜合性大學農學學科方向上高原多、高峰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一流學科方向稀少,國際頂級學術大師匱乏。如以第四輪學科評估為例,在農學9大學科中獲得A+學科的僅有兩所綜合性大學,遠低于高等農業院校;而納入綜合性大學“雙一流”建設的農學學科也不多。同時,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的人才培養機制還不健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在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組織方式上發生了深刻變革,但農科高等教育與農業產業之間“兩張皮”現象突出。新農科創新人才目標難以在傳統農科人才培養實際教育過程中準確把握和具體落實,具體體現為知識、能力、素養有效貫通與有機融合不足,系統化培養機制不健全,創新實踐能力培養機制缺乏,致使人才培養機制與“新農科”理念吻合度不夠。
3.在綜合保障層面,新農科建設的新格局和新激勵需要進一步強化。科學合理的新農科學科資源配置機制、激勵投入機制尚未完全成型,符合“雙一流”學科組織發展的人才評價和職業發展體系都需要不斷完善。從現實來看,綜合性大學整體建設與農學學科之間綜合性與專業性的張力、研究性與應用性的張力、優勢學科與冷門學科的張力依舊存在,綜合性大學農學學科的建設基礎、工作環境、資源條件、待遇情況、政策環境等還不足以吸引國際頂級學術大師來學校工作。從評價來看,由于目前學科劃分過細,學校學科眾多,加強績效考核、建設學科特區、改善評價機制等一系列措施的落實還有待于進一步強化。如何進一步加強學科研究團隊的力量,探索學科績效評價模式,制定研究成果認定辦法,優化學科資源配置,加大資金投入力度,建立新農科建設常態化機制等等,都需要探索。
(二)綜合性大學加強新農科建設的優勢
1.綜合性大學“厚基礎”要求有利于打牢新農科發展基礎。建設一流的學科需要發展一流的本科教育、培養一流的人才。綜合性大學在長期的辦學歷史中,能夠始終把人才培養作為核心任務,把本科教育放在突出重要的地位,形成學科綜合環境、研究環境、開放環境等,有利于鑄造學生“基礎扎實”的良好素質。吉林大學牢固樹立“人才培養是根本使命、提高培養質量是核心任務”的辦學理念,確立了“志高遠、敢擔當,基礎厚、能力強,會創新、適應廣”的新時期人才培養指導思想,本科教育傳統優勢地位進一步鞏固,形成了積淀雄厚的本科教育優勢和特色。學校“厚基礎”的人才培養要求,有利于打牢新農科發展基礎。
2.綜合性大學“多學科”環境有利于改造傳統涉農學科。擁有一定數量一流學科,是綜合性大學的重要標志,也是“雙一流”建設的重要支撐[12]。同時,建設多個一流學科也是綜合型大學建設中形成的“共性”特征。由于不同學科所植根的文化環境和承載社會使命的差異,多學科的環境有利于傳統涉農學科在建設中用更高的標準、更開闊的視野、更長遠的目光,從學科外延式發展轉到追求質量的內涵式發展上。例如,吉林大學擁有一級碩士學位授權點63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49個、交叉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2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33個、博士專業學位授權點6個,為新農科學生寬口徑培養、大類招生改革,用新技術改造傳統涉農學科奠定了堅實的建設基礎。
3.綜合性大學“學科交叉”有利于發展新興涉農學科。利用綜合性大學多學科優勢,傳統優勢學科的學術風尚和學術文化得以繼承和發揚,涉農學科可以在充分吸納其他學科先進理念的基礎上有所創造、有所改進,創造有利于學科交叉的條件和氛圍,有利于產生和發展新興涉農學科[13]。如,吉林大學學科門類齊全,涵蓋13個學科門類。學校在支持文史交叉、文理交叉、理工交叉、理醫交叉等傳統優勢學科交叉的同時,激勵扶持農學與理學、醫學、工學、信息學、地學、管理學、經濟學交叉,有利于培育產生新興學科專業,為新農科建設奠定了寬厚的專業基礎。
三、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的構建與實施
(一)構建頂層設計機制,完善新農科建設組織架構
頂層設計是新農科建設的“牛鼻子”工程,是實施新農科建設的前提和基礎。吉林大學根據學科綜合特點和建設任務情況,加強頂層設計。一是成立專門的組織機構。鑒于學校同時承擔國家“四新”建設任務的實際,成立“四新”建設工作領導小組,下設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四個建設工作組和領導小組辦公室,各工作組下設專家組和辦公室。領導小組由校長擔任組長,負責研究“四新”建設學校規劃和重大宏觀問題決策;各建設工作組由四位分管副校長分別擔任組長,分頭負責“四新”建設組織實施工作;各專家組負責本學科建設方面的論證咨詢工作;教務處和相應學部(校區)教學辦負責各辦公室日常管理協調工作。二是制訂專項建設規劃。學校把“四新”建設納入“十四五”建設發展規劃,并制定新農科建設行動專項計劃,明確“探索建設機制、優化學科專業、改革培養模式、加強協同育人”的建設思路,以教育部、省級、校級新農科建設研究項目為牽引,全面推進新農科建設,計劃5年內完成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及其涉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研究,改造4-5個傳統的涉農專業,新建2-3個新興涉農專業,建設1個綜合性校內新農科實踐教學科研基地,建設4-5個高水平校外產學研融合協同育人基地。三是創新人才培養目標。學校貫徹以學生為中心、成果導向和持續改進的教育理念,提出培養“有家國情懷、品判性思維、創造創新能力,懂交流、善合作”,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人才總體目標。涉農專業面向新農業、新鄉村、新農民、新生態,服務鄉村振興戰略,培養知農、愛農的創新性復合型新型卓越農業人才。
(二)構建學科交叉機制,培育新興涉農學科專業
學科交叉是培育產生新興學科的有效途徑[14]。吉林大學圍繞國家戰略需求和服務經濟與社會發展,發揮學校學科綜合優勢,把實現學科交叉融合、培育產生新興交叉學科作為學科建設的發展戰略。一是成立新興交叉學科學部。學校在人文學部、社會科學學部、理學部、工學部、信息學部、地學部、醫學部、農學部8個學部基礎上,為適應學科建設發展需要,增設新興學科交叉學部。二是開展學科交叉融合創新項目培育工作。通過“學科交叉融合創新”項目培育和傾斜投入,引導和激勵新興交叉學科建設,扶持農學與理學、醫學、工學、信息學、地學、管理學交叉,培育新興學科專業。三是面向國家戰略需求設立新興學科專業。學校遵循“同一健康,同一醫學”理念,迎接SARS、禽流感、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衛生安全的新挑戰,在國際上率先成立了首家人獸共患病研究所,并迅速發展成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通過學科交叉融合,學校建成了農學與醫學大健康、農學與理學大生命兩大“雙一流”交叉學科群,高標準、高起點建設并獲批人與動物共有醫學、仿生科學與工程兩個交叉學科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還計劃增設“人與動物共有醫學”“智慧農業”等2-3個新專業(方向)。
(三)構建專業優化機制,改造傳統涉農學科專業
專業優化調整是高校專業建設的有效手段,是推進新農科建設的必要措施[15]。吉林大學擁有16個涉農專業(方向),包括6個國家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劃試點專業,學校制定了本科專業建設標準和專業建設規劃及管理制度,按照“扶優扶特、升級改造、優勝劣汰”專業建設思路,優化專業結構,促進涉農專業建設水平提升。一是重點扶持、傾斜投入,突出加強6個卓越農林計劃專業2.0建設,近年成功獲批涉農類國家級一流專業6個。二是守正創新、突出特色,加強動物醫學、植物保護、食品科學等涉農特色專業建設。三是升級改造、內涵建設,利用校內生物技術、工程技術、信息技術資源,改造提升農業資源與環境、園藝、食品質量與安全、農林經濟管理等傳統涉農專業。四是優勝劣汰、動態調整,主動撤銷或停止招生弱勢涉農類專業2個。
(四)構建科教融合機制,培養創新人才和服務鄉村振興
科教融合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核心辦學理念,是高校培養創新人才的必然選擇[16]。吉林大學充分發揮科教融合優勢,助力創新人才培養和鄉村振興。一是把學科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學內容。要求每個學科、每門課程、每名教師,特別是涉農等應用學科,都要及時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恰當地引入教學,保持教學內容的先進性。二是強化高層次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學校打造“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計劃”唐敖慶理科實驗班、“卓越農林人才教育培養計劃”動物醫學拔尖創新人才實驗班,實驗班每年免試推薦研究生比例高達80%-100%。三是加強創新創業實踐訓練。實施“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推廣本科生導師制,讓本科生廣泛參與科研工作,加強培養學生科研創新實踐能力。四是建立榮譽培養計劃。設立榮譽課程、榮譽學分、榮譽實踐體系、榮譽學位,通過設置多軌道、高階性、挑戰性、開放式的榮譽課程和榮譽實踐環節,強化“因材施教”和“個性化培養”。五是開展科技扶貧。學校充分發揮科研優勢,組織教師開展科技扶貧,將科研成果轉化為扶貧項目,在定點扶貧的吉林省通榆縣累計投入11個科研項目、100余名科技專家開展科技扶貧,研究鹽堿地治理,建立作物栽培技術試驗示范基地,連續3年持續增產,新品種創造了增產80.9%的歷史新高,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1名教授榮獲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榮譽稱號,1名教授榮獲全國脫貧攻堅創新獎。
(五)構建協同育人機制,提高人才培養質量
協同育人是高校人才培養改革的新模式,是新農科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17]。吉林大學高度重視協同育人,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一方面,深入推進校內“三全”協同育人。2018年10月,學校以“傳承紅色基因,培育時代新人”為主題,入選全國首批10所“三全育人”(全員、全過程、全方位)綜合改革試點建設高校。試點建設以來,學校堅持高位謀劃、重點攻堅、層級推進,從課程育人、科研育人、實踐育人、文化育人、網絡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資助育人、組織育人10個方面設置10個專項工作組,針對12個方面的90項建設指標,明確了287項預期成果,率先編寫12個學科的課程思政指導教材,成功獲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發展中心(心理育人方向),全面形成全員育人、全方位育人、全過程育人的大思政格局。另一方面,加強校外產學研協同育人。學校通過強化與農業企業、科研機構的合作,創建產學研協同育人機制,推進新農科人才培養鏈與產業鏈對接。學校涉農專業目前已與中國農業科學院特產研究所、吉林省農業科學院、長春皓月集團、長春國信現代科技有限公司等單位簽署合作育人協議,共同打造產學研協同育人基地。
(六)構建綜合保障機制,提升新農科建設質量
吉林大學堅持以高質量內涵式發展為主題,以“吉大特色的思政工作體系引領工程”“良性互動的學科生態體系平臺工程”“現代科學的學校治理體系基礎工程”為牽引,緊緊抓住東北全面振興全方位振興的戰略機遇,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和新文科建設。一是強化新農科的資金支持。學校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出,要聚焦“四個面向”,圍繞生物育種、大生命健康等主動開展研究;將包括農學學科在內的生命科學納入學校“雙一流”建設體系,加大新農科資源配置和資金投入。二是加強高水平新農科師資建設。出臺《吉林大學“匡亞明/唐敖慶學者”人才崗位聘任管理辦法》等配套文件,農學學科先后獲評學校卓越教授、領軍教授、英才教授、青年學者20余人次,新增各類人才10余人次,打造了“近者悅、遠者來”的新農科人才生態體系。三是完善新農科建設制度保障。印發了《吉林大學深化教育評價改革工作方案》,將服務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納入學校總體評價方案;擬制農學學科建設規劃,以制度形式規范新農科建設發展;建立學科交叉融合創新培育項目制度,形成一批體現吉林大學學科優勢的新興戰略和學科交叉專業。四是探索建立新農科建設評價機制。突出立德樹人導向和服務國家戰略導向,堅決破除“五唯”,擯棄“以刊評文”,將服務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戰略成果納入農學學科績效評價和教師評價,單獨開展“脫貧攻堅”系列教師職務評審,累計評審高級職稱8人。
總之,通過初步探索構建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發揮學科綜合優勢和基礎研究力量,優化傳統農科專業,深化科教融合,強化農工、農理、農醫、農管學科交叉融合,綜合性大學將成為新農科建設的重要推進力量。從服務國家鄉村振興戰略和新農科建設考慮,學校將對新農科建設機制進一步實踐完善,著力推進形成新農科發展的新樣態。推動農學學科與其他學科間的協同發展,實現不同學科間的相互促進與支撐,為農學學科發展夯實科學基礎;面向世界農學科學前沿,開展融合研究、融合學習和融合實踐,推動農學學科質量不斷提升;創新研究新農科人才培養模式,面向新農業、新鄉村、新農民、新生態,全面深化農科學科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改革,為新農科教育提供具有綜合性大學特色的新方案、新路徑、新經驗。
參考文獻:
[1]焦新安,俞洪亮,楊國慶, 張勇.涉農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的思考與實踐[J].中國大學教學,2020(5):22-25.
[2]吳巖.從“試驗田”到“大田耕作”——深入貫徹總書記回信 全面展開新農科建設[EB/OL].https://www.eol.cn/news/dongtai/201912/t20191206_1697531.shtml,2019-12.
[3]孫元明.國內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創新的基礎理論構建與機制設計應用[J].信訪與社會矛盾問題研究,2018(5):16-34.
[4]孔偉艷.制度、體制、機制辨析[J].重慶社會科學,2021(2):96-98.
[5]王欒井.有關學科發展理論與實踐的三個問題[J].中國高等教育,2003(6):12-13.
[6]胡文龍.論學科發展觀及其演進[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0(1):118-122.
[7][美]利奧尼德·赫維茨,斯坦利·瑞特.田國強等譯.經濟機制設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6.
[8]劉一彬.里斯與特勞特定位理論對我國高校定位的啟示[J].現代大學教育,2009(5):71-76.
[9]賈衛東,周脈樂,袁壽其.新工科新農科融合的涉農專業集群建設[J]中國高等教育,2021(5):10-12.
[10]王從嚴.“新農科”教育的內在機理及融合性發展路徑[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20(1):30-37.
[11]高樹仁,宋丹.行業特色型大學“新學科”發展邏輯與行動策略[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0(11):32-37.
[12]楊振明,丁洪浩,馬利凱,梅士偉.“雙一流”背景下綜合性大學涉農學科建設的思考與實踐[J].中國農業教育,2017(6):1-6.
[13]謝靜波,汪玲,吳鴻翔,吳海鳴.發揮綜合性大學學科優勢 創新復合型人才培養機制[J].中華醫學教育雜志,2017(1):9-11.
[14]董樊麗,聶文浩,張兵.美國高校學科交叉融合發展借鑒及啟示[J].科學管理研究,2020(5):161-167.
[15]呂志強.高校專業結構優化調整分析[J].科技創新導報,2017(13):215-218.
[16]鐘秉林.科教融合與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J].中國高校科技,2012(5):4-5.
[17]唐未兵,溫輝,彭建平.“產教融合”理念下的協同育人機制建設[J].中國高等教育,2018(8):14-16.
(責任編輯:趙淑梅)
A Study on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Constructive Mechanism of Emerg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Taking Jili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ANG Lifeng,YANG Zhenming,DING Honghao,MEI Shiwei,MA? Likai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5, China )
Abstract: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involv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are important bases for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ut also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talents in these discplines. With Chinas implementation to develop emerg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how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needs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in terms of its constructive mechanism. At the theory level,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eories, mechanism design theories, positioning theories have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s for th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Chinas “Four New Constructions” and “Trilogy” of Emerg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Construction have provided the policy basis for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with the mechanism for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mechanism for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mechanism for comprehensive guarantee forming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Taking Jili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ducts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challenges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encounter and the advantages they possess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is paper further studies the practice approaches to the constructive mechanism of emerg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 in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from six perspectives: top-level design, interdiscipline, professional optimizatio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cooperative edu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supports.
Key words: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emerging agricultural sciences;mechanism
[收稿日期]2021-08-23
[基金項目]教育部新農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及其涉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研究與實踐”(《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公布新農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的通知》(教高廳函〔2020〕20號));2020年度吉林省本科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立項課題重點項目“綜合性大學新農科建設機制及其涉農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研究與實踐”(《關于公布 2020 年度吉林省本科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立項課題名單的通知》(吉教高〔2020〕17 號))。
[作者簡介] 王利鋒(1964-),男,吉林雙陽人,法學博士,吉林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法學理論、高等教育管理。楊振明(1963-),男,吉林通化人,農學博士,吉林大學農學部學部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植物逆境生理及分子生物學、高等教育管理。丁洪浩(1963-),男,湖北天門人,農學碩士,吉林大學督學辦主任、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梅士偉(1979-),男,山東棗莊人,教育學博士,吉林大學學生工作部副部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馬利凱(1981-),男,湖北孝感人,管理學博士,吉林大學發展規劃處副處長、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