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性、絕望感與文學的可能性命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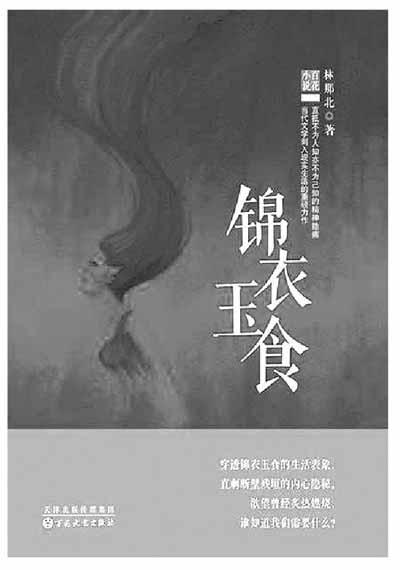
某種意義上,對林那北的任何一種解讀都是有限的,這是因為,當我們閱讀林那北的小說時,我們會想到那個叫北北的作家,而當我們把林那北看成是小說家的時候,林那北其實又是一個博物學家,她對物的隱晦或隱秘的含義有著近乎癡迷的熱情,以至于當我們認為理解了林那北時,其實是南轅北轍。這不僅僅是因為林那北有著多重身份——小說家、散文家、童話作家等——她常在多重身份間游移,還是因為林那北的作品具有一種深重的反諷性:在她作品的表面明晰的敘事下隱藏著其對人生、社會的復雜到近乎內在分裂的認知。她的作品暗藏著某種令人震驚的冷靜與清醒,及其因此而散發著的絕望感。
一
誠如作者所說:“一部小說不過是某種精神疼痛或焦慮或躁動或渴求的隱秘的圖,經線緯線的走向,都藤蔓一樣沉默。”①真正要想揭示林那北小說中的“經線緯線的走向”,無異于探險,她的小說中布滿太多的“陷阱”,稍不留神,便可能是離題萬里誤入歧途。長篇小說《劍問》可以看成是林那北小說創作的一個隱喻。小說情節曲折,線索明快,扣人心弦,讀完后卻讓人疑惑重重。無數的證據都指向一點,李宗林家藏有一把價值連城的寶劍,小說中的主人公們為了這把傳說中的寶劍可謂費盡心機,耗盡心血。歷經周折后,眾多的贗品一一搜尋出來,都在昭示著真品的靈光,寶劍存在的真實性毋庸置疑。但最終,經過眾人不懈的艱苦卓絕的尋找,寶劍卻并沒有浮出水面。這不禁讓人懷疑,寶劍存在嗎?這是否意味著,假的寶劍不斷出現,只是表明真的空無或缺失?即是說,假的寶劍背后只是一個空無,正是這真的空無和幻象才造成假的無限延宕。如此說來,真的寶劍其實就是一個無限的游移的能指,它促使人們殫精竭慮、義無反顧甚至奮不顧身,換來的卻是所指的空無。這種內在空無的基底上的無望而又充滿希望的徒勞尋找也就構成人的命運的隱喻性內涵。
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文學的獨有意義。文學的意義就在于尋找且賦予本質缺無的生活以意義和價值。林那北無疑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從其取名“錦衣玉食”寄意人間煙火的吃穿二項(《錦衣玉食》)中可以得到直觀的印象。但事實卻是,不管你的態度如何,生活本身卻是拒絕意義和方向感的。生活本身有其近乎執拗的邏輯和荒誕的內核,朝著某種宿命般的道路自顧行駛。生活有方向,但卻拒絕方向感;即是說,生活具有其特定的語境上下文關系,需要結合具體語境加以把握和理解,這就需要文學賦予它形式。某種程度上,林那北的小說就是這一賦予生活以形式的表象。
這應該說是林那北小說的內核之所在。
而說生活有其方向,有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方面,生活的發展有其自身的慣性或邏輯,不以各人的意志為轉移。我們都是被這慣性所推動著的微不足道的個體,既不能創造歷史,甚至連自身的命運也不能主宰。另一方面,雖然我們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甚至我們“誰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錦衣玉食》宣傳冊語),但我們并非沒有自己的主動性,我們仍可以有我們的選擇和我們的意志。兩種方向,在林那北那里,并不總是一致的,因而構成某種張力緊張關系。人的命運的反諷性也正體現在這種緊張關系中,任你怎么努力,都不能左右生活自身的慣性或歷史的“詭計”。比如說老米(《老米》),本以為當上副處以后尚有可為,沒想到他那個處最后卻成了省里機構改革的對象。他為之奮斗而得來的副處長職位,終究成為一個所指被掏空的虛幻能指。林那北并不是要去否定目標和努力,而只是表明人生的無奈和不可把握。
林那北小說中的主人公們的生活,有其方向,但卻拒絕方向感,這種看似矛盾之處,其所反映出來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即對人的主動性和主體性的充分肯定。這使得她的小說主人公的命運大都呈現為意識主導下的宿命結局。其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晉安河》,木穗的人生從她母親投河那天起就已經命定和不可更改:她的一生成為母親命運的延續和重復,這都是在對母親為何要投河的反復不斷的追問中被設定的。林那北小說主人公們的命運,與其說是性格決定命運,毋寧說是意識決定命運,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主人公們行為舉止的“個體意向性”傾向。這是一種“有意識的意向狀態”②。意向性并不追求意識明確,也不屬意整體,它只關心它所關心的,邏輯明確而執拗單一。
雖然說,這樣的主動性,在生活的方向或慣性面前常常顯得微不足道,但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主動性或者說固執,生活才并不顯得枯燥平庸,生活才有其質感和堅硬的屬性在。這樣一種固執,用作者的話說就是“精神潔癖”③,其一再顯現于她的小說主人公身上,比如說木穗(《晉安河》),她的怪異的行為表現出來的,是對父親不潔的無言批判,時刻指向母親投河的那一天:是父親的不潔導致了母親的跳河自盡。再比如說王以娥(《憶秦娥》),她之所以突然不辭而別是因為丈夫秦同明失手用發號槍打死了愛子虎奔,為了推卸責任卻說是虎奔自己走火所致,她不能忍受這樣一種懦弱,最終只能離開。
應該看到,“精神潔癖”在林那北的主人公身上并不表現為通常意義的現實生活的邏輯,她們遵循的是精神的邏輯軌道。即是說,她們的某些行為雖看似有悖常情常理,其實自有精神上的內在理路。比如說《錦衣玉食》中錦衣感動于男友劉格拿送給她的鉆石賣掉用于給父母買電視,但不能容忍他用假的鉆石欺騙母親,雖然她對母親有各種刁鉆的批評和不滿;柳靜能接受丈夫唐必仁出軌漂亮的女下屬,但不能容忍他把漂亮的女下屬獻給副市長上司作為自己仕途晉升的階梯。在她們眼里,與真有關的真實、真誠或真性情可能是最為看重的品質,其他的則可以忽略甚至被原諒。柳靜的邏輯,在《床上的陳清》中俞小靜那里有另一種形式的呈現。俞小靜并沒有因為丈夫陳清的不斷出軌而離婚,雖然她也曾設想過沒有嫁給陳清會是什么樣的人生,但她并不后悔,她的默默忍受里有著對丈夫品性的評估:他并非虛偽之人,也無意玩弄女性或欺騙她們的感情——他的每一次出軌里都閃現著源自內心的坦蕩和擔當,用作者的話就是“一直到老,他都沒有世故圓滑”,都“始終保持”著“與生俱來的單純天性”④。
不難看出,這樣一種“精神潔癖”的存在,其實就是泰勒所說的“本真性”——即“對我自己真實”⑤——的表現。林那北的小說讓人明白一點,這看似至為簡樸的目標,其實是對每個人的最大考驗。一個能始終保持住“單純天性”的人,即使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也是多么的可親、可愛和可敬。柳靜們的邏輯在另一個主人公杜奇(《張飛老師》)那里有同樣的顯現。杜奇的生活看似沒有目標且容易滿足,內心其實是篤定而執著的:在他那里,慵懶的生活的另一面是對內心本真的堅守。他可以接受別人對他癡和傻的嘲諷,但不能忍受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虛偽本相。因此當看到傲氣聰明的杜薇同庸俗勢利的常天兵之間關系曖昧的視頻后,毅然辭職并離家出走,雖然這兩個人一個是他所崇敬的姐姐,一個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老板。此時,杜奇的內心世界已然坍塌。這已然是一個沒有了方向感的世界,漂泊因此就成為林那北的小說主人公們必須要面對的人生困局:何去何從作為一個問題凸顯在他們面前。
二
“精神潔癖”的存在若隱若現,某種程度上也使得缺失和尋找構成林那北小說的隱喻式結構。這樣一種缺失與尋找,在林那北的小說主人公們那里呈現一種矛盾的分裂狀態。比如說木穗(《晉安河》)的堅硬和強勢之下其實掩蓋的是虛弱和無助,馬蘭花(《坐上吉普》)的決絕背后是無望,馬念和牛越的執著背后是柔弱(《憶秦娥》)。缺失是林那北的小說主人公性格的背景性存在。他(她)們生活在一個布滿缺失的世界,他們渴望圓滿,渴望原初意義的秩序,但世界一旦“缺失了一塊”(《憶秦娥》),也就意味著永遠的失落:不可能找補回來了。但很多事情,恰恰就是這樣。越是證明它存在,其實越加顯示出它的虛無。林那北的小說顯示出來的也許就是這種深刻的悖論之所在。她的主人公越加顯示出對“精神潔癖”的固執,越加顯示出人生的無奈: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種假想中的可能或者說虛構的純粹呢?這也使得尋找主題,在林那北那里格外顯得悲壯且具有反諷意義。
尋找與缺失⑥的隱喻結構,也使得林那北的小說多有寓言的性質。比如說《有病》,堪稱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的文學表現。小說中某一個小城因出現第一例艾滋病而引起的恐慌顯示出來的就是“疾病的隱喻”的表征。比如說《唇紅齒白》,雙胞胎作為人生鏡像結構的隱喻,某種程度上表明人生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結合:雙胞胎姐妹都想從對方身上尋找甚或推演自己的命運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一男一女》中,封閉的與世隔絕的火車車廂是一個有著極強隱喻性的特定情境,在這個情境里,兩個深愛著的青年男女毫無遮蔽地彼此敞開,他們之間的本性甚或人性的劣根性因而得以充分暴露,其結果他們最后走向了分手。小說中主人公的名字就具有隱喻色彩——甲哥和丙妹,這是無數個同類的無名化的象征。
大體上看,尋找與缺失的關系,在林那北那里以三種方式呈現。首先是缺失后的尋找。這種缺失,可以從實存和精神兩個層面加以理解。實存層面缺失的例子,以《尋找妻子古菜花》為代表,小說中,對妻子的“‘尋找正是源于‘不在”⑦。林那北的小說更多是從精神層面的缺失入手。比如說《晉安河》中的木穗,她的人生定格在母親跳河自殺的那一刻。母親的跳河自殺,既是創傷體驗,也是缺失,讓她對人性的缺失和不純有著近乎瘋狂的怨恨,她渴望純粹的夫妻關系,因而選擇三山就成為對純粹人性的追求和尋找的象征。但事實上,純粹只是她的原初的假想、預設和虛構,真正的純粹是不可能的和不存在的,三山選擇她并不是出于一見鐘情或所謂的愛情,而是出于經濟上改變自己處境的考量。他的行為背后有著諸多出于樸素的和本能的因素,很難說臟與不臟。再比如說《天橋上的邱弟》,邱弟對花姑村的執著中,有著對人性美好的想象,而事實上,隨著花姑村的改造而來的,是他父親的官職越來越高和他父親的本性漸漸失去。花姑村的現代化與人性的缺失構成一種奇異的對應關系。邱弟的尋找背后,是永遠的缺少:現代化使得美好的東西注定只能失落。
其次,是尋找之后的空無。她的小說主人公甫一出場,就表現出積極尋找的態勢:他(她)們都被某一傳說中的某物所吸引、所誘惑,而去努力奮力尋找。比如說《劍問》和《鏡子》。在這里,寶劍和寶鏡,構成小說主人公尋找的對象,他們只是聽說過有這寶物存在,他們被聽說和傳聞所左右。但尋找到最后,卻發現,尋找的結果其實是更大的和更多的疑點,是本質上的虛無。寶劍和寶鏡,某種程度成為一個空洞的閃光的能指符號,誘惑著對它進行指認和填充。尋找正是這指認過程,但填充和尋找的結果,只是更加掩蓋著背后的虛無,尋找其實是對虛無的凸顯。林那北通過這類小說所告訴我們的是,人們往往被表象所迷惑、所困擾和執迷不悟,表象背后有無真實存在,他們并不關心,亦無法確認。比如說《我欠了誰》,在一場酒局中,喝醉了酒的大陳說“我”欠了他5000塊,雖然他并沒有要“我”還的意思,但“我”深感震驚和屈辱,因為“我”沒有絲毫印象,而為了證明“我”并沒有欠錢,接下來“我”干出了一系列的蠢事,但有字據顯示,“我”確確實實欠了大陳5000塊錢,至少看起來如此。在這里,證據就成為指涉真實之存在的痕跡,循此痕跡,“那段往事一點點浮上來了”(《我欠了誰》)。但這一證據就能真正證明欠錢的事實嗎?顯然,林那北是把這一證據視為一個空洞的能指,并不能賦予它確切的所指——這并不能簡單看成是遺忘和記憶的故事。這其實是告訴我們,在幻象的迷霧包裹下的表象世界,遺忘和墮落構成我們人生的兩大情狀,就連事件中的我們自己,也并不真正認識自己。我們很大程度上身處尼采意義上的頹廢狀態:在一個不能確認自己和不斷遺忘的情境中,我們只能活在當下和表象構成的虛幻世界——距離真實的自己越來越遠。“我”有殺人嗎?(《殺人嫌疑》)呂非玉結過婚嗎?(《呂非玉的往事》)等等,這些都是需要重新打上引號的存在。對林那北而言,不懈的和無盡的尋找之后,是更深的困惑:“現在的問題是,向人借五千元錢都會忘記,我到底還忘了什么?”(《我欠了誰》)這里的邏輯很明顯,不去尋找,我們還處于一種自我圓滿的虛幻之中,尋找反而是缺失之始,尋找之旅因而構成了我們人生缺失的隱喻。
因此可以說,在林那北那里,缺失后的尋找,和尋找之后的空無,是一體兩面的存在。這是一個沒有初始狀態的循環和宿命。林那北的主人公就深陷于這樣的宿命中。她的故事,情節明朗,人物陽光,但本質上卻是充滿了悲觀和絕望。絕望和明朗,構成林那北小說鮮明的兩極和對照,看不到明朗背后的絕望感的存在,可以說是對林那北的誤讀。小說《峨眉》就是如此。主人公“我”生活在父親的各種版本的故事中,“我”的生活歷程實際上成為一部尋父的歷史,但也正是這種種的版本所建構的父親形象,讓人產生一種深深的絕望:生活在父親的故事中的“我”,始終見不到父親,接觸到的只是父親的形象。那么,此時,父親這一能指的意義,其實就變得可疑了:作為能指的父親雖然存在(每個人都有一個父親),但這一存在卻是以作為所指的父親的永遠延宕作為前提的。這注定了尋找父親只能是尋找父親的形象了。這與尋找寶劍最終找到的只是一個個贗品(《劍問》)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在《劍問》中所指的延宕——一個個贗品被挖掘出來——帶來的是對能指(寶劍)的疑問。
最后,是對“原初”的尋找。林那北的小說常常預設一個“原初”的存在,她和她的主人公們并不能根除對“原初”的原鄉式的懷念和思想,她們要以絕望的或荒誕的抗爭來表達這種“情感結構”。比如說《坐上吉普》中的馬蘭花,她被從原始的深山老林中帶入現代都市的過程,本身就是純粹和質樸的被玷污的過程,她的絕望從她步入現代都市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的。這也意味著,抗爭注定了只能是絕望地和義無反顧地沖向懸崖與大海:她那朝向懸崖和大海的奮力一踩(油門)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絕望的飛翔。再比如說《玫瑰開在我父親懷里》,父親的失敗早已注定;這頗有點像堂吉訶德朝向風車的奮力沖殺,他們都把表象(比如風車)當成了不存在,他們尋找的是表象背后的各種可能性。
因此,對林那北而言,過程很多時候比結果更重要,比事物的存在本身(而非表象)更重要。人們既然很多時候對自己和世界,并不真正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意識,尋找過程本身顯示出其意義來:其既表明結果的虛妄和難以獲得,又表明對表象世界的始終如一的審視與批判。她通過小說的寫作,其實是提出了過程美學的命題,個人意向性命題正是在這一點上表明其價值。這構成了對“原初”的尋找的另一種類型,即堂吉訶德式的荒誕尋找本身。
三
尋找與缺失的辯證關系,其實也是J·希利斯·米勒在《小說與重復——七部英國小說》中所說的“重復”的兩種形式的纏繞。比如說《一男一女》中的甲哥和丙妹,他(她)們因為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才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但這種相似和重復關系卻因一次突然的置于與世隔絕的語境中而顯示出他(她)們之間差異的本質來:人與人之間的相似,并不是建立異中之同的基礎上,事實是相異的事物之間產生了同的因素。同因異而產生,而不是相反。即是說,人與人之間的相異構成了人的存在的本質。認識不了這點,便會對人生充滿失望。但也恰恰是認識不了這點,她的小說主人公們才始終處于一種尋找的處境之中,這也可以說是林那北小說的獨有貢獻。她充分認識到外在世界之陌生的和異己的本相,但卻絕望地和義無反顧地去追求。這可能也就是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對“存在的可能性”⑧的探索吧。
這種探討在她的《玫瑰開在我父親懷里》中有集中呈現。父親是一個與他的身份和處境不相吻合的不切實際的人。他是一個農民幻想家。他的想法常常具有一種浪漫的氣質——熱衷于造飛機、寫小說,等等。沒有幻想的世界,是一個讓人絕望的世界,父親的存在讓敘述者“我”看到了瑣碎庸俗現實的多重可能性,這或許是小說的敘述者更喜歡父親而不是母親的重要原因。雖然說現實與幻想處于一種二元對立的狀態,林那北想表達的其實就是這樣一種可能性,現實本身是否可以容許幻想的存在?畢竟,只有幻想才能使得生活飛翔起來,幻想讓人看到希望,幻想是生活之光的體現。
這種重復現象背后,不難體察林那北對世界和自我的認知。世界充滿著表象和幻象,世界其實處于一種永恒的循環狀態中,日復一日的彼此重復著。我們被幻象所迷惑。因此對我們來說,要么生活在這種幻象中,不自知,被裹挾著向前;要么表現出一種決絕或反抗的姿態。林那北的主人公更多屬于后者,這是她的主人公的主體性的表現。我們作為個體的人的主動性,就體現在人生的偏移、意向性和對自我的確認上。世界對個人的形塑作用,使得我們很多時候以一種意向性的方式表現其反應,我們很多時候并不自知。只有當我們被某個生活的裂縫所刺激從而表現出偏離或偏移的時候,才能感到并確認自己的存在,這也意味著,認識自我,源于生活中的事件及其偏移或溢出。因此,在林那北那里,事件的意義就顯得尤其重要。比如說《唇紅齒白》中杜鳳相親前的牙疼這一事件,成為導致其后人生一系列變軌和變故的重要象征。比如說《右手握拍》,李威妻子杜若懷孕時心臟病突現,導致前途一片大好的李威的人生陷于停頓,她的心臟病的反復發作,因而也成為李威人生的左右搖擺狀態的映照關系;這篇小說,講述的是個人無法左右自己的命運的故事,各種力量、各種偶然的和意外的事件,左右著人生的走向,人能否左右自己的命運呢?小說告訴讀者,很多時候主動性的意念和決定,仍舊是必須的,哪怕僅僅是微不足道的一次主動選擇。
從這個角度看,在林那北那里,尋找主題所涉及的其實就是自我認知的命題了。一個沒有自我認知的,或自我認知不夠的人,才會有尋找的必要。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些渾渾噩噩的人,他們是不需要表現出尋找的“意向性”的。尋找只針對那些對現實人生或有不甘的人。比如說《唇紅齒白》中的杜鳳,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她對自己隱秘的欲望和思想,并不總是清楚。她后悔于當年錯過了歐豐沛,因此,當歐豐沛官越做越大,她對丈夫李真誠的不滿就越加明顯;她想象自己是歐豐沛的妻子,卻又并不想破壞家庭。當她一步步陷入歐豐沛的懷抱的時候,她的自我意識才開始慢慢復蘇,她逐漸意識并表現出幡然醒悟的過程,她的自我正是這時產生;但反諷的是,在她確認自我的時候,她的人生卻沒有了退路可走。人生就是這樣的悖論。沒有自我意識的人生可能是渾渾噩噩的人生,但也可能是安全的人生。清醒的人生往往是令人痛苦的。不自知,可能才會是幸福的,比如說柳靜(《唇紅齒白》),她始終活在一種懵懂無知的過程中,但隨著她的自我認知的逐漸清晰(伴隨著對女兒的認知,女兒其實構成了柳靜的鏡像關系),她開始感到不安、緊張和痛苦。人的精神潔癖,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懵懂無知的象征和隱喻。是清醒使得懵懂無知變得不可能,林那北的小說,往往表現出一種清醒的痛苦感,用孟繁華的話說,這是“以一種悲憫的情懷體現著她對文學最高正義的理解”⑨。林那北的小說正是在這一點上具有“心靈史”的味道,但若僅僅把它定位在“現實生活所造成的精神迷茫和心靈上對回歸的渴望”⑩的二元性上,又似顯不夠。
四
作家金仁順對林那北的小說有過一段十分敏銳的直覺概括,她說:“北北的芯是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的:清醒的認識,冷靜的判斷,精致的細節,不多也不少的傷感,對理想的堅持,對詩意的追求,以及悲憫的情懷。”11“清醒”“冷靜”“悲憫”但又有似乎“不多不少的傷感”和“對理想的堅持”,這看似矛盾,其實是道出了林那北小說的內核:林那北的小說在明快的故事和節制的敘述所構成的張力關系中蘊藏著某種更為深刻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指向。她的小說在如下兩點上顯示出其深刻之處,即對本質存在的懷疑,和對不可能之物的尋找。兩者之間的張力,構成了她的小說的整體氛圍。這里,很難說哪一個命題在前,哪一個在后,唯一能確定的是,這是互為因果的兩個命題。你很難說那把曠世珍寶的劍不存在,只能說你還沒找到,甚至可能永遠找不到(《劍問》);你很難說絕對純粹之人和絕對潔凈之人世界上沒有,只能說你沒有遇到(《晉安河》);等等。兩者之間其實是一種辯證關系的體現。《請你表揚》中的楊紅旗,最后強奸女大學生就表明兩者的對立關系:好事(即解救女大學生)和壞事(強奸女大學生)之間往往會瞬間轉換,人之為“人”其實并不純粹。
而這,正反映出林那北的小說的某種傾向,即指向世界和自我的雙重困惑及雙向堅守。正是因為對世界有了困惑,才有守住“精神潔癖”的執著;而恰恰是“精神潔癖”又顯示出對自我的不自信。她的小說主人公的主體性正體現在這種雙重的困惑和雙重的抗爭之中,同樣可以說,林那北小說的藝術張力也正體現在這里。
【注釋】
①北北:《自序:有一條路在內心蜿蜒》,載《請你表揚》,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序言第3頁。
②[美]約翰·塞爾:《人類文明的結構》,文學平、盈俐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第26頁。
③林那北:《世界是扇形的》,載《錦衣玉食》,百花文藝出版社,2014。
④林那北:《在歲月中春暖花開》,《芳草》2020年第5期。
⑤[加]查爾斯·泰勒:《現代性的隱憂: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第57頁。
⑥關于林那北小說的“缺失”內涵,另參照林秀琴:《從破碎到荒誕——試論北北的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3期。
⑦林秀琴:《從破碎到荒誕——試論北北的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3期。
⑧[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第59頁。
⑨孟繁華:《林那北和她小說的表情》,《小說評論》2018年第2期。
⑩馬季、桫欏:《重建普通人的精神譜系——談林那北小說創作中的精神指向》,《時代文學》(上半月)2011年第3期。
11金仁順:《北北和林那北》,《時代文學》(上半月)2011年第3期。
(徐勇,廈門大學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