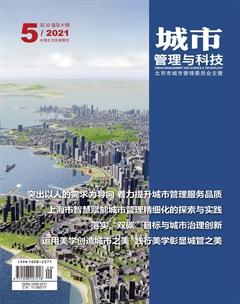特大城市“大應急”治理體系建設的典型模式及經驗啟示
紀曉嵐 王伯承
2020年以來,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而疫情主要爆發于人口密度高的特大城市。以武漢為代表的中國特大城市率先成功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在進入疫情防控常態化階段后,北京、深圳等城市也陸續偶發零星疫情,但總體上“可防可控”。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聚焦打贏疫情防控攻堅戰阻擊戰,中國特大城市取得了疫情應對的重大成就。同時,在快速推進的城市化進程中,特大城市越來越多地面臨來自城市空間、社會秩序、生態環境、自然災害、公共衛生等多領域風險的挑戰和壓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變得越來越突出。隨著“大應急、大救援、大安全”觀念日益深入人心,時代呼喚并催生著全險種覆蓋、全過程介入和全社會參與的“大應急”治理體系的構建。
一、特大城市“大應急”治理體系的典型模式概述
(一)北京的“局辦合一”模式
北京市形成了具有首都特色的“局辦合一”的應急管理機構模式。2018年國家機構改革后,北京市順應國家對應急管理的改革,成立應急管理局,共設置12個內設機構,各自承擔不同職責。原來以市、區兩級應急委及其下設專項應急指揮部為主體的應急管理體制和工作機制總體不變,保留市應急辦并整體劃轉至新組建的應急管理局,繼續以市政府總值班室、市應急辦名義履行信息匯總、綜合協調、應急管理等職能,同時還承擔了防汛、森林防火、地震、生產安全、應急救助在內的五個專項應急指揮部辦公室的職能。并且設置差異化的區域應急處置權限,根據地理位置、區域任務、應急工作要求的不同,賦予不同區域應急處置權限,提升突發事件的預防和處置效能。
(二)深圳的“統一領導”+“專項行動”先行示范模式
深圳市較早提出了要打造具有總體性內涵的城市應急體系,一方面,通過設置專門性應急管理指揮機構達到整合不同部門應急職能的效果;另一方面,又在海上應急、城市臺風洪澇、地震海嘯等專項事故災害中完善專業化救援力量和預案機制。“大應急”理念提出旨在實現全災種的系統應對和緊急處置。置身于牽涉全局的重大災害風險的境遇下,深圳市通過正確處理應急管理“統”的辦法,城市應急采取非常規化和跨體制原則的“統一領導”將各個部門的資源和行動統一在同一個應急目標原則下,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將“統籌邏輯”落實在特大城市應急的方方面面。同時深圳市作為特大型城市的應急管理除了面對“巨災風險”,還通過對“常規風險”的精準判定和識別能力將突發風險力爭消滅于無形。“巨災風險”意味著需要整合特定區域內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在這種情形下采用“統一領導”;相應地,“常規風險”采用“專項行動”就可以及時消弭風險或是防止風險的蔓延與擴大。
(三)重慶的“城鄉融合一社會動員”模式
重慶市區位情況極為特殊,該區域集大城市、大山區、大庫區、大農村、老工業區于一體,防范化解安全風險任務重,于是提出通過社會動員和要素整合來達成對城市災害事故風險的有效治理。通過媒介深度嵌入城市應急管理,激活新媒介社會動員對城市應急管理的積極功能。改變過往“命令式”動員的行動慣性,將社會動員的理念認同轉化為科學參與、協同行動。拓展新媒介參與應急管理的領域,不斷提升新媒介在災后心理介入、關注弱勢群體、社會救援等領域的功能。
(四)青島的“應急人才隊伍培育+企業合作”模式
應急治理體系構建時間早、應急治理隊伍專業人才多,是青島市“大應急”治理模式的兩個主要優勢。構建時間早,主要體現在多個全國“首次”方面。青島在全國范圍內率先構建城市風險一張圖,啟動綜合性風險評估。在青少年應急科普教育中,打造國內第一部應急題材兒童舞臺劇。在全國同類城市中首個舉辦了家庭安全應急產品展覽會,也打造了國內首個“公共安全+”領域的智慧城市創新公共服務平臺。在專業人才方面,青島市除了強化專業應急救援隊伍的建設,還通過定期培訓等方式加強社區“大應急”專業人才隊伍的建設,聯合高校開展安全與應急管理專業人才的教育。同時,實施社會培訓萬人計劃,依托應急管理學院組織開展應急指揮人員、專業救援人員、企業員工等群體培訓。
(五)上海浦東的“城運中心+”模式
上海市浦東新區依托區城運中心綜合管理平臺,構建每班“1+3+X”聯合值班力量配備模式,實現多部門聯合值守,力量統籌整合,工作協同配合、信息互聯互通。區應急辦、安監局、“120”急救調度中心、防汛指揮中心、城管執法局信訪分隊等單位在區城運中心集中辦公,區公安分局、城管執法局、市場監管局、建交委、環保市容局、衛計委、規土局、教育局等部門派駐人員到區城運中心辦公。這種模式試圖將城市運行體系與應急治理體系相整合,建立起了平戰協調統一、緊密結合、迅速轉換、融合發展的應急管理體系。
二、特大城市“大應急”治理體系建設的有效路徑
(一)合理協調“統一領導”與“專項行動”之間的關系
特大城市應急面臨重大災害境遇下,應采取非常規化和超體制原則的統一領導、總體指揮機制,將各個部門的資源和行動統一在同一個應急目標原則中;常規風險則只需要動用特定資源力量對特定風險進行有預期和可規范的應急管理。所以,必須正確處理應急管理“統”與“分”的辯證關系,合理協調城市應急管理中“統一領導”與“專項行動”之間的關系,在總指揮中心下相應地完善和設立多個高度專業化的應急救援分指揮中心,如防汛防臺應急指揮中心、氣象災害應急指揮中心、危化品應急指揮中心、公共衛生安全應急指揮中心、社會安全事件應急指揮中心,等等。當發生某類重大突發事件時,在市應急總指揮中心統一領導和指揮下,以相應的應急分指揮中心為主并啟動預案,其他相關的應急分指揮中心輔助和配合,共同開展重大災害事故等中突發事件應急處置和應急救援等工作。各應急救援分指揮中心統一受市應急總指揮中心的領導和指揮。
(二)應急執行層面應落實應急處置的工作明確化、責任具體化
“大應急”的領導力需要變為執行力,就離不開應急處理處置的責任具體化,這樣才能將工作落到實處。在這方面,北京市的突發事件時序性應急響應機制值得借鑒。它以突發事件處置過程為主線,進一步明確了各部門響應時序和響應等級提升過程。屬地政府負責第一時間組織到場單位開展先期處置。按照北京市主要領導提出的“街鄉吹哨、部門報到”要求,對公安、交管、衛生、消防、應急、宣傳等部門提出了“六必到”的要求,有關部門必須第一時間參與現場處置。整個突發事件處置流程中,依次實施組建區級現場指揮部、開展市級態勢研判與力量調動、啟動市級部門響應、組建市級現場指揮部等行動。此外,特大城市基層應急管理應打造以“社區為軸”的城市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網絡,進一步確保整個城市社區基層所應該具備的應急管理功能。
(三)構建更為有效的風險監測預警機制和應急預案體系
不論是“巨災風險”,還是“常規風險”,均應塑造以“預防為主、防控結合”的機制架構,才能最大程度地控制風險的量級。應將應急管理理念融入到教育、預警、科研、監測、媒體、社區等城市生活的各個相關領域,從而最終構建起系統而又完善的應急機制。對城市進行綜合風險評估,以此為基礎對風險進行更全面的預測、預防和應對。譬如,青島市正推進市級突發事件預警發布中心建設,建立監測預警和災情報告發布制度,繪制突發事件一覽圖。2019年,青島市累計發布氣象、海洋、交通和高火險天氣預報預警信息30余萬條。此外,應急預案作為應急響應的指導方針,應根據應急演練和應急救援中暴露的缺陷,以及應急指揮的變化情況進行定期修改。不斷完善應急預案體系,才能更好地發揮應急預案在應急處置中的作用。
(四)建立一支專常兼備、平戰結合的應急隊伍
通過應急事件中自組織能力的專業化發展,實現處置社會化,最小限度地減少災害事故損失。深圳市在提升應急管理社會化方面,主要圍繞著“主體吸納、知識凝聚、宣傳演練、群防群治”四個工作重心展開。主體吸納立足于激活社會不同主體參與服務城市應急管理的潛能和空間。一是構建以綜合應急救援隊伍(消防)為核心,以應急志愿者隊伍為補充的應急隊伍體系。二是加強應急隊伍標準化建設,提升應急救援效率。三是重視基層應急救援技術隊伍的建設,完善全社會參與,提升群防群治能力。四是與高校合作,強化應急專業人才培養與隊伍建設。青島市在開展安全與應急管理專業人才教育方面,加強應急管理學科建設,聯合本地的中國石油大學和山東科技大學建成青島市應急管理學院和安全科學研究院。該研究院是山東省第一所本碩博人才培養和安全實訓“一體化”的安全與應急管理學院。
(五)開展政企間應急管理科技合作,將企業納入城市應急治理體系
政府與企業開展應急管理科技合作與應用,合作創建智慧型的公共安全城市。譬如,青島市與企業合作構建“公共安全+智慧城市創新空間”,推進應急管理科技創新。2016年,由海信網絡科技公司與青島市政府應急辦、青島市應急產業聯盟根據各自優勢共同創建“公共安全+智慧城市創新空間”項目,打造了國內首個“公共安全+”領域的智慧城市創新公共服務平臺。2020年4月,青島市應急管理局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全面開展應急管理科技和信息化戰略合作,實施智慧應急工程建設。
(六)加強居民的自救和互救能力,加快推進全民應急教育普及
開展中小學生應急科普教育,建立家庭應急安全演練實訓基地,舉辦相關展覽會等應急知識宣傳。為了加強居民的自救和互救能力,2017年青島市應急管理局編制了《青島市民應急安全要點指南》,內容涵蓋4大類37項市民日常生活應急知識點。制訂了社會應急安全萬人培訓計劃、基層單位綜合減災能力提升計劃和市民家庭應急能力提升計劃。2015年7月3日建成4處大型應急安全體驗館,累計培訓市民近35萬人,共建成國家、省、市綜合減災示范社區293個、地震安全示范社區53個。截至2019年,青島是現有應急救援力量302支21000余人,其中主力志愿者救援隊伍12支1800余人。
三、特大城市“大應急”面臨的挑戰及其展望
一是在體制機制設計上,當前政府職能部門的應急管理局主要是圍繞“小應急”思路進行應急體系建設和部門職能定位,存在與“大應急”定位不匹配的問題。突出表現為應急災種和相應職能的不匹配,各級應急管理局面對的是“大應急”局面,應急災種包括了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在內的四類突發事件。但在應急體系的設計上,應急管理局的職責僅包括自然災害和事故災難兩類,這就出現了權責和定位不匹配的局面。
二是應急治理的具體職能部門存在著內部關系未理順,信息系統融合程度不理想的狀態。“大應急”治理體系涉及政府部門之間或機關層級關系下,存在信息阻隔、溝通不暢、信息系統及其數據庫不能即時共享的現象,影響應急治理的處置效果,不符合“大應急”的現實需要。
三是應急治理強調多元力量協同共治,社會、市場力量是除行政力量之外應急治理的重要力量。而目前在應對突發事件過程中,基層存在過多倚重行政力量,基層面臨層層加碼的應急任務和需要不斷熟悉新技術手段的現實挑戰,存在基層負擔過重等風險隱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正是因為數據信息系統的建設與使用的制約,導致社會、市場、志愿者力量在應急治理中缺乏一定的發揮空間和參與渠道。如企業、社區等自愿力量不能依托向民眾開放的大數據信息系統,難以自主開展應急治理工作,只能“被動地”配合政府工作或協助處理突發事件。
總之,“大應急”治理體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持續改進與完善。因此,對應急治理體系的科學建構,需要隨時代變化,充分吸收國內外的經驗教訓,進行準確、全面、深入的危險辨識與風險防控,以求最大程度地滿足風險應對的實戰要求和現實可操作性。
(責任編輯:陳希文)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