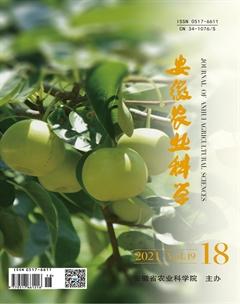基于Logit-ISM模型的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杜森 鄭紀芳



摘要 基于山東省西南地區375份麥農的問卷調研數據,運用二元Logit模型和ISM模型實證分析了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影響因素及其遞進結構關系。結果表明: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受文化程度、職業選擇、種植規模、專業化程度、農藥防治效果認知、病蟲害壓力以及施藥技術培訓7個變量的顯著影響,其中農藥防治效果認知和病蟲害壓力是表層直接因素,專業化程度和施藥技術培訓是中層間接因素,麥農文化程度、職業選擇和種植規模是深層根源因素。
關鍵詞 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影響因素;遞階結構關系
中圖分類號 S-9;F 32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17-6611(2021)18-0219-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1.18.053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Analysis on the Pesticide Over-application Behavior of Wheat Farmers Based on Logit-ISM Model
DU Sen,ZHENG Ji-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Taian,Shandong 271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of 375 wheat farmers in southwest Shandong Province,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relations of pesticide over-application behavior by wheat farmers,by using binary Logit model and ISM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esticide over-application behavior by wheat farmers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7 variables,including educational level,occupational choice,planting scale,specialized level,the recognition of pesticide effectiveness,pest and disease pressure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raining.Among them,pest and disease pressure and the recognition of pesticide effectiveness are direct factors on the surface,specialized level and pesticid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raining are middle-level indirect factors,educational level,occupational choice and planting scale are the deep-rooted factors.
Key words Wheat farmers;Pesticide over-application behavior;Influencing factors;Hierarchical structure relation
作者簡介 杜森(1995—),男,山東菏澤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農業經濟與政策。*通信作者,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從事農業經濟政策與法規研究。
收稿日期 2021-01-16
農藥作為一種重要的保障性生產資料,在防治農田有害生物、促進農作物生長發育以及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中國現階段的農業生產中,由于農藥自身毒性以及中國農戶不科學的農藥施用,尤其是過量施用,造成了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與環境問題[1-3]。為減少農藥施用量,中國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7 年國務院提出“到2020年主要農作物農藥使用量實現零增長”的目標;2020年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治理農村生態環境突出問題,深入開展農藥化肥減量行動”的要求。農戶是農藥施用行為主體,要實現農藥施用的“減量化”,必須從規范農戶施藥行為入手。
國內外學者們普遍認為農戶存在過量施藥行為,并證實了這一觀點[4-7]。為控制農戶的過量施藥行為,相關研究表明,文化程度的提高顯著規范了農戶的施藥行為[8];風險規避程度較高的農戶會選擇使用種類更多、價格更高的農藥,并會加大施用量[9];隨著家庭人口數與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農戶更傾向于施用高劑量農藥[10];土地面積的增加可以降低單位面積土地施藥量,而土地細碎化程度則會削弱這一影響[11];基于損失厭惡,農業收入占比高的農戶會更傾向于過量施藥[12];加入合作社會顯著減少農戶的過量施藥行為[13];病蟲害壓力對農戶的過量施藥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14];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會提升農戶的農藥施用強度[15];農業技術培訓能夠顯著降低農戶的農業化學投入品施用量,并具有一定的技術擴散作用[16]。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從多角度分析了影響農戶過量施藥行為的因素,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對象,已有研究多集中對經濟作物種植戶施藥行為的研究,而對種植面積更廣闊,對生態環境影響更持久的糧食作物種植戶的施藥行為少有研究;第二,方法學,已有研究側重于對施藥行為顯著性因素的判斷及其作用方向與程度的探究,而缺乏對各因素間關聯關系和遞階結構的分析。鑒于此,筆者以糧食作物小麥為例,首先運用Logit模型分析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影響因素,再運用解釋性結構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分析影響因素之間存在的關聯關系和遞階結構,并提出規范麥農施藥行為的建議,以期為實現中國農業的綠色、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1 概念界定、分析框架與變量選擇
1.1 概念界定
麥農的施藥行為是指在小麥種植過程中,在病蟲害壓力下,麥農通過施用農藥的方式來保護小麥生長發育,維持小麥產量,以確保自身收入的一系列活動。舒爾茨認為,農戶作為理性的“經濟人”,會在帕累托最優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與生產要素,從而獲得最大利潤。然而在實際的生產過程中,農戶的行為是復雜的,無法完全用經濟因素解釋。結合已有研究,該研究將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內容劃分為兩方面:①施藥量過多行為,即在施藥過程中所使用的農藥量超出說明書規定的標準用藥量;②施藥次數過多行為,即農藥施用次數超出農作物生長所需次數(根據小麥用藥實際,參考相關專家及植保專業人員指導意見,規定小麥農藥施用次數超過4次為過多)。只要麥農存在一種及以上上述行為,則判斷該麥農過量施藥。
1.2 分析框架
基于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概念和內容,結合已有研究成果,將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影響因素劃分為農戶(個體與家庭)特征變量、經營特征變量、認知特征變量和外部條件變量。
農戶特征包括農戶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2類。其中,個體特征包括年齡、文化程度和職業選擇。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文化程度的提高,麥農對糧食安全問題更加關注,發生過量施藥行為的可能性越低。兼業麥農投入小麥生產勞動時長較短,可能更傾向于過量施藥。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數和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越多,農戶生計壓力越大,為保證小麥產出而更依賴農藥投入。家庭收入越高,可能會造成麥農對生產資料投入量的忽視,從而更可能發生過量施藥。
經營特征包括種植規模、專業化程度和組織狀況。其中,種植規模用小麥種植面積表示,專業化程度用農業種植收入所占總收入的比重來表示,組織狀況指麥農是否加入當地種植合作社。種植規模大的麥農可以獲得規模經濟效益,降低單位面積土地上的農藥施用量。專業化程度越高的麥農,對小麥種植收入的依賴性越高,越傾向于投入過量的農藥等生產要素。加入種植合作社的麥農,可從合作社中得到更多有關農藥施用所需的知識、技術和信息,降低過量施藥的可能性。
認知特征包括農藥管理政策認知、農藥防治效果認知和農藥殘留危害認知。其中,農藥管理政策指包含《農藥管理條例》在內的一系列農藥政策,農藥殘留危害包括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和對生態環境的危害。一般而言,高水平的認知是規范行為實施的關鍵。對農藥管理政策認知越準確,對農藥防治效果越認同,對農藥殘留危害認知越清晰的麥農,其發生過量施藥行為的概率越低。
外部特征變量包括病蟲害壓力和施藥技術培訓。其中,病蟲害壓力指麥田病蟲害發生的嚴重程度。當麥農所受病蟲害壓力加大時,更傾向于過量施用農藥。有效的施藥技術培訓增加麥農對農藥用法、用量的了解,從而規范農藥施用行為。
1.3 變量選擇
根據上文分析框架,該研究將5類13個變量引入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計量經濟模型。變量的名稱、含義及其預期方向詳見表1。
2 模型構建與數據來源
2.1 二元Logit模型 麥農農藥施用是否過量(y)是一個二分類變量,因此選用二元Logit回歸模型對影響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顯著因素進行研究。將麥農存在過量施藥行為定義為Z=1,不存在過量施藥行為定義為Z=0。假定Z=1的概率為P,則二元Logit模型的分布形式為:
P=F(Z)=11+e-Z(1)
其中,Z是自變量x 1,x 2,…,x n的線性組合,根據前文研究假設,麥農是否選擇過量施藥受農戶(個體與家庭)特征變量、經營特征變量、認知特征變量及外部條件變量共5類13個變量的影響,令b i表示第i個影響因素的回歸系數,則:
Z=b ix i=b 0+b 1x 1+b 2x 2+…+b 13x 13(2)
根據式(1)、(2)進行變換,得到如下的Logit函數形式:
y=ln(P1-P)=b 0+b 1x 1+b 2x 2+…+b 13x 13+ε(3)
式(3)中b 0為回歸截距,ε為隨機干擾項。b 0和b i(i=1,2,…,13)的值采用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估計。
2.2 ISM模型
ISM模型以定性分析為主,通過利用專業人員經驗知識,借助現代計算機技術,構建多級遞階結構模型,明確復雜經濟系統中各因素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該研究選用ISM模型對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影響因素間的關聯關系和遞階結構進行研究。其步驟為:
假設影響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因素有k個,用S 0表示麥農是否存在過量施藥行為,S i(i=1,2,…,k)表示影響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k個顯著影響因素。根據ISM分析方法的具體步驟,作出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及其影響因素間的邏輯關系圖。
根據式(4)所定義的構成元素,構建影響因素間的鄰接矩陣R。
a ij=1,S i與S j有關0,S i與S j無關(i,j=0,1,…,k)(4)
根據式(5)計算得到可達矩陣M。
M=(R+I)λ+1=(R+I)λ≠(R+I)λ-1≠…≠(R+I)2≠(R+I)(5)
式(5)中,I為單位矩陣,2≤λ≤k。
根據式(6)確定最高層級因素L 1。
L i={S i|P(S i)∩Q(S i)=P(S i);i=0,1,…,k}(6)
式(6)為P(S i)可達集,Q(S i)為先行集。P(S i)和Q(S i)的表達式如下:
P(S i)={S i|m ij=1},Q(S i)={S j|m ji=1}(7)
式(7)中m ij和m ji均是M的元素。
在原可達矩陣M中刪除L 1中因素對應的行與列,得到矩陣M′。對M′重復進行式(6)與式(7)操作,得到第二層的L 2的因素,依此類推,直至求得所有層級的因素。最后,用有向邊連接同一層次及相鄰層次間的因素,即可得到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影響因素間的關聯關系及遞階結構。
2.3 數據來源和樣本情況 該研究的數據由山東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調研團隊于2019年暑假期間對山東省西南地區的牡丹區、鄄城縣、鄆城縣等3個縣區麥農施藥行為進行的實地調查獲得。為保證數據的科學性與準確性,調查采用分層逐級抽樣和隨機抽樣的方法選取樣本,在每個縣(區)按照經濟發展水平由高至低選擇3個鄉鎮,并在每個鄉鎮按同樣的方法選擇3個村,在每個村隨機選擇12~18名具備施藥經驗的麥農進行訪談。此次調查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有效問卷375份,問卷有效率93.75%。其中,257位麥農表示不存在過量施藥行為,占68.5%;118位麥農表示存在過量施藥行為,占31.5%。
從樣本農戶基本特征來看,被調查者多為男性,占63.2%;年齡偏大,50歲以上占75.9%;文化程度相對偏低,學歷在初中以下者占63.9%;兼業農戶占36.2%;家庭人口少于4人的占69.0%;家庭年收入呈橄欖狀分布,78.5%的農戶家庭年收入>1萬~5萬元;調查對象多為小規模經營主體,種植規模在0.2~0.533 hm2者占65.2%;農業收入比重小于60%者占87.3%;有18.9%的麥農加入了種植合作社。總體而言,樣本特征符合現階段下中國小農的一般特征,具有較高的代表性和可信度。根據375份調查問卷,得出各變量的描述統計特征,詳見表1。
3 結果與分析
3.1 估計結果
3.1.1 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影響因素分析。該研究運用SPSS統計軟件,對375份問卷調研數據進行Logit回歸處理。首先,考慮所有自變量對(3)式進行估計,得到模型 Ⅰ;隨后,剔除在回歸中不顯著的變量,得到模型 Ⅱ。具體數據詳見表2。在模型 Ⅱ 的回歸結果中,-2對數似然值為365.144,差異顯著性水平為0.000,具有統計學意義;Hosmer and Lemeshow Test的檢驗值為0.861>0.05,整體擬合效果良好。由模型 Ⅱ 可知,除常數項外,共有文化程度、職業選擇、種植規模、專業化程度、農藥防治效果認知、病蟲害壓力、施藥技術培訓等7個變量通過顯著性檢驗。
3.1.2 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影響因素的遞進關系分析。將文化程度、職業選擇、種植規模、專業化程度、農藥防治效果認知、病蟲害壓力和施藥技術培訓7個顯著變量分別用S 1,S 2,…,S 7表示。在分析、討論并咨詢有關專家學者和植保專業技術人員意見的基礎上,得出上述7個影響因素間的邏輯關系,見圖1(列因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行因素記作“A”,行因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列因素記作“V”)。
根據圖1和(4)式做出影響因素間的鄰接矩陣R(略);運用 Matlab軟件,結合式(5)對鄰接矩陣R進行變換,得到可達矩陣M(見(8)式)。
對可達矩陣M進行層次分解。由式(6)和式(7)得到L 1={S 0},以此類推,得到L 2={S 5,S 6},L 3={S 4,S 7},L 4={S 1,S 2,S 3}。根據L 1、L 2、L 3、L 4重新排列M,得到排序后的層次結構矩陣N。
由式(9)可見,S 0處于第一層,S 5和S 6處于第二層,S 4和S 7處于第三層,S 1、S 2和S 3處于第四層,構成了一條具有邏輯關系的影響因素鏈。用有向邊連接同一層次和相鄰層次間的影響因素,即得到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影響因素間的關聯關系與遞階結構,詳見圖2。
3.2 結果討論
由圖2可知,在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影響因素中,農藥防治效果認知、病蟲害壓力是表層直接因素,專業化程度、施藥技術培訓是中層間接因素,文化程度、職業選擇、耕地面積是深層根源因素。
農藥防治效果認知和病蟲害壓力是影響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表層直接因素。農藥防治效果認知影響系數為-0.892,機會比率為0.410,表明農藥防治效果認知對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行為學理論認為,認知影響態度,態度決定行為。相較于認為現有農藥防治效果良好的麥農,認為現有農藥防治效果不好的麥農往往傾向于加大農藥施用量,以此來保證小麥產量的安全。病蟲害壓力的影響系數為0.950,機會比率為2.585,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病蟲害發生增加區域麥農出現過量施藥行為的概率會增加158.5%。這是因為病蟲害壓力加大的麥農,為了起到消滅病蟲害、保護小麥成長的效果而加大了農藥施用量。此外,農藥防治效果認知受到來自中層間接因素與深層根源因素的直接或間接影響。
施藥技術培訓和專業化程度是影響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中層間接因素。施藥技術培訓的影響系數為-1.463,機會比率為0.232,表明施藥技術培訓對麥農的過量施藥行為具有顯著負向影響。施藥技術培訓可以增強麥農對農藥用法、用量的了解,是提高農藥施用合理性的重要手段,定期舉辦施藥技術培訓,將有助于減少過量施藥行為。專業化程度的影響系數為0.426,機會比率為1.531,表明專業化程度越高,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發生概率會提高53.1%。可能的解釋是專業化程度高的麥農收入結構單一,基于損失厭惡,更傾向于通過增加農藥施用量的方式來保證農業種植收入的穩定。此外,上述2個因素均受深層根源因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文化程度、職業選擇和種植規模是影響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深層根源因素。文化程度的影響系數為-0.549,機會比率為0.578,表明文化程度對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具有顯著負向影響。文化程度的提高可以減少麥農盲目追加生產投入的現象,提升施藥技術培訓的效果,使麥農施藥更具科學性與針對性。職業選擇的影響系數為0.633,機會比率為1.884,表明相較于純農業麥農,兼業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概率會高出88.4%。這是因為與純農業麥農相比,兼業麥農的農業勞動投入時間會減少,根據要素替代,麥農會通過增加農藥施用量來彌補減少的勞動量。種植規模的影響系數值為-0.461,機會比率為0.631,表明隨著種植規模的擴大,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概率會顯著降低。從市場角度來看,市場規制對種植規模廣、產量高的農戶更具約束力,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根據規模經濟規律,種植規模大的麥農可以更好地應用農藥等生產要素,并采用更先進的生產技術,降低單位面積土地農藥施用量。
綜上所述,7項顯著性影響因素既獨立發揮作用,又相互關聯,形成完整的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影響因素系統,沿著“文化程度、職業選擇、種植規模”→“施藥技術培訓、專業化程度”→“農藥防治效果認知、病蟲害壓力”的正向傳導關系,從源頭上減少麥農的過量施藥行為。
根據模型 Ⅱ 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麥農年齡、家庭人口數、家庭年收入、組織狀況、農藥殘留危害認知、農藥管理政策認知等6項因素對過量施藥行為沒有顯著影響,其原因如下:小麥作為傳統糧食作物,在長期生產過程中形成了其固有模式,導致年齡的影響作用被淡化。與種植經濟作物相比,種植糧食作物利潤較低,對家庭生計影響較小,造成了家庭人口數和家庭年收入變量的不顯著。調查區域內的合作社起步較晚,運營尚不完善,沒能發揮好規范麥農施藥行為的作用,因此組織狀況對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影響不明顯。農藥殘留危害認知和農藥管理政策認知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原因可能是,即使麥農已正確認知農藥管理政策與農藥殘留危害,但由于過量施藥造成后果的“外部性”,麥農依然會選擇過量施藥。
4 結論與政策啟示
農戶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微觀行為主體,其行為的轉變是化肥、農藥等農資品實現“減量化”的關鍵。該研究基于第一手實地調研數據,把Logit模型與ISM模型結合起來,實證分析了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影響因素及其遞階結構。研究結果表明:文化程度、種植規模、農藥防治效果認知和施藥技術培訓對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職業選擇、專業化程度、病蟲害壓力對麥農過量施藥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在這7個影響因素中,病蟲害壓力、農藥防治效果認知是表層直接因素,專業化程度、是否參加施藥技術培訓是中層間接因素,文化程度、職業選擇、種植規模是深層根源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提出以下減少麥農過量施藥行為的建議:第一,通過電大、函授和培訓等多種方式,提高農戶科學文化素質與施藥技術水平;第二,促進適度規模經營,實現小麥種植規模化、專業化;第三,充分發揮小麥保險作用,減少麥農對農藥的依賴;第四,加大低毒高效農藥研發力度,提高農藥防治效果;第五,促進農藥合理輪換與混配,降低麥田有害生物的抗藥性。
參考文獻
[1]
SCHREINEMACHERS P,TIPRAQSA P.Agricultural pesticides and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in high,middle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J].Food policy,2012,37(6):616-626.
[2] 王常偉,顧海英.市場VS政府,什么力量影響了我國菜農農藥用量的選擇?[J].管理世界,2013(11):50-66.
[3] ZHANG C,HU R F,SHI G M,et al.Overuse or underuse? An observation of pesticide use in China [J].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5,538:1-6.
[4] 姜健,周靜,孫若愚.菜農過量施用農藥行為分析:以遼寧省蔬菜種植戶為例[J].農業技術經濟,2017(11):16-25.
[5] HOI P V,MOL A P J,OOSTERVEER P,et al.Pesticide use in Vietnamese vegetable production:A 10-year stud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2016,14(3):325-338.
[6]? HUANG J K,HU R F,ROZELLE S,et al.Transgenic varieties and productivity of smallholder cotton farmers in China[J].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2,46(3):367-387.
[7] 金廣,程紅莉,宋寶清.糧食安全·農戶行為與發展對策研究:基于湖北省農戶的調研數據分析[J].安徽農業科學,2016,44(1):289-291,297.
[8] ABHILASH P C,SINGH N.Pesticide use and application:An Indian scenario[J].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2009,165(1/2/3):1-12.
[9] 米建偉,黃季焜,陳瑞劍,等.風險規避與中國棉農的農藥施用行為[J].中國農村經濟,2012(7):60-71,83.
[10] 李昊,李世平,南靈,等.農戶農藥施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來自魯、晉、陜、甘四省693份經濟作物種植戶的經驗證據[J].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8,32(2):161-168.
[11] 高晶晶,史清華.農戶生產性特征對農藥施用的影響:機制與證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9(11):83-99.
[12] 朱淀,孔霞,顧建平.農戶過量施用農藥的非理性均衡:來自中國蘇南地區農戶的證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4(8):17-29,41.
[13] 王雨濛,于彬,李寒冬,等.產業鏈組織模式對農戶農藥使用行為的影響分析:以福建省茶農為例[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20,19(3):271-279.
[14] ROBINSON E J Z,DAS S R,CHANCELLOR T B C.Motivations behind farmers pesticide use in Bangladesh rice farming[J].Agriculture & human values,2007,24(3):323-332.
[15] 張超,孫藝奪,孫生陽,等.城鄉收入差距是否提高了農業化學品投入?——以農藥施用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19(1):96-111.
[16] 應瑞瑤,朱勇.農業技術培訓方式對農戶農業化學投入品使用行為的影響:源自實驗經濟學的證據[J].中國農村觀察,2015(1):5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