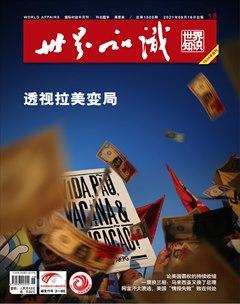黎巴嫩敲響中東政治危機的警鐘
牛新春
最新的世界銀行報告認為,黎巴嫩已經陷入1850年以來全球嚴重程度排名第三的經濟危機,僅次于1930年的西班牙經濟危機和1926年的智利經濟危機。黎巴嫩經濟危機始于2019年,2020年演變成國家債務違約。目前黎巴嫩鎊與美元的匯率也從1500鎊兌1美元貶到23000鎊兌1美元,民眾財富轉瞬間縮水90%以上。民眾最低月工資從450美元降到35美元,貝魯特一個警察的月工資還不到100美元。因為價格變化太快,價目表都來不及修改,所以一些商店、飯店干脆不再出示價目表。為解決吃飯問題,軍隊開始經營旅游項目,乘坐軍用直升機觀光一次收費150美元。真主黨總書記納斯魯拉還呼吁市民在窗臺、陽臺上種植蔬菜,以渡過難關。
在中東,黎巴嫩本不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歷史上曾因經濟發達、族群多元、社會開放、教派分權共治等特色,被稱為“中東小巴黎”。2018年人均名義GDP已達8012美元,現在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場經濟危機,實質上卻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危機。長期以來,中東危機往往同外國入侵、內戰、教派沖突、恐怖主義相關聯,但黎巴嫩卻是個顯著的例外。最近20年黎巴嫩在上述問題上相對平靜,卻遭遇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但從經濟角度看,黎巴嫩危機并非深不可測。黎巴嫩是一個人口600多萬、領土一萬多平方公里的小國,目前負債83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歐、海灣國家都愿意施以援手,前提是黎巴嫩必須有一個可靠的政府。而這恰恰是黎巴嫩的軟肋,黎巴嫩政府因內斗長期處于癱瘓狀態,2020年8月4日貝魯特大爆炸后,總理哈桑·迪亞布率內閣總辭職,迄今三次組閣均告失敗。即便國際社會想施以援手,都不知道該把錢交到誰手里。2021年7月15日前總理哈里里放棄組閣權時說:“愿上帝保佑這個國家”,似乎這是黎巴嫩唯一的出路了。
其實,黎巴嫩政治危機不是中東的個案,而是具有相當廣泛的普遍性。“阿拉伯之春”十年后,利比亞、敘利亞、也門仍然處在內戰狀態,阿爾及利亞、蘇丹、伊拉克、黎巴嫩四國2020年因大規模街頭示威而發生政府更迭。突尼斯曾是“阿拉伯之春”僅存的一個“花骨朵兒”,但過去十年也歷經了九屆政府更迭,2021年7月25日總統突然解除總理職務、解除議會,國家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這個“花骨朵兒”能夠開花結果的前景日趨暗淡。
在中東幾個大國里,伊拉克2005年議會選舉投票率約70%,2018年下降到44.5%;伊朗2017年總統選舉投票率約73%,2021年下滑到48%;埃及2012年總統選舉投票率約52%,2018年跌到41%。投票率大幅下滑,反映出老百姓對政治的態度越來越冷淡。十年前,中東街頭的群眾要民主、要選舉,近兩年街頭的群眾仍然對現任領導人、現行體制不滿,卻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黎巴嫩最具典型性,人們不想要政黨、不想要政府甚至不想要國家,甚至有人提出要求法國重新接管黎巴嫩。這是人民對政治絕望的極端體現。政黨、政府是人類政治文明的主要成果,中東卻面臨“去政治化”的強大潮流,人們厭惡政治人物、政黨、政府甚至國家。正因為如此,去年上臺的蘇丹、伊拉克、黎巴嫩領導人均是清一色的“政治素人”。
1952年后“復興社會主義”席卷中東,1979年后“政治伊斯蘭主義”風生水起,1990年后“新自由主義”要終結歷史,近百年來各種思潮在中東你方唱罷我登場,可惜沒有一個經得住時間的考驗。
黎巴嫩危機不僅是中東政治危機的縮影,而且具有全球性象征意義。半個世紀以來在“新自由主義”的語境下,國際社會普遍相信政治參與是改善國家治理能力的前提。但在全球各地數以億計的人民為新自由主義試驗付出沉重代價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相信,沒有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民主、自由是脆弱的,只能帶來混亂和災難,國家治理能力才是前提和基礎。可見全球性政治發展不僅面臨現實挑戰,而且迫切需要理論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