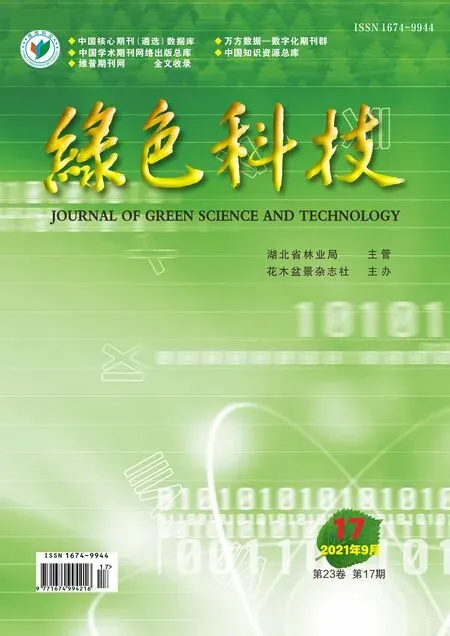空間·戀地·權(quán)利:校園人地關系研究中的三個側(cè)重
周潔瑤,吳 博
(西安科技大學 藝術(shù)學院,陜西 西安 710600)
1 引言
都市環(huán)境區(qū)別于鄉(xiāng)村環(huán)境的最大特質(zhì)在于人地關系從供給轉(zhuǎn)向索取,人們不再只限于攫取土地的表面價值而是追求更為全面而立體的多角度土地及其上方空間。對于土地態(tài)度的變化時刻被社會、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等因素影響,人地關系的變化也不僅限于改善,同時也有著分割和矛盾。對于人地關系的研究是關乎人文地理領域前沿發(fā)展很重要的一個方向[1~3],同時也與城鄉(xiāng)規(guī)劃、建筑學、生態(tài)學、心理學、風景園林學、地理學等學科有著緊密關系。不同的視角對其闡述會有不同的解讀,其中地理學與人地關系最為密切,地理學的研究核心即為人地關系地域系統(tǒng)。早在中國古代,人類通過生產(chǎn)活動對周圍環(huán)境逐步認識,對早期的地理知識進行積累。春秋戰(zhàn)國時期我國出現(xiàn)了多種人地觀,如天人感應、因地制宜等思想。此后,大量人文地理著作出現(xiàn),可反映中國古代社會人類十分重視人類社會活動等地理問題[4]。中國近代時期,錢學森提出要在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匯合的基礎上建立地理科學體系的見解。在西方近代時期,亦有學者對地理學與人地關系內(nèi)在規(guī)律進行探索,提出人地關系的研究還關系到地理學本身的生存與發(fā)展,同時對促進我國向前發(fā)展提供最大的動力[5]。從遠古至近代地理學的發(fā)展,反映地理學和人地關系間是緊密聯(lián)系的。馬克思認為人類活動和地理環(huán)境存在一定的關聯(lián)并相互作用,雙方通過物質(zhì)交換產(chǎn)生聯(lián)系。人對地具有依賴性,地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唯一物質(zhì)基礎或活動空間,兩者之間起相互制約的作用[6]。隨著城市化的發(fā)展,人地關系研究對我國具有巨大的現(xiàn)實意義。校園作為人地關系的一種表征,是體現(xiàn)人類的文化情感與場所發(fā)生關聯(lián)的重要載體,其中空間[7]、戀地[8]和權(quán)利[9]對促進校園空間人地關系和諧具有重要作用。
2 校園人地關系
2.1 城市土地衍生的人地關系
人地關系是人們對人類與地理環(huán)境之間關系的一種簡稱,指人類社會生存發(fā)展或人類活動對地理自然環(huán)境的關系[10]。縱觀歷史和當今發(fā)展,人地關系多指鄉(xiāng)村環(huán)境背景下,人類和自然環(huán)境間的關系。鄉(xiāng)村土地的人地關系從泥土中來,彼此為供給關系。長期以來,農(nóng)民習慣通過觀察自然條件、土地形貌來判斷適宜的耕作時間,可在古文中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體現(xiàn),這是基于經(jīng)驗積累和祖輩傳授。由此,人地關系的長期穩(wěn)定發(fā)展造就了鄉(xiāng)村土地以生長性為根本目的。
而城市環(huán)境下,權(quán)利、空間和戀地對城市人地關系變化有著緊密聯(lián)系。從權(quán)利角度看,空間的生產(chǎn)過程亦是城市居民追求城市的過程[11]。城市化發(fā)展,人與土地的互動方式被極大的擴展,人類不再僅限于單純的游憩和逛街,人作用于土地的形式發(fā)生了改變,不再是以耕作的方式與土地發(fā)生互動,而是對土地的不斷占有,并通過限制他人進入空間的時間減少他人享用空間的權(quán)利。這種具有時效性的占有,滿足了人們享用空間時的心理。當人們享用的空間在所處社會占據(jù)一定的階級地位,身處其間的人群便和城市土地空間構(gòu)成了特殊聯(lián)系。從戀地的角度看,人類活動的介入,純粹的地理空間逐漸“人文化”,不再是空洞、乏味的空間。“空間感”是每個人潛在的本能,是個體對自己熟悉的空間的印象,對城市人地關系的影響也有好壞之分[12]。從空間的角度看,空間是產(chǎn)生權(quán)利、形成“空間感”的前提。空間的合理規(guī)劃,有助于城市空間地域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
2.2 校園人地關系
校園人地關系從城市人地關系衍生而來,是城市規(guī)劃發(fā)展的一部分。校園環(huán)境,指學校教學或生活的用地范圍,可理解為人類在校園學習、活動、工作、商業(yè)等所處的空間,并不是單一功能的游憩空間,以教研性質(zhì)為主組構(gòu)而成的綜合環(huán)境,其本質(zhì)為知識性空間,在城市區(qū)域上具有超然的地位。人們通過維護和涵養(yǎng)校園環(huán)境,反哺于人一定的由校園環(huán)境帶來的社會身份。基于校園區(qū)域所處的社會方位、土地自身的經(jīng)濟價值和政治屬性對土地價值具有一定的影響,可借鑒通過社會力量共同籌建的西湖大學。相反,一些院校因地域偏僻,所處區(qū)域缺少一定的經(jīng)濟空間配置性,對土地空間的認同感便降低。這種由于校園土地自身的諸多因素所形成的空間在與人進行互動的同時,可給人身份上帶來認同感和同一感,進一步激發(fā)人與校園土地關系的親密性。
3 物理空間視角下的校園人地關系
3.1 空間圍合影響校園的空間肌理
校園物理空間,其圍合程度與校園周邊環(huán)境有著緊密關聯(lián),超越這一范疇會架空校園內(nèi)部空間的功能性,使得校園的社區(qū)性下降。校園空間肌理,即校園所有建筑、平面布置的總和,例如,道路、地面鋪裝、植物、空間圍合邊界等。前者對后者產(chǎn)生影響即校園空間圍合影響校園空間肌理,學校可通過拓寬校園道路,對校園前廣場或開闊大草坪進行景觀提升改造、減少廢棄建筑增加新建筑等校園景觀改造手段進行空間圍合,改變空間肌理。通過改變空間肌理,將校園空間以社區(qū)形式劃分,有助于提升人和土地關系,但目前校園社區(qū)空間被社會其他形式的物理空間逐漸占據(jù),部分高校為追求宏大的空間尺度致使校園存在許多消極空間(閑置空間),大量的綠地和閑置場地占據(jù)了學生日常活動空間,校園不再是唯一的學生社區(qū),學生可以從社會找到更多可以替代校園社區(qū)空間的形式。從物理空間的視角下,如何提升校園的社區(qū)感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3.2 在地化的可利用形式轉(zhuǎn)變
校園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自由,這種強制性的在地化很難從根本上進行改變。校園在地化后并沒有給予學生更多的空間利用,缺失了部分固有的功能。基于校園在地化所帶來功能缺失或混亂的現(xiàn)象,可通過利用校園閑置空間創(chuàng)造有意義的戶外空間,進一步激活校園空間活力,提升校園社區(qū)感、校園質(zhì)量。例如,清華大學對勝因院前灰色空間帶進行改造升級,將原始單一的線性空間轉(zhuǎn)換可停留使用并具有景深的積極空間;同濟大學對可利用的屋頂建造屋頂花園,為師生提供登高小憩場所。對校園可利用空間進行重組改造,提升校園景觀,學生對空間產(chǎn)生積極的“地方感”,激發(fā)校園內(nèi)部空間活力,對促進校園人地關系和諧具有重大意義。
3.3 空間形式?jīng)Q定人地關系
校園被社會的接納程度以及自身的空間形狀和體積決定了校園在廣義范圍內(nèi)的使用情況,校園規(guī)劃過于松散或最終形態(tài)過于抽象,不利于人地關系的和諧發(fā)展,會出現(xiàn)局部區(qū)域重點被關照,另一部分處于閑置狀態(tài)。例如,美國俄勒岡大學總體規(guī)劃中,運用一套獨特的校園規(guī)劃設計模式語言,開放的分片式空間形式,倡導師生積極參與空間活動,并不斷地自我診斷和協(xié)調(diào),從而建設一個有機的社區(qū)型校園;西湖大學規(guī)劃主要呈環(huán)形分布(圖1),形成相互貫通和協(xié)作的空間,目的為鼓勵不同領域之間合作與交流,有利于促進校園人地關系。

圖1 西湖大學鳥瞰圖及規(guī)劃分布
4 戀地情結(jié)與人地關系
“戀地情結(jié)”概念最早由法國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于1957年提出,后來由著名地理學家段義孚對此概念進行系統(tǒng)性闡述,成為目前較為廣泛引用的概念,其主要闡述人地間如何相依共存,發(fā)掘人類經(jīng)驗的復雜性及心理感受。通過研究人類對環(huán)境的價值觀、感知和態(tài)度來探討人地之間的關系[13]。人類的“戀地情結(jié)”,多指的是“關系性的空間”,在人類與空間產(chǎn)生互動下,形成空間邊界,對空間范圍產(chǎn)生不同情感。無論從城市更迭迅速的視角、人居環(huán)境改造、校園空間等視角下,皆可看到兩者相互之間緊密聯(lián)系、互相影響。
4.1 戀地與逃避
校園空間具有明確的邊界,其空間的圍合程度要求不同,空間層次不同。在不同性質(zhì)的使用空間下,人們對物理空間認知的感覺便不同。人的戀地細微而精妙,在校園內(nèi),學生根據(jù)不同的需求去選擇空間,若所選的空間由于個人心理原因產(chǎn)生厭惡感或所建設空間與學生心理使用規(guī)范標準不符、空間景觀效果較差等,人們往往選擇的便是逃避。從心理學的視角分析,學生需要可分為生理、安全、交往等需要。學生根據(jù)自身的需要選擇適當?shù)目臻g環(huán)境和層次。例如:交往需要可分為友情需要或愛情需要,其需要不同對空間層次性要求也不同。友情需要可理解為朋友聚會或團隊聚會聯(lián)誼,所需的交往空間較為開放,具有公共性,能夠滿足團體間的溝通。相反,若為愛情需要,則所需的交往空間私密性較高,有一定限定感。
4.2 空間支配到城市征服
前者是被動的,后者是主動的。人類基本的空間使用功能是空間支配的,例如:工作、教育、生活等,被限制在指定空間內(nèi)進行,處于被動狀態(tài)。但人類天生對土地具有控制的欲望和情感的需要,對空間進行征服。人類雖被分配在不同空間里活動,但當具有可支配時間,人們會擺脫空間支配的束縛,對城市其他環(huán)境進行征服,例如:在城市其他環(huán)境游玩、觀賞等。空間支配轉(zhuǎn)向城市征服時,人地關系隨之發(fā)生改變,被動轉(zhuǎn)為主動,同時在主動空間內(nèi)活動時產(chǎn)生“戀地”,對人地關系產(chǎn)生影響。
4.3 室外空間是室內(nèi)空間的外延
室內(nèi)空間是人類工作、學習等的建筑內(nèi)部活動空間。室內(nèi)空間對人的視角、視距等方面具有一定限制,具有有限性;在其之外的稱為室外空間,具有無限性。室內(nèi)外空間之間具有滲透性和層次性,人類基本的空間使用功能多在室內(nèi)空間進行,室外空間是室內(nèi)空間的延展,同時室內(nèi)空間是人地關系的核心。人的心理需求是無止境的,但都具有渴望共聚的本性和心理,希望將自身經(jīng)驗放置于外部自然空間得以印證,通過實踐檢驗真理;將情感衍生到室外空間,擺脫冷酷的室內(nèi)空間等,對城市征服。例如:在校園中,學生通過教學活動將所得知識放置于戶外空間進行驗證,并通過實踐加深理論知識印象。同時課余可支配時間內(nèi)常到室外空間,即校園外部進行游憩娛樂,將活動、情感延展到室外空間。
5 權(quán)利在人地關系中的影響
任何人群都具有利用空間的愿望,此舉源于人類對于自我肢體的掌控,但肢體掌控的空間范圍是有限的,肢體是意識的延伸,因而對于肢體延伸不到的地方,人們渴望獲得空間的權(quán)利與支配。掌握更多空間的權(quán)利,將有助于人類實現(xiàn)自我價值認同。
5.1 空間具有時空性
空間是具有屬性的,隨著時間跨度,空間會隨之重新規(guī)劃,人的權(quán)利發(fā)生改變,對人地關系產(chǎn)生影響。例如:古時周代“宵禁”的嚴格管制到宋朝的自由開放,隨著時間變化,人們享用空間的權(quán)利逐漸得到釋放,人地關系的和諧促進唐宋時期的經(jīng)濟繁榮。
時代的發(fā)展,城市破敗上個世紀的廉租房、大型生產(chǎn)工廠內(nèi)居住區(qū)醫(yī)院、陳舊的校舍等,這些具有時空痕跡的空間雖破敗,但人類依舊以資產(chǎn)的角度看待,因為空間的在地性會使土地發(fā)生流轉(zhuǎn),這一過程便具有商品屬性,這也符合人類天生具備占有的欲望和驅(qū)使的本質(zhì),對土地進行再次修復利用,掌握更多的空間權(quán)利。
5.2 空間是流性的
其隨著城市的發(fā)展向周邊漸進、隨機、離散的蔓延,無法界定城市環(huán)境條件下“空間”的真實樣貌,這種獨特性和神秘性激發(fā)并提高了空間權(quán)利的地位。在校園邊界中,學生是流動邊界的主要群體。進入空間的內(nèi)部,學校權(quán)利提高,并利用對應的權(quán)利對校園進行管治。
5.3 空間的權(quán)利具有限制的功能
空間的結(jié)構(gòu)規(guī)劃限制人類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觀進行游覽觀賞。基于校園在地化后,校園的空間結(jié)構(gòu)具有一定的交通屬性和政治屬性,通過一定的介入性,對學生線路進行干預。但這種干預符合人類的特質(zhì),符合人類自身對空間的使用習慣和要求,可對學生給予便利交通的同時帶來優(yōu)美的校園景觀路線,可理解為軟性的限制。
6 案例討論
針對西安科技大學秦漢校區(qū)校園的現(xiàn)存問題,分別從空間、戀地、權(quán)利三個側(cè)重點出發(fā),對校園景觀提出規(guī)劃設計建議。通過對秦漢校園的實地考察可得,校園空間的圍合對校園內(nèi)部產(chǎn)生較大的影響,周圍環(huán)境較為偏僻。整體校園規(guī)劃呈矩形分布,內(nèi)部空間聯(lián)系性單一、功能性較弱,且校園內(nèi)部的空間圍合層次單一;校園規(guī)劃單調(diào),學生常被困于枯燥的空間內(nèi),對外部城市環(huán)境向往的欲望加強,不利于校園人地關系和諧;空間使用功能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學生介入空間的權(quán)利,功能的缺失及粗糙的校園肌理,放大了空間對人們的限制,從而使學生積極性下降,影響了校園人地關系(圖2、圖3)。

圖2 西安科技大學秦漢校園局部鳥瞰

圖3 校園場地現(xiàn)狀
6.1 空間圍合、空間形式和可利用空間的轉(zhuǎn)換
校園在地化后可利用閑置的空間豐富校園環(huán)境,對功能缺失部分進行填補,增設校園活動休憩空間、戶外運動空間、集會空間等,增強校園空間底圖關系(圖4、圖5)。利用建筑前的灰色空間,創(chuàng)造師生交流空間,同時增添校園景觀,豐富空間層次和豎向設計,給予學生私密性空間。在空間形式上可采用折線型,增添場地趣味性,在道路通達性強的前提下豐富校園肌理。

圖4 總體規(guī)劃設計
6.2 增設戀地情結(jié)與“記憶場所”空間
人對空間的感知,在地方生存中的主觀性和情感性,形成戀地情結(jié)的地理因子,即地方感。人類的感知是動態(tài)而非靜止的,是開放而非封閉的。人的感知可隨著地方的環(huán)境變化或人文活動變化而變化。因此,可利用人類的“地方感”,對校園內(nèi)部可利用的閑置空間進行轉(zhuǎn)換,通過豐富綠化種類多樣性、校園景觀文化性、豎向設計豐富性、空間層次多樣性等,創(chuàng)造有意義的戶外空間,例如,文創(chuàng)園、創(chuàng)造建筑前灰色休閑空間等,增設“記憶場所”空間,提高校園“社區(qū)性”。

圖5 功能分區(qū)
6.3 校園空間權(quán)力的釋放與平等
校園垂直型權(quán)力分布,使學生一定程度上失去參與學校公共管理的機會,學生積極性下降,促使校園內(nèi)部空間活動性弱化。對此,秦漢校園內(nèi)部可在豐富校園環(huán)境的同時,增添有效性的校園活動和大賽,例如:植樹節(jié)種植活動、校園景觀規(guī)劃提升設計大賽等;設立共享型空間,學生和教師共同分享;豐富空間層次,例如:添加私密性強的休憩空間、開放型的聚會或戶外運動活動空間等,學生可依需求選擇性地介入空間;豐富校園肌理,交通路線富含趣味性,緩解空間給人帶來的限制感。
7 結(jié)語
本文利用定性研究和案例研究的方式對人地關系在校園環(huán)境下的處境情況作出初步的理解與分析,主要是從物理空間、戀地情結(jié)、權(quán)利三個維度進行闡述。人地關系是具體表征人類與自然關系的一種重要顯性要素,通過建立協(xié)調(diào)的人地關系,人類能夠選擇并適宜地去改造土地的形態(tài)及其空間,不僅是處理土地緊張和土地矛盾的良好方式,同時,對于回歸自我,審視人類自身在環(huán)境空間中的地位亦有裨益。校園是特殊的人地關系載體,由于其承載的文化功能,使其人地關系趨向于回歸“人類”本身,又不失傳統(tǒng)人地關系的特質(zhì),校園空間的細致變化均會帶來直觀的人地關系影響變化,因此,在以西安科技大學秦漢校園為例的案例研究中,重新審視校園空間以及潛在出現(xiàn)的人地關系矛盾是有利于提升校園的空間品質(zhì)整體性,通過可利用的閑置空間轉(zhuǎn)換成“記憶場所”空間,同時適當增設共享開放空間,開設課余活動,提升學生參與性和積極性,豐富校園空間層次。以秦漢校區(qū)作為先鋒示范,提供給校園規(guī)劃者一定的經(jīng)驗,力求為建設和諧校園人地關系帶來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