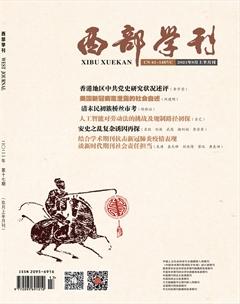清末民初簇橋絲市考
摘要:清末民初四川省內(nèi)各地漸形成較大規(guī)模的民間絲市,成都簇橋絲市是其中之一。絲的供應(yīng)與生產(chǎn)活動、絲的販運與銷售、對市場秩序的監(jiān)督以及活躍于其間的絲業(yè)工人及其幫會、幫助買賣雙方交易的經(jīng)紀(jì)人、外地絲商及其會館、絲綢店鋪等主體展現(xiàn)出當(dāng)時簇橋絲市的面貌。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隨著四川絲業(yè)危機(jī),簇橋絲市也漸趨衰頹。對簇橋絲市興衰概況的探討,有助于了解四川絲業(yè)的發(fā)展情況及其社會背景。
關(guān)鍵詞:簇橋;絲市;四川絲業(yè)
中圖分類號:K203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17-0020-04
一、簇橋絲市興起的歷史背景
(一)簇橋的地名與隸屬沿革
簇橋位于現(xiàn)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qū)西南部,為古代南方絲綢之路的一大驛站,有濃厚的蠶絲文化氛圍。簇,由小麥、油菜等農(nóng)作物的稈制成,供蠶吐絲做繭,從地名上即可看出與蠶絲的關(guān)聯(lián)。據(jù)說此地秦代時為笮人住地,河上用竹木架橋,漢代被稱之為笮橋,但笮橋這個地名應(yīng)該與笮人無關(guān)。有學(xué)者認(rèn)為這應(yīng)是對《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中“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一句的誤讀[1]。笮也可指竹索,笮橋可理解為用竹索編織而成的架空吊橋,這或許是得此地名的原因。
唐宋時期的簇橋有“繭橋”[2]127“蔟(蠶蔟)橋”[3]128“簇(蠶簇)橋”[4]等稱呼,可見受日趨繁盛的蠶絲加工和交易活動影響,此地在名稱中也流露出蠶桑的痕跡。到清代時此地得名“簇橋”,也稱“簇錦橋”,民國時簇橋還稱“簇錦鎮(zhèn)”。
簇橋的區(qū)域分屬也幾經(jīng)變動。民國時期,簇橋分屬華陽縣和雙流縣;解放后,簇橋由雙流縣管轄;1956年原華陽縣華興鄉(xiāng)并入簇橋鄉(xiāng);1960年,簇橋被劃入成都市金牛區(qū);1990年,簇橋被調(diào)整劃入成都市武侯區(qū)[2]129-132。
(二)四川民間絲市的興起
蠶桑絲綢業(yè)在四川有悠久歷史。唐代到北宋是成都蠶市最鼎盛的時期,蠶市上人頭攢動、燈火通明,“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燈火上紅樓”說的便是當(dāng)時成都蠶市的情景[5]。此后歷代川絲的產(chǎn)品種類、運銷、市場皆有所變化發(fā)展。
隨著太平天國占領(lǐng)南京,江南織造中心轉(zhuǎn)向成都,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四川蠶織業(yè)發(fā)展和民間絲市的興起[6]。二十世紀(jì)初的四川有“本年蠶事甚旺,新絲上市后,絲價日減”[7]的記錄。四川蠶絲界的改良活動亦促進(jìn)了蠶絲生產(chǎn)及貿(mào)易的發(fā)展:“四川舊產(chǎn)黃絲、潼綿上貨,運滬外銷,價值高下不出三四百元之間,自合州張武卿孝廉召集民股,開辦四川蠶桑公社,改良蠶種,仿用日本人力坐繅絲車,講求新法后,歷年制出之絲,附商銷滬者,均比川絲高售一二百兩。”[8]相應(yīng)的團(tuán)體組織也活躍于蠶絲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中,如當(dāng)時南充的相關(guān)商會各幫:綢緞疋頭幫,由成渝運回或本埠機(jī)房定購回店躉售,成員約計百余家;綾綢機(jī)房幫,自造花素綾綢、湖縐等出售,成員約計三十余家;絲線幫,專制彩線出售,成員約計五六家;絲廠幫,自造絲品出口外售,成員約計二十余家;絲幫,買絲出口或自用或運往別地,成員約計五十余家[9]。足見當(dāng)時絲業(yè)發(fā)展之情形。
清末隨著蠶事絲業(yè)之興盛,在四川省內(nèi)各蠶絲產(chǎn)區(qū)以及絲織業(yè)較集中的城市中,普遍興起了一批生絲市場,如南充雞市口生絲市場、岳池板橋生絲市場、西充城隍廟生絲市場、閬中高家坎生絲市場等,成都簇橋生絲市場也是其中之一[10]。到新絲上市販賣時,各類人士活躍于其間,頗顯熱鬧。如西充有一類販運商被稱為“絲滾子”,他們就地買進(jìn)蠶農(nóng)自產(chǎn)的土絲后,化零為整,再轉(zhuǎn)手出售給織機(jī)戶,如此不斷買進(jìn)賣出,以謀生計[11]。南充雞市口生絲市場亦有“絲滾販子”的說法。其中本錢小的俗稱“鏟子”,他們就地買進(jìn)一兩把絲,等到3個月內(nèi)價格稍漲即售,或看行市異地出售,賺取差價。本錢大的俗稱“屯戶”,他們在城內(nèi)或鄉(xiāng)下收絲,然后在雞市口轉(zhuǎn)手出售,牟取厚利[12]。
二、簇橋絲市的運作模式
(一)絲的供應(yīng)與生產(chǎn)活動
1.絲的來源
簇橋匯集四川省內(nèi)多地所產(chǎn)之絲。川南新津、彭山、邛崍、蒲江、丹棱等縣所產(chǎn)之絲,或售入成都,或運銷重慶,或由重慶販運至上海,簇橋即為一集中發(fā)散地點[13]。川西北所產(chǎn)之絲也被簇橋絲市吸納。如崇慶縣城有一些富戶先在本地購買百余捆絲,待絲價上漲后運至成都簇橋絲市銷售。1910年的一份四川各絲價目表中,川北絲、梓潼絲也被明確地歸入簇橋絲路下[14]。“川省新絲,現(xiàn)已陸續(xù)上市,屯積簇橋地方”[15],簇橋儼然是省內(nèi)的絲綢交易中心。
簇橋本地也生產(chǎn)加工蠶絲。待可采繭時,少部分被留作蠶種,絕大部分蠶繭用于抽絲,經(jīng)繅絲加工后成為蠶絲,即生絲。由于當(dāng)?shù)匦Q桑環(huán)境較優(yōu)質(zhì),形成的繭子較勻凈,抽絲較長,因而產(chǎn)生出民間游戲“纏絲絞絞”:用開水泡上二至三個繭子,小碗盛好。將竹筷剖開,用線纏好底部,再在開口處取一根火柴棒,便做好了簡易的絞絲工具[16]。
以傳統(tǒng)土法繅制之絲為土絲。二十世紀(jì)初以來,新式繅絲方法對川絲生產(chǎn)影響加深,所產(chǎn)蠶絲呈現(xiàn)出更豐富的面貌,按所用原料及繅制方法,可分為土絲、直繅絲、揚返絲、搖經(jīng)絲等。土絲與直繅絲以蠶繭為原料,揚返絲與搖經(jīng)絲以初步繅制之絲為原料;土絲與搖經(jīng)絲均沿用土法繅絲,直繅絲與揚返絲均采用新法[17]51。不同絲的價格不同,如做經(jīng)之細(xì)絲為每把五十六兩銀,做緯之細(xì)絲則為每把四十四、五兩,織緞緯線則為每兩三錢五、六分銀,相當(dāng)于每把七十一二兩[18]。簇橋制絲的手工工序有索緒、理緒、添緒等,繅絲工將蠶繭煮熟,軟化粘在絲上的蠶膠,然后在沸水中找出線頭,將十余個蠶繭中抽出的線頭再理緒并合,繞在竹木絞車輪上,待冷卻干燥后經(jīng)絲膠粘合即形成生絲。后續(xù)還有復(fù)搖、留緒、絞絲、稱絲、配色、換包成件等處理過程,最終制好成形絲片,運輸、貯藏、織造錦緞都較為便利[19]134-135。
為避免蠶蛹孵化咬開蠶繭,蠶繭需要在夏季到來前繅絲完畢,這是簇橋最為忙碌的時候,各大絲廠、絲店會招攬附近居民繅絲。為盡早處理好生絲,比別家更早出售以搶占市場先機(jī),這些幫工被迫終日工作,由于長時間泡在沸水里,雙手被泡得又白又腫[19]136。
2.簇橋本地的絲綢業(yè)幫會
簇橋當(dāng)?shù)丶械慕z綢產(chǎn)銷活動催生出相關(guān)的幫會團(tuán)體,成員受其保護(hù)制約。有的幫會團(tuán)體間有所聯(lián)系,如長機(jī)幫和三皇會。長機(jī)幫因織錦木機(jī)又高又長而得名,三皇會則由長機(jī)幫工人組織起來,奉伏羲、神農(nóng)、軒轅三皇,本意為維護(hù)長機(jī)幫工人利益,限制老板的壓榨。但幾經(jīng)演變,會首被老板把持,并規(guī)定擁有超過四張機(jī)子者才可被選為會首,工人受到變本加厲的剝削。
從事拋絲、打線、織機(jī)等工作的工匠有時會受到雇主的欺壓。由于織機(jī)高而工作的機(jī)房屋頂?shù)桶厣贤谟旋R腰深的機(jī)坑,長機(jī)幫織機(jī)工人長期在有積水的機(jī)坑內(nèi)工作,濕氣較重。老板則以豆芽有除濕作用為由,以豆芽做菜供給餐食,故長機(jī)幫也被稱為“豆芽幫”[20]385。工資問題也常有爭執(zhí),如雇主將較費力的改良細(xì)絲的工作交給生縐幫工人做,卻還是按和粗絲一樣的價格開工錢,這樣工人吃虧不少,對此簇橋生縐幫工人罷工,最終通過談判取得轉(zhuǎn)機(jī)[21]。長機(jī)幫工人也多次展開反抗老板的斗爭,如1927年時,為增加工資,長機(jī)幫工人進(jìn)行罷工,最終實現(xiàn)目的,工資增加百分之五十五[20]389。
每年9月16日是三皇會的會期,屆時會請川戲班子唱幾本大戲,分早中晚三場進(jìn)行,若交幾吊銅錢,還可以吃九斗碗。整體辦會氣派[22]。簇橋的繅絲工匠也有自己的幫會,名曰太陽會。因繅絲、勻經(jīng)都需要有太陽曬干,雨天則做不成,為討好口彩而得名。太陽會人窮錢少,每到會期只好借廟辦會,輪流操辦。各類幫會的活動折射出簇橋絲業(yè)從業(yè)者的生活百態(tài)。
(二)絲的販運與銷售
1.市場網(wǎng)絡(luò)與交易情形
四川在清末興起了一批生絲市場,到民國時,這些生絲市場逐漸形成三個層次,即原始市場、中級市場和消費市場。原始市場位于產(chǎn)絲各地的鄉(xiāng)鎮(zhèn),中級市場位于主要的產(chǎn)絲城市,其中三臺為最大,閬中、合川、宜賓等地次之。而消費市場也可稱為終點市場,集中各地之絲供給本市場織造綢緞之用,成都簇橋絲市之外,樂山、南充等地的絲市也可歸入這一級[17]72。這三個層次的市場是針對省內(nèi)蠶絲貿(mào)易而言的,消費市場所匯集的生絲還大量運銷省外,據(jù)清宣統(tǒng)時期的統(tǒng)計資料,川北、川東等地每年所產(chǎn)之絲,于四、五月份匯集簇橋,其中的大宗絲貨再運銷至云南、貴州、陜西、河南、湖北等地[19]。
絲市中參與生絲交易的人士大致分為消費者、生產(chǎn)者、販運商、經(jīng)紀(jì)人等。消費者多為絲織業(yè)、絲絨業(yè)、絲線業(yè)等以生絲為生產(chǎn)原料的產(chǎn)業(yè)的從業(yè)者,大多活躍于消費市場。生產(chǎn)者既有自行養(yǎng)蠶繅絲的蠶農(nóng),也有專門購繭繅絲的大小絲廠,因所產(chǎn)之絲運銷范圍不同,蠶農(nóng)及小絲廠生產(chǎn)的少量生絲大多就近在原始市場賣給販運商,大絲廠則運至中級市場或消費市場,乃至運銷省外。
販運商亦有大小之分,往返于不同類型的市場和地域間。一般來說,小販運商在原始市場就近收取小絲廠、繅絲作坊和自繅絲的蠶農(nóng)所產(chǎn)之絲,運至中級市場出售;大販商可分為省內(nèi)、國內(nèi)、國外貿(mào)易三種。經(jīng)營省內(nèi)貿(mào)易之絲商,多向中級市場收絲,運往消費市場出售;經(jīng)營國內(nèi)貿(mào)易者,大多收集本省所產(chǎn)之絲,運銷上海;經(jīng)營國外貿(mào)易者,在各大絲市收集生絲后運銷至緬甸瓦城等地。如云南的茂延記商號便常托寶源號在簇橋絲市按一定規(guī)格收購生絲,而后再運往騰沖,交春延記商號運往緬甸銷售[23]。
在蠶絲買賣雙方之間,還有介紹交易、撮合洽商的經(jīng)紀(jì)人。由經(jīng)紀(jì)人經(jīng)手的蠶絲交易須付傭金,再加上蠶絲運銷過程中繳納的各種稅款,形成了一筆額外開銷。簇橋絲市征收的稅款包括落地稅、轉(zhuǎn)口稅兩種,落地稅由運往簇橋的絲照章繳納,轉(zhuǎn)口稅針對的是在簇橋售出,將由轉(zhuǎn)運商販?zhǔn)鬯幹z。簇橋當(dāng)?shù)刂z因自然會轉(zhuǎn)運往他埠,故繳納的是一種二重稅,每一把絲抽銀三角。絲業(yè)經(jīng)紀(jì)方面所抽取的相當(dāng)傭金,每把在一角上下[13]。絲行為買賣雙方提供了洽商交易的場所,也收取一定的傭金,簇橋絲市“向有絲行五家,公設(shè)行秤,每束絲收費一百五十文,取之賣主者二,買主者一”[24],蠶絲交易興旺時,絲行亦能增加較多收入。
2.簇橋的絲綢店鋪
與絲市的熱鬧情形相配套的,是簇橋諸多的批發(fā)商店和零售絲綢店。清末民初時簇橋最著名的絲店有五家,為恒豐店、恒泰絲店、泰興絲店、泰順絲店、泰安絲店。據(jù)統(tǒng)計,到解放初期,簇橋尚有恒豐店、恒泰店、泰安店、同春店等絲店[3]129。絲店也稱絲號或絲棧。當(dāng)時這些大絲店多是臨街開設(shè),為磚木結(jié)構(gòu),采用前店后棧的模式,即前面為店鋪,后面為貨棧。出于防潮的需要,貨棧的柏木地板可達(dá)一寸之厚。絲店中還有雙天井,前一個天井是消防需要,后一個天井則是廚房用水,雙天井兩旁便是貨棧。因擔(dān)心老鼠進(jìn)入造成破壞,生絲店鋪貨棧的門窗一律緊閉,天井的另一作用更顯得突出——它采光良好,較為明亮,利于觀察生絲的成色[16]。
恒豐店即可體現(xiàn)四川蠶絲交易鼎盛時期商業(yè)店鋪的典型風(fēng)格。其鋪面正中是貼金垂花大門,中間是通道,兩邊為廂房,院落面積較大,有雙天井,四周有避風(fēng)火的高墻。退光土漆柜臺、貨架以及長凳放置在門廳賬房內(nèi),便于交易。穿過花照門廳后有天井,天井兩側(cè)各是一排檐廊,檐廊后有住人和存放蠶絲的小間用房[19]137。蠶絲存放、經(jīng)營的痕跡都體現(xiàn)在店鋪的建筑風(fēng)格中。
3.簇橋的會館
為便利絲貨經(jīng)營,外地絲商在簇橋修建起同鄉(xiāng)會館,也稱同鄉(xiāng)家廟。會館會設(shè)立公約,推舉會首,須保護(hù)同鄉(xiāng)人利益。會館內(nèi)供奉有同鄉(xiāng)人所尊崇的神像牌位和祖先牌位。每年的祭祖日或者吉慶之日,在會首主持下,同鄉(xiāng)人進(jìn)行祭祀或設(shè)宴聯(lián)誼,抒發(fā)思鄉(xiāng)之情。對外地絲商而言,同鄉(xiāng)親進(jìn)行聯(lián)絡(luò)增進(jìn)感情時,也可相互交流商業(yè)信息。
清末民初簇橋共有會館四座,為陜西會館、江西會館(萬壽宮)、湖廣會館(禹王宮)及廣東會館(南華宮)。這些會館建筑整體上與四川民居風(fēng)格相融合。如湖廣會館,其正門為重檐金柱,上方置有三重吊檐,垂柱花罩上的紋式做工精致。整座會館進(jìn)深三間,有雙天井,四周廂房相連,房架高大且粗壯。會館內(nèi)部住房體現(xiàn)出長幼尊卑的差異,上方正屋是安置祖先牌位和議事用房,同鄉(xiāng)人住兩邊廂房,晚輩居住在過廳后兩側(cè)廂房,長輩住在院內(nèi)上房。建筑整體氣勢莊嚴(yán)[25]。
(三)市場秩序的監(jiān)督
在參與蠶絲貿(mào)易的各類人士之外,政府機(jī)關(guān)、同業(yè)組織等團(tuán)體對簇橋絲市進(jìn)行著相關(guān)的監(jiān)督管理。如商務(wù)總局曾對簇橋絲市一件弊賣案進(jìn)行批示,認(rèn)為被控告者并無蒙混行為,并未給絲市商民帶來不便,要求成都府再加核查定奪[26]。簇橋絲業(yè)益源分會的執(zhí)行委員李榮興,也曾以功效無多而耗費甚大為由,呈請撤裁簇橋保商警所,而這是由簇橋絲商暨紳首等人再三開會討論協(xié)定的[27]。簇橋的生縐幫,也曾因一種名為四八縐的絲制品的經(jīng)紀(jì)人介紹費標(biāo)準(zhǔn)不統(tǒng)一而呈請社會局定奪,經(jīng)最終議定,由社會局布告公示標(biāo)準(zhǔn),要求絲市商民均須遵照執(zhí)行[28]。
進(jìn)行監(jiān)督管理,維持絲市紀(jì)律的團(tuán)體在當(dāng)時四川各地的絲市中也有存在,如梓潼縣的絲業(yè)買賣市場專派商會會董八人,每場輪管,并抽取管理費用,部分歸公用,部分為經(jīng)紀(jì)秤費,費用收取統(tǒng)歸商會經(jīng)理[29]。蜀中的蠶絲貿(mào)易還曾有一種被稱為“打潮”的現(xiàn)象,即在上市前一天預(yù)先將絲吹水露地,希望增加些許分兩以賣得高價。對此,勸業(yè)道進(jìn)行了監(jiān)管,明令禁止此種行為,違者嚴(yán)懲不貸[30]。
三、簇橋絲市的衰落
到1911年,簇橋地區(qū)專門從事絲業(yè)經(jīng)營的多達(dá)300余家,從業(yè)的工匠約有五六千人[3]129。盡管清末民初時發(fā)展興盛,到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時,簇橋絲市一度衰落。《四川月報》將其衰頹的原因歸為四點:“一、銷路減少,生產(chǎn)過剩則價自跌,二、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日見枯窘,育蠶繅絲為農(nóng)村副業(yè),無從發(fā)展,日就衰敝,三、歷年戰(zhàn)禍,各方損失甚巨,絲業(yè)亦遭受變故,四、稅款繁重,成本增高,使銷路愈減,此實不振之極大原因矣。”[13]生產(chǎn)運營成本的高昂與獲利的微薄使簇橋絲市不復(fù)昔日盛況。在省內(nèi)絲業(yè)普遍蕭條的背景下,簇橋絲市的衰落也是有跡可循的。
資本主義世界經(jīng)濟(jì)危機(jī)其影響波及中國絲業(yè),“世界經(jīng)濟(jì)恐慌,達(dá)于極度。各國實行緊縮,購買力亦隨之下落。絲織品本為消費之奢侈品,其價格之低降,乃自然之趨勢。”[31]面對海外銷路需求量的減少和價格的走低,川絲被迫低價傾銷,其外銷出口的獲利已嚴(yán)重受損,而人造絲與日本所產(chǎn)之絲價格低廉,質(zhì)量較好,擠占了國際市場對于川絲的需求,更加劇了川絲的損失和四川絲業(yè)的困境。“本市絲業(yè),年來因受舶來品人造絲之抵制,價格大跌,各商因虧折過多,以致停貿(mào),而育蠶之家,因絲價下跌,無利可圖,亦多停飼,昨今兩年絲繭,出量已較往昔銳減。”[32]
絲商既虧損甚多,為其提供部分原料的農(nóng)村蠶戶也“以繭價低賤,地價又復(fù)增高,植桑及養(yǎng)蠶無利可圖,致多砍去桑株。”[33]即便有蠶繭上市,也面臨著難以售出的窘境。如1934年新繭將上市時,各廠家尚無買繭之舉動,致使“各地養(yǎng)蠶之家,互相蹙額,誠存憂慮之念云”[32]。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之困境與川絲之危機(jī)互相影響,加速絲業(yè)之衰頹。
在絲市較盛之時,四川省內(nèi)蠶絲的主要運銷點有成都、樂山、南充等,外銷線路則主要為運銷上海再轉(zhuǎn)銷歐美,通過云南的商幫運銷緬甸等地。具體的運輸路線為:樂山—宜賓—昆明—八莫—緬甸瓦城;三臺—上海—轉(zhuǎn)銷歐美;南充—重慶—上海—轉(zhuǎn)銷歐美;合川—重慶—上海—轉(zhuǎn)銷海外[18]。而連年的戰(zhàn)禍影響了川絲的運輸通道,“至民國二十年滬戰(zhàn)發(fā)生以來,川省絲業(yè)益入沉迭之途,雖有熱心提倡之商人,屢次運往滬上角逐,終因成本不敵,結(jié)果仍歸于失敗”[32]。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隨著上海淪陷,川絲原有的通過上海轉(zhuǎn)銷出口的道路被迫封閉,其銷售更加艱難。
稅款之繁重也沉痛打擊了絲市。1934年四川稅局曾將川綢旱包稅提高,對于販運之絲織品入關(guān)者所征稅額提高了十五倍以上,“從前每擔(dān)征收七元余者,現(xiàn)須一百二十余元”[32],加上運輸途中各關(guān)卡的稅額,絲市中征收的落地稅、轉(zhuǎn)口稅等稅款,實是一筆不小的花銷,這極大地減少了絲的販運。
簇橋絲市在四川絲業(yè)的危機(jī)中逐漸衰頹,不復(fù)清末民初時之興旺。
四、結(jié)語
簇橋因絲市的興起而發(fā)展出多彩的蠶絲文化:為保障蠶絲質(zhì)量和搶占絲市先機(jī),終日忙碌工作的幫工手被沸水泡得又白又腫;采用前店后棧結(jié)構(gòu)的絲店,設(shè)有防潮的柏木地板、采光的天井,體現(xiàn)出特色風(fēng)格;外地絲商在簇橋修建起會館;簇橋當(dāng)?shù)匦纬傻膸蜁M織,在會期展開一系列活動并對成員的利益加以維護(hù)……這些現(xiàn)象由蠶絲的產(chǎn)銷經(jīng)營而產(chǎn)生,與簇橋絲市密切相融,成為簇橋地區(qū)蠶絲文化的一部分。簇橋絲市歷經(jīng)較為復(fù)雜的歷史形勢,其興衰發(fā)展也可視作當(dāng)時社會經(jīng)濟(jì)狀況的一個縮影,對簇橋絲市興衰原因的分析,也有助于探討哪些因素影響著市場的發(fā)展,又是如何具體發(fā)揮作用的。
如果將簇橋絲市放置在更宏大的四川絲業(yè)格局中加以看待,那么簇橋絲市是四川絲業(yè)興衰歷程的一個具體見證者,對簇橋絲市加以探討的過程,也是從一個具象化的角度對四川絲業(yè)發(fā)展歷程加以探討的過程。
參考文獻(xiàn):
[1] 馬駿.關(guān)于簇橋得名起源的考證[M]//武侯文史資料第9輯.成都:武侯區(qū)政協(xié)聯(lián)絡(luò)與文史委員會,2005:245-246.
[2] 吳心全,劉矩.古鎮(zhèn)春暉化簇橋——簇橋鄉(xiāng)建置沿革簡述[M]//武侯文史第7輯.成都:武侯區(qū)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1998.
[3] 羅樹林.雙流是蜀錦最大的生產(chǎn)基地和交易市場[M]//田宏梁,王澤枋.千古蠶叢路? 滄桑話雙流.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
[4] 杜受祜,張學(xué)君.近現(xiàn)代四川場鎮(zhèn)經(jīng)濟(jì)志:第1集[M].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1986:46.
[5] 孫先知.蠶市[J].四川絲綢,2001(3).
[6] 袁杰銘.近代四川絲綢貿(mào)易(續(xù))[J].四川絲綢,1997(4).
[7] 各省新聞:蜀中絲市[J].北洋官報,1905(698).
[8] 四川:絲業(yè)改良[J].廣益叢報,1907(153).
[9] 劉澤許.南充地方志蠶絲資料匯編[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64.
[10] 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四川省志·絲綢志[M].成都:四川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98:218.
[11] 政協(xié)西充縣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解放前西充的絲綢概況[M]//西充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南充,1984:5.
[12] 易立權(quán),馬小秋.這些地名與絲綢有關(guān),見證南充發(fā)展[N].南充日報,2018-02-08(7).
[13] 最近簇橋絲市概況[J].四川月報,1934(3).
[14] 庚戌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止各絲價目[J].成都商報,1910(1).
[15] 各省新聞:川省絲市[N].北洋官報,1903(90).
[16] 袁慧君.簇橋:千年不衰的絲綢加工地[N].華西都市報,2015-03-29(10).
[17] 鐘崇敏,朱壽仁.四川蠶絲產(chǎn)銷調(diào)查報告[M].漢口:中國農(nóng)民銀行經(jīng)濟(jì)研究處,1944.
[18] 簇橋絲價[J].四川官報,1904(16).
[19] 劉孝昌.二十世紀(jì)初簇橋的絲、絲店、會館[M]//武侯文史:第8輯.成都:武侯區(qū)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1999.
[20] 成都市總工會工人運動史研究組.成都工人運動史資料:第2輯[M].成都:成都市總工會工人運動史研究組,1983.
[21] 成都市總工會工人運動史研究組.成都工人運動史資料:第3輯[M].成都:成都市總工會工人運動史研究組,1984:65-67.
[22] 李仕偉.簇橋:養(yǎng)蠶繅絲興盛地[N].華西都市報,2015-07-18(10).
[23] 黃槐榮.茂恒商號簡介[M]//大理市文史資料:第8輯.大理,1999:126.
[24] 簇橋絲業(yè)[J].四川官報,1905(12).
[25] 李豫川.簇橋又名簇錦橋[N].成都日報,2009-11-02(12).
[26] 商局批示:武舉劉恒泰店等稟呈簇橋絲市弊賣一案經(jīng)商務(wù)總局批示云[J].四川官報,1904(27).
[27] 批簇橋絲業(yè)益源分會執(zhí)行委員李榮興等呈請裁撤簇橋保商警所并請加委市政所長一案文[J].成都市市政公報,1929(3).
[28] 布告生縐幫羅俊之呈報四八縐每疋改收大洋三仙議決通過一案文[J].成都市市政公報,1930(21).
[29] 絲業(yè)買賣設(shè)市[J].成都商報,1910(5).
[30] 示禁賣絲打潮[J].成都商報,1910(3).
[31] 薛弘訓(xùn).中國絲業(yè)之衰落及其救濟(jì)[J].商學(xué)期刊,1934(8).
[32] 蠶絲:蓉市絲業(yè)危機(jī)[J].四川農(nóng)業(yè),1934(5).
[33] 范崇實.四川蠶絲業(yè)之經(jīng)過及將來[J].建設(shè)周訊,1937(6).
作者簡介:侯雅涵(2000—),女,漢族,四川成都人,單位為西南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史。
(責(zé)任編輯:馬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