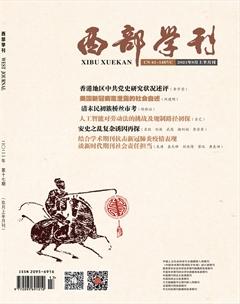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金磚國家信任建設的挑戰與對策
摘要:長期以來,金磚國家因為面臨多元因素的挑戰,信任關系呈現出不穩定的狀態,阻礙著合作的深度與力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金磚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給信任建設帶來了阻力,認知疑慮為信任建設帶來風險,集體行動力不足使信任建設缺乏內在動力。推動建設金磚國家之間互信關系,要以“和合”理念為原則,通過展開充分的對話和交流,深化金磚國家的認知,化解國家間的分歧;以合理公正為原則,通過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保障金磚國家間信任的可持續性;以包容互鑒為原則,通過增進跨文化交流,促進金磚國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共識。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金磚國家;信任建設
中圖分類號:D81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17-0028-04
信任在人類社會中廣泛存在,它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的基礎,也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紐帶。美國學者肯尼斯·紐頓認為,信任能將自利、自我的社會成員較好地聯合起來,成為具有共同利益的團體[1]。同樣,在國際社會中,信任也能將利益、文化、歷史等各項因素互不相同的國家聯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礎上,達成共同認識,形成合作伙伴關系。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國家間互信的建立尤為重要,它不僅有助于理念共識的形成,而且也推動了實踐的順利進行。金磚國家①組織自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國家之間的務實合作,經過十余年的發展,金磚國家之間已經構建了緊密而牢固的伙伴關系。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金磚國家之間伙伴關系的深化與合作關系的拓展,亟需提升國家之間的信任關系,化解分歧與矛盾。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長期以來就重視國家間互信的構建,尤其進入新世紀以后,國家領導人頻繁地對其他國家的訪問及睦鄰友好關系、戰略伙伴關系的建立,都說明了信任這一因素正慢慢地浸潤到中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以及國際組織的關系之中,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正逐步提升,其他國家對中國持信任、認可的態度。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長期以來弘揚的平等互信精神是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前提之一。首先,“平等互信”這一觀點的提出主要是針對目前國際社會普遍存在的“信任赤字”[2]而言的,平等是互信的基礎。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依舊存在不平等問題,南北對話的提倡仍說明國際社會需要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通過平等關系的建立,各國之間確立了信任關系,西方國家動輒就對非西方國家懷疑、誤解等問題就會減少。其次,發展中國家也需要加強南南對話,在不同領域進行溝通與交流,在建立信任的基礎上緩解種族沖突、文化沖突、宗教沖突等,消除恐怖主義的威脅,實現深層次的合作。有學者認為,互信關系的維持可以使國家保持和平和實現合作,遠離戰爭[3],也有學者認為,信任的建立可以保證國家間、地區間的各方安全[4]。比如邊界爭端能否和平解決主要決定于兩個地區的社會信任水平[5]。因此,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只有建立信任關系,國家間才能保持和平,促進經濟的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蘊含的“以和為貴”的觀點有助于協調金磚國家之間的分歧與矛盾,推動國家間的信任與合作。同樣,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
作者簡介:程娜娜(1989—),女,漢族,陜西西安人,單位為陜西省西咸新區灃東新城管理委員會,主要從事國民經濟統計工作。
史耀東(1979—),男,漢族,陜西寶雞人,單位為陜西省西咸新區灃東新城管理委員會,主要從事國民經濟統計工作。
馬玉珍(1991—),女,漢族,陜西西安人,單位為陜西省西咸新區灃東新城管理委員會,主要從事國民經濟統計工作。
(責任編輯:朱希良)現與“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也需要國家間互信的建立,信任的形成或維持能為這一思想及實施途徑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金磚國家組織是具有全球影響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機制。近年來,金磚國家組織的凝聚力日益增強,務實合作不斷深入,影響力持續上升,成為國際事務中一支積極穩定和建設性的力量。多年來,金磚國家不斷加強多領域多層面的合作,在科技、安全、人文等方面探索“金磚+”合作模式。各國也在不斷發展本國科技、經濟實力,比如印度就提出“印度制造”的主張,巴西制定“強大巴西”的產業計劃等。在全球治理方面,以開放包容為理念不斷提供公共產品,提出以多邊主義維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在2019年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上,習近平主席強調金磚國家要展現應有責任擔當,倡導并踐行多邊主義,營造和平穩定的安全環境;把握改革創新的時代機遇,深入推進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伙伴關系;促進互學互鑒,不斷拓展人文交流的廣度和深度。然而,在金磚國家合作第二個“黃金十年”之際,各類風險的出現對伙伴關系產生了一定沖擊,國家之間的合作與信任面臨著更多危機。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之下,金磚國家合作抗疫的力度并未呈大幅提升,反而受逆全球化思潮影響,產生了民粹主義傾向。2020年,俄羅斯作為金磚國家組織輪值主席,提出金磚國家應團結合作共同抗擊疫情[6],然而事實證明,金磚國家之間并沒有采取與預期相符的合作行為,各國疫情防控各有差異。新冠疫情的暴發進一步說明增信釋疑是當前金磚國家共同應對挑戰、建設命運共同體的必經之路。
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背景下金磚國家信任建設面臨的挑戰
長期以來,金磚國家因為面臨多元因素的挑戰,信任關系呈現出不穩定的表現,阻礙了合作的深度與力度,對全球治理的貢獻并不突出,這與以互利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存在一定差距。為此有必要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觀測點,分析金磚國家信任建設面臨的挑戰。
(一)金磚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為信任建設帶來阻力
金磚國家重視合作共贏的伙伴關系建設,但是在面對各類安全威脅之時,各國仍存在矛盾分歧,這為信任建設帶來了阻力。
在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金磚各國通過多邊合作,在聯合國框架內積極探索解決國際爭端的合理途徑,比如氣候問題、恐怖主義的治理等,通過成立反恐工作組、網絡安全工作組等機制進行長期磋商,為全球治理貢獻了不可小覷的力量。但是由于各國政治制度、歷史傳統、經濟狀況等因素的干擾,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過程中,金磚國家的合作能力、信任水平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蝕。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金磚各國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應對措施,但是巴西卻主張取消國家封鎖,并跟隨美國的腳步,準備退出世界衛生組織,這嚴重阻礙了金磚國家共同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巴西政府對疫情的忽視導致當地疫情確診人數持續攀升,經濟發展更為脆弱,這不僅干擾了全球疫情防控,而且阻礙著金磚國家之間信任合作的提升。
雖然非傳統安全威脅在當代國際社會日益凸顯,但在金磚國家內部依舊存在著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傳統安全問題,這主要表現為中印邊境沖突。中國與印度之間邊境沖突是金磚國家彼此構建緊密信任關系的嚴重障礙,雖然中印雙方就邊境問題的解決展開了多輪對話,但是由于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長期以來這一問題仍未得到妥善處置。中印雙方的邊境沖突嚴重破壞了彼此的親密關系,給金磚國家內部信任關系的建設帶來阻力。比如2017年印度因洞朗事件險些缺席金磚國家廈門峰會,2020年印度在加勒萬河谷地區挑起的新一輪軍事沖突,引發了國際社會對金磚國家合作的負面認知。
(二)金磚國家間的認知疑慮為信任建設帶來風險
國家間信任選擇的核心指標主要是利益的獲取,由此而生成的理性選擇信任影響著金磚國家之間信任關系的維系與上升。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在和平穩定的同時經濟呈高速發展態勢,近幾年更以“中國夢”為目標在各領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在此基礎上,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然而,面對新興國家的崛起,抱著“霸權主義”“強權主義”思想的西方大國開始對中國指指點點,交替提出“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面對中國的和平發展,滿是質疑與指責。
除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的諸多質疑與猜忌,金磚國家也在認知上存在疑慮與誤解。比如南亞和印度洋一直被印度視為自己的后院,除巴基斯坦外,印度在南亞地區的經濟、政治參與度很高,對南亞各國有著大量的投資和援助,因此印度對南亞有著近乎偏執的情感。同時印度洋對于印度而言也有著重要的戰略利益,印度不僅在印度洋地區擁有漫長的海岸線,而且該區域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礦物及其他生物與非生物資源為印度提供了能源與工業,目前印度大部分海外貿易都依靠印度洋展開和運輸。“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加快了中國與區域沿線國家的合作,印度認為這是中國借此提升地區存在感及軟實力、擴大自身影響力、試圖消解“珍珠鏈戰略”的負面作用,嚴重威脅印度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傳統地位。正如印度國家海事基金會的執行主任格普雷特-庫拉納的說法,如果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任其發展,最終將會在印度洋地區形成一個軸輻的地區架構。這個架構將以中國為軸心,印度將在這一架構中被逐步邊緣化[7]。從安全角度上看,印度認為中國目前80%的原油進口需要經過印度洋地區,保證這條運輸線的通暢與安全是中國急需解決的問題,也是緩解“馬六甲困境”的有效途徑,因此中國將通過“海上絲綢之路”擴大其在印度洋地區的海軍實力并建造海軍基地,這將威脅到印度在該地區的安全利益。另外,“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將從中國西部穿過喀喇昆侖山脈的中巴邊境抵達巴基斯坦西南部瓜達爾港,所途徑的克什米爾地區是印巴之間存在爭議的領土,新德里認為中巴在這一區域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侵犯了印度的主權,中巴的合作行為削弱了印度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印度對中國的誤解與戰略疑慮不僅不利于中印雙方戰略合作,而且增強了雙方的敵對情緒。2016年以來,印度與美國簽署了四份基礎性軍事協議,包括2020年雙方簽署的《地理空間合作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BECA),建立了美印日澳四國機制,試圖以此遏制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與經濟實力,這無疑為金磚國家內部信任關系的提升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三)金磚國家的集體行動力不足使信任建設缺乏內在動力
在全球化不斷發展的今天,國家間關系緊密、命運相連,國家行為體單獨行動有時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過于追求個體的利益會陷入“公共地悲劇”,損害所有“牧民”的利益,為此必須改變個體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依靠集體的行動獲得利益的均衡,實現集體行動和個體行動的融合,我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就是提倡合作共贏、共同應對人類社會面臨危機的中國方案。然而,由于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國家間的合作常常陷入所謂的“囚徒困境式的博弈模式”,雖然它是非零和博弈,但仍站在個體利益的角度來處理共同問題,并不是最優化的集體行動,也達不到集體利益的帕累托結果,這在金磚國家內部也有所體現。一些國家因考慮自身利益可能受損而逃避責任擔當、拒絕合作,這直接導致國家集體行動力不足,降低了集體利益的獲取,使其他參與者缺失對共同體的可依賴性,“搭便車”行為更是損害了金磚國家共同情感的培育,從而難以推動國家間信任關系的建設。比如,金磚國家遙感衛星星座項目是各方都受益的項目,但至今為止五國尚未在此問題上達成共識。2019年2月,巴西拒絕聯署由中國和印度等10個發展中國家提出的針對美國改革提案的分析文件。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金磚國家信任建設的路徑
如何推動建設金磚國家之間互信關系?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本文認為可以采取三個方面的措施:
(一)以“和合”理念為原則,通過展開充分的對話,深化金磚國家間的認知,化解國家間的分歧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和社會學系教授尤爾根·哈貝馬斯曾經提出過“商談共識”這一概念,他認為共識的形成應該建立在公平對話的基礎上,主體和客體能夠通過商談討論,達成共同思維、共同觀點,主體在向客體傳達觀點的過程中,應有恰當的表達,能夠使客體充分理解、分享知識,以便客體相信并接受這一觀念,并最終達到雙方認同的效果[8]。另外,哈貝馬斯還提出共識的形成應建立在多元話語的基礎上,以包容為前提,而不是一味地以強制或支配的方式。
借鑒“商談共識”的觀點,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達成多方共識,中國作為提出方應先積極與金磚國家開展各領域、各層級的雙邊或多邊對話,擴大共同體理念的認知范圍,使各方對“一帶一路”、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相應的實踐平臺有深入的認識。
此外,政府間、民間等層面應展開積極有效的對話溝通,協商解決矛盾分歧,化解疑慮。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金磚國家不搞一言堂,凡事大家商量著來”。首先需要通過領導人熱線、定期會晤以及戰略對話等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加強政府層面的溝通。其次在民眾層面,應通過多種文化活動加強金磚國家內公眾對彼此文化的認知與理解,同時促進他國以包容的姿態認識、了解中國文化,通過使中國文化“走出去”,增進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信任。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國家攜手并進、合作共贏提供了對話協商、溝通交流的途徑,并從實踐的角度證明了這一方式的可行性。
(二)以合理公正為原則,通過建立合理的制度,保障金磚國家間信任的可持續性
通過制度建立信任源自羅伯特·基歐漢的“新自由主義”,這一流派重視制度在國家行動及國際社會中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稱為“制度自由主義”。制度自由主義認為,制度的建立與參與有助于降低國家間行為的風險,尤其是好的制度能夠增加行為體之間的透明度,提高信息質量,消除國家間疑慮,促進信任的生成,進而建立合作,避免沖突。如果沒有各種制度的建立作為行為體交往的保證,國家間已有的信任度就會降低,或者新的信任無法形成[9]。1975年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簽訂了《建立信任措施暨特定安全與裁軍文件》,在這一文件中就出現了“建立信任措施”一詞,雖然會議最終并沒有達成實質性協議,但說明國際社會已經開始重視通過一系列措施的制定建立國家間信任、達成合作的方式。在國際社會,不同領域都可以建立相關的信任措施,各國在尋求國家利益的同時通過制度與其他國家建立信任,以確保和平、達成合作是具有可行性的。長期以來,中國始終重視制度建立或參與國際制度,以提升與其他國家間的信任關系,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為了消除一些國家對這一倡議的疑慮或誤解,我國逐步制定、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強制度的透明性,比如《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國際投資爭端仲裁規則(試行)》《外商投資企業知識產權保護行動方案》等,在一定程度上取得其他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同,增進了多邊信任。
但是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制度信任的確立必須首先保證制度的合理性、針對性。首先,在尋求本國利益的同時,能夠兼顧其他國家的利益,實現利益的共享。2018年,習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八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提出,中阿增進戰略互信,就是要使“中東政策順應中東人民追求和平、期盼發展的強烈愿望,在國際上為阿拉伯國家合理訴求代言,愿為促進地區和平穩定發揮更大作用”[10]。也就是說,信任的建立需要依靠制度,而制度的建立應該滿足各方的利益,如果無法均衡利益,制度必然有偏頗和不公平,這既不符合國際道德,也不符合國家收益原則,同時還影響國家聲譽,導致信任無法建立。
其次,制度的建立應根據不同國家的特點,具有針對性。每個國家有自身的利益追求、文化底蘊、歷史沿革,這就導致群體心理文化因素各有差異,那么在對待同一方案或行動時都會有不同的態度。同樣在金磚國家內部,由于不同國家獨有的文化心理,對待彼此的倡議、政策、方針會有不同的反應。另外,國家的政體、內部政治調整以及第三方國家的介入也會影響國家的態度和戰略決策。所以在制度建立過程中,應根據各國特點有針對性地區別制定,在符合行為體心理文化的基礎上,按照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制定滿足雙方利益的制度,并逐步實現戰略對接,使制度具有可行性,這樣才能確保國家間互信的建立“有跡可循”。
(三)以包容互鑒為原則,通過增進跨文化交流,促進金磚國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共識
共識的建立,能夠維系金磚國家之間的信任關系,推動信任關系的提升。全球化進程中,多元文化的存在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群體不可避免地出現沖突和碰撞,亨廷頓認為,文明的沖突是當今世界和平穩定的最大影響因素,文化交流是避免戰爭最大的保證,雖然亨廷頓過于強調文明的重要性,但是也不能忽視文明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有助于增進民眾對不同文化的認識與理解,對基于文化所建立起來的國家政策、方案予以包容或認可,進一步消除雙方的誤解與分歧,促進了相互間的信任,以求達成共識,建立合作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提出起,就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大部分國家都對這一思想予以稱贊,但是也有少數不和諧的聲音,比如2019年美國將中美之間的矛盾定義為“文明間的沖突”,這不僅無法解決兩國間復雜的關系,而且阻礙了人類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影響了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共識的達成。對此,只有承認文化的多樣性,并在此基礎上增進不同文明間的對話,在不同民族、地區、國家深化文化的交流,才能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過程中消除分歧與誤解,推動各國的共同發展,最終對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中國方案給予認可,達成共識。
注釋:
①金磚國家(BRICS),因其引用了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中國(China)、和南非(South Africa)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該詞與英語單詞的磚(Brick)類似,因此被稱為“金磚國家”。2001年,美國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師吉姆·奧尼爾首次提出“金磚四國”這一概念,特指世界新興市場。
參考文獻:
[1] 肯尼斯·紐頓.社會資本與現代歐洲民主[M]//李惠斌,楊雪冬.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381.
[2] 習近平.為建設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貢獻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9-03-27(3).
[3] ANDREW H.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4] 英·基佐.建立信任措施:歐洲經驗及其對亞洲的啟示[J].現代國際關系,2005(12).
[5] FLORIAN JUSTWAN,SARAH K,FISHER.Generalized Social Trust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J].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2016(5).
[6] 新華社.金磚國家就支持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發表主席聲明[N].人民日報,2020-02-13(3).
[7] 林民旺.印度人怎么看中國的“一帶一路”[EB/OL].新浪網.(2015-06-17).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50617/090022453
371.shtml
[8] 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M].張博樹,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3.
[9] 王正.信任的求索:世界政治中的信任問題研究[M].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76.
[10] 習近平.習近平談“一帶一路”[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223.
作者簡介:戴薇薇(1980—),女,漢族,湖南長沙人,博士,長沙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外交、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責任編輯:王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