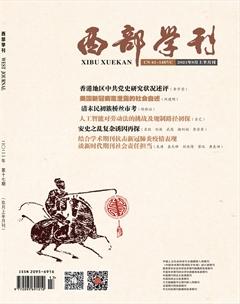維貝克“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及其價值
摘要:維貝克“道德物化”思想在吸收福柯的主體自我建構理論和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的同時,也借鑒了伊德的后現象學技術這些分析路徑。在反思傳統的人本主義倫理學的同時,開啟了技術人工物的“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的思考。維貝克“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將技術人工物這一曾經的倫理學的客體納入倫理學主體的位置,既反思了傳統的人本主義倫理學,也挑戰了傳統技術倫理轉向后的外在主義困境,通過技術設計將倫理、道德的規訓范圍囊括到“物”上,讓技術人工物代替人成為新的道德主體,將技術設計成一種能夠實現倫理、道德目標的手段,由人和技術人工物來共同承擔,責任劃分也需要在人與技術人工物之間進行,從而對人的行為造成道德意義上的規范、調節與引導。維貝克“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在理論、實踐、現實意義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指導價值,但其合法性還需要通過更多不同角度的論證來進行反思與探討。
關鍵詞:維貝克;道德物化;技術倫理;人本主義倫理學
中圖分類號:B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1)17-0041-03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技術人工物都只是被當作為人所用的工具。而在技術倫理愈加凸顯、技術文化愈發深入的當下,我們看到人對技術的依賴越來越全面,技術對人的行為、思想的改變也越來越明顯,技術人工物作為人與世界之間的中介和橋梁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人的決策與道德行為在被技術人工物干預的過程中,也就不再是享有完全自主性的道德主體了。那么“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為人本主義奠定理論基礎的名言也與當前愈發凸顯的技術倫理不符,也使得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人與技術、倫理、道德之間的關系,而彼得·保羅·維貝克(以下簡稱維貝克)“道德物化”思想正好為我們的審視提供了方向。
一、維貝克“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的核心觀點
維貝克是荷蘭特溫特大學哲學系技術哲學專業的教授、哲學系主任,國際哲學和技術協會主席,荷蘭人文科學委員會委員,也是技術哲學的荷蘭學派的代表人物,其“非人本技術倫理學”思想的核心觀點是技術道德化,將技術人工物這一曾經的倫理學的客體納入倫理學主體的位置,提出了以技術為主體的“非人本主義倫理學”,在人與技術、道德、倫理的復雜關聯中賦予技術人工物以道德性。他既反思了傳統的人本主義倫理學,也挑戰了傳統技術倫理轉向后的外在主義困境,向“先驗地對技術持單邊否定態度和悲觀態度”[1]的經典技術哲學發起了挑戰。他集中論述了技術道德化的倫理路徑,提出要通過分析技術人工物的道德主體地位的可能性,與技術人工物“道德物化”的具體方法,從而構建一種“非人本主義倫理學”體系。
(一)針對傳統技術倫理學
自啟蒙運動以來,道德的根源只能是獨立個人的人,這既是傳統倫理學研究的根本特征,也是承載倫理與道德的唯一主體,而倫理學的研究必須受制于主體范圍內,作為人的主體如何在作為非人類的客體中運動則是主要方向。現代倫理學也是在傳統倫理學的基礎上將主客二分作為核心。然而這種以人為主體的人本主義倫理學在現代主義路徑中顯得尤其狹隘,主體與客體的絕對分離,造成了關于人的整體思考也被切割成了實在論和人本主義。但是在技術文化日益深入的當下,作為主體人的決策與行為早已同非人類客體交雜在一起,早已不是能夠享有完全自主性的絕對主體,人本主義或現代主義也就無法成立,正如法國哲學家拉圖爾所說,“我們從未現代過”。
維貝克受拉圖爾啟發,主張由物來作為承載、調節、塑造道德的主體,從非現代的視角指明了非人本主義的方向。拉圖爾早就通過“腳本”的概念指出技術人工物可以作為聯結、跨越人與物、主體與客體之間界限的中介,對人的行為進行塑造與規訓。但需要注意的是,拉圖爾也對此進行了注釋,認為技術本身無法承載道德且毫無意義,只能通過與人的互動和關聯發揮作用,也就是說技術的能動性只能存在于人與技術人工物的共同作用中。維貝克站在拉圖爾的肩膀上,將這一觀點進一步深化,使得技術扮演著調解者的角色,賦予了技術在人與物的關聯互動中具備充分的能動性。這在避免將技術等同于道德本身的固有觀點的同時,也沒有將人劃分為道德行動與決策權的絕對主體,而是強調技術作為聯結人與物的中介所發揮的關聯性作用,維貝克的“非人本主義倫理學”并沒有站在“人本主義倫理學”的對立面,從來都沒有將技術置于人的對立面,他指出單獨的技術毫無意義,技術只有在與人的互動和關聯中才會具備能動性,成為獨立的道德行動體。
(二)針對外在主義困境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因為技術的迅猛發展帶來了一系列諸如戰爭破壞、環境威脅、工程事故等的反思,也促使倫理學和技術哲學分別將技術的倫理問題納入自身的研究范圍,繼而促成了技術哲學發展的“經驗轉向”,以及后續的“倫理轉向”。然而,“倫理轉向”之后的技術倫理學致力于一種自上而下的技術規訓和準則,將原本緊密聯系的技術與倫理一分為二。其直接后果就是倫理學家以人作為主體的倫理作為衡量技術在設計、制作、使用過程中的標尺,促使倫理學家與技術人工物設計者互為對立,指責對方在工作上對自己造成的干涉。
維貝克從溫納的技術政治理論中汲取靈感,針對這一現象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美國當代技術哲學家溫納指出,政治秩序、社會秩序會與技術人工物的前期部署和設計融為一體,在投入使用前會以一種理念的方式體現人的意圖,并在投入使用后施加對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影響,總是會承載一定的政治因素。維貝克在這一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技術伴隨(technology accompaniment)理論。以減速帶為例,在減速帶投入使用以前,都是由書面提示為主的方式告知、提醒司機前方存在高速駕駛的風險,減速帶的設計就在時效層面與經濟層面遠優于書面提示,更能通過發揮作為技術人工物的時效性而影響司機減速。維貝克認為,技術人工物在設計之初就應該納入相對應的倫理考量,從而在決策和使用的過程中對人類產生影響。與外在主義倫理學給技術使用施加的規范不同,維貝克這種人與技術互相雜合、同時行動的技術伴隨倫理學,強調了兩者共同發揮的倫理作用,技術在兩者共同發揮的倫理作用中是具備道德性的。減速帶的例子也說明維貝克的技術伴隨倫理學確實為規范人類的行為方式做出了法律強制自律、道德他律以外的第三種手段——道德物律。其既彌補了法律強制自律手段存在的滯后與不足,也避免了道德他律效果低下客觀存在,技術伴隨式的“道德物化”作用范圍與強度都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
二、維貝克“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在實踐中的責任劃分
在維貝克的觀點里,既然技術人工物在設計之初就應該納入相對應的倫理考量,從而對作為使用者的人的使用與決策產生影響,對人的行為進行塑造與規訓,強調人與物共同發揮的倫理作用。這也意味著“道德物化”概念中責任劃分的核心問題,即人需要對受到技術人工物引導、塑造、規訓后,共同促成的行為負責嗎?如果需要,具體該如何負責?責任如何劃分?既然技術人工物在設計之初就納入了相對應的倫理考量,通過與人的互動和關聯發揮作用,那技術人工物的道德該如何鑒別?
以人臉識別技術為例。以保障安全為目的的人臉識別攝像頭如果將無辜的人當成了嫌疑犯,那應該由人臉識別的系統設計者、攝像頭制造商還是攝像頭使用者來承擔責任?維貝克針對“道德物化”中較為復雜的責任劃分提出了兩種不同指向的責任形式。首先是道德責任。維貝克認為,“道德責任只有在一個人蓄意且自主地發出某一行為時才會產生。”[2]其次是因果責任。維貝克指出,“因果責任是指如果一個人成為某一事件或某種時態產生的原因,那么他就應當對此承擔因果層面的責任。”[2]技術人工物通過與人的關聯互動進行了道德活動的參與,在產生道德責任的同時也溝通了因果責任。人們對技術人工物的行為通常只做因果層面的理解與判斷,但由于技術人工物在設計之初就應該納入相對應的倫理考量,從而在決策和使用的過程中對人類產生影響,在其互動的過程中對人施加的意向性影響就已經深入了道德層面,繼而完成了道德層面的責任參與及共塑。
維貝克的“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中的道德責任由人和技術人工物來共同承擔,責任劃分也需要在人與技術人工物之間進行。維貝克進一步指出,通過“道德物化”來推定技術人工物的道德責任并非要隱去或削減作為客體的人所需承擔的責任,而是以此重新規制責任承擔的新維度。前文中以人臉識別技術為例,指出了當人臉識別攝像頭出現錯誤時的責任規制問題。技術人工物本身是不具備自由意志的行為體,所以也不能以人的方式承擔道德責任,鑒于技術人工物在設計、制造、使用的過程中都會與對應的設計者、制造者、使用者產生關聯性的道德責任,所以技術人工物只是作為承擔道德責任的載體,將道德責任分別賦予了設計者、制造者和使用者,在法律強制自律、道德自律的基礎上,以“物律”的方式對人實行約束。維貝克指出,人在“道德物化”體系中并非簡單被動地接受技術的規訓與控制,而是要主動地與技術進行互動與關聯,通過對技術的調節來完成對自身能動性的建構。維貝克指出,要達成這一目的,就要具備相對應的使用技巧(techniques of using technology),即在適當的時間里,以恰當而審慎的方式使用技術人工物,并在此過程中以技術調節的方式來塑造技術對人施加的影響,繼而使得技術人工物的使用更為合理,結果更為恰當。使用者也會因此而不斷調整與優化自己與技術人工物互動、關聯的方式,最終形成人在“道德物化”中作為主體的自我建構。
三、維貝克“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的現實意義及其局限性
不同于技術哲學長期囿于理論而缺少實踐意義的模式,維貝克的“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較好地轉化到了實踐之中,所以,技術人工物所承載的道德行動需要通過實踐來加以完善。維貝克認為技術人工物的設計階段就具備了倫理活動的價值,對設計者這一承擔不可推卸倫理責任人的引導必不可少。“技術物成了內在的道德實體,這就意味著設計者可以以一種物質的方式從事倫理活動:對道德進行物化”[3]。“設計師‘物質化的道德性……所有設計中的技術最終要調解人類行動和體驗”[4]。在維貝克看來,技術人工物的設計者是不折不扣的技術倫理學實踐者,認為設計者在從事技術人工物設計的工作時,其所占的倫理學研究屬性要多于工程師屬性。在這一認知前提下,維貝克對技術人工物的策劃、設計、評估等環節在內的多種方法論,詳細地描述了道德調節作用在對技術人工物的設計者倫理、責任方面的影響,為“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的實踐提供了一般性指導。其中,對策劃環節的影響主要以“建設性技術評估”為主,即通過情景模擬、推測來盡可能地提前發現技術人工物在使用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的情況,從而在設計與使用的過程中提前做出規劃與防范。設計環節則通過使用具有調節作用的設計語境來平衡腳本邏輯與用戶使用邏輯上,使得技術人工物、設計者、使用者都能被視為起調解作用的處于平等地位的主體。維貝克的“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成功地將使用者的語境同設計者語境聯系了起來,其評估方式也較為細致地展示了技術在“道德物化”中起到的調解作用。
維貝克“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在理論、實踐、現實意義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指導價值,但其合法性還需要通過更多不同角度的論證來進行反思與探討。“道德物化”思想在未來的實踐中依然存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重重困難,如何權衡人與物在主體能動性中的比重,以及設計師在技術人工物設計過程中的權力約束都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探索。
四、結語
維貝克的“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將技術人工物視為道德的行動者,強調了人與技術人工物在互動與關聯中共同發揮的倫理作用。認為技術人工物設計之初就應該納入相對應的倫理考量,從而在決策和使用的過程中對人類產生影響。不同于技術哲學長期囿于理論而缺少實踐意義的模式,維貝克的“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較好地轉化到了實踐之中,成為一種為了推進技術倫理積極實踐而設立的道德活動準則。本研究從理清維貝克“非人本主義倫理學”的角度出發,從與傳統倫理學、傳統倫理學的外在主義困境的比較中扼要地分析了維貝克“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的核心觀點;繼而分析了維貝克“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在投入技術人工物設計、使用實踐中的責任劃分;并就維貝克“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的現實意義進行了梳理,認為他的“道德物化”思想改變了技術哲學界將技術視為具有侵犯性的單一風險評估,發展出了將道德反思融入技術倫理的新嘗試,成為技術哲學第三次轉向的先鋒;最后,我們在對維貝克“非人本主義技術倫理學”在理論、實踐、現實意義等方面具有貢獻的前提下,對其局限性進行了反思與探討。
參考文獻:
[1] 潘恩榮.技術哲學的兩種經驗轉向及其問題[J].哲學研究,2012(1).
[2] PETER-PAUL VERBEEK.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Persuasive Technology:The Blurring Boundaries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J].Nanoethics,2009(3).
[3] VERBEEK P-P.Materializing morality:design ethics and technological mediation[J].Science,technology,& human values,2006(3).
[4] VERBEEK P-P.Moralizing technology: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the morality of things[M].Chicago and La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90.
作者簡介:趙悅(1994—),女,漢族,山西保德人,單位為太原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方向為科技哲學。
(責任編輯:馬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