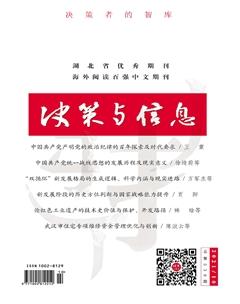論紅色工業遺產的技術史價值與保護、開發路徑
韓晗 李卓
[摘 ? ?要] 紅色工業遺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形成的工業遺存,是百年來我國工業化建設的見證。紅色工業遺產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成體系的技術史價值。紅色工業遺產因技術“轉移-再造”而存在,通過技術轉移形成知識再造,并通過全球化形成的技術交流與互助,促使工業遺產加速形成。紅色工業遺產的核心價值彰顯出黨史價值,同時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遺存,其技術史價值也不容忽視。對于具有技術史價值的紅色工業遺產的保護與開發,首先要將紅色工業遺產保護利用與“四史”教育有機結合,突出紅色工業遺產的社會價值;其次在保護和開發中應注重對紅色文化符號IP價值的挖掘與提升,促進紅色文化價值的穩定傳播;最后要加強對技術檔案遺產的數字化保護,深入挖掘檔案當中被遺忘或被遮蔽的歷史材料,重新進行IP賦能,以實現基于技術史價值紅色工業遺產的活化煥新。
[關鍵詞] 紅色工業遺產;技術史價值;紅色文化;工業文化;技術檔案遺產;文化旅游;文化遺產保護
[中圖分類號] F427;G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1)10-0056-07
紅色工業遺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形成的工業遺存,是百年來我國工業化建設的見證。紅色工業遺產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成體系的技術史價值。因此,紅色工業遺產不但是重要的革命文物,而且還是重要的技術史遺產。
人類研究工業遺產源于對技術史的反思,因此從邏輯上講,技術史價值是工業遺產的基本價值,紅色工業遺產的技術史價值不僅表現在工業遺產的科技發展、工藝流程,還更加豐富地體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技術“轉移-再造”。因此,立足于中共黨史視域,探討紅色工業遺產的技術史價值與保護利用路徑,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
目前,學界在工業遺產的技術史價值研究上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工業遺產的技術史價值不等同于技術價值,其更傾向于工業遺產的核心與內在屬性[1]。大多數學者認為工業遺產的技術史價值,主要體現在某項技術、設備在行業中所具有的開創性上,見證了工業遺產在科學技術上做出的突出貢獻[2][3],因此要將在技術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業遺產優先保護起來[4]。同時,技術史價值也是工業遺產確定、分級的重要基礎[3]。此外,在具體研究上,學者方一兵等(2015)聚焦于冶金工業遺產的技術史價值,其以鐵橋峽谷為例,提出了冶金工業遺產保護中應體現的四點技術史價值,即“核心技術的發明或意近,新舊技術體系的交替,冶金產品機器重要景觀的形成,新技術及其生產系統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5]。學者劉伯英(2018)借鑒科技史的研究方法,梳理了我國工業遺產研究的定位,探討了科技轉移、社會影響等問題,提出要注重工業遺產在科技史層面的研究[6]。
本研究擬以中共黨史視域下紅色工業遺產為研究對象,結合技術“轉移-再造”這一背景,探討紅色工業遺產的技術史價值及保護、開發路徑。
一、技術“轉移-再造”背景下的紅色工業遺產
人類技術的發展,都是技術轉移的結果,在轉移的過程中,又因地制宜形成了技術再造,即通過技術轉移獲得某項技術后,再實現技術的落地與本土化。
紅色工業遺產是我國工業現代化的產物。由于歷史原因,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我國都不是原發國家,所以與世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類似,我國的工業現代化也源自于現代科學技術轉移。技術轉移過程中的科技進步、社會變遷、政策改革等因素構成了紅色工業遺產的價值,并通過對紅色工業遺產的改造和利用得以重現。
具體來說,技術“轉移-再造”對紅色工業遺產的形成起到了如下兩重作用:一是技術轉移形成的知識再造,二是因全球化形成的技術交流與互助,這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與“后冷戰”時代的經濟一體化密不可分,這兩重作用見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現代化建設的艱辛開拓之路。
(一)技術轉移形成知識再造
技術轉移形成知識再造,指的是通過技術的轉移,形成人才培養、制度的落地乃至工業文化的生成等現代工業知識的本土化再造。這是工業遺產得以形成的文化基礎。
紅色工業遺產從誕生之初就與技術轉移分不開,最早形成的紅色工業遺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動工人運動的廠礦、鐵路交通線遺存。黨領導早期工人運動的廠礦、鐵路基本上有三個來源:一是外資在華進行資源掠奪的產物,如中東鐵路;二是晚清洋務運動發生并由官僚資本控制的企業,如“漢冶萍”公司;三是民族資本控制的現代企業,如長沙裕湘紗廠等。從技術上看,這些工廠都是技術轉移的產物。如津浦鐵路就是由英國人為工程師,所用的機車、車輛都為德國制造,而中東鐵路長期聘用日本工程師與管理人員,等等。
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了大量有技術、有知識的工人階級的產生,在風起云涌的世界工人運動之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逐步推行“八小時工作制”“月薪制”“每周休假制”與“傷亡撫恤金”等工人福利,而工人們也通過組建工會、組織罷工等工人運動來要求將工人福利制度化。
中國共產黨一俟成立,就派早期共產黨員到工廠中創辦工人學校、工人運動俱樂部,建立起工會和黨組織,通過工人運動為工人爭取制度化的福利。如“漢冶萍”公司曾成立過5個黨領導的工會,并組織了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為黨早期發展積蓄了重要的工人階級力量;而商務印書館則是黨在印刷行業中較早設立黨組織的機構,1923年7月,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決定,將上海的53名黨員,按居住較近、便于掩護、方便活動的原則,進行重新編組,共分四個組。住在閘北一帶的黨員編在第二組,命名為商務印書館小組,有13人。組長為董亦湘,組員有沈雁冰、張國燾、劉仁靜等人[7],之后黨中央派陳云到商務印書館,領導了1925年的大罷工。
這些因工人運動而生的工礦、鐵路交通線成為最早形成的紅色工業遺產。這些企業當中不少產業工人有一定的知識修養,甚至一些印刷工人還通曉外語,有較強的文字表達與工作能力,客觀上承擔著技術轉移的職能。因此,間接上也為黨領導工人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知識再造的基礎。
這種技術“轉移-再造”還體現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與改革開放時期,“一五”計劃期間,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對華進行援助,不僅提供了最先進的工業設備、技術和工藝圖紙,還派外籍專家進行指導工作。通過技術轉移,建設了以“一五六”工程為核心的近千個工業項目,涉及能源、機械、電子、原材料等多個重點領域和行業,奠定了我國工業化的基礎,初步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現代技術和工業體系,培養了大量的技術人才,提升了我國的工業技術能力。當中以“三線”建設為代表,1964年,由于中國周邊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緊張,考慮到可能存在敵襲的可能性,在“三五”計劃中提出了“三線”建設的戰略任務。“三線”建設的任務一經發布,位于一、二線地區的工人、干部和技術專家在“好人好馬上三線”的號召下,將一、二線地區的生產設備一分為二搬遷到西部地區,按照“山、散、洞”的選址原則,重新建立完整的工業生產體系,涉及核工業、航空航天、電子、化工、機械等多個行業,當中不少內遷的項目是援建工程,這也為“全國一盤棋”的工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以深圳蛇口工業區、上海浦東工業區為代表的改革開放前沿地區,大量引進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設備與制度,并通過派出學習、人才引進等方式,實現了技術轉移和知識再造,從而提高我國工業生產的總體能力。
(二)全球化形成的技術交流與互助
除了技術轉移實現知識再造之外,技術“轉移-再造”還體現在全球化形成的黨領導工業建設的技術轉移與互助上,這主要是黨從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后,由黨領導的對外技術合作工作中所反映。
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互助,當中以前蘇聯援建的“一五六”工程、前捷克斯洛伐克援建的“中捷友誼廠”、前民主德國援建的“北京798廠”等為代表。通過技術轉移,我國在工業技術、制度建立與工業文化普及上得到長足發展,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成果。舉例而言,“北京798廠”本是前民主德國援建的北京華北無線電聯合器材廠(即718廠),之后更名為北京第三無線電廠(即798廠)。在決定援建伊始,在建筑規劃、功能布局、業態配給中均以前民主德國的廠區為范本,由前民主德國專家與國內團隊配合建造,總設計由柏林克佩尼克區國營重型機器制造中心設計院承擔,建筑部分由當時的民主德國德紹(Dessau)設計院工業建筑設計室設計,是我國最具典型的包豪斯風格建筑,見證了前民主德國技術的對華轉移,是當時民主德國在中國援建的最大工程,如今798廠已經改造為國內最具代表性的工業遺產藝術區之一。
二是上世紀70年代,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交流。1970年代,中美關系開始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并先后與18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國際外交環境得以改善。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聯名向周恩來報送國家計委《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建議引進中國急需的設備和材料,該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批準[8]。1973年1月5日,國家計委又提交了《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之后又陸續追加了一批項目,計劃進口總額達到51.4億美元。利用這些設備并通過國內配套和改造,興建了27個大型工業項目[9]。當中以引進法國設備的南京棲霞山化肥廠(現中國石化金陵石化化肥廠)為代表,目前該廠是央企直屬的重要化肥生產基地,也是關于技術轉移的重要工業遺產。改革開放以后,通過對外開放,引進國外先進技術,開設經濟特區與開發區,一批目前仍在使用或部分被改造更新的改革開放工業遺產也應運而生。如深圳蛇口港碼頭、上海石洞口發電廠,等等。同時,改革開放也催生出了一大批其他紅色工業遺產,改革開放后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原有的部分“一五六”工程企業和“三線”企業等新中國建設時期企業,在產能更新、技術升級的過程中,歷經兼并重組、分割建立、搬遷重建,原有的企業廠址和生產設備被改造更新,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紅色工業遺產。
紅色工業遺產既是見證中共黨史、新中國史、社會主義發展史與改革開放史的重要歷史文物,又在技術轉移的過程中,科技不斷進步,帶來了產業的變遷,“催生了作為產業文明載體的工業遺產加速生成”[10] 451。這些工業遺產見證了黨領導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歷史,蘊含了豐富的紅色文化內涵。
二、紅色工業遺產所承載的技術史價值
紅色工業遺產的核心價值彰顯出黨史價值,同時也包括建筑審美價值、區位價值、年代價值與地域文化價值等多重價值。但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遺存,其技術史價值不容忽視。立足中共黨史視域我們發現,紅色工業遺產承載著不可忽視的技術史價值,這主要體現在生產工藝與豐富的檔案史料上。
(一)生產工藝的先進性和行業的開創性
紅色工業遺產見證了黨領導國家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是現代中國工業史、技術史的重要見證,具有重要且多元價值的紅色工業遺產其他價值茲不贅述。這里主要從技術史的角度談紅色工業遺產生產工藝的先進性和行業的開創性。
舉例而言,在“一五六”工程中,前蘇聯負責完成各項設計工作和設備供應,給予其他各種技術援助,并派專家到我國提供技術資料,幫助培養科技人才和管理干部[11] 223。在短短10年內,我國工業技術水平從落后工業發達國家近一個世紀迅速提升到20世紀40年代的水平[12]。這一時期的工業幾乎涵蓋了全部重要的工業行業,對新中國工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此外,我國相繼通過前民主德國、波蘭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對華援助和技術轉移,實現了無縫鋼管、超導玻璃纖維、高精度硅半導體等產品生產技術的落地與本土化。
在“三線”建設時期,往往是由多個企業進行支援,將最先進的技術、設備轉移到了三線,如由前蘇聯援建的第一汽車制造廠、沈陽第一機床廠、太原重機廠、第一重型機器制造廠。與此同時,部分高等院校、科研單位也隨之內遷,為中西部地區集聚了科技研究的人才力量,形成了先從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技術轉移,再向我國中西部地區技術轉移的“雙重轉移”。而在“四三方案”時期,我國又開始從日本、前聯邦德國、法國、美國、荷蘭等國大規模地引進工業設備,建設了26項大型工程。如1974年6月引進到武鋼的一米七軋板連續熱軋項目[13],這一技術水平在當時處于國內領先水平,填補了我國有關產品不能自主生產的空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大力從發達國家引進外資,引進技術規模不斷擴大,1975-1990年間,我國共引進軟技術2027項,國家重點引進3000項先進技術,并與數十個國家締結了政府間經濟合作協定,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交流關系[14]。不言而喻,紅色工業遺產在形成過程中,不僅代表了黨領導國家現代化建設中最先進的工業技術水平,而且在行業上也具有開創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技術史價值。
(二)紅色工業遺產包括豐富的技術檔案遺產
紅色工業遺產因其距今時間較短,遺留下了大量的技術檔案資料。這些檔案資料數量巨大,涉及的行業領域非常廣泛,如早期的選址、布局、建設,工藝設備的購買,企業黨組織的發展情況,技術人員的聘請等方面,形成了包括行政管理檔案、科技檔案、人事檔案和財會檔案等在內的科技檔案遺產。它們是紅色工業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工業檔案遺產見證了我國工業技術發展的變革。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業技術發展綜合體現了黨領導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過程,具有技術史與黨史雙重價值。通過研究紅色工業遺產中的檔案遺產,有助于把握我國工業發展規律,從中總結經驗教訓。不僅如此,工業檔案遺產還能夠考察工藝技術和設備的沿革。如“化工企業因連續化生產、自動、專業化強,擁有獨立的化工生產裝置,每一個裝置的設備檔案、化工生產活動形成的產品檔案都需要保持其完整性、成套性”[15]。工業檔案遺產詳細地記錄了當時的生產工藝和生產設備,雖然其中一些工藝技術因生產技術的不斷發展已經逐步被淘汰,但通過對相關檔案遺產的解讀,有助于重現失傳工藝技術,進而對我國工業技術史、產業史有更為深刻、全面的認識。
紅色工業遺產中的檔案遺產在國內數量巨大,內容豐富,涉及到了工業生產的方方面面。以“一五六”工程檔案遺產中有關前蘇聯技術的檔案為例,其見證了前蘇聯對華援助過程,如實地記錄了當時的工業建造水平、工藝流程和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尤其記錄了我國如何吸收、借鑒、利用這些先進技術進行工業化建設的過程。三線工業遺產檔案不僅大量存留在三線企業內(如攀鋼公司形成的檔案材料有352094卷[16],上海的八五鋼廠藏有三線建設時期的檔案716卷[17]),省、市級檔案館也藏有相當數量的三線檔案,如上海檔案館藏有有關三線建設的卷宗數量就達2247卷,北京市檔案館有關三線建設的卷宗有100多卷、宜都市檔案館現藏有焦柳鐵路三線建設工業遺產檔案1060卷[18]。這些史料既是技術史的重要史料,也是黨史的重要資料,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三、基于技術史價值的紅色工業遺產的保護與開發路徑
筆者認為,基于技術史價值下,紅色工業遺產應與其他工業遺產一致,采取保護利用并舉的策略,實現其活化煥新。但紅色工業遺產又有其特殊屬性,具體來說,基于技術史價值的紅色工業遺產保護與開發路徑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將紅色工業遺產保護利用與“四史”教育有機結合
這主要體現在強調紅色工業遺產的社會價值上,即對“四史”與技術史的關系值進行挖掘。紅色工業遺產核心價值具有“四史”價值,特別是具有黨史價值,從技術史角度來看,紅色工業遺產又是黨領導國家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工業化的重要文物,因此其所蘊含的技術史價值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技術史價值。
目前,紅色工業遺產保護利用的路徑仍以商業化開發為主,如改造為園區、步行街、酒店或商業綜合體項目,但許多項目只是依賴于工業遺產本體的區位價值與建筑審美價值,而忽視了其“四史”價值,特別是忽略了本應重視的技術史價值,未能充分地將相關文化資源活化煥新,予以挖掘利用。
但現有項目中,也有結合較好的例證,如宜昌809小鎮,原是“三線”軍工企業華強機械廠,軍工編號809。目前由宜昌市文旅公司改造為以提供游學、度假、餐飲與兒童樂園為主題的“809小鎮”。其在園區內設立了大量的宣傳板,記錄了“三線”工程的技術史意義及“華強機械廠”之前所承擔的一些技術革新任務,取得了較好的社會教育反響和意義。
(二)保護利用注重紅色文化符號的IP價值
紅色文化符號是紅色工業遺產的底色,也是紅色工業遺產技術史價值的文化體現。目前紅色工業遺產這一概念尚未被完全闡釋與提出,保護和開發導向也多以市場開發為主,部分納入到文物保護范疇內的也多以年代價值考量。
就工業遺產而言,紅色文化符號為紅色工業遺產所獨有。紅色工業遺產見證了黨領導國家現代化建設從零起步的艱辛歷程,從中央蘇區兵工企業的“一把鐵錘開張”,到今天我國全門類、多樣化的工業生產技術體系,其技術史發展脈絡本就是一部紅色文化沿革變遷史。
舉例而言,以寧波和豐廣場為例,這原本是1925年和豐紗廠工人運動的發生地,是重要紅色工業遺產。近年來,寧波市政府推動紅色工業遺產保護利用與城市改造更新相結合,將和豐紗廠舊址改造為和豐黨群中心與綜合商業體和豐廣場,通過深入對紅色文化符號IP價值的挖掘與提升,形成了“黨群中心+商業體”的復合城市公共空間,既促進了紅色文化價值的穩定傳播,又使之成為在全國具有示范性的紅色工業遺產改造項目。
(三) 加強對技術檔案遺產的數字化保護
盡管紅色工業遺產技術檔案當中部分保存較好,但目前工業遺產技術檔案總體保護水平仍較低,特別是一些企業因為改制、兼并或破產,導致大量重要檔案文獻散佚到民間,當中不少被作為廢紙處理。比如通過“孔夫子舊書網”以“工廠檔案”為關鍵詞進行模糊檢索,會發現有近3000種國有企業的統計報表、干部檔案、介紹信、政審記錄、圖紙等重要材料已經作為舊文獻類商品出售,甚至當中不乏成套圖紙、軍工檔案以及一些明確標明密級的重要文件。這些都是珍貴的技術檔案遺產,是紅色工業遺產的重要組成,理應得到妥善保護。
數字化保護是目前檔案保護的主流方式,即通過掃描成像形成數字文檔,有條件還可以上傳到區塊鏈上,對檔案內容進行永久保存。但目前國內尚無一家具有紅色工業遺產的企業或開發機構將相關技術檔案予以數字化管理,即使保管相對較好的技術檔案遺產,也因為經費、技術等各方面原因,導致其數字化保護水平較低。在檔案數字化保護已經成為大趨勢的今天,紅色工業遺產技術檔案的數字化顯然遠遠低于國內檔案管理的平均水平,導致大量檔案文件要么束之高閣,要么破損毀滅或流落民間,倘若長此以往,紅色工業遺產的許多技術檔案將不復存在。
技術檔案遺產的數字化保護有兩種利用路徑。一是深入挖掘檔案中被遺忘或被遮蔽的歷史材料,特別是一些被遺忘的勞動模范、人物英雄或反映國際援助合作中的感人事跡等具有社會教育意義、能夠服務于我國對外宣傳工作的人物和事件,將其重新進行IP賦能,改編為文藝作品、非虛構文學或作為博物館陳列宣講資料,使之起到“四史”教育的積極作用;二是作為數據庫向學界開放,為研究技術史、黨史的學者提供重要的一手資料。
紅色工業遺產技術檔案的湮滅速度遠遠超過目前的保護力度,令人扼腕。因此其數字化保護是一項時不我待的工程,也是紅色工業遺產保護利用當中亟需重視的一個關鍵課題。
四、結語
就目前現狀而言,紅色工業遺產的技術史價值基于“四史”特別是黨史價值而存在,而其保護開發路徑也應圍繞著推進“四史”教育的社會價值屬性而開展。再次重申,紅色工業遺產的技術史價值不只是一般意義的技術變革史或門類技術史,而是包括“四史”這一宏大敘事的歷史,可謂茲事體大,理應在全社會引起足夠關注與重視。
[參考文獻]
[1] ?潛偉.技術遺產論綱[J].中國科技史雜志,2020,(3).
[2] ?楊明.工業遺產的科技價值及其實現[D].沈陽:東北大學,2013.
[3] ?季宏,徐蘇斌,青木信夫.工業遺產科技價值認定與分類初探——以天津近代工業遺產為例[J].新建筑,2012,(2).
[4] ?張柏春.留住工業與技術發展的里程碑——技術史視野中的中國工業遺產[J].工程研究-跨學科視野中的工程,2017,(5).
[5] ?方一兵,姚大志.論冶金工業遺產的技術史價值[J].工業建筑,2015,(5).
[6] ?劉伯英.關于中國工業遺產科學技術價值的新思考[J].工業建筑,2018,(8).
[7] ?汪守本.商務印書館第一任黨支部書記董亦湘[EB/OL].商務印書館,2014-07-13.https://www.cp.com.cn/Content/201
4/07-31/1459424043.html.
[8] ?陳東林.70年代前期的中國第二次對外引進高潮[J].中共黨史研究,1996,(2).
[9] ?陳東林.20世紀50-70年代中國的對外經濟引進[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4,(6).
[10] ?陳凡,呂正春,陳紅兵.STS視角下工業遺產價值生成探析[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5).
[11] ?陳夕.中國共產黨與156項工程[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
[12] ?陳夕.156項工程與中國工業的現代化[J].黨的文獻,1999,(5).
[13] ?石其寶.復交后的中日經貿關系研究(1972-2004)[D].天津:南開大學,2006.
[14] ?吳奇志,聶文星.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技術引進:回顧與前瞻[J].上海市經濟學會學術年刊,2008.
[15] ?高俊.工業遺產檔案開發利用研究[D].南京:南京大學,2014.
[16] ?攀鋼檔案處.三線建設中的攀鋼檔案工作[J].四川檔案,1989,(6).
[17] ?徐有威.中國地方檔案館和企業檔案館小三線建設藏檔的狀況與價值[J].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2017,(1).
[18] ?馮明,周長柏.焦柳鐵路(宜都段)沿線三線建設工業遺產檔案整理與研究[J].檔案記憶,2019,(3).
[責任編輯:汪智力]
On the Technological History Valu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Red Industrial Heritage
HAN Han, LI Zhuo
Abstract: The red industrial heritage is an industrial relic form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hip of the people's modernization drive. It is a testimony to my country'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d industrial heritage, a self-contained technological history value has been formed. The red industrial heritage exists because of the "transfer-reengineering" of technology. Knowledge reengineering is formed through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and mutual assistance formed through globalization promote the accelerated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he core value of the red industrial heritage demonstrates the value of party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as an important relic of the country's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 value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cannot be ignored.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d industrial heritage with technological historical value,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he red industrial heritage should be organically combined with the "four history" education to highlight the social value of the red industrial heritage; secondly,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ed culture i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excavation and promotion of symbolic IP value promotes the stable spread of red cultural value; final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digital protection of technical archives heritage, deeply excavate the forgotten or obscured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archives, and re-enable IP to realize technology-based The revitalization and renewal of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red industrial heritage.
Keywords: red industrial heritage; technological history value; red culture; industrial culture; technical archives heritage; cultural tourism;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收稿日期] 2021-08-10
[基金項目] 本文系文化和旅游部2018年度文化和旅游智庫項目“基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公共文化服務效能評估體系研究”子課題“公共文化服務效能量化指標化體系構建”成果。
[作者簡介] 韓晗(1985-),男,北京市人,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教授、武漢大學景園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化產業史、文化產業基礎理論與國家文化建設研究;李卓(1997-),女,山西臨汾人,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