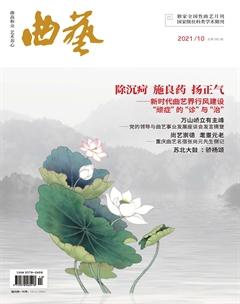蘇州彈詞流派唱腔摭談
沈鴻鑫
彈詞流派唱腔的發展是一個縱向傳承、橫向吸收、精心創造的過程。其傳承、創造大體有幾種類型。筆者僅就自身所知,梳理簡述,恭請評正。
第一種是有明顯的師承關系的。如從【馬調】到【魏調】到【沈調】【薛調】再到【琴調】,就可以充分看到他們之間的師承關系。【馬調】是清咸豐、同治年間彈詞藝人馬如飛所創。馬如飛繼承發展乃父馬春帆的《珍珠塔》,有“塔王”之譽,他是清“評彈后四家”之首。【馬調】在書調基礎上,吸收民歌【東鄉調】的音樂,常在下句第六字拖腔時用頓音,以突出韻腳,形成特色。【馬調】以吟誦為主,樸實流暢,節奏明快,長于敘事。【魏調】是彈詞藝人魏鈺卿所創。魏鈺卿(1879—1946),是馬如飛12弟子之一的姚文卿之徒,也擅唱《珍珠塔》。【魏調】突破原有節奏,更趨靈活自由,疊句連唱是其特點,往往一瀉而下,下句第六字拖腔自成一格,長段、急口也是它的特色。【魏調】唱腔爽利委婉,韻味醇厚,又稱“馬派【魏調】”,代表作有《寫家信》《陳翠娥痛責方卿》等,傳人有徒鐘笑儂、薛筱卿、沈儉安、王燕語,子魏含英,孫女魏含玉等。沈儉安(1900—1964),先隨寄兄沈勤安學藝,后投《珍珠塔》名家朱兼莊的門下,再拜魏鈺卿為師。他在【馬調】到【魏調】基礎上進行改進,豐富了曲調,特別是小轉腔的靈活運用加之其啞糯的嗓音,讓他的演唱顯得飄逸委婉,情味濃郁。【沈調】傳人有周云瑞、陳希安、湯乃安等。薛筱卿(1901—1980)也是魏鈺卿的徒弟,他長期與沈儉安拼檔,任下手,他嗓音清脆明亮,咬字清晰鏗鏘,唱腔旋律明快流暢,對疊句連唱頗有心得,如此便形成了自己清麗、流暢、遒勁的【薛調】。他的琵琶技巧十分嫻熟,創造了支聲復調的伴奏方法,有“薛派琵琶”之稱。傳人有徒龐學卿、郭彬卿,女兒薛惠君等。
新中國成立后,【馬調】一脈下又出現了【琴調】【小飛調】等。【琴調】由朱雪琴所創。朱雪琴(1923—1994),初隨養父朱蓉芳彈唱長篇《雙金錠》《描金鳳》,后師從沈儉安改唱《珍珠塔》,她根據自己中氣足、本嗓好、高音上得去的先天條件,在【沈調】的基礎上,加快速度,增強節奏的跳躍,強化咬字吐音的力度,對原唱腔或向上翻高,或加花演變,突出旋律中的跌宕和棱角,以及拖腔的氣勢,并且全用本嗓演唱,創造了激越豪放、爽朗流暢的【琴調】,在女聲腔中唱出了陽剛之氣。朱雪琴演唱時鏗鏘明朗揮灑自如,加上灑脫的三弦和下手郭彬卿繁密的琵琶伴奏,突顯出曲折多變、歡快跳躍的藝術特征。【琴調】代表作有《珍珠塔·七十二個他》《梁祝·英臺哭靈》《沖山之圍·游水出沖山》,開篇《擊鼓戰金山》《瀟湘夜雨》《南泥灣》《好八連》等。20世紀50年代末由彈詞演員薛小飛所創的【小飛調】,也由【魏調】【沈調】發展而來。薛小飛(1939—2012),師從朱霞飛習唱《珍珠塔》,后又拜師魏含英,長期與邵小華拼檔演出。除《珍珠塔》,還演唱過長篇《梁祝》《何文秀》,為蘇州人民評彈團演員。【小飛調】脫胎于【魏調】和【沈調】,同時吸收【蔣調】的某些因素加以變化發展,兼有【魏調】的明快爽朗和【蔣調】的醇厚韻味。節奏明快,上下句的連接常常不用過門,數十句唱詞疊句猶如貫珠連環等是【小飛調】的特點,代表作有《方卿哭訴陳翠娥》《方卿見娘》《打三不孝》,開篇《我的名字叫解放軍》等。
第二種是兼有師徒傳承和借鑒發展的情況。前者如從周玉泉的【周調】到蔣月泉的【蔣調】,再到尤惠秋的【尤調】,后者如蔣月泉的【蔣調】之于張鑒庭的【張調】和徐麗仙的【麗調】。
周玉泉(1897—1974),師從張福田習《文武香球》,后又從王子和學唱《玉蜻蜓》,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他以張福田、吳昇泉等的書調唱腔為基礎,借鑒京劇譚派老生、程派青衣的唱腔,結合自己的嗓音,創造了曲調悠揚、清勁雋永、溫文端莊、舒徐大度的【周調】,代表作有《文宣哭觀音》《云房產子》《智貞描容》等。有徒蔣月泉、周伯庵、華伯明、薛君亞等。20世紀30年代末,周玉泉的徒弟蔣月泉在【周調】的基礎上創造了【蔣調】。蔣月泉(1917—2001),初學《珍珠塔》,后從張云亭、周玉泉學唱《玉蜻蜓》,一度與周玉泉拼檔。【蔣調】繼承了【周調】的間架和基本旋律,再借鑒京劇余派、楊派老生的唱腔、潤腔唱法,行腔上加了若干裝飾音。在【周調】基礎上形成的【蔣調】,旋律更加豐富婉轉,韻味更加濃郁醇厚,極富抒情性,呈現出一種雍容華美、瀲滟濃彩的風格。后來成為彈詞中影響最大的流派唱腔,代表作有開篇《杜十娘》《刀會》《戰長沙》《鶯鶯操琴》《寶玉夜探》,選曲《玉蜻蜓·庵堂認母》《玉蜻蜓·廳堂奪子》《海上英雄·游回基地》《王孝和·寫遺書》等,傳人有王柏蔭、潘聞蔭、蘇似蔭、秦建國等。【尤調】為彈詞演員尤惠秋所創。尤惠秋(1930—2000),初拜彈詞藝人吳筱舫學唱《白蛇傳》《玉蜻蜓》,后拜沈儉安補學《珍珠塔》。新中國成立初期,尤惠秋向蔣月泉學習長篇彈詞《林沖》,頗得【蔣調】的真諦。他還演唱過《梁祝》《王十朋》《釵頭鳳》等長篇,為江蘇省曲藝團主要演員。尤惠秋嗓音低沉渾厚,在【蔣調】【沈調】的基礎上,發揮中低音特長,借鑒吸收京劇老生唱腔,加強小腔的變化,運用裝飾音、顫音、共鳴等技巧,創造了委婉流暢、軟糯細膩的【尤調】。代表作有開篇《諸葛亮》,選曲《梁祝·送兄》《王十朋·撕報單》等。
蔣月泉和張鑒庭、徐麗仙同一時代,所擅長書目也頗不相同,他們之間不存在師徒關系,但是【張調】【麗調】與【蔣調】又有著一定程度的傳承關系。【張調】是20世紀40年代由張鑒庭所創。張鑒庭(1909—1984),幼年唱過紹劇、髦兒班、小熱昏,后師從彈詞藝人朱詠春學唱《珍珠塔》《倭袍》,后自編自演長篇彈詞《十美圖》《顧鼎臣》,20世紀30年代末走紅書壇。張鑒庭在【蔣調】基礎上,化進夏荷生的【夏調】的藝術因素,并吸收京劇老旦的唱腔,充分利用自己嗓音高亢、音域寬廣、中氣充沛的條件,在拖腔轉腔方面加以發展,形成節奏穩健、唱腔激越、力度強烈、韻味濃重的【張調】。【張調】的戲劇性較強,很有藝術感染力和劇場效果,代表作有《誤責貞娘》《鍘美》《鐘老太罵敵》《望蘆葦》《留鳳》等,傳人有子張劍琳,徒周劍萍、陳劍青、王正浩、黃嘉明、王錫欽等。
徐麗仙的【麗調】創于20世紀50年代。徐麗仙(1928—1984),幼年入普余社錢家班,后與師姐拼檔彈唱《倭袍》《啼笑因緣》。從20世紀50年代起,徐麗仙與劉天韻拼檔彈唱長篇《杜十娘》《王魁負桂英》《雙珠鳳》等。徐麗仙的氣息不是非常充沛,嗓音并不太亮,但較糯而寬厚。她發揮自己的音樂天賦,在【蔣調】基礎上向婉約方面加以發展。她演唱時并不多用高音,而是常常采用跌宕對比的方法,讓旋律先下行而后翻高,有時干脆采取低徊的旋律。她大膽吸收了評劇、錫劇、粵劇、京韻大鼓、梅花大鼓、中外歌曲的各種營養,在彈詞一般采用五聲音階的基礎上,適當加進“4”“7”兩個音,又巧妙地融入戲曲板腔體的一些手法,形成了委婉俏麗,新穎優美的獨特風格,世稱【麗調】。【麗調】比較善于表現婦女哀怨纏綿的感情,但是也可表現明朗活潑的內容。代表作有《情探·梨花落》《杜十娘·投江》,開篇《新木蘭辭》《六十年代第一春》《黛玉焚稿》《黛玉葬花》《飲馬烏江河》《望金門》等。【麗調】的從者眾多,現已成為蘇州彈詞中主要的女聲唱腔。
第三種情況是沒有師承關系,主要是藝術上的傳承。如從【俞調】到【祁調】和【侯調】。【祁調】由彈詞藝人祁蓮芳所創。祁蓮芳(1908—1986),長期與舅父陳蓮卿拼檔,任下手,彈唱長篇彈詞《雙珠鳳》《文武香球》《繡香囊》等,20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走紅。他在老【俞調】的基礎上,吸收京劇程派唱腔加以變化發展,其旋律比【俞調】更為哀怨凄切,拖腔起伏婉轉,節奏舒緩。【俞調】以假嗓為主,兼用真嗓,但其發聲方法偏于低沉內抑,特別善于抒發沉郁凄婉、纏綿悱惻的感情,又有“催眠調”之稱,代表作有《雙珠鳳·霍定金私吊》《繡香囊·夫妻相會》等。后來周云瑞譜唱的開篇《秋思》也是【祁調】的名作,邢晏芝在彈唱《楊乃武》時,在【祁調】中揉進【俞調】【侯調】的因素,又使【祁調】有了新的發展。【祁調】傳人有徐文萍、嚴燕君、徐淑娟、邢晏芝等。20世紀50年代由彈詞女演員侯莉君所創的【侯調】也是從【俞調】腔系發展而來。侯莉君(1925—2004),幼年入普余社錢家班習藝,從師陳亞仙,一度輟演,1950年后與徐琴芳拼檔演出《落金扇》,此后又演唱《梁祝》《情探》等,是江蘇省曲藝團主要演員。侯莉君嗓音不夠寬亮但柔細,她充分利用這一特點,在【俞調】基礎上,揉進京劇程派悠長低徊的長腔,并吸收錫劇等地方戲曲的行腔,加上她特有的顫音、泣音,創造出了一種字少腔多、九曲三彎、纏綿哀怨、婉轉俏麗的【侯調】。【侯調】代表作有《鶯鶯拜月》《英臺哭靈》等。傳人有女侯小莉,徒唐文莉、潘莉韻、高莉蓉等。
【馬調】一系發展也有類似的情況,如朱耀祥的【祥調】、李仲康的【仲康調】等。朱耀祥(1894—1969)曾學蘇州灘簧,后拜彈詞名家趙筱卿習彈詞《描金鳳》《大紅袍》,20世紀30年代與趙稼秋拼檔演唱長篇彈詞《啼笑因緣》而成名,并創造了【祥調】。它是從【魏調】衍化而來,在繼承【馬調】系統平緩流暢特點基礎上,【祥調】吸收蘇州灘簧行腔特點。唱腔高亢、醇厚、嘹亮,經常運用“6”音行腔,長腔跌宕多姿,顯得蒼勁而雄健。【祥調】后又吸取【沈調】的唱法,下句拖六點七的轉腔有較明顯的【沈調】韻味。朱耀祥在彈詞表演中首次嘗試用二胡伴奏,別具一格,傳人有子少祥、幼祥、小祥,徒程美珍、高美玲、陳平宇等。【仲康調】由彈詞演員李仲康所創。李仲康(1907—1970),幼年即隨父李文彬習唱《楊乃武與小白菜》,后為蘇州人民評彈團演員。他嗓音高亢,行腔近似于【沈調】【祥調】,演唱時加強力度和節奏感,以本嗓為主,間以小嗓,旋律多變化,其子李子紅的琵琶伴奏運用多種手法,強烈而富活力,別具一格,更襯托出唱腔的鏗鏘遒勁。【仲康調】傳人有子李子紅,徒張如秋、余韻霖、金麗生等。
20世紀50年代末,彈詞女演員王月香(1933—2011)創造了【王月香調】。王月香的伯父王斌泉、父親王如泉均為彈唱《雙珠鳳》的彈詞藝人,她幼年從父學藝,8歲即與姐蘭香、再香拼三檔彈唱《雙珠鳳》。20世紀50年代中期加入蘇州人民評彈團,與徐碧英拼檔彈唱長篇《梁祝》。她在【魏調】【薛調】基礎上,加重感情色彩,響彈響唱,節奏明快,大段疊句連唱,一瀉千里,聞之淋漓酣暢。【王月香調】注重感情投入,尤長于表現悲怨凄切的內容,唱到動情之處,往往聲淚俱下,有較強感染力。代表作有《英臺哭靈》《三斬楊虎》等。傳人有趙慧蘭等。
第四種可稱為融合發展情況。如【小陽調】。20世紀初,【小陽調】由彈詞藝人楊筱亭所創。楊筱亭(約1885—1946),師從沈友庭學唱《白蛇傳》《雙珠球》,對兩部書目均有所加工。他在書調基礎上,吸收【俞調】【馬調】的因素,形成了曲調高旋低落,悠揚婉轉,真假嗓并用的藝術風格。他演唱的上句多用假嗓,下句轉真嗓,在第六字拖腔時又用假嗓。評彈術語稱真嗓為“陽面”,此調用假嗓多于真嗓,故稱“小陽調”。【小陽調】適于單檔演出時用,楊筱亭之子楊仁麟,對【小陽調】又有所發展。
20世紀20年代后期,彈詞藝人徐云志創造了【徐調】。徐云志(1901—1978),師從夏蓮生習《三笑》,他吸收【俞調】委婉多變的行腔方法,還融入了江南民歌旋律、京劇女老生露蘭春的唱腔因素,創造了【徐調】。【徐調】節奏從容穩健,曲調優美輕盈悠揚,拖腔跌宕多姿,又稱“糯米腔”,傳人有嚴雪亭、邢瑞庭、祝逸亭、華士亭、王鷹等。嚴雪亭(1913—1993),初從徐云志習唱《三笑》,后改唱長篇《楊乃武與小白菜》,20世紀30年代,嚴雪亭在快【徐調】的基礎上,吸收【小陽調】的藝術因子,形成自身運腔質樸、簡潔、爽利,吐字清晰,假嗓俏麗的藝術風格。嚴雪亭演唱時真假嗓并用,常用假嗓翻高腔,輔以裝飾性小腔,最終創造了兼擅敘事抒情、親切雋永的【嚴調】。【嚴調】代表作有《楊淑英告狀》《密室相會》《祝枝山說大話》《孔方兄》及開篇《一粒米》等。傳人有朱一鳴、胡國梁等。
20世紀30年代初,彈詞藝人夏荷生創造了【夏調】。夏荷生(1899—1946),其父在嘉善開設夏廳書場,他自小受到熏陶。曾從伯父夏吟道學《倭袍》,后從錢幼卿習《描金鳳》,20世紀20年代便享譽書壇。夏荷生嗓音高亢清亮,其【夏調】特點是響彈響唱,真假嗓并用,曲調剛健挺拔,唱腔簡而不繁,跳進多于級進。由于音域較高,【夏調】上半句多用假嗓,下半句轉用真嗓,轉換自然,對比鮮明,有徒徐天翔等,張鑒庭、楊振雄、凌文君等都唱過【夏調】,并受其影響。
徐天翔(1921—1992),1936年師從夏荷生習唱《描金鳳》,后還彈唱過長篇《白毛女》《寶蓮燈》,中篇評彈《東海女英雄》等。為浙江曲藝團主要演員。20世紀50年代,他在【夏調】基礎上,吸收【蔣調】【薛調】以及京劇的某些音調和唱法,有時還將“九轉三環調”融進某些唱段之中,基本采用本嗓,強調抑揚頓挫,快、慢,強、弱,遒勁、飄逸的對比鮮明,形成了明朗昂揚、具有時代氣息的【翔調】。代表作有《東海女英雄·乘風破浪》《描金鳳·董賽金策馬下山坳》等。
楊振雄(1920—1998),幼年即隨其父楊斌奎習唱《大紅袍》《描金鳳》,后自編自演《長生殿》。楊振雄在【夏調】基礎上,吸收【俞調】及昆曲等的音樂素材和演唱方法,衍變發展出了【楊調】。其唱腔可高亢雄健、典雅深沉,又可委婉凄切。【楊調】演唱時真假嗓并用,以真嗓為主,常運用滑音、顫音等技法增強氣氛,主要采取響彈響唱、快彈慢唱、緊彈散唱等形式,靈活多樣,代表作有《劍閣聞鈴》《昭君出塞》《武松》等,有徒沈偉辰、孫淑英等。
【姚調】是在20世紀40年代由彈詞藝人姚蔭梅所創。姚蔭梅(1906—1997),始學評話《金臺傳》、彈詞《描金鳳》,后改唱長篇彈詞《啼笑因緣》。在長期演出過程中,姚蔭梅逐步形成自己的演唱風格,世稱【姚調】。【姚調】受【小陽調】的影響,其唱腔旋律平直,節奏從容,真嗓為主,偶用假嗓,行腔自由靈活,突出語言因素和敘事特點,有時字多腔少,近似白話,唱腔中時常夾入說白,說和唱銜接自然,通俗曉暢。一般以單檔演出,三弦伴奏。代表作有《舊貨攤》《煉印》《楊光林轉變》等,傳人有蔣云仙、江肇焜等。
彈詞流派唱腔是伴隨著評彈藝術的發展、變革而興盛、發展的。在各個歷史時期,一些有創造意識的演員,在已有書調或前輩所創造的流派的基礎上,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唱腔和演唱風格。流派的形成,與該演員的個人稟賦、審美取向、師承關系,以及擅長書目和人物表現需要等方面密切相關,在傳承、嬗變、創造的過程中往往呈現出先仿后創、廣采博納、揚長避短、自創一格等特征。歷經長期發展,蘇州彈詞的音樂唱腔已經形成流派眾多、精彩紛呈的局面,大大提升了蘇州彈詞音樂的藝術表現力和審美價值,吸引了更多的聽眾。
(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