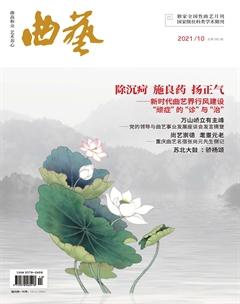從明清以來的“口傳心授”到體系化教學建設
施吟云
口頭傳統表演存在于各個國家、地區、民族和社群之中。各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以“口傳心授”為傳承方式的表演藝術形式,大致包括了口頭敘事、故事詠唱、民間歌曲及其他說唱形式。在我國,這類基于民間口頭文學和歌唱藝術的故事講唱,一類是曲藝,一類是戲曲。
曲藝與戲曲之間最直接的區分方式,大約是以表演形式決定的。曲藝的表演者可以概括為“我是我,我又非我”,演員以自己的真面目出現,一人分飾多角,在角色中“跳進跳出”。他們的語言有時是本我的心聲,有時是作為故事外“第三只眼”的抒發,有時是角色的代言;或千軍萬馬,或氣象萬千,或兒女情長,都存在于演員的講唱之中。演員與觀眾處在同一個空間,同時,演員也用自己的講唱帶著觀眾進入不同的時間與空間。戲曲則須以“必定非我”的一人一角方式,拋棄自我,通過服、化、道的媒介,完全沉浸在角色之中進行演繹;戲文雅致,演員與觀眾之間處在同一個空間,卻又處在完全不相干的兩個時空。也因為這樣有著不同側重的演繹形式,曲藝一向被認為更貼近老百姓,而愛好戲曲的更多是文人士大夫。然而曲藝“下里巴人”“泥土氣重”的特質是否就決定了曲藝的價值相對不如別的藝術門類呢?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有意思的是,在全球很多地方,敘事性說唱的表演形式在歷史傳承中,通過被遷移成為文學作品并得以保留。例如,家喻戶曉的荷馬史詩,在有文字記錄前就已經在南斯拉夫的史詩詠唱傳統中流傳已久,如今更是被視為杰出的文學作品。除了文學性,口頭表演中以演唱為主的藝術形式,通常兼有精彩的樂器演奏和高超的聲樂技巧。人們精心地保存、表演、發展、創作,口頭藝術傳統藝術才代代相傳,源遠流長,并推動著每一種形式成熟為獨立的表演藝術傳統。這群人在蘇州評彈這一藝術形式中被稱為“說書先生”,或者叫“說書人”。
蘇州評話、蘇州彈詞先后形成于明末清初,到清代乾隆、嘉慶年間已經成熟。蘇州評彈(簡稱“評彈”)作為長江三角洲的代表性民間藝術形式,指稱的是用蘇州方言表演的評話(說書)和彈詞(唱書)這兩種說唱傳統。因為文字記載的資料很少,現在雖然難于詳細描述這段發展過程的脈絡,但通過一代代說書先生精彩絕倫的軼聞紀事,仍有依稀可見的線索讓我們一窺。例如,明末的莫后光和他著名的“在座忘”理論,要求說書人演出時“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貴要,忘身在今日,忘己姓何名,于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曾在乾隆皇帝御前說書的王周士為后世說書人立下的“行業標準”《書品·書忌》,他在蘇州宮巷第一天門創立了蘇州評彈界同業組織“光裕公所”(后改稱“光裕社”),今天這一舊址仍然矗立著蘇州評彈標志性的表演場所“光裕書場”。王周士先前演繹過的文學作品《落金扇》《白蛇傳》至今仍是蘇州評彈老聽客們百聽不厭的熱門書目。
今天我們所熟知的“評彈”一詞,實際上是20世紀50年代才產生的復合詞匯,并得以廣泛使用。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在陳云同志的發起和支持下,成立了蘇州評彈學校。這是中國曲藝藝術事業中第一所專業學校,20世紀80年代復校。蘇州評彈學校積極地探索集體教育和個別傳書相結合的教學方法,在保留了蘇州評彈以“流派”為傳承的基本方式的同時,努力培養與時俱進、兼具專業性與藝術性的優秀傳統藝術傳承人。
然而這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陳云作為一名評彈愛好者,不僅促成了蘇州評彈學校的成立,還為學校寫下了校訓“出人、出書、走正路”。陳云還撰寫過一篇對評彈影響深遠的文章——《目前關于噱頭、輕松節目、傳統書目的處理的意見》,意在清除評彈書目中各種荒謬下流的因素以及亂插噱頭的行為。顯然,他迫切地希望評彈能夠有自己的發展方向。塑造評彈的未來,促使他決心成立蘇州評彈學校。直到今天,培養新一代、創作新書目、滿足觀眾期待和口味這一系列的核心觀念,依舊為一代代的評彈人奉為圭臬,綱舉目張地為蘇州評彈這門藝術的繼承和發展提供了方向。陳云的“意見”在今天仍然發揮著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為了培養專業的蘇州評彈工作者,蘇州評彈學校設置了3年制中等職業教育和2年制大專教育,并得到國家教育部承認。在這樣的體制下,青年演員的文化水平,包括文學和音樂的素質普遍提高。蘇州評彈學校培養了一大批青年演員,已經培養了幾代評彈藝術傳承人。現在,除了一些社會上的掛靠藝人,當今活躍在舞臺上的中年評彈演員大部分都曾經在蘇州評彈學校接受過基本訓練。
蘇州評彈學校以學校科目為學習框架的現代教育體系和傳統師承做法迥異。傳統的“師父帶徒弟”的方法讓學徒和師父之間保持著“亦師,亦父”的關系,這對學生深刻領會本門藝術流派的精髓有著極大的好處,相對來說,真正能夠“出師”的徒弟可謂是鳳毛麟角。但是,學生們日后經過自我的不斷錘煉,也極有可能成為蘇州評彈的大家。蘇州評彈學校的教學體系內有完整的教學大綱、教學方案,一對一指導,以及考試等制度。在前4年里,學生應該掌握全部必備的評彈表演技藝。第5年,學生們將接受強化訓練,尤其被選入“傳承班”的優秀學生更將得到重點培養。盡管這個被稱作“職業教育”的制度競爭激烈,相較于傳統上由一個師父口傳心授的有限學習方式來說,蘇州評彈學校提供了自明清以來蘇州評彈傳統學習方法中得不到的全面性、豐富性、深刻性。此外,1980年成立的蘇州評彈研究會,在其活動并展開藝術研究工作的10年間,召開了多種類型的藝術研討會,有對演員的專題研究、對書目的專題研究和對書目整舊創新的專題研究。一批真正對評彈藝術充滿了熱情、懷抱敬畏的老先生們筆耕不輟,用自己日積月累的聽覺經驗、史料考據,為蘇州評彈的學習、研究留下了一大批寶貴的資料。
在邁入21世紀的第3個10年,蘇州評彈作為蘇州的文化基因,仍然深深地根植于蘇州人日常的生活之中。無論技藝高低,每個說書人的保留書目都是他們對師承流派的繼承。說書先生們向人們展示蘇州的傳統藝術,同時他們身處傳統之中,成為傳統的一部分。但是作為新時代、充滿著文化自信的藝術傳承者,蘇州評彈的傳承者們必然需要以一種更寬廣的視野、篤定的心態去面對這一門歷史悠久的傳統藝術文化。那么,21世紀的、甚至邁向22世紀的評彈繼承者們應該接受怎樣的學習呢?
這本由中國曲藝家協會和遼寧科技大學組織編寫的教材《蘇州評彈表演藝術》或許就為蘇州評彈傳承者們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全書共分7個章節,集中就蘇州評彈的歷史鉤沉、藝術本體的形態分析、表演大家與其表演特征、文化審美與價值等方面進行了詳述,在理論層面上為蘇州評彈的傳承者們提供了一個認識這門藝術的全景式的描寫。每一章節的最后,編者并未糾結于知識要點的考核,而是以思考題的方式為使用該教材的學生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的機會。這也讓我們看到這本教材的編寫團隊對未來蘇州評彈傳承者們的期許:曲藝的傳承不僅是學習如何進行表演,傳承者們首先應該對這一門藝術有一個宏觀的認識。這種認識不能只局限在自己擅長的書目、流派,而應該帶著一種對歷史的觀照、對藝術理論更高的重視、對自我藝術修為更深刻的定位去傳承好一門藝術。
《蘇州評彈表演藝術》凝結了蘇州評彈一代代的表演藝術家、理論家、工作者的心血與汗水。盡管藝術來自百姓,脫胎于民間的娛樂功用、社會化功用,只有當它能夠以體系化、理論化的方式去總結一代又一代人的創造,留下評彈表演藝術在歷史發展中的高光時刻,升華總結表演行家的豐富經驗,讓追隨者們認識到這門藝術的價值,以及自己承擔的文化歷史使命,這門藝術才更有可能以成熟的面貌流芳百世。
中國傳統說唱藝術在維系社會凝聚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些傳統藝術形式折射出了特定的地理和地域民風、方言和文化風格。蘇州評彈作為吳方言區最重要的曲藝藝術之一,包含的不僅是引人入勝的故事、婉轉動聽的曲調音律。蘇州評彈承載的是蘇州2500年以來“崇文尚武”的民風,是倡導“忠孝仁義”的價值觀與人文情懷,是蘇州方言的軟糯美好,是蘇州人如涓涓流水般、不疾不徐的性格。這些吳地文化的特色,是如何反映在蘇州評彈的藝術理論之中的,《蘇州評彈表演藝術》從藝術本體分析的角度,也給出了答案。
在現代化的蘇州城內,蘇州評彈這一藝術傳統一直在延續著,代表著蘇州人閑適的生活方式。說書人臺上說,聽客們臺下聽,兩百多年來口耳相傳,日久成書迷。筆者認為,蘇州評彈這門藝術的優秀傳承者,可以說是幸福的。這種幸福感來自百年來一代代表演藝術家日積跬步留下的千里足印,來自評彈理論家案牘前的孜孜不倦,來自蘇州評彈愛好者們的殷殷期盼。筆者希望,使用這本教材的學子,能夠從這本《蘇州評彈表演藝術》中充分吸取幾代評彈人留下的養分,心懷曲藝傳承的大格局,從學術層面深刻認識蘇州評彈的豐富性,精心打磨自己的技藝,站在前人鑄就的“高原”之上,再次向藝術的“高峰”前進,為蘇州評彈的未來發展繪出22世紀的藍圖。
(作者:蘇州交響樂團節目策劃部經理、英國杜倫大學音樂學博士)(責任編輯/陳琪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