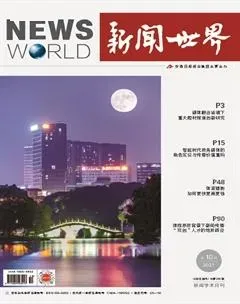多模態視域下的跨文化傳播策略
王瑤琦 徐佩琦
【摘? ? 要】作為全球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冠疫情使國際涉華輿情呈現復雜狀態。在此背景下,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在武漢封城一個月后推出的英文紀錄片《武漢戰疫紀》取得了顯著的跨文化傳播效果。本文從跨文化傳播視角出發,立足于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以語篇、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的話語三維模式為框架分析《武漢戰疫紀》,認為通過跨文化傳播話語策略,災難紀錄片具有改善國家形象和建構民族認同的功能。
【關鍵詞】跨文化傳播;多模態話語分析;紀錄片;新冠疫情
作為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冠疫情使國際涉華輿情呈現復雜狀態。我國在疫情防控上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國際輿論場中暗潮洶涌,形勢嚴峻,破壞國際合作抗疫的言行層出不窮。因此,提出行之有效的跨文化傳播策略、改善我國在疫情議題上的國際形象成為目前許多新聞從業者和跨文化傳播研究者努力的目標。
基于這樣的前提,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于2020年2月28日推出了時長33分鐘的英文新聞紀錄片《武漢戰疫紀》(The Lockdown: One month in Wuhan),講述了疫情發生以來武漢封城一個月發生的故事。《武漢戰疫紀》相繼在美國廣播公司(ABC)、日本朝日電視臺等21個國家和地區的165家境外電視頻道和新媒體平臺播放,觀看量總計破億。《武漢戰疫紀》能達到理想的跨文化傳播效果并非偶然,探究當中的原因將對優化我國的跨文化傳播策略、建構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上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具有積極作用。
一、當前跨文化傳播視域下的紀錄片研究
透視當前跨文化傳播視域下的紀錄片研究,不外乎兩種研究范式:既有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效果研究,和引導紀錄片實現有效跨文化傳播的策略類范式研究。首先,在效果研究的類別上,分別有研究者對國家形象紀錄片、美食紀錄片、人文紀錄片、生態紀錄片、災難紀錄片等跨文化傳播效果進行探討。研究者從受眾角度為中國紀錄片的有效跨文化傳播提供分析視角。其次,在引導紀錄片實現有效跨文化傳播的策略類范式研究中,研究者從成功的中外合拍紀錄片或中國題材的外國紀錄片中汲取經驗。“他者”的視角讓這類紀錄片帶有某種權威性和客觀性,研究者讓這種權威性和客觀性在跨文化傳播理論中具體化,能為我國外宣事業做出良好的策略參考。
若從研究題材上聚焦我國的災難紀錄片,現有的跨文化傳播框架下的災難紀錄片研究數量較少。王曉芳認為我國災難紀錄片的創作環境越發寬松,災難紀錄片的客觀性和真實性逐漸加強;創作環境為災難紀錄片的有效跨文化傳播奠定了基礎。[1]何蘇六等將央視拍攝的有關新冠疫情的紀錄片根據傳播目的分為展現宏觀視野下的國家使命、傳達個體命運背后的人文關懷、提升跨文化傳播效果這三個類別。[2]
綜上所述,目前跨文化傳播視域下的紀錄片研究范式已經形成,研究角度豐富且貼合跨文化傳播的理論框架。但是,對于災難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研究則較為匱乏。一方面,災難紀錄片拍攝難度較大;另一方面,實現有效跨文化傳播效果的災難紀錄片個案較少,難以從紀錄片角度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的國家形象建構提供行之有效的策略。紀錄片是國家形象跨文化傳播的優勢載體,[3]本文從更廣泛的跨文化傳播角度看待災難紀錄片,以期建構紀錄片研究更完整的圖景。
二、多模態話語分析在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的適應性
跨文化傳播離不開話語分析。福柯認為,話語在社會和文化中產生、發展,同時又對社會產生建構作用。傳統的話語分析聚焦于文字文本的形式與結構,無法觀照到多種媒介共存的復合話語。[4]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多模態話語分析是把文字文本與圖像、聲音等文本結合起來,從整體角度分析各類符號所組成的表意系統和話語意義,以更好地解釋跨文化傳播中交際和互動的話語分析方法。多模態話語分析起始于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1977年提出的視覺圖像在意義表達上與語言之間的相互作用,[5]近年來被中國學者引入跨文化傳播研究領域。肖珺通過文獻綜述總結出,多模態話語分析框架適用于跨文化傳播視域下的全球化與本土化視角研究和隱喻與轉喻視角研究;[6]潘艷艷等通過對中國國家形象片的多模態分析描述國家形象的建構是如何達致的;[7]還有研究將多模態話語分析方法作為研究香港廣告和城市多重成分的框架體系,該研究分析視覺和語言素材如何被應用于廣告中,從而建構香港廣告話語的多重認同現狀。[8]至此,已有大量研究驗證了多模態話語分析框架對于跨文化傳播研究的適應性。
本文從多模態話語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視角出發,從語言模態、視覺模態和聽覺模態三個角度對《武漢戰疫紀》進行分析,展示其在突出主體、形象樹立和情感傳遞等方面的功用,并從紀錄片制作的社會背景出發,闡釋創作者所處的社會語境及其通過多模態協作實現認同建構的過程。
三、對《武漢戰疫紀》的多模態話語分析
(一)語言模態分析:突出主體
在紀錄片中,語言模態的功能大部分由解說詞和同期聲承擔,起到加深影像意義的作用。韓禮德(Halliday)將語言的三大元功能(meta-function)概括為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語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首先,概念功能包括及物性和轉換等,及物性中物質過程則最能反映語言使用者要表達的主要意思。解說文本中多次出現以Cities across China(中國的城市)以及Hubei Province and the city of Wuhan(湖北省武漢市)等為主語,chaired(主持), started to put(開始實施措施),saw(看見)為物質過程,medical supply factories back to work(醫療器械工廠恢復工作)和a change in leadership and more stringent measures(換帥并實施更加嚴格的舉措)為目標的表達。這些物質過程描述中國在疫情暴發初期的決策與行動,反映出中國對疫情反應的迅速和果斷。
其次,人際功能包括語氣和情態等。對紀錄片中記者和采訪對象的問答文本進行分析發現,記者和被采訪者多使用偏積極傾向的表達。記者詢問感染者“救治是否及時”,得到了肯定的正向回答。從感染者口中說出的話,比起由記者或者解說等第三人稱口吻給出的文本更能體現真實性。最后,在語篇功能層面,句子主位和述位的劃分以及句子的排列規律會影響語篇的結構和意義,其中由主語擔任主題主位的表達在解說文本中占絕大多數,基本上都是與疫情密切相關的人物主體或者事件,比如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奔赴武漢救援的各省醫務人員、臨時建成的方艙醫院,體現出聚焦疫情真相的敘事重點。
此外,紀錄片開頭串聯了不同個體對疫情的擔憂和焦慮獨白,緊接其后的第一句解說詞點明武漢于1月23日封城的事實。兩者的銜接在內容上由模糊到清晰,情感上由激動、復雜趨于平靜,逐漸擴展語篇,奠定探尋真相的基調,引導觀眾繼續跟隨敘事了解實情。對方艙醫院內隔離患者的采訪,由采訪對象對政府舉措進行評價,展現出政府部門為感染者提供良好隔離環境的事實,對建構國家形象起到了正面作用。
(二)視覺模態分析:樹立形象
紀錄片中的圖像不僅能準確傳達時空信息,還能通過景別切換、鏡頭移動等方式實現信息轉換和情感傳達。作為將文本信息具象化的方式,圖像在充實情節、傳遞情感和解釋內涵上具有更豐富的表達空間。克瑞斯(Gunther Kress)和勒文(Theo van Leeuwen)在韓禮德系統功能語法的基礎上提出了視覺語法的再現意義 (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互動意義(interactional meaning)以及構圖意義(compositional meaning)。[9]再現意義分為敘事再現和概念再現,兩者的區別在于是否有矢量的出現。紀錄片中就醫片段即屬于敘事再現的范疇,其通過參與者的行動過程、反應過程和言語過程矢量傳達意義(表1),如片段一:兩個鏡頭分別體現了就診病人視角和醫護人員視角,他們是此敘事片段的矢量發出者和參與者,他們的目光作為矢量,目標是就診人群。一系列的圖像結合呈現出醫院面臨的緊急情況。觀眾被引導至關注目標——醫護壓力。片段二的畫面屬于概念再現的范疇,象征著回歸正常生活的信心。
互動意義關乎圖像的制作者、圖像表征事物和圖像觀看者之間的關系,主要通過接觸、社會距離、情勢關系和情態來實現。片段三通過鏡頭取景、視點和情態標記與觀眾對話,引導觀眾思考。在這個片段中,對因為封城無法返鄉的農民工的取景是中近景,主要露出了肩膀和頭部,這樣的取景框呈現出來較近的社會距離,營造出記者和農民工親切的交談氛圍。同時,第一個鏡頭呈現的交談畫面和第二個鏡頭呈現的農民工讀書的畫面,均是平視拍攝,讓觀眾與圖像中的人物處于同一水平線。此外,整體的畫面偏暗,農民工和記者的服裝也沒有明亮的顏色,傳遞出的情態是灰暗的。
最后,構圖意義指的是圖像的整體構成。[10]根據克瑞斯和勒文的理論,任何特定的元素在整體中的角色取決于它被放置的位置。置于上方的是“理想的”信息,也是信息的最顯著部分。[11]從片段四對火神山醫院的建造過程進行了展現,將時間和地點標注于畫面的右方,可見建造速度之快是創作者想要傳達的“理想的”信息。同時,這一段使用了倍速的播放效果,通過快速的畫面變化和銜接體現出基建效率之高。
(三)聽覺模態分析:傳遞情感
在紀錄片中,聲音除了解說和同期聲之外,還包括背景音樂。幾種聽覺模態的有機結合能夠實現情境建構的理想效果,更好地傳遞情感,讓圖像和文本展示出來的內容和主旨得以深化。張德祿認為,多模態的使用是由于人們在交際中難以通過一種模態表達清楚意義,所以需要其他模態進行強化、補充、調節、協同,使信息得到充分表達。[12]因此,對聲音模態的分析應從其與語言模態、視覺模態協同共建意義角度出發。片段五(表2)針對李文亮醫生的去世,運用語言、視覺和聽覺三種模態的協同表達,傳遞出民眾對李文亮事件的情緒和對政府處理的肯定態度。該片段通過解說和圖片向觀眾描述李文亮醫生的經歷,通過播放記者與李文亮醫生的聊天記錄營造對話情境,同時搭配沉重的背景音樂,輔以哭泣聲,傳遞悲傷的情緒與觀眾互動,實現人際功能。該片段以李文亮醫生在病床上的自拍和人民日報刊發的報道為對象,強化認知。銜接李文亮醫生因病去世和中央派遣調查組調查兩件事,向觀眾傳遞政府對李文亮事件的態度。
(四)社會實踐分析:建構認同
《武漢戰疫紀》中,文本、圖像和聲音的多模態協同作用帶給觀眾豐富的感官體驗,同時也協同建構國家形象和群體認同。紀錄片不僅是對現實的記錄和描繪,更是承載諸多信息的媒介產品。費爾克勞(Norman Fairclough)的話語分析強調,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分析,才能了解文本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文本背后的交際過程以及社會語境之間的關系。[13]《武漢戰疫紀》發布于我國疫情防控的緊急階段,國際輿論場中暗潮洶涌,形勢嚴峻。CGTN作為中國的對外傳播機構及時通過紀錄片為海外民眾呈現真相,建構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上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在跨文化傳播視角下,來自海外受眾的文化差異和其對中國的刻板印象要求紀錄片創作者在語篇的素材選擇和銜接設計上多下功夫。例如,紀錄片不僅強調封城和醫療支援的舉措,也不避諱感染者對當地政府的批評,帶著質疑和反思的色彩,改變傳統外宣紀錄片的編導思維。除此之外,創作者有意識地加入世衛組織對我國疫情防控的贊揚畫面,從國際組織的角度肯定了中國的抗疫舉措,向海外傳遞了呼吁全球人民聯合抗擊疫情的信息,契合我國倡導和踐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最后,整個紀錄片的色調偏暗,考慮到制作和發布期間全球都已經出現新冠疫情,創作者營造的沉重的視覺效果更能在海內外引發共鳴、建構認同,呼吁國際社會關注和借鑒中國疫情防控的經驗。
四、跨文化語境下災難紀錄片的話語策略
(一)欲揚先抑:消除刻板印象
海外受眾受西方中心主義與文化偏見的局限,對中國不可避免地帶有刻板印象,這是跨文化語境中的紀錄片創作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武漢戰疫紀》給災難紀錄片提供了參照個案:不回避疫情中出現的問題,敢于自我批評、敢于表達負面情緒。《武漢戰疫紀》沒有避諱病人談到“當地政府在疫情初期的應對很遲鈍”、社區居民對于政府工作人員的排斥情緒,在素材的選擇上立體、全面,提升了紀錄片的真實性和可信度。
(二)主體強調:達致國家形象
國家形象不僅取決于國家自身的客觀實際,很大程度上還依靠主動建構與傳播。[14]我國在2008年正式啟動國家形象片拍攝工作,國家形象片《人物篇》和《角度篇》是其中的范例。在YouTube視頻平臺上,《人物篇》的播放量是2.2萬,《角度篇》的播放量是8.1萬。《武漢戰疫紀》的播放量為1807萬,雖然播放量不是衡量紀錄片質量的唯一標準,但足以反映出海外受眾對于紀錄片的接受程度。災難紀錄片是我國達致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的重要手段,通過災難紀錄片在跨文化傳播實踐中建構國家形象的效果較好。
(三)隱喻:情感認同的建構
隱喻是傳達創作者情感態度的主要手法。隱喻手法用于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概念映射:在《武漢戰疫紀》末尾,醫生說:“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災難、恐懼、疾病都跳出來了。但盒子里面的最后一樣東西,就像希臘神話里說的,就是希望。”此時創作者配以遠景下緩緩升起的朝陽畫面、路人跑步的畫面,以及鳥群飛起飛遠的畫面。這幾個意象隱含了情感認同:抗擊疫情充滿了希望,人們的生活將會完全恢復。《武漢戰疫紀》廣泛運用概念隱喻,其綜合運用文字、視覺和聽覺模態表征的多模態隱喻“中國人民終將戰勝疫情”,這也給全球抗疫合作傳遞了信心。
結語
從跨文化傳播視域下的多模態話語分析角度出發,《武漢戰疫紀》的語言模態、視覺模態以及聽覺模態之間互相支持、補充,呈現出真實的武漢新冠疫情防控情況的語篇意義。從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的角度出發,《武漢戰疫紀》對國家形象和民族認同的建構具有積極作用,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背景下的災難紀錄片拍攝提供了實踐經驗。紀錄片的跨文化傳播是國家對外文化傳播整體戰略的重要部分。[15]紀錄片從業者要站在更廣泛、更多元的視角去研究個案、汲取經驗和繼續創作。
注釋:
[1]王曉芳.中國災難題材電視紀錄片研究[D].中國藝術研究院,2012.
[2]何蘇六,李寧.生死時速 溫情呈現——總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報道中紀錄片創作評析[J].電視研究,2020(06):18-21.
[3]沈悅,孫寶國.“一帶一路”視閾下中國夢的多維建構與全球想象——以紀錄片跨文化傳播為視角[J].云南社會科學,2019(02):174-181+187+189.
[4]李戰子,陸丹云.多模態符號學:理論基礎,研究途徑與發展前景[J].外語研究,2012(02):1-8.
[5]BARTHES R. Rhetoric of the Image. London: Fontana.1977:32-51.
[6]肖珺.多模態話語分析:理論模型及其對新媒體跨文化傳播研究的方法論意義[J].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7(06):126-134.
[7]潘艷艷.多模態視域下的國防話語研究初探[J].外國語言文學,2016(03):153-157+207.
[8]Graham Lock. Being International, Local and Chinese: Advertisements on the Hong Kong Mass Transit Railway[J]. Visual Communication,2003(2):195-214.
[9][11]KressG.&van Leeuween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London: Rouledge,1996:154-163.
[10]袁艷艷,張德祿.多模態電影海報語篇的社會符號學分析[J].濟寧學院學報,2012(02):35-39.
[12]張德祿.多模態話語分析綜合理論框架探索[J].中國外語,2009(1):24-30.
[13]Fairclough N.Language and Power[M].United Kingdom: Longman, 2001:57-130.
[14][15] 曾廣,梁曉波.國家形象的多模態隱喻建構——以中國國家形象片《角度篇》為例[J].外語教育研究,2017(02):1-8.
(作者:均為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國際新聞學碩士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