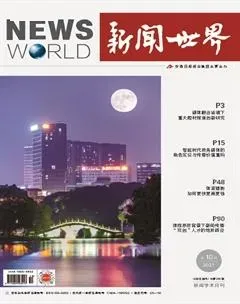真實與間離:紀錄片中的情景再現研究
任戌盈 楊夢圓
【摘? ? 要】本文引入布萊希特戲劇理論中的間離概念,通過文獻研究和案例分析方法,分析在紀錄片中使用情景再現時塑造間離感的必要性及其手段,認為在情景再現中塑造間離感保證了紀錄片的真實性,但也削弱了紀錄片的影像表現力。目前的虛擬影像技術對兩者間的矛盾有良好的調節作用。在紀錄片娛樂化浪潮下,創作者使用情景再現仍應堅守真實性底線,把握塑造間離感的合適尺度。
【關鍵詞】紀錄片;情景再現;間離
自羅伯特·弗拉哈迪在紀錄片《北方的納努克》中首次應用情景再現方式還原愛斯基摩人的生活場景以來,學界和業界對這種表現方法的爭議一直存在,相繼有學者對此進行深入研究。
在情景再現方式出現初期,為保證紀錄片內容的絕對真實,創作者對該手法的使用相當謹慎。而在現階段,隨著紀錄片創作不斷向娛樂化與故事化方向延伸,創作者在應用情景再現時更多采用了劇情片式的表達技巧,愈發敢于提供細節和人物對白,在一定程度上讓紀錄片的真實性受到挑戰。
如何平衡影像表現力與真實性之間的矛盾是創作者在應用情景再現時必須思考的問題,而塑造適度的間離感則是解決該問題的一種有效思路。
一、情景再現與間離效果概述
(一) 情景再現
情景再現是以客觀事實為根基、以畫面或聲音為載體、通過扮演或搬演的方式來還原已發生的事件或解釋人物心理的一種手段。目前,這種表現手法在紀錄片創作中有著較為廣泛的應用。
歷史上首個應用情景再現手法的紀錄片是由羅伯特·弗拉哈迪執導的《北方的納努克》。他使用搬演的方式實現了對愛斯基摩人近百年來生活場景的再現。情景再現在我國的應用可以追溯到1995年,中央電視臺出品了第一部情景再現樣片《忘不了》。隨后,情景再現手法在國內的紀錄片創作中不斷普及。[1]
情景再現的表現方式主要有三種,即資料摘錄、搬演和扮演。資料摘錄是指引用既往的影像資料來作為情景再現的段落;搬演是指在營造與歷史事件氛圍相似的場景后,讓親歷者對事實進行還原;扮演是指邀請演員來扮演人物,并利用服裝、道具等來實現對歷史事件的再現,是目前較為常用的一種表現形式。
(二)間離效果
間離的概念,最初起源于德國的貝爾托·布萊希特所著的《布萊希特論戲劇》。他在該書中將間離詮釋為“將事件或人物的某些不言自明、一目了然的因素進行剝離,使人對之產生驚訝和好奇心”。[2]
該概念自提出以來,在戲劇領域中的傳播不斷深入,我國學者將此概念引入國內并在《中國戲劇表演藝術中的間離效果》中首次提出。在戲劇表演中,間離原則旨在通過利用某種手段規避觀眾“入戲”,來借此塑造演出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感。這樣有利于觀眾保持自我的獨立情緒和思考,從故事中抽離,進行思辨。 [3]
與戲劇不同,電視節目的不連續性使其能夠通過對聲音或畫面的合理剪輯來實現間離效果的營造。[4]情景再現與擺拍的明顯區別在于對“再現”行為本身的不隱瞞,而這一區別正是間離手段的重要特征體現。縱觀現階段電視紀錄片中的情景再現段落,不難發現大多有意識進行了間離感的塑造,然而由于國內對于情景再現的使用限度尚未有明確的界定與標準,也導致在運用方面相對混亂。[5]
(三)情景再現中塑造間離感的必要性
盧梭提出,說假話與隱瞞事實真相并非同一概念,但二者卻能產生相同的效果。將其理論應用至情景再現中,可將說假話喻為素材虛構,將隱瞞事實真相喻為不將情景再現這一表現手法予以說明,從而最終造成相同的欺騙觀眾的效果。
對于情景再現如何使用,英國《獨立電視新聞公司指南》給出界定:若事實真相并未被最終確認,則不得進行相關信息的隨意捏造。情景再現在使用時應以不誤導事實真相為前提,且必須同時反復出現情景再現的提示。未經合理運用的情景再現將造成觀眾對于事實真相的誤解,從而導致觀眾對事件本身心存疑慮。
真實的實現是傳播的開端與終端共同完成的,是傳播者與接受者對真實的一致理解。在使用情景再現時,傳播者本意是將真實事件傳遞給接受者,但若在此過程中間離意識缺失,則會大概率導致“以假亂真”現象的發生。[6]因此,在紀錄片中使用情景再現必須塑造適度的間離感。
二、塑造間離感的藝術性處理手段
在情景再現中塑造間離感,最簡手法是直接加字幕提示此畫面為情景再現畫面,但這種簡單直接的方式在紀錄片中并不常見。相反,紀錄片創作者常常會通過對畫面進行藝術性處理的方式來提示觀眾哪些畫面是情景再現。
(一)避實就虛,對人物進行模糊化處理
紀錄片創作者在情景再現中塑造間離感最常采用的是模糊化處理人物的手段。這將使觀眾對事件有較為清晰直觀的感知,卻又避免提供演員的細節。這種手段又分為以下幾種具體方式。
1.利用虛焦
紀錄片《故宮》的第二集講述了故宮所遭遇的諸多磨難以及此后進行的修繕工作。在其中一段情景再現畫面中,一位老人在擺弄木制的模型,而畫面焦點落在了前景的一塊木頭上。創作者正是以這種方式避免了向觀眾提供不真實的人物畫面和無法被證明是否真實的工作細節。
2.改變景別
在情景再現中使用特寫和遠景都有助于塑造間離感。利用特寫時,畫面僅提供局部信息,回避無法證實的細節。以2017年8月13日的《今日說法》為例,其在對死者與他人吵架場景進行重現時,鏡頭僅給到了死者飲酒的嘴部和酒杯特寫,避免呈現演員樣貌。而利用遠景時,也避免了強調無關細節,僅使觀眾對主體行為動作有大體了解,但又不至于留下固定形象。遠景作為表意鏡頭,可以達到氛圍真實的效果。
3.特殊角度拍攝
特殊角度拍攝的藝術性處理手法在《故宮》第二集中也有體現。片中在講述順治帝和故宮的故事時,運用了人物扮演的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從頭至尾,順治帝的幾次出場都沒有露臉,而是采用背影或側面剪影的角度來回避呈現演員的樣貌,對人物進行模糊化處理。
4.巧妙利用光影
光影結合可以構成諸多不同的造型。通過這種方式,影片也能避免表現人物的具體細節,從而塑造間離感。以《絲綢之路》為例,在進行“玄奘西行”這段歷史故事的重現時,鏡頭只給到了玄奘騎馬前行的影子特寫,避免了呈現演員樣貌。在這段畫面中,觀眾只能接收到一個身穿僧袍的僧侶騎行于大漠的信息。
(二)利用影像認知習慣,處理畫面色彩
除了對情景再現中的人物形象進行技術處理,創作者還會運用一些手段來塑造環境中其他元素的間離感。其中,畫面的色彩改變是一種比較常用的手段。
影像色彩的發展是從黑白到彩色。基于此,在進行剪輯時,往往會利用黑白色來對已經發生的事情予以表現。在紀錄片中也有類似利用人們對影像認知的習慣來塑造間離感的方式。例如,在紀錄片《圓明園》中,情景再現畫面都采用了偏暖的如泛黃老照片一樣的色調,將再現畫面和真實畫面清楚區分。
(三)使用虛擬影像,重構場景或合成資料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虛擬影像技術不斷成熟與完善,在紀錄片創作中所發揮的作用愈發顯著。虛擬影像相較于真人搬演或扮演的情景再現而言,自身就帶有“非真實”的間離感。
用計算機制作動畫來重構場景是使用虛擬影像進行情景再現的一種方式。如紀錄片《圓明園》90分鐘的全片中,CG動畫大約占了35分鐘,再現了圓明園從規劃、建筑、完工、改造、擴建到被外來侵略者所燒毀的完整歷史脈絡。
借助計算機技術將諸如書籍、照片等靜態資料進行動態化展示則是另一種方式。以《紅色氣質》為例,其取材多源于新華社中國照片檔案館。當解說詞說道“每到歷史轉折的重大關頭,總是他們,擔當著國家與民族的使命”時,畫面是拉纖繩、攀鐵索、登雪山、森林滅火等紀實照片。照片中的纖繩和鐵索微微晃動,雪花、火苗也是動態變化的。該片充分利用計算機技術,在保證情景再現間離感的同時賦予了歷史資料動態敘事的生命力。
三、間離感與影像表現力的矛盾
情景再現中間離感的塑造保證了傳者和受者對真實的一致理解,符合紀錄片創作真實性原則的要求。但僅就紀錄片本身而言,間離感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畫面影像表現力的損失。
(一)間離感影響畫面的細節表現
一部優秀的紀錄片,細節刻畫尤為重要。而當紀錄片創作者利用避實就虛的方式強化影片間離感時,細節就被有意忽略了,其影像表現力也大大下降。在2003年中國新聞獎的獲獎作品《天使》中,有個片段是黃永杰丈夫因不愿收養大雁而與黃永杰鬧矛盾的場景。為了避免表現出無法被證明真實發生過的吵架細節,《天使》的制作團隊僅拍攝了一個黃永杰與丈夫背對著坐在炕上的鏡頭。相較于真人搬演再現吵架場景,這樣的表現手法缺乏視覺沖擊力。
(二)間離感影響畫面的表意能力
在紀錄片的情景再現畫面中,為了強化間離感,制作者通常會用表意模糊的鏡頭搭配解說詞的方式進行敘事,這將影響畫面的表意能力。例如,紀錄片《故宮》在講述鈞瓷的故事時,僅搭配了一段屋檐落雨的鏡頭,而故事情節的講述完全是通過解說詞完成的。就這種方式而言,紀錄片中敘事和表意的主要工具是解說詞,而非畫面。當有解說詞存在時,畫面才能夠完成表意功能。若將二者進行分離處置,則最終所呈現出的效果將會大打折扣。[7]從這種意義上說,間離感的塑造大大削弱了畫面的表意能力。
(三)虛擬影像調和間離感和影像表現力的矛盾
間離感和影像表現力間的矛盾并不是無法調和的,虛擬影像尤其是CG技術的出現為兩者之間的平衡提供了可能。相較于真人扮演或搬演的情景再現,虛擬影像本身會提醒觀眾這是非真實畫面。通過這種方式,創作者可以大膽還原人物的容貌、衣著和言行舉止,大膽刻畫細節,而不用擔心觀眾對此產生是否真實的疑惑。例如在紀錄片《再見,好年華》中,創作者用手繪動畫的方式對當時的車站送別場景進行了情景再現,這種方式使得情景再現的間離感和影像表現力同時得到了保障。
四、紀錄片娛樂化和消逝的間離感
間離感的塑造取決于創作者的主觀選擇,而外界文化環境的改變對這個選擇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現階段的紀錄片創作為迎合市場需求,不斷向娛樂化方向靠攏。紀錄片娛樂化指的是基于某些特定的敘事手段,通過講故事的形式賦予紀錄片更加形象化與生動化的內容,確保其更易被觀眾所接受。[8]
為了迎合市場需要和大眾審美需求,一些紀錄片創作者為了追求情景再現而忽略紀實手法的運用,導致創作誤入歧途。紀錄片中使用情景再現的表現手法和技巧與劇情片的界限也越來越模糊,隨著時間的推移,故事片與紀錄片在演變過程中不再有著明顯的虛實界限。虛構與紀實作為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目前僅僅表現出了手段上的差異,卻沒有了本質的不同,[9]間離感的塑造正面臨著巨大危機。
紀錄片《外灘》在播出時,就因為使用大量的情景再現,大膽的人物出演引起了學界爭議。雖然演員表演和歷史影像材料之間無縫連接,但細心的觀眾仍然對劇情產生了質疑。例如,周璇居所為石庫門樣式,與真實歷史中的洋房有明顯出入;赫德穿著松垮,與真實歷史中的租界官員制服嚴重不符。沒有服裝、道具等各方面細節的考證,《外灘》雖然在市場上受到歡迎,卻失去了紀錄片的真實性。
情景再現旨在對真實歷史予以還原與解釋,它既不能憑空杜撰歷史事件,也不能不顧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隨意編造史實。在紀錄片娛樂化不斷延伸的今天,創作者仍然需要以真實性原則為底線,間離感的塑造仍需被著重強調。
結語
間離感塑造作為紀錄片中使用情景再現時的重要原則,是確保紀錄片能夠最大限度還原真實的有效支撐。在紀錄片娛樂化浪潮下,創作者在使用情景再現時,既要順應大眾文化潮流,也要守住真實性底線。只有懷著對歷史的尊重,以真實性原則為指導,把握塑造間離感的合適尺度,才能夠既實現與市場需求的高度契合,又實現對真實歷史的有效揭示。
注釋:
[1]郭赫男,劉遠軍.電視紀錄片情景再現之真與失真[J].東南傳播,2010(02):61-62.
[2]周才庶.布萊希特間離學說的文學倫理反思[J].外國文學研究,2015(03):135-142.
[3]陳俊.布萊希特間離效果的影視應用[J].電影文學,2011(03):22-23
[4]董健.論間離效果在電視節目中的存在意義及運用技巧[J].學習與探索,2015(08):141-144.
[5][6]馬云云.簡述電視新聞中的情景再現[D]. 山東大學,2009.
[7]劉晨輝.我國歷史文化紀錄片故事化影像研究[D].湘潭大學,2016.
[8]楊麗.電視紀錄片的娛樂化探析[J].山東視聽,2005(02):37-39.
[9]劉潔.紀錄片的虛構:一種影像的表意[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7:110.
(作者:任戌盈,中國傳媒大學電視學院碩士研究生;楊夢圓,中國傳媒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