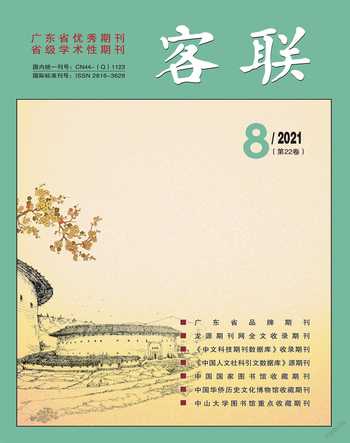談俄語一般疑問句間接表達請求時的兩種情況
梁春雪



摘 要:句子和詞一樣也有虛擬意義和當前意義。在實際交際中,不同語境輔以相應語調能使同一語句表達不同的當前意義,而間接語力對句子當前意義的解讀至關重要。本文主要利用間接言語行為相關理論,旨在闡釋借助俄語一般疑問句間接表達請求言語行為時主要存在兩種類型? (X) →! X和? (X) →! Y,二者的疑問語句X間接語力的推導對于語境的依賴程度有所不同:第一種類型語境依賴程度低,是規約型間接言語行為;第二種類型語境依賴程度高,是非規約型間接言語行為。無論是哪種類型,其間接語力的推導均可以借助由疑問語句X在該語境下所觸發的典型行為路線來確定,這種典型行為路線是交際雙方的語境共有知識。
關鍵詞:俄語一般疑問句;當前意義;間接言語行為;語力;典型行為路線
一、引言
俄語中的句子可以從多個角度劃分。從交際目的出發,可以把句子分為陳述句、疑問句和祈使句(黃穎2008:330):陳述句用于陳述或描寫事實;祈使句用于祈使聽話人做或不做某事;疑問句用于提出問題(張家驊,彭玉海等2005:513)。
然而在實際交際時,經常出現形式層面和表意層面的二元不對稱,表現為一種形式可以表達多種意義或一種意義可以借助多種形式表達。例如,人們使用俄語疑問句,除了可以表達其基本意義——疑問之外,還經常用疑問句的形式表達請求意義,前者是疑問句的基本功能,后者是其派生功能(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1980: 394)。當俄語疑問句用于表達請求意義時,即出現了間接言語行為,間接言語行為是通過實施另一種施事行為的方式來間接地實施某一種施事行為(Searle 1979: 31)。
間接言語行為理論是塞爾對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的繼承和完善。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起源于施為句的提出,他認為許多言語行為通過說出施為動詞而完成,而言語行為成功的條件不是別的,正是一些釋義要素。維日彼茨卡(Wierzbicka)以order為例,認為“將詞語order分解為各語義要素,其實就是分析命令言語行為的言外力量”(轉引自Е.В.Падучева 2011: 343)。但在實際使用時,尤其是在表達請求時,基于雙方社會等級關系等語境因素的考慮,人們很少使用顯性施為句,而是更常使用疑問形式表達請求意圖。可見說話人在表達自己的言外意圖——請求時,不僅僅可以使用施為動詞,而且更經常會出現沒有動詞表達相應的言外意圖的情況,這是因為語言可以表達非常細微的言語意圖,而這些意圖不歸結于某個動詞的意義(同上:343)。
二、虛擬意義與當前意義
科博澤娃(Кобозева И.М.)在《語言語義學》(Кобозева 2000: 54-55)中以огонь(火)為例,指出在意義概括程度軸上存在兩級,虛擬意義(вирту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和當前意義(акту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假設有一個說話人和一個聽話人,說話人對聽話人說出огонь這個詞,并且在此之前什么也沒有說,什么語境也沒有交代,那么聽話人在聽到該詞后能想到的,就是該詞在語言系統里的意義,這就是該詞的虛擬意義,虛擬意義特點是高度概括,抽象和籠統,任何母語是俄語的人處在聽話人的位置上,聽到這個詞都能得到這樣的信息,甚至在該詞轉義使用時,也能有這樣的聯想,例如“發火““開火”等。
在具體的交際場景中,比如說話人和聽話人坐在燃燒的壁爐前,這時說話人對聽話人說Нам пора уходить. Погаси огонь(我們該走了。你把火滅了吧),那么這句話中的огонь在此語境下傳遞的信息要更加的具體,此時огонь的當前意義指的就是具體的在這個語境下的火的意義,即說話人和聽話人面前壁爐里的那個火,是用于取暖的火,且場景越具體,火的當前意義越具體。
佩什科夫斯基(Пешковский А.М.)在談論虛擬意義和當前意義的關系時談到“我們要區分兩種形象:一種是僅說出獨立的詞,該詞所引發的形象;另一種是將該詞放在詞組中的形象。第一種是從大量的第二種形象中抽象得來的,不改變本質。即使是從大量中抽象出來的,但是第一種形象還是存在的,是活生生的心理學事實,而詞或詞組的具體形象是第一種形象的變體”(Пешковский 1952:93)。這里提到的第一種形象指的就是虛擬意義,第二種形象是當前意義。可見虛擬意義是當前意義抽象的結果,當前意義以虛擬意義為依據。
不僅是詞,句子的意義也有虛擬意義和當前意義之分(Кобозева 2000: 55)。科博澤娃以Я поговорю с твоими родителями 為例,該句的虛擬意義指的是不管該句子是誰說的,在什么場景下,出于什么目的對誰說的,該句子均表示句子的說話人將在說出這個句子之后的某一時刻和聽話人的父母交談。如果將該句子置于具體的上下文語境中例如:
(a) А: Мне придется на время отлучиться. Чем бы тебе заняться, пока меня не будет?
Б: Я поговорю с твоими родителями.
(б) Опять ты пропускаешь занятия. Я поговорю с твоими родителями.
(в) А: Мне не разрешают идти в поход с ночевкой.
Б: Не переживай. Я поговорю с твоими родителями.
此時無論是語境(a)還是(б)還是(в),任何一種語境下句子的內容層面已經不僅是虛擬意義而是當前意義。很明顯,句子的當前意義包含但不僅包含虛擬意義。除了包含構成虛擬意義的信息之外,當前意義還主要包括說話人的目的信息以及談話主題信息。
例如在語境(a)中,說話人的目的信息僅僅是告知聽話人他在等聽話人回來的時候將要做什么,和聽話人父母談話的主題是不受限的。在語境(б)中,說話人的目的是制止聽話人曠課的行為,如果聽話人再次曠課,那說話人將要采取有損聽話人的行為,即和聽話人的父母談一談,顯然談論也是關于聽話人曠課的事情。在語境(в)中,說話人的目的是攬下要采取有利于聽話人的行為,和其父母談論的話題也是上文提到的遠足活動(同上:56)。由此可見,虛擬意義+增加的意義=當前意義,增加的意義包含了說話人的目的,談話的內容。
在上述三個語境中從視覺上看均具有同一個句子Я поговорю с твоими родителями,因為在這三個語境中該句子都有相同的虛擬意義,表示是說話人在此之后將和聽話人的父母交談,但需要指明的是,這個句子在不同語境下的調型邏輯重音不同,因此我們認為這是同一個句子在三個不同語境下的變體。從言語行為的角度來看,上述三個句子在語境(a)、(б)和(в)下,分別實施的是三種不同行為:告知行為、威脅行為和承諾行為。并且第一個是直接言語行為,第二和第三個間接言語行為。
句子的虛擬意義和詞的虛擬意義一樣,需要脫離具體的使用語境,即何人?何時?何地?為何?等信息均缺失,那么該“孤立”句子的內容層面就是該句子的虛擬意義。而在具體語境下,該虛擬意義附著該語境下“增加的意義”就是該句子的當前意義。
通過上述對科博澤娃例子的分析,可見語境下“增加的意義”對句子當前意義的理解十分重要,且從間接言語行為理論角度來看,在“增加的意義”中最重要的實際上是該語境下句子的間接語力(即施事語力)。俄語一般疑問句在實際使用時,出于說話人的需要,經常用來表達請求、建議、邀請等祈使意義,此時聽話人如何從疑問句的虛擬意義推導到其當前意義?塞爾曾經闡述過間接言語行為的邏輯推導過程,我們嘗試基于塞爾的間接言語行為相關成果,以俄語一般疑問句間接表達請求為研究對象,從而提出另外一種間接語力的推導過程,以期簡化間接語力的推導步驟。
三、區分? (X) →! X和? (X) →! Y
用一般疑問句表達請求言語行為時,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種類型:? (X) →! X和? (X) →! Y,這兩種類型的差別在于,疑問句本身的命題和以它為基礎推導出的祈使句的命題是否一致。
第一種類型? (X) →! X,疑問句本身的命題和以其為基礎所推導出來的祈使句的命題一致。例如:
Можете ли вы передать мне соль? → Передайте мне соль пожалуйста!
Вы могли бы мне помочь? →Помогите мне, пожалуйста!
以上述第一個例子為例,[1] Можете ли вы передать мне соль? (您可以把鹽遞給我嗎?)字面語力是“提問”,詢問聽話人遞鹽的能力,而實際上表達的間接語力是“請求”,即請聽話人把鹽遞給說話人 [1’] Передайте мне соль пожалуйста! (請您把鹽遞給我!)。
第二種類型? (X) →! Y,疑問句本身的命題是 “X” ,而實際表達的請求意義則屬于實現另外一個命題 “Y” 。例如:
Вы выходите? → Пропустите меня, пожалуйста!
Вам не холодно? → Закройте окно, пожалуйста!
Вам не жарко? → Откройте окно, пожалуйста!
以上述第一個例子為例,說話人想下車,于是對站在地鐵門口的人說 [2] Вы выходите? (您下車嗎?),字面語力是“疑問”,詢問聽話人是否下車,而間接語力是“請求”,即實際上說話人想向聽話人傳遞的是請求意義 [2’] Пропустите меня, пожалуйста!(請允許我過去)。
四、兩種類型的間接語力推導與語境關系
第一種類型? (X) →! X,因為在疑問句本身的命題部分和以它為基礎推導出的祈使句的命題部分是一致的,所以該類型的間接語力推導比較容易。
例如,在聽到 [1] 后,聽話人很自然地就能通過句子本身的字面語力疑問,成功地推導出說話人想表達的間接語力是請求。這種情況下,聽話人之所以能夠如此自然地在字面語力“疑問”和間接語力“請求”間進行轉換,迅速理解說話人想要表達的言外之意,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人們能夠習慣地根據Можете ли + глагол (сов.)?這一句法結構,自然地推導出它的間接語力是請求。通常來講,話語含義的準確理解離不開語境。語境是指一句話或一段話語以及一個言語行為的語言環境,也指某個短語或詞語的語境(武璦華 2006: 25)。然而,類似Можете ли+ глагол (сов.)?這種結構可以說是禮貌地表達請求意義的慣用形式,這種情況下由字面語力到間接語力的推導對語境的依賴程度并不大,是一種規約性的間接言語行為(索振羽 2018: 159)。禮貌地表達請求意義的這種規約是存在在熟練地操某一種語言的人們的大腦中,因此,在聽到 [1] 后,聽話人會自然地將該 “詢問” 理解為 “禮貌的請求”,因此會立刻把鹽遞給說話人,而不是僅回答 “Да, могу” 。
第二種類型? (X) →! Y,疑問句本身的命題部分和以它為基礎推導出的祈使句的命題部分不一致,疑問句本身的命題是“X”,而以它為基礎推導出來的祈使句的命題是“Y”。與對語境依賴程度不大的第一種類型? (X) →! X不同的是,第二種類型? (X) →! Y,其疑問句本身能否進行間接解讀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言語行為發生的語境,一些語境下可以將該疑問句理解為間接表達請求,而一些語境下則應理解為純疑問句。
例如,如果是在地鐵上,說話人想下車,他對站在門口擋住他下車路徑的人說出 [2] ,那么說話人想向聽話人傳遞的實際上是請求意義 [2’] Пропустите меня, пожалуйста! (請允許我過去)。如果換做是另外一種語境,說話人對剛從座位上站起身的朋友說出 [2] ,那么該語境下這句話則是一種純疑問句,說話人僅是想從聽話人那里獲得某一未知信息,即“聽話人是否要下車”,這種語境下,如果再對語句 [2] 進行類似于 [2’] 或其他的間接解讀則是不恰當的。由此可見,第二種類型? (X) →! Y的間接解釋對語境依賴程度很大。因為我們研究的是疑問句的間接用法,因此我們只考慮上述提到的該類型的第一種情況,即用疑問句表達與疑問句本身命題不同的間接請求。
五、兩種類型的典型行為路線圖
能夠間接理解疑問句的關鍵是典型的行為路線(схема поведения)的存在,這種行為路線對于說話人和聽話人來說,在某些預定的目標層次上是顯而易見和自然的,且不同的問題會觸發不同的行為路線(Р. Конрад 1985: 357)。
假設語境①:
1. 說話人S想要鹽;
2. 聽話人H的位置能夠拿到鹽。
因此,如圖1所示,由 [1] “Можете ли вы передать мне соль?”這個問題開始,可能出現以下幾種情況:
1. P1-P2-P4:H以否定答復“Нет”回答S的問題“Можете ли вы передать мне соль?”,之后H沒有把鹽遞給S,S沒能通過H拿到鹽。
2. P1-P3-P5-PE:H以肯定答復“Да”回答S的問題“Можете ли вы передать мне соль?”,之后S繼續補充,進一步表明自己的請求“H, передайте мне соль, пожалуйста(H, 請把鹽遞給我)”,H于是把鹽遞給S,因此S順利地通過H拿到鹽,達到自己的交際意圖。
3. P1-P3-PE:H以肯定答復“Да”回答S的問題“Можете ли вы передать мне соль?”,之后H立即將鹽遞給S,因此S順利地通過H拿到鹽,達到自己的交際意圖。
第3種情況和第2種情況很相似,區別在于H以肯定答復回答S問題之后,無需S進一步表明自己的交際意圖 “H, передайте мне соль, пожалуйста”,而是直接把鹽遞給S。
假設語境②:
1. 說話人S想離開;
2. 聽話人H所處的位置阻礙了說話人S實現這個目標;
因此,如圖2所示,由 [2] “Вы выходите?”這個問題開始,可能出現以下幾種情況:
1. P1-P2-P4-PE: H以肯定答復“Да”回答S的問題“Вы выходите?”,之后H下車,因此H不再是S下車的阻礙,所以S能夠順利下車。
2. P1-P3-P5-P6-PE:H以否定答復“Нет”回答S的問題“Вы выходите?”之后, S繼續補充,進一步表明自己的請求“H, пропустите меняя, пожалуйста. (H,請允許我過去)”,H于是靠邊站,因此H不再是S下車的阻礙,所以S能夠順利下車。
3. P1-P3-P6-PE:H以否定答復“Нет”回答S的問題“Вы выходите?”之后,H立即靠邊站,因此H不再是S下車的阻礙,所以S能夠順利下車。
4. P1-P3-P7-P8: H以否定答復“Нет”回答S的問題“Вы выходите?”之后,S沒有進一步表明自己的交際意圖,因此H沒有站到一旁給S讓路,所以H仍是S下車的阻礙。
第3種情況和第2種情況很相似,區別在于H以否定答復回答S問題之后,無需說話人S進一步表明自己的交際意圖 “H, пропустите меня, пожалуйста”,而是直接站到一旁給S讓路。
圖1和圖2所示的行為路線圖均包含一種情況(P1-P3-PE / P1-P3-P6-PE),即聽話人在以肯定或否定的答復回答完說話人的問題之后,無需說話人進一步表明自己的交際意圖(請聽話人遞鹽/讓路),聽話人直接用自己的行動(遞鹽/讓路)表明,基于說話人之前所有的行為,包括提問事實和問題內容,聽話人明白了說話人的交際意圖,并且預料到了說話人為達到這個交際意圖所預期的所有行為路線。因此,聽話人在聽到說話人的問題后,心里預料到說話人接下來的步驟是P5(即給說話人遞鹽/讓路),所以直接用自己的行動向說話人表明無需其明說。
圖1的P1-P3-PE與P1-P3-P5-PE相比,以及圖2的P1-P3-P6-PE與P1-P3-P5-P6-PE相比,實際上是縮短的行為路線(сокращенная схема поведения),這種縮短有普遍性(Р. Конрад 1985:367)。在語境①和語境②中,聽話人缺少行為路線圖中間的某個步驟也是有可能的。例如,在語境①中,聽話人在聽到問題 [1] 后,很有可能直接將鹽遞給說話人。在語境②中,聽話人在聽到問題 [2] 后,很有可能直接讓到一邊來作間接回答,即他不僅對之前聽話人期待的請求作出回應,還避免了讓自己說出否定回答。一些情況下,甚至問題本身也可以省去,如果注意到說話人即將來到出口,聽話人很有可能趕在說話人前面說出:“我也要下車”或者直接讓到一邊。
對于語句 [1] 而言,因為Можете ли + глагол (сов.)?這種句式結構是禮貌地表達祈使意義的規約是操同一種語言的說話人和聽話人的共有知識,因此,在聽到 [1] 后,聽話人能夠習慣地根據這一句法結構,自然地將該 “詢問” 理解為 “禮貌的請求”。
如果說由于對于第一種類型? (X) →! X而言,由字面語力到間接語力的推導主要依賴某種規約,所以聽話人理解語句 [1] 的言外之意并不困難,然而對于對語境依賴程度較大的第二種類型? (X) →! Y而言,聽話人之所以可以正確地理解語句 [2] 的間接語力是請求,即 [2’] Пропустите меня, пожалуйста!(請允許我過去),不僅基于對該疑問句所有可能意義的語言分析,而且還要基于聽話人所熟知的由語句 [2] 能夠引發的所有有可能的行為路線(圖2所示)。換言之,這種情況下聽話人確定語句 [2] 的言外意圖不是基于某種固定的,總是疑問句所特有的“轉義”(比如,祈使),而是基于他能夠辨清事情發展的能力和能夠心里預測到事情接下來的發展。說話人一方同樣知道,聽話人具有這種能力,并且在他得到否定回答后,期待聽話人能夠實施某個行為(在我們討論的這種情況下,即讓路)。
無論是第一種類型? (X) →! X,還是第二種類型? (X) →! Y,說話人之所以沒有直抒胸臆,沒有直接表明自己的交際意圖(Передайте мне соль пожалуйста! / Пропустите меня, пожалуйста!),而是以拐彎抹角采取間接的方式詢問聽話人(Можете ли вы передать мне соль? / Вы выходите?),這是出于禮貌的考慮。
根據利奇的禮貌原則,禮貌級別是個連續統,根據不同的尺度,可以劃分不同的禮貌級別(Leech 1983:107)。從“直接表達方式-間接表達方式的尺度”來看,“以言行是”,用直接方式表達的話語禮貌程度差;用間接方式表達的話語更有禮貌(索振羽 2018:91)。尤其是在請求言語行為中,更要注重禮貌。因為請求言語行為的肇事人為說話人,完成行為對說話人有利,雙方社會等級關系是RS≤RH,即說話人地位不高于或等于聽話人。正是由于社會地位不高,又要求對方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說話人意欲實施請求行為時,就不能不顧及聽話人的反應(張家驊,彭玉海等 2005:499)。因此說話人采用以疑問表達請求的手段,話語語力減弱,更帶有試探性傾向,正如圖1和圖2所示,當說話人向聽話人提出問題,可能會得到聽話人肯定的答復(情態認同反應),也可能會得到聽話人否定的答復(情態相異反應)。正是由于說話人對聽話人反應的顧及,所以在請求他人做某事時,說話人往往采取用疑問表達請求的技巧,這是出于禮貌的考慮,使聽話人有選擇的余地(Да / Нет),聽話人心領神會,樂于合作,因此能夠促成成功的交際。
六、初始疑問意義是否有保留之爭
關于使用疑問句來間接表達請求言語行為時,疑問句的基本意義(疑問)是否有保留這一問題,不同學者持有不同觀點。
早先以萊考夫(Gordon D., Lakoff G. 1975:86-87,104)為首的學者們普遍認為,疑問句表達間接言語行為時,其基本意義喪失,因為詢問聽話人能否完成某個行為,等同于請求實施某行為,此時疑問意義隱藏,外顯的僅是話語的間接語力。因此他們認為,使用疑問句時可以要么表達疑問,要么表達祈使,但是不能同時表達兩者。
塞爾等學者質疑上述普遍認同的觀點,認為用疑問句表達間接言語行為時,疑問句的疑問意義有保留,他強調間接意義是由疑問句基本意義派生而來(Searle 1975:31-35)。例如,說話人使用Вы сейчас выходите? 間接表達請求時,該語句最初僅是問題,之后也沒有丟失疑問意義,因為聽話人確實想得到某種知識。我們也贊同這種觀點,如例(1):
(1) а. Вы посмотрите мои картины?
б. Вы не посмотрите мои картины?
(1a)表達的是疑問,而(1б)是某種語氣比較緩和的句子,實際表達的言語意圖是邀請(轉引自Падучева Е.В. 2011: 343)。可見Вы сейчас не выходите?并不適合前述語境②,而更適合“說話人邀請聽話人一起下車”時的語境。所以對于語境②而言,更合適的是使用Вы сейчас выходите? 來表達疑問,并且和這個問題一起,說話人還為事情進一步發展準備了其他句子,這一連串的情景序列的存在是因為一定的禮貌原則,如果沒有和社會習慣接受的行為準則相違反的話,那么交際者的意圖就是明確的。疑問句并不能總是被視為間接言語行為,僅當給予問題以肯定或否定回答時,才被解釋為間接言語行為(Р. Конрад 1985:367)。從這一點也可以得出,疑問形式表達請求意圖時,初始疑問意義是保留的。
七、結束語
從由字面語力(疑問)到間接語力(請求)的推導對語境依賴程度的角度來看,第一種類型? (X) →! X對語境依賴程度較低,聽話人很容易就能夠根據疑問句中的某些禮貌地表達請求意義的慣用形式(例如,Можете ли + глагол (сов.) ...?),自然地推導出它的間接語力是請求,是一種規約性的間接言語行為。第二種類型? (X) →! Y,由于疑問句本身的命題是“X”,而以它為基礎推導出來的祈使句的命題是“Y”,這種命題的不同直接導致正確解讀該疑問句的交際意圖有一定的難度,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聽話人之所以依然能夠正確理解聽話人使用疑問句時想要表達的間接語力,是因為交際共同體在交流的過程中總是在不知不覺地進行著各種預測,而這些預測的主要依據就是語境(Halliday M.A.K. , Hasan 1985: 9)。根據語境可以預測一連串的情景序列,即由疑問句觸發的典型行為路線,這種典型的行為路線是在該語境中交際共同體的一種共有知識。
參考文獻:
[1] Кобозева. И.М.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M]. М.: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0.
[2] Конрад. Р.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ы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как косвенные речевые акты.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В. А. Плунгяна[A].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ыпуск XIV: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агматика[C]. М.: Прогресс,1985.
[3] Пешковский. А.М.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M]. М., 1952.
[4] Шведова Н.Ю. (гл. ред.).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M]. т.2, М.: Наука, 1980.
[5] Gordon D. Lakoff G. Conversational postulates[A]. Syntax and Semantics[C]. New York, 1975.
[6] Halliday, M.A.K. &Hasan, R. Language, Text and Con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M]. Geelong: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7]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3.
[8] Searle, J.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9] 黃穎. 新編俄語語法[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8.
[10] 索振羽. 語用學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11] 武璦華. 語境因素辨析[J]. 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6(4).
[12] 張家驊,彭玉海,孫淑芳,李鴻儒. 俄羅斯當代語義學[M].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
[13](俄)Е.В.帕杜切娃著,蔡暉譯. 詞匯語義的動態模式[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