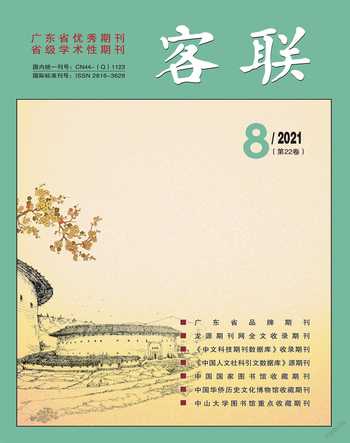后現代社工視角下的“黃昏戀”
張冬杏
摘 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目前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億,占比18.70%,表明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老年人的問題和需求也日益受到關注。其中,“黃昏戀”就是一個典型的存在。然而,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國家雖然有立法保障老年人再婚的權利,黃昏戀在現實中卻頻頻遭到現實阻礙。作為社工,我們應該持后現代理念打破這種傳統觀念束縛,通過“去標簽化”為老年人爭取權利。
關鍵詞:后現代視角;社工;黃昏戀
個案背景:陳伯伯生活在相對保守的內陸省份,今年七十歲,年輕時在沿海城市經商養大三名子女,每月只回家幾天,現在孩子都已經成年及各有成就,家庭經濟充裕。陳伯伯妻子自十年前開始因腦梗而四肢癱瘓,陳伯伯六十歲退休后主要工作就是與家人所聘的中年女看護一起在家照顧妻子,然而妻子最終于今年逝世,當所有后事辦妥之后,陳伯伯告訴子女要跟已經照顧妻子近五年的看護姑娘結婚,卻遭到子女猛烈反對,令陳伯伯感到十分困惱,遂向社工求助。
概念明晰:后現代是一種態度、視角、框架,它是現代主義的倒影,不是另一種固定的論述。后現代理論則是一種文化理論或人文學科,它是通過文化批判,從微觀層次上去解構現代社會,以便把人從社會(制度、結構、實踐、話語)的結構化和壓制中解放出來。后現代拒斥現代理論的一致性預設和因果觀念,推崇多元性、片段性、不確定性。但這并不否定后現代理論中有社會思想和社會理論的內容[1]。黃昏戀指那些喪偶的老年人再次結婚或者是尋找自己的屬于老年人的愛情的行為。
后現代理論視角強調社會工作者是從全知到未知、從有權到沒權的社工,需要社工在最困難的個案中為服務對象找尋出路、為最邊緣的群體找尋突破。
案例中,陳伯伯的子女們都已經成年及各有成就,家庭經濟充裕,此時的陳伯伯已經不需要年輕時那樣需要對子女們承擔撫養和教育的任務。加之老伴的去世,其實陳伯伯個人是享有自由決定自己婚姻的自由權利的,而且這種婚戀的自由權利也是受到法律保護的。但是一個看起來對于陳伯是另一種人生的開始的黃昏戀卻遭到了孩子們的反對。我認為有以下兩個重要原因。
首先,子女們受到傳統的婚戀價值觀的影響,在情感上不能接受失去母親后,父親找個在子女們眼中是“外人”的護工來接替母親的地位。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傳統的婚姻觀,一般都是講百年好合,一定終身。尤其在中國古代,婚姻對女子的束縛更為嚴重,另一半去世后,“守寡”受到社會的褒獎和認可,甚至給予終身守寡的婦女以“烈女”“立牌坊”的榮譽。當然,對男性并非如此嚴苛,但是這個“一定終身,始終如一”的傳統是一直在中國的主流社會中得到認可的。這是人在社會制度、結構和話語中被壓制和束縛的表現。而后現代主義則是要打破這種“約定俗成”的、甚至不合理的規定,拒斥現代理論的一致性預設和因果觀念,推崇多元的價值觀和個人選擇。具有后現代視角的社工則更要求其價值觀是對服務對象是沒有偏見的,是理解的、接納的、尊重的,不以傳統的道德觀念去要求和束縛服務對象,相信服務對象的自主和潛力。需要社工在困難的個案中為服務對象找尋出路、為最邊緣的群體找尋突破。后現代主義就要求社工將服務對象從傳統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壓迫中“解構”出來。在本案例中陳伯伯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且與子女間存在撫養與贍養的責任義務,而子女的順利長大成年各有成就相當于意味著陳伯伯已經完成了自己作為父親對于子女的撫養義務。他的再婚并不影響子女的健康成長發展需要。而且從題目中看到,他雖然七十歲了,但是并不存在“腦子不清醒”等生理障礙,即他是具有獨立的經濟能力和行為能力來決定自己對伴侶選擇的。孩子的反對,并不是基于擔心陳伯伯生理能力問題考慮的反對,而是基于傳統婚戀觀念里的反對,這是一種情感上的不接受。其次,從法律和道德層面上講,陳伯伯并沒有違反與妻子的婚姻關系,也是在妻子逝世后才提出再婚要求的,題目中也沒有任何婚內出軌的跡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年8月通過,2018年12月最后一次修正)第二十一條,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護。子女或者其他親屬不得干涉老年人離婚、再婚及婚后的生活。這件事在道德層面是合理的,在法律上是允許的,只是對于子女來說卻是傷害了子女對于母親的感情。案例中也強調了陳伯伯是生活在相對保守的內陸省份,陳伯伯的再婚肯定會受到他人的非議,子女也擔心自己需要承受這樣的輿論壓力。在這里,子女的反抗純粹也是為了自己的情感利益受到維護,而并非考慮父親或者他人的層面。歸根到底還是子女自私的需求,并且在老人處于社會能力減弱、家庭地位下降的階段的強權政策罷了。
其次,在本案例中孩子為什么會反對陳伯伯的黃昏戀,從經濟利益方面考慮。父親的再婚子女們擔心自己的經濟利益受損。社會中存在標簽和偏見,認為像案例中的女護工經濟條件比較差,接近有錢的陳伯伯是有目的的,這是社會中容易對經濟地位較低的女性產生的刻板偏見。后現代認為人們看到的都是被各自“建構”的,因此存在許多種“問題”。一個問題要被建構為常態的偏離,首先需要確定的是:常態是否有 “問題 ”,它取決于人們對正常社會狀態的界定和建構,因此不同人群對同一社會現象的建構明顯有異, 具有話語霸權的人在認定社會問題之時就占據主導地位。既然,社會問題是被建構的,那么解決社會問題就需要從重新建構著手。一種可能的社會問題的解決方式就是 “去問題化”。女護工的社會身份一旦被社會建構為弱勢的、接近經濟條件較好的陳伯伯的形象,她自己是很難去打破這種刻板認知的,也很難去改變別人對自己身份的看法。因此,作為具有后現代視角的社工就應該從自己做起,打破這種刻板認知,為服務對象“去標簽化”。
對本案列社工處理的方法:1.針對原因一,社會工作者可以跟陳伯伯的子女們做思想工作,告訴他們老年人也有自己的戀愛需要,作為子女,應該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父親。跟他們的子女們普及法律知識,告訴他們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護。子女或者其他親屬不得干涉老年人離婚、再婚及婚后的生活。2.針對原因二,社會工作者應該主動打破標簽化,告訴他們陳伯伯與女護工是彼此有真感情,有互相陪伴、照顧和愛的需要,并不是社會標簽的“騙錢”的交往目的,而且陳伯伯自己那部分的財產自己也有規劃的權利。
參考文獻:
[1]樂國林.后現代的社會理論與后現代之下的社會工作[J].社會科學輯刊,2002,(04):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