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法與施蟄存的作品分析
王海婷
(五邑大學(xué),廣東 江門529000)
一、前言
二十世紀,弗洛伊德開始對人類無意識領(lǐng)域探索,這無疑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偉大的壯舉,并在西方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國文學(xué)界,魯迅、郁達夫、沈從文等作家均受到該理論思想的影響,在創(chuàng)作中多多少少帶有“弗”味。施蟄存也是其中一員。除了學(xué)習(x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施蟄存還通過自己獨有的表現(xiàn)方式,展現(xiàn)著心理分析小說獨特的魅力。下文筆者就從精神分析學(xué)的角度入手,談?wù)劸穹治龇▽κ┫U存創(chuàng)作影響及施蟄存本人對精神分析法的獨特表現(xiàn)。
二、以意向入手,以線索的形式表現(xiàn)弗洛伊德人格系統(tǒng)理論
在精神分析學(xué)理論中,弗洛伊德將人格分為三個部分:本我(伊徳)、自我與超我。其中本我是完全是無意識的,按“快樂原則”活動;自我代表理性,滿足本能要求,按“現(xiàn)實原則”活動;超我代表社會道德準則,壓抑本能沖動,按“至善原則”活動。弗洛伊德認為,本我和超我經(jīng)常處于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中。毫無疑問,施蟄存也認可這一觀點,并在創(chuàng)作中深受這一觀點的影響,通過對小說的分析,筆者得出結(jié)論:施蟄存經(jīng)常通過意向推動,寫出本我與超我的激烈沖突。
以小說《春陽》為例,作者就以春陽這一意向作為推動,以春陽的出現(xiàn)與消失,寫出了嬋阿姨情欲的消失,闡明了本我、自我、超我之間的沖突與爭斗。故事的女主人公嬋阿姨是一個寡婦,她因抱著牌位結(jié)婚受到社會的贊譽,她本人也把恪守婦道當作一種美德,這種道德強化從前儀式上嚴重抑制了小說主人公的本能欲望,于是,嬋阿姨即使從小鄉(xiāng)鎮(zhèn)來到大城鎮(zhèn),即使手中掌握著許多財富,她“左看看,右看看”,在大減價的店鋪里也什么也沒有買。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嬋阿姨這時受著超我的支配,她依然按照社會道德的規(guī)范行事、依然按照她本人所恪守的準則行事。隨后,春陽出現(xiàn)了,那燦爛的陽光讓她的心“灼熱地?zé)饋怼保活櫼磺械淖非罂鞓罚@是追求情欲的本我在發(fā)揮作用。嬋阿姨的情欲(本我)被壓抑了太久,所以力量太過強大,即使偶爾自我會出來阻止,用現(xiàn)實原則提醒著她,讓嬋阿姨想起人群中眼底的誹笑與譏諷,想用擁有“抱著牌位結(jié)婚的忠貞女性”這一社會輿論贊美的她就此“沉郁下去”也無濟于事。嬋阿姨內(nèi)心深處的情欲本能驅(qū)使她去尋求快樂,當她看到男子因找座位經(jīng)過她身旁時,她幻想著那雙有著文雅的手的年輕的銀行職員會坐在他身邊,幻想著他會約她去看電影,幻想著他們之間會發(fā)生一段美好的愛情。這時強烈的無意識本我已經(jīng)完全控制了嬋阿姨,她已經(jīng)不再顧她守著卻不敢花的財產(chǎn),不顧自己寡婦的身份。性本能促使她上前與那位男子搭話,可那男子的一句“太太”,又把嬋阿姨拉回了現(xiàn)實,寡婦的身份重回她的腦海,超我又占據(jù)了主導(dǎo)地位,提醒著她應(yīng)該遵循道德原則。于是春陽也便沒了,“眼前陰沉沉的,天氣又變壞了。”嬋阿姨也只能一如既往,在那獨身禁欲的寂寞的境遇里打發(fā)日子。她又變回那個受超我束縛的、擁有道德贊譽的寡婦了。
另一篇小說《梅雨之夕》也是如此,以雨作為意向,推動著矛盾沖突的發(fā)生。該故事發(fā)生在一場大雨時,主人公“我”與一位少女的邂逅。當主人公“我”看到女主時,強大的本我便開始發(fā)揮作用,“我”下意識地接近少女,最后用雨傘蔭蔽著送女子回家。在途中,“我”的心理發(fā)生了激烈的斗爭,想到自己已經(jīng)是一個結(jié)過婚的男人了,“我”十分擔(dān)心,既怕兩人的熟人看見,又怕自己的妻子看見,“我”“把傘沉下了些,遮擋住眉額,除非別人低下身子才能看到臉面。”從這點可以看出,超我意識正在與本我意識做著激烈的斗爭,一方面“我”止不住對女子的欽慕,一方面“我”又擔(dān)心自己所作所為不合乎道德標準,會惹人唾罵,只能由本我調(diào)和,把傘調(diào)低,偷偷地滿足自己的欲望。在這一過程中,“我”細心觀察著女子,觀察著女子的唇,觀察著女子被打濕的衣襟。這種中描寫無不體現(xiàn)著無意識對人物行為的支配。但最終,美好的體驗總要結(jié)束,就像《春陽》一樣,如此短暫。雨停了,女子主動提出不用送了,“我”只能悻悻離開,回到家向妻子撒謊,超我意識又占據(jù)了主導(dǎo)地位。
由此看來,在施蟄存的小說中,作者經(jīng)常將描寫人物心理與意向相結(jié)合,以意向來促發(fā)人物無意識的發(fā)展,具有明顯的個人化色彩。
三、與中國文化相結(jié)合——充分考慮讀者接受語境下的俄狄浦斯情結(jié)
弗洛伊德認為,在人格發(fā)展的第三階段,即生殖器階段,兒童會產(chǎn)生一種驅(qū)使兒童去愛異性雙親而討厭同性雙親的心理。于是,男孩把母親當作性愛對象而把父親當作情敵,產(chǎn)生了“俄狄浦斯情結(jié)”。作為中國人,施蟄存深知這種心理與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格格不入,于是他便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將俄狄浦斯情結(jié)對人的影響與中國文化背景相結(jié)合進行表現(xiàn),給人一種“新感覺”。
如在小說《將軍底頭》中,作者結(jié)合歷史,以花驚定將軍的心理為線索,講述了他在吐蕃和大唐之間的猶豫以及對姑娘的向往和軍規(guī)的兩對矛盾。最終,將軍戰(zhàn)死沙場,沒有頭的身體在心愛少女的譏笑下,傷心的死去。筆者認為從俄狄浦斯情結(jié)角度分析該作品,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故意設(shè)置,以有著一半吐蕃血統(tǒng)一半漢人血統(tǒng)的將軍想要歸根父系溯源,回歸吐蕃祖國(認父),卻被迫替大唐征討祖國(弒父)的矛盾沖突著手,塑造故事。使人物活動與心理這既符合中國人常規(guī)“血濃于水、追根溯源”的倫理原則。而通過隱喻訴說故事中所隱含的弒父娶母情結(jié):將吐蕃隱喻為父親,將大唐(和在邊境愛上的大唐少女)隱喻為母親。為了得到心愛少女的欽慕去攻打鄉(xiāng)人,構(gòu)成邏輯上的弒父。可這一過程并不容易,主人公花驚定與《哈姆萊特》主人公一樣,在實施“弒父”這一動作上都有著猶豫,無法對“父親”下手。在故事的最后,將軍的頭被吐蕃將領(lǐng)割下,也正代表著這次弒父行動的失敗。當然,僅用一篇作品來證明作者的戀母情結(jié)傾向還十分單薄,實際上作家還有很多作品也同樣運用中國歷史背景表現(xiàn)出主人公的戀母情結(jié)。
如在《石秀》中,石秀嫉妒義兄楊雄“一尊黃皮大漢,卻有一個賽西施在家中”,對嫂嫂潘美云產(chǎn)生了性幻想,甚至在夢中他還囈語到:“如果沒有楊雄,我一定娶了你。”可見在某種程度上,石秀也有弒父(兄)娶母的心理。只是這種心理被倫理道德所束縛,只能在夢中實現(xiàn)。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闡述俄狄浦斯情結(jié)時,將其放在中國歷史背景下,與傳統(tǒng)歷史故事相結(jié)合進行創(chuàng)作,充分考慮到了讀者語境,更符合中國人的審美價值觀,體現(xiàn)了作者對精神分析法的獨特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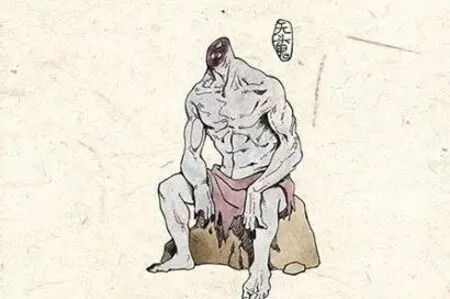
四、以夢寫實——考慮到作家與作品的社會性
弗洛伊德認為,夢所表現(xiàn)的是被壓抑的人的本能欲望。在施蟄存的作品中,作者多描寫的是都市人的夢,借都市人的夢來表達都市生活的變態(tài)與扭曲,頗具現(xiàn)實主義意味。
如在《獅子座流星》中,原不會生育的女主到醫(yī)院檢查完身體,發(fā)現(xiàn)是丈夫的原因后,便對丈夫產(chǎn)生了不滿的情緒。于是,被壓抑的欲望十分巧妙地連成夢,使主人公的潛意識愿望在夢中得到實現(xiàn)。《薄暮的舞女》也是如此,作品寫出一位叫素雯的舞女,在昏暗朦朧的夜色里,把一只小狗當成她情人的“幻影”,在幻境中開始新生活的故事。
從以上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創(chuàng)作的種種故事都將潛意識的夢與現(xiàn)實主義的因素聯(lián)系起來,人們的幻想都依附于現(xiàn)實,依附于情感。與弗洛伊德無意識主導(dǎo)一切的觀點有所不同,體現(xiàn)了作者對精神分析法的獨特創(chuàng)造。
五、結(jié)語
小說家施蟄存在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吸收的基礎(chǔ)上有所創(chuàng)新,對三重人格理論、俄狄浦斯情結(jié)和夢與無意識都有自己獨特理解,對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值得我們學(xué)習(xí)與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