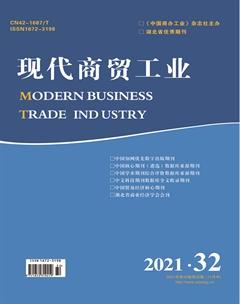論動機論及其困境
徐雨杉
摘 要:隨著倫理學的不斷發展,針對道德的評判問題,學者提出了種種解決方案,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統一論、效果論以及動機論。本文主要是對動機論進行分析研究,主要分析此方法應用于道德評判根據上是否可行,并提出其理論的不充分的問題以及對應的現實難題,表明作為具有內在性和私人性的動機,是難以解決作為道德評判根據的時候產生的善意傷人的道德悖論的難題。雖然動機論作為道德評論根據來說尚有難度,但是它對于人們具備善良的動機的教育仍是非常珍貴的。
關鍵詞:動機論;動機;道德評判根據;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2.058
總的來說,本文中所強調的道德評判根據中的“根據”所指的是解釋和還原的關系。其在理論中的邏輯關系如下:若A能還原成B,那么,B就是A的根據;進一步來說,若是還有其他的子理論同樣也能還原成B,但是B不能夠被還原,那么,B就叫作最終根據。舉個例子,善和惡,雖然作為通常的道德評判的結果,但其是受主觀決定的,并且具有個體差異性。動機論指的是以人的行為動機為道德的評判根據,而把最終的結果與效果作為根據的則被稱為效果論;另外,將這兩種根據結合起來進行評斷的被叫作統一論。那么,在進行道德評判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選擇就成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了,而這個問題的答案的得出應該遵循有效性原則。
如今,許多專家學者對此問題的爭執依然不斷,執每個觀點的學者也都能夠自圓其說,然而,有效性原則常常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學者往往陷入的道德評判標準是動機還是效果問題的泥淖之中。針對這個現狀,本文通過剖析動機論,闡明其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里所遇困難,并試圖反思它的有效性。
1 動機論概述
1.1 動機論的常規定義
動機論首先是一種主觀的態度,具體地來說就是人在做出行動之前內心想要實現的預期。倘如打算決定做什么事,其動機就是做出這件事情的緣由,以及其合乎道德的或者是非道德的目的。它認為善與惡只跟行為發生者的動機有關,而與行為所產生出來的效果毫不相干。因此,在善惡評價上的唯一需要考慮的只有動機這個因素了。這兩個釋義的共同點有兩點:一是兩個皆預先默認了動機可以被作為公共對象的這個設定;二是兩者皆是含糊的,都沒有十分明晰的主體。綜述以上,道德評判就沒法找到和明了道德的結構了。然而,只有在道德結構這個范圍內,我們才能夠精準地定義動機論,才能進一步地進行動機論的有效性研究。動機論在道德結構的范圍內可以被概括為:動機論是把行為的發出者的動機當作道德評判依據的;換句話說,動機論是把行為發出者主觀的意愿作為道德評判依據的。在動機論的情況下,道德評判的邏輯如下:當且僅當行為的動機是善良的、道德的,那么這個行為才能被認定為是道德的,而與其他的因素無關。動機論的支持者在世界上曾引發熱潮,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康德。在他的《實踐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學原理》等多部著作中都有關于動機論的闡述:“手段的有價值或無價值當然只取決于目的”;“意志的客觀根據叫作動機”;“只有出于責任的行為才具有道德價值,責任就是由于尊重規律而產生的行為的必要性”;“關于道德價值的問題,我們要考慮的不是我們能看見的行為,乃是我們看不見的那些發生行為的內心原則”。
1.2 動機論的基本預設
動機論首先是一種主觀的態度,具體地來說就是人在做出行動之前內心想要實現的預期。倘如打算決定做什么事,其動機就是做出這件事情的緣由,以及其合乎道德的或者是非道德的目的如果要使得動機成為公共對象,則必須具有公共性。如果進行道德判斷,那么其判斷對象就必須明確。除了施行事件者本人,還需要一個應事者來進行道德評判。從這個角度上看,動機不單單需要被施事者知曉,被除此之外的人知曉也是同樣重要的。因此,動機如果不能被第二者知曉,就無法成為公共對象,也就無法作為道德的評判對象和根據了。縱觀之前的研究,沒有提出預設動機論的并且并未提出動機是無法成為公共對象的問題,就會造成不少的無用研究。
2 動機論面臨的理論困境
動機論里,施事者的動機是道德評判根據的標志,對于動機的評判才能形成行為善惡的結論。并且,想要知曉和剖析施事者的動機到底是什么,就必須先要讓評判的人知曉施事者的動機。鑒于此,評判者如何得知施事者的動機就成了一個疑問。施事者有可能知道自己的動機,同樣地,施事者在當時也有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動機,事后經過他人的詢問和相關提示后才會知曉自己的動機。那么,到底別人怎樣才能知曉施行者的動機呢?別人有可能從施事者行為的最終效果來判斷施事者的動機,但是,怎樣才能使得評判人了解的與施事者本身的動機是完全一致的呢?進一步說,怎樣使得這種評判是可靠的呢?答案是否定的。這也就表明動機是沒辦法處于一個能被公共認識的對象地位,也同樣沒辦法被大家共同感知的。動機,是具有完完全全的私人性的,它只內在于施事者這一方,是無法徹底地、準確地外化出來的,因而其他人也難以精準把握施事者的真正動機,從這來看,動機就沒法成為道德評判根據了,那些把動機看作依據的就少了說服力。舉個例子,《論語》里“子見南子”的場景里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孔子的弟子子路質疑孔子與南子相見的用心坦蕩的時候,孔子卻沒有辦法來證明自己懷有正大光明的動機,只能無奈地說出“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的誓言。可見證明動機的善惡之難!人生在世,第一無法辦成的就是向別人“證明”自己的行為的動機;人生第一無奈的就是不得不向別人證明自己的動機的善良。遇上這種事情,就連“道如日月之明”的孔子都只能對天發誓而有心無力。這是動機不可知所產生的道德評判的困境。如果在道德評判的時候,由于動機本身是沒辦法被證明的,而若是只能依靠發毒誓來證明自己的動機,也就太過于荒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