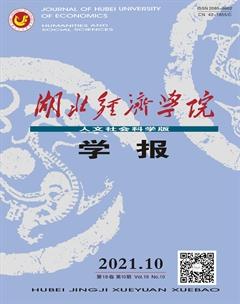儒家“正名”視域下荀子“性惡”論再審視
譚紹江 涂愛榮
摘 要:“正名”是孔子創立的儒家理論范疇。其包含有解決國家治理難題的三層顯性內涵和傾向人性“惡”的隱性內涵;同時,還體現孔子重視“符合實際”的思想特征。荀子傳承發展這一范疇,在《正名》篇中圍繞“化解‘民無所措手足”的治理難題,從多個方面詳細解釋了人性范疇相關內容,并為“性惡”論奠定基礎。在《性惡》篇中,荀子則通過“符合實際”的檢驗方式,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證“性惡”、反對“性善”。按照孔子“正名”視域審視荀子“性惡”論,可以進一步發現荀子思想的內在統一性,對學界長期熱議的“荀子是否‘性惡論者”的焦點問題進行有益回應。
關鍵詞:孔子;正名;荀子;性惡
荀子“性惡論”長期是學界的熱點問題,其問題焦點之一在于探討“荀子擁有一種相容一致的人性理論么”[1]?圍繞此焦點,當前學界的研究大體分為兩大陣營,一方認同“性惡”思想與荀子整體思想一致(簡稱“認同”陣營),另一方則認為其不相一致(簡稱“反對”陣營)。“認同”陣營對荀子“性惡論”的意蘊進行各種解讀,化解矛盾①[2]。“反對”陣營的研究者則試圖通過語義辨析、版本考證等多種方法,論證“性惡”非荀子本身思想,乃為其后學乃至后人偽造②[3][4]。這其中大家一致認可的思路在于,荀子究竟是否主張“性惡”,一定要與其思想的整體結構相關聯[5]。尤其要注意他對儒家創始人孔子諸多思路的繼承。基于此種考慮,筆者擬從孔子所創立的“正名”視域對荀子“性惡”論予以再審視。
一、孔子“正名”范疇的內涵及荀子的傳承發展
“正名”范疇由孔子提出,并在后世儒學傳承中得到不斷充實,發展為儒家比較重要的一種理論原則和獨特的研究視域。
(一)孔子“正名”范疇的顯性與隱性內涵
“正名”范疇是孔子在與子路的一次著名對話中提出來并進行初步論證的。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6]133-134
孔子所說的“正名”究竟所指何事,歷來有眾多解讀。楊伯峻先生綜合各家,分析指出,“我這里用‘名分上的用詞不當來解釋‘名不正,似乎較接近孔子原意。但孔子所要糾正的,只是有關古代禮制、名分上的用詞不當的現象,而不是一般的用詞不當的現象。一般的用詞不當的現象,是語法修辭范疇中的問題;禮制上、名分上用詞不當的現象,依孔子的意見,是有關倫理和政治的問題,這兩點必須區別開來”[6]135。確如楊先生所言,孔子所論之“正名”的最顯性內涵,正是聚焦“如何實現國家的良好治理”問題,按照“是什么”“為什么”“怎么辦”的三個層次來展開的。
第一層是講“名是什么”。師徒二人對答中所講的“名”并非一般性的語言邏輯問題,而主要是指在國家治理中涉及的“名稱”“名分”問題。
第二層是講“正名為什么重要”。這就與國家治理的成敗密切相關,孔子用“反證法”按照遞進的邏輯從五個方面予以論證。他指出,“名稱”“名分”的問題依次關乎理論論證(言)、權責分配(事)、制度規范(禮樂)、獎懲規則(刑罰)和具體行動(民錯)的成敗與否。一旦在“名稱”“名分”問題上不清晰甚至不正當,那么之后的一系列國家治理措施都會失敗。也可以說,“正名”之目標就是要化解“民無所措手足”的治理難題。
第三層是講“怎么做到正名”。孔子闡述了從理論論證(言)和實踐行動(行)兩方面予以驗證的要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從理論論證上來說,“正名”就要使所主張的“名稱”“名分”在道理能講通(必可言);從實踐行動上來說,“正名”就要使“名稱”“名分”在實踐中是可行的(必可行)。這兩方面都不要茍且馬虎對待,就是真正的“正名”。孔子的這三層論述,最終要達到的顯然是第三層要求,即提出了人們應該怎么去“正名”的規則。雖然孔子對此沒有詳細展開,但他的要求已然明確無誤——這就是“正名”必須真實、符合實際,不能虛假、違背實際。一定意義上,他對子路的反駁也是在說明這一點。我們注意到,子路是用“迂”來評價孔子的“正名”原則的。孔子堅決反對這一評價,也就是說,他對“正名”的自我評價是“不迂”——也即符合實際、可以接受實踐檢驗。
在這三層顯性內涵之外,孔子對“正名”的論述中還有一層隱性內涵——即人性“惡”的判斷。雖然孔子言論中未直接說“性善”還是“性惡”,但在這里他有同意“性惡”的傾向,或者最起碼不認可“性善”說。因為,如果人人“性善”,就不至于在“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的情況下無所適從(所謂“民無所措手足”)。外在的禮樂教化、賞罰制度對于人們生活秩序至關重要,良好的社會秩序絕不單純寄希望于激發人們自身內在的善性。換句話說,要以“正名”來化解“民無所措手足”難題,以承認人性“惡”為思考前提。
(二)荀子傳承發展孔子“正名”范疇的內涵
孔子探討“正名”問題的這些顯性和隱性的內涵成為荀子闡述相關問題的依循。荀子著有《正名》一篇,在文章開頭即鮮明體現了對孔子“正名”的三層顯性內涵的遵循。
后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于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7]476。
首先,他所列舉的四種“名”中,“刑名”“爵名”和“文名”是非常直接的國家治理內容,而“散名”中亦有大量內容與治理相關。這就界定了他探討“名”的界限是國家治理,正與孔子“正名”所說一致。
其次,他也強調了“正名”在國家治理方面的重大意義。對比孔子論述的與“正名”相關的諸種國家治理措施,可以發現荀子之所以列舉以上四種名稱絕非隨意而為,他與孔子之說有嚴格對應。“刑名”顯然對應孔子所言“刑罰不中”,“爵名”基本對應孔子所言“事不成”,“文名”主要對應孔子所說“禮樂不興”,最后的“散名”也基本可與孔子所言“民無錯手足”相對應。需要指出的是,雖則“散名”沒有像“刑名”“爵名”“文名”一般有明確典章記載,但在實際認定過程之中,也必然不能違背“刑名”“爵名”“文名”的基本規則。也即,這幾種“名”都要服務于國家治理實效這一最大的目標。荀子在后文有更多內容來強化這一點。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奸。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托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謹于循令矣。如是則其跡長矣。跡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于守名約之功也[7]477-478。
荀子所言“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與孔子“名不正則言不順”的系列邏輯若合符節。當然,在此處,荀子著重從正、反兩面來談孔子所重視的“刑罰不中”“民無錯手足”問題。他先按照孔子當時假定的說法描述了“刑罰不中”的狀況——“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奸。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即表現為一些人玩弄詞句、擅自混淆(刑罰方面的)名稱,造成人民失去了所遵循的刑罰方面的標準,從而各執一詞,陷入無休止的辯訟之中。故而,這種人之罪名如同偽造軍事行動的“符節”和經濟方面的“度量衡”的一樣,都是罪大惡極之奸徒。那么,從正面來說,就需要對這些奸徒進行嚴厲懲處,使人們都不再妄自擾亂(刑罰方面的)名稱,從而內心誠實而聽從國家號令、對國家刑罰嚴格遵循,這樣事實上就避免了“民無錯手足”的問題。這樣才可以達到最優良的國家治理效果。
再次,荀子更著重凸顯了如何“正名”的要求——符合實際。按他的說法,“刑名”“爵名”和“文名”的標準是比較確定的,但更多地涉及萬事萬物的“散名”之標準就不那么絕對化,而需要考慮實際情況來確定。其標準既要考慮到中原(諸夏)地區的風俗習慣,也要考慮到和邊遠地區溝通交往的實際情況(因為之通)。那么,荀子將“散名”與之前三種“名”相區別,是否說明其在國家治理中地位低呢?從后文論述篇幅來看,并非如此。與其說荀子這樣處理是出于地位高低的考慮,倒不如說他是更多從凸顯孔子關于如何“正名”的“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原則的考慮。一定意義上講,“刑名”“爵名”和“文名”都擁有相對權威和深厚的歷史根據,在國家治理中更多起到宏觀性、綱領性要求,可討論的余地不大。而真正深入到國家治理的細節中后,恰恰面對的是大量細碎事情之“散名”的界定問題。能否處理好“散名”才是考驗統治者國家治理能力和效能的關鍵所在。荀子力圖告訴持儒學立場的統治者,怎樣在不違背“刑名”“爵名”和“文名”的綱領性要求的前提下,充分結合實際狀況來制“名”,實現有效國家治理。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于舊名,有作于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7]478。
在這里,“舊名”更多指的是儒家的綱領宗旨,“新名”則指大量“散名”。而“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是指向“新名”的相關因素,包含著要求“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原則。
二、荀子在“正名”視域下論證“性惡”
前文指出,孔子對“正名”的論述包含判斷人性“惡”的隱性內涵。這內涵及其意義被荀子敏銳注意到了。因之,荀子即在嚴格遵循孔子“正名”范疇的基礎上,把“性惡”這一隱性問題做了公開、細致地論證。
(一)荀子以“正名”思路闡述“人”之“性”
荀子的論證思路以《正名》中對“散名”的解釋為基礎。
散名之在人者……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也[7]477。
這段話的開頭一句“散名之在人者”明確顯示,荀子注意到了孔子“正名”隱含著的對“人”(人性)的判斷。這一內容孔子沒有明言但卻很重要,因之荀子就將其凸顯出來。結尾一句,“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后王之成名”將“散名”與掌握權力的“王”密切聯系起來,同樣體現他所講的“名”仍然聚焦國家治理難題,以化孔子所說的“民無所措手足”的局面。
具體來看荀子論證的主體內容。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7]477。
這里的三句話分成了兩個層次。第一句是第一層次,開宗明義申明他接下來講的是關于“人”之“性”的問題(不是寬泛地討論所有生命的“性”)。他沒有把人的生命直接稱為“性”,而是把生命背后的根據——“所以然”者稱為“性”。黃彰健先生對此認為:“《荀子》所言‘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也只是說‘生之所然的那個道理,或者是‘所以生之理謂之性而已”。[8]梁濤教授也指出,“‘生之然或‘生之所然是情、是欲,而‘生之所以然則是理”“生乃一具體生命之存在,而此生命之所以如此生,即是其性”“‘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翻譯過來就是:(一生命物)之所以生長為這樣的原因就是性”。[9]依此邏輯,他對“人性”的界定就還需要回答:“人之所以生長為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從前文所說的傳承孔子“正名”傳統來看,這不僅是單純的語言分析問題,更涉及“民無所措手足”的國家治理實效的問題。考慮到當時的社會還具有極其濃厚的神學氛圍,這個原因尤其要說清楚——“人之所以生長為人”是不是反映了某種更高的神秘主宰者的意志?還是人自己的意志?或者根本沒有什么意志呢?
因之,后面兩句話同屬于第二層次,從兩個方面是對人之“性”進一步說明。
第一個說明是“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楊倞注解曰:“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和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10]885。這里解釋人的生命狀態,在如實描述人的各種感應能力的基礎上,著重說明了“不事而自然”的問題。其意在說明,人之所以擁有生命,并不受某種人之外的力量來委任、驅使,而是自然產生。這就能明確與神靈主宰劃清界限,有利于駁斥將鬼神引入國家治理的妄想。第二個說明是“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相比“性”那種自然的平靜狀態,此處闡述出人的種種情感帶有了主動、活躍的特點。這種人性中情感的活躍性為人的生命提供了動力來源,亦為針對人所進行的國家治理提供根據。
至此,荀子用了三句話對“性”(主要是人性)之名進行了直接界定,展示給我們一種“一體兩面”的結構:“一體”即“生之所以然”,“兩面”即靜態的“不事而自然”和動態的“情”。其中,“不事而自然”有駁斥鬼神干擾的效果,“情”有表現人之區別于萬物之活躍的意義。
但荀子的論證并不止于此。因為,他要講的“人”之“性”,不是單純的名詞解釋,按照他對孔子“正名”范疇的傳承,他是要解決“民無所措手足”的治理目標問題。如果要達到讓民“錯手足”,還需要回答的問題包括但不限于:“民”是怎樣產生想法的?又如何將想法付諸實踐?他們在說話做事時有沒有可以把握的心理運行規律?諸如此類問題都要解釋,所以荀子必須繼續解釋“心”“慮”“偽”等一系列“名”。
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7]477。
熊公哲注曰“情然,情有所動,意謂有所欲也”[7]480。“好、惡、喜、怒、哀、樂”諸多情感潛藏著可以發動的屬性,但其真正的主動權在“心”那里,荀子在《解蔽》等文中以“天君”“君”來界定“心”之地位: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7]460。
“心”被稱為“天君”,它只發出命令而不接受命令,對情感之發動進行抉擇,形成確定的“思慮”。
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后成謂之偽[7]477。
“思慮”就如同人在行動之前的決心,最終會引起行動——“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后成謂之偽”。荀子在這里又講到兩個關鍵范疇“能”與“偽”。就“能”而言,荀子在類似語境談到的“能”并非寬泛的才能,而應特指天官之“官能”。結合上下文來看,從“生”到“情”、從“情”到“思慮”再到“官能”,事實上完成了一個由外在感官感知到內在之心思慮決定,再返回到感官采取行動的過程。就“偽”而言,荀子創造了一個自己思想體系中十分重要的范疇,即融入之思考、行動與結果為一體的“偽”。③
接下來他探討的是“為”——相當于是“偽”在行動層面的內涵:
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7]477。
人若為只是利益而“為”就是單純的工作,但通過“為”來實現道義那就是德行、功績。再接著,荀子講到人的認知能力。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7]477。
人自身本有認知能力,但需要發揮這種認知能力去充分認識外物才能收獲“智慧”。
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7]477。
與上文講“認知”的內容銜接,荀子在這里講的“能”仍屬于“官能”之義。第一個“能”指人所具有的不同的天官之能力,第二個“能”則指人有將各種天官之辨別合成一個整體之能力,這種合成能力正是從“天官”進入“天君”的渠道。他這個解釋近似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中所說的感性認識之第三層次“表象”,再發展就進入理性認識之“概念”層次。
最后,荀子以“病”與“命”來總結:
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7]477。
既然“性”是指“人生長為人的原因”,那么“性傷”所指的就是阻礙“人生長為人”的因素,這稱為“病”,這等于是講不利于“性”的東西;反之,“人生長為人”所遭遇的外部條件就稱為“命”,這是講有利于“性”的東西。荀子把這些“名”講解清楚了,那么,他所重視的“正名”視域下如何化解“民無所措手足”的難題就有了一整套可以把握的規律,這也為他繼續論證孔子“正名”視域中隱含的“性惡”主張奠定了理論基石。
(二)荀子以“正名”思路論證“性惡”
正是從荀子《正名》篇中論證的理論基石出發,我們才能更清晰認識他對“性惡”的論證。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7]507。
從字義上看,《性惡》開篇的話直接翻譯就是:人性是惡的,人所做的善是偽帶來的。問題在于,他所說的“人性”是指哪一層面?《正名》中探討的“人性”是一個“一體兩面”的結構,其中,管總的“一體”是“生之所以然”(即“人之所以生長為人”的原因),但是若只講這個管總的定義意義不大,因為這基本還是一個形式命題,沒有內容[9]。所以,要進一步審視“人性”之“兩面”:“性之……不事而自然謂之性”與“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那么,是否這兩面都與“惡”有關,或者說其中某一面與“惡”有關呢?這就涉及對“善”“惡”的理解問題了。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7]507。
荀子列舉了三種對立的“惡”與“善”“爭奪”“殘賊”“淫亂”與“辭讓”“忠信”“禮義文理”。這兩組范疇雖然在價值上相反,但是作為概念范疇它們具有相同的特點:一是都是帶有主動性,不是純粹被動、無意識的內容;二是都與人與人的關系有關,而不是僅就單獨的個體而言。我們以這樣的“善”“惡”界定再返回到“人性”兩面討論,就可以發現“性之……不事而自然謂之性”這一面也不在“善”“惡”討論之列,因為這里著重強調“人性”只是自然造就,那就既不關乎主動性,也不關乎人與人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荀子在其他地方講的人性“樸”是在強調這一面。這樣一來,與“善”“惡”相關的就只剩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這一面了。恰恰這一面既具有主動性,又涉及人與人的關系,正好可以用來探討“善”“惡”。從主動性的一面來看,荀子就以不完全歸納的方式列舉了人性中“好利”“嫉妒厭惡”“好聲色”三個方面,主要涉及了“好”與“惡”兩種情感。而這兩種情感一旦“順是”——無限制擴展開去,就會導致“惡”果的產生。從人與人關系來看,“好”與“惡”兩種情感的無限擴展,最終傷及的就是他人和社會——奪他人之利、殘賊他人之生命和淫亂的社會秩序——這正是“惡”之典型。荀子的論述也證明了我們的推理,他明確宣稱:
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7]507。
也即,導致“惡”的正是人性中具有主動性的“情”之一面。
以上是我們對“人之性惡”的分析,接下來看看“其善者偽也”。同樣還是要從《正名》中對“偽”的論述出發來看。荀子明言:“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后成謂之偽”,前文指出,荀子之“偽”是融入之思考、行動與結果為一體的。與上文所言“情”之“惡”對比,荀子承認“偽”與“情”之發動有關,毫無疑問也帶有主動性。但關鍵在于“心”要對情之發動進行揀選與最終抉擇,可以將“情”之發動無限擴展之趨勢予以控制,約束在合理的范圍內。
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于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于亂?故治亂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7]496。
作為“人”行為主宰者的“心”,其認可之事合乎“理”,則“欲”即使很多,也不會對“治”(安定)有損害。人之行動有時會超過所欲之限度,就在于“心”之驅使。反過來,“心”所認可之事偏離“理”,則即使“欲”很少,也不能阻止“亂”的產生。所以“治亂”的根本系于“心”所認可是否合“理”,不在于“情”所生發的欲望。
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7]507。
“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正是為“心”提供“中理”的根據。有此保障,則由“情”所發動之“偽”,具有善的屬性。某種程度上說,“人之性惡”問題,也與“心”聯系密切。“在荀子,‘性與惡之間雖然有著直接的關聯,但‘性并不是人之為惡的責任者,因為最終的善惡并不是由‘性而是由‘心決定的,是‘心為主,而不是‘性為主。這就好比一條狗咬傷了人,它的主人家是要負責的”[11]160。我們甚至可以說,“就現實性而言,人是為善還是為惡,并不在性之情欲本身,而完全取決于心,取決于心之所可是‘中理還是‘失理”[11]160。事實上,遍觀《荀子》全書,荀子對“心”與“善”的關聯論述極多,而非常注意將“性”與“善”進行切割。即便我們不看《性惡》一篇④的文字,也能結合荀子的其他文章從側面感受到他認可“性惡”的傾向。
當然,從邏輯上講,荀子所說的是“善”來自“偽”、與“心”相關,并沒有說“偽”全是善、“心”必定善。荀子力圖證明,即便是“人心”與善有關,依然不能說人性天然為善。
三、荀子在“正名”視域下反對“性善”
“性惡”論是荀子嚴格遵循孔子的“正名”視域的必然結論,與之相對,他激烈反對孟子所主張的“性善”論。
(一)從邏輯與生活現實角度反對“性善”
荀子按照孔子“正名”所要求的“言之必可行”原則,以邏輯與日常生活常見現象來予以檢驗。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7]509。
荀子首先是樹靶子。這里就涉及到“性善”與“失喪其性”的邏輯關系問題。楊倞注曰:“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許多注家根據這一注解對文本進行了修正。劉師培根據楊注指出,“將”字本應是“惡”字;梁啟雄根據楊注指出,“故”與“也”兩字中可能少了一個“惡”字;包遵信與王天海甚至認為“性善”之“善”本應為“惡”字[10]940。按楊、劉、梁的意見,此處孟子之言是先言人之“性”為善,以此為基礎再言人之“性惡”在于失喪此“善”性之故。若按包、王意見,則干脆孟子就是在直接討論“性惡”問題[7]510。無論如何,此處荀子是以模仿語氣闡述了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的立場。
以孟子立場為對象,荀子把攻擊點就集中在“失而喪之”的說法上,從邏輯上說明其不可行。
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樸,離其資,必失而喪之。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7]509。
他指出,即使人們真的像孟子說的那樣在最初、最本始的人性中就有“善”的話,那么人在現實中一出生就開始背離了這些“善”,生下來就喪失了孟子所說的那些“善”的內容。既然“善”已經喪失,那么人性就應是“惡”而不是“善”。
接下來,荀子就把這個“檢驗”從細節上進行了擴充。一方面,他對“性善”之說予以邏輯上的檢驗:
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樸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樸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7]509。
對此一段話,楊倞注曰:“使質樸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于耳目”[10]941。正是荀子對孟子“性善”說的一種描述。在他看來,持“性善”說者就是把人之“善”看成了與人之目自然能見、人之耳自然能聽一樣的東西。荀子仿佛是讓讀者們自己來看看,主張“性善”會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把人的“善”“美”當作了與人眼睛能看、耳朵能聽一樣的東西了。如果是“善”“美”只是人這種自然而然的天性的話,人后天的言行就只有很低的價值了。況且,從“目”“耳”角度說,世上亦存在著天生的聾人、盲人,根本沒有視力與聽力;若“善”也是憑天性,豈非存在著天生失去“善”能力之人?
另一方面,荀子以“今人之性”狀況進行檢驗,以現實中人們的言行來檢驗孟子的說法。
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于情性矣。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7]509。
按照孟子“性善”之說,則人們應該天生懂得在飲食面前“子之讓父”,在辛勞面前“子之代父”,但事實上人們面對饑餓、寒冷、勞苦時天生的欲望情感卻是個人之飽暖、休息。以此現實來看,有些人能做到“子之讓父”“子之代父”反而是對天生欲望情感的違背了。而人們實際上能做到那些屬于“善”的禮義孝道,正是后天文化教育治理的結果。所以說,完全順從人天生情感欲望,就會違背辭讓之“善”;完全促成辭讓之“善”就必須要違背天生情感欲望。
(二)從國家治理角度反對“性善”
進一步,按照孔子“正名”視域的國家治理性質和化解“民無所措手足”難題的目標要求,荀子重視從國家治理層面舉例來檢驗,證明孟子“性善”說之危害,同時再證“性惡”之成立。
孟子曰:“人之性善。”
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矣[7]514。
荀子指出,自古及今,“善”“惡”都是有確定涵義的。“善”就是天下的“正理平治”,“惡”就是天下的“偏險悖亂”。荀子的這種定義帶有很強的政治哲學色彩,“善”“惡”在他這里指的是整個社會秩序治亂,而不是只看個人的道德言行的好壞。
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圣王,惡用禮義哉?雖有圣王禮義,將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7]514?
在“正理平治”這樣的“善”涵義下,若是人“性善”,則無疑等于說人憑自然本能可以使社會達到“正理平治”,甚至可以等于社會自然會達到“正理平治”,荀子對此當然無法接受。
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7]514。
荀子認為,從現實中那些強害弱、眾暴寡、天下悖亂的情形來看,無論如何,社會秩序不可能自動變得“正理平治”,“圣王”“禮義”乃至“刑罰”是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這也正是政治措施的價值所在。
今當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強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嘩之,天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7]514。
因此,此處顯示了荀子與孟子在認識“性善”之“善”概念上的差異。眾所周知,孟子說“性善”是說人“心”中均有仁、義、禮、智四德之“善端”,擴充之可完成個人道德修養及天下之治。毋寧說,荀子所謂的天下“正理平治”的“善”在孟子這里只是“善”的一個層次,是人之“善端”擴充之后的結果。以此來看,荀子認為孟子所說的“性善”是把結果當成了原因,有嚴重的邏輯錯誤。對這種“性善”,他當然要不遺余力地反駁。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圣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圣王,貴禮義矣。故檃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7]514。
楊倞注“節”為“準”、“征”為“驗”[10]949,荀子認為言說古之理論必須要在現實中得到檢驗,言說“天”之理論必須要在人世間得到驗證。理論之貴在于有分有合[10]949,能檢驗。也就是說要既能言說,又能立法度,并且可以公布施行[10]949。而孟子的“性善”說,既無法把古今、天人關系在分的基礎上統一起來、沒有檢驗標準,雖能言說,卻不能在現實中立法度,也無法實行。按照孔子“正名”原則的內涵,這不就是明顯的“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最終導致“民無所措手足”的后果嗎?換句話說,荀子始終緊扣孔子“正名”原則的顯性與隱性內涵在批判“性善”說。
綜之,荀子一貫以儒學思想中“禮學”傳承者著稱,如“性惡”論等看似突兀的論點實際上都非常注意傳承早期儒家特別是孔子思想中對于國家治理有所裨益的思路。孔子提出“正名”原則,荀子即專門撰寫《正名》篇目以傳承并張大之。我們亦正是通過深入分析荀子《正名》相關篇章,探尋到荀子的這種忠實的傳承發展思路,從而進一步把握到了荀子提出并力證“性惡”的內在理路。按照孔子“正名”視域審視荀子“性惡”說,可以進一步發現荀子思想的內在統一性,對當前學界熱議的“荀子是否‘性惡論者”的焦點問題進行有益回應。
注 釋:
① 美國學者何艾克(Eric Hutton)認為,荀子之“性惡”并非認為人性“天生邪惡”,而是因為一些外部原因,具有向惡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可以呼應“人性是一個過程”的現代哲學觀念;其“性惡”論中反而有一些天賦的“愛的情感和對他人的關注”,參見注[1]。梁濤教授通過用《郭店楚簡》中“上為下心”來解釋《荀子》中“偽”字,闡述了荀子“性惡、心善”思想。參見注[2]。
② 周熾成、林桂臻等學者都進行了大量論證。周熾成通過分析荀子“性惡”說法只在《性惡》篇中出現,并與其“性樸”觀念、整體思想沖突,認為《性惡》篇非荀子本人作品,為荀子門人雜著而成。見注[3]。林桂臻主要通過發現荀子論證“性惡”的邏輯中存在的矛盾來進行質疑。當然他不同意整篇皆偽作,而是認為“性惡”這一個詞出現了篡改或錯版,原文應為“性不善”而非“性惡”。見注[4]。
③ 梁濤教授對此問題有較新的闡述,他結合郭店楚簡的相關文獻考證,認為此處“偽”應為“上爲下心”,與“偽裝之偽”本為兩字。可備一說。見注[2]。
④ 許多學者即認為,《荀子》只在《性惡》一篇中提到“性惡”,因之懷疑這一主張與荀子整個思想背離。見前注②。
參考文獻:
[1] Eric Hutton,Does Xun zi Have a Consistent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ee Virtue, Nature, and Moral Agency in the Xunzi,by T .C.Kline III and Philip J. Ivanho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2000: 220-236.
[2] 梁濤.荀子的人性論辨正——論荀子的性惡、心善說[J].哲學研究,2015,(5).
[3] 周熾成.以性惡論說荀子的困境及其擺脫[J].現代哲學,2017,(1).
[4] 林桂榛.揭開二千年之學術謎案——《荀子》“性惡”校正議[J].社會科學,2015,(8).
[5] 劉旻嬌.荀子論“性惡”——當代港臺與大陸研究的一個比較總結[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2).
[6]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7] 熊公哲.荀子今注今譯[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
[8] 黃彰健.孟子性論之研究[J].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55,(26).
[9] 梁濤.“以生言性”的傳統與孟子性善論[J].哲學研究,2007(7).
[10] 王天海.荀子校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1] 路德斌.荀子與儒家哲學[M].濟南:齊魯書社,2010.
基金項目:湖北省教育廳2020年度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項目(思想政治理論課)(20Z042)
作者簡介:譚紹江(1981- ),男,湖北恩施人,湖北經濟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儒家哲學;涂愛榮(1970- ),女,湖北鄂州人,湖北經濟學院教授,法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儒家倫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