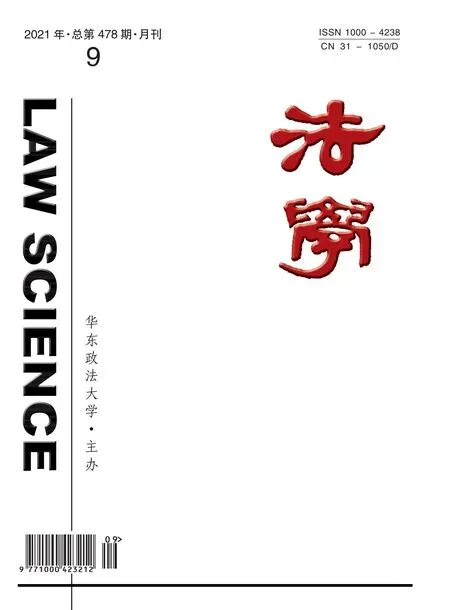論懲罰性賠償與罰金的司法適用關系
●王承堂
一、問題的緣起
基于大陸法系損害賠償法的損失填平原則或得利禁止原則,“懲罰性賠償是侵權法體系最具爭議的方面”。〔1〕[奧]瓦內薩·威爾科克斯:《英國的懲罰性賠償金》,載[奧]赫爾穆特·考茨歐、瓦內薩·威爾科克斯主編:《懲罰性賠償金:普通法與大陸法的視角》,竇海陽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頁。在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日趨融合的時代語境下,我國《民法典》兼收并蓄,以準用條款將懲罰性賠償確認為一種民事責任,并適用于侵犯知識產權(不正當競爭)、破壞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情形,充分體現了“我國民法典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實踐特色和時代特色”。〔2〕王利明:《民法典的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載《光明日報》2020年8月21日,第10版。
事實上,在我國產品責任領域懲罰性賠償的立法與司法實踐已探索經年。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4年10月23日發布)和《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改革試點方案》(最高人民檢察院2015年7月2日發布)的部署,應積極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即根據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決定,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發現污染環境、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在沒有適格主體或者適格主體不提起訴訟的情況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進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就公益訴訟起訴資格的一般原理而言,私人可能才是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適格主體。〔3〕參見陳承堂:《公益訴訟起訴資格研究》,載《當代法學》2015年第2期,第82頁。然而,檢察機關代位私人享有民事公益訴訟起訴資格這一制度創新,為2017年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第55條第2款所明確,并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8〕6號,以下簡稱《檢察公益訴訟解釋》)第20條所拓展。具體而言,在對破壞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犯罪行為提起公訴時,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一并提起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自此,我國檢察機關不僅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而且可以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
在“張勿宜生產、銷售偽劣產品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以下簡稱“張勿宜案”)中,被告張勿宜伙同他人通過淘寶、微信等渠道,以零售方式銷售含有“西布曲明”成分減肥膠囊的價款是21108.8元;以批發方式銷售大量散裝膠囊的價款是139500元,其中含有“西布曲明”成分的減肥膠囊價款是3744元。經審理,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決:(1)被告人張勿宜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25萬元;(2)繳獲的偽劣產品及犯罪工具一并沒收;(3)被告人張勿宜于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支付其所生產、銷售的偽劣減肥保健品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共計248528元;(4)被告人張勿宜于判決生效之日起30日內,就其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在國家級媒體上向社會公眾賠禮道歉。〔4〕參見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2018)滬0109刑初第391號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判決書。
張勿宜之所以被判處25萬元罰金,是因為根據《刑法》第140條,生產者、銷售者在產品中摻雜、摻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兩倍以下罰金。張勿宜之所以被判處248528元懲罰性賠償金,是因為根據《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經營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張勿宜生產并銷售含有“西布曲明”成分減肥膠囊的價款合計24852.8(21108.8+3744)元,檢察機關代位消費者提起總額為248528元的十倍懲罰性賠償金訴訟。在“張勿宜案”中,法院不僅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還判處了數額相當的懲罰性賠償金。
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只是其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邏輯延伸,并無實質變化。唯一的變化可能是,罰金刑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與民事責任(懲罰性賠償)在同一份判決書中呈現,而非分別體現于刑事判決書與民事判決書之中。實際上,在《檢察公益訴訟解釋》施行之前,法院對同一違法行為先后判處罰金與懲罰性賠償金已經引起人們的關切。
在“劉邦亮生產、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民事公益訴訟案”(以下簡稱“劉邦亮案”)中,劉邦亮的代理律師認為,罰金與懲罰性賠償都具有懲罰性質,檢察機關對劉邦亮同一行為再追究其賠償責任的做法,與一事不再罰原則相悖。〔5〕參見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01民初第383號民事判決書。然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則認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3〕28號)第14條的規定,劉邦亮因其犯罪行為可同時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在法院已經追究劉邦亮刑事責任的情況下,再行追究其民事侵權責任并不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而且,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同屬懲罰性債權,前者是私法債權,后者是公法債權。懲罰性賠償金在已被上繳國庫的情況下,性質已經發生轉化,與罰金事實上是類似的。故法院可參照罰款與罰金并處時的處理原則裁判,即劉邦亮被判處的8萬元罰金在120萬元的懲罰性賠償金中抵扣,劉邦亮實際支付112萬元懲罰性賠償金。〔6〕同前注〔5〕。
一事不再罰作為一項法律原則,目前只有《行政處罰法》對其予以具體化。顯然,“劉邦亮案”的裁判依據也在于此。但是,由檢察機關提起的全國首例民事公益訴訟案的指導意義卻在于“罰款或罰金均不屬于民事侵權責任范疇,不能抵銷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侵權損害賠償金額”。〔7〕“江蘇省常州市人民檢察院訴許建惠、許玉仙民事公益訴訟案”(檢例第28號)。可見,能否以罰金抵銷侵權損害賠償金(懲罰性賠償金),取決于法院對懲罰性賠償性質的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同時適用懲罰性賠償與罰金之所以有可能構成一事再罰,個中原因也在于學界對懲罰性賠償性質的界定。對此,陳聰富教授認為,“依據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發展歷史,懲罰性賠償在性質上具有‘準刑事罰’的性質”。〔8〕陳聰富:《侵權歸責原則與損害賠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頁。曼恩(Mann)教授甚至將懲罰性賠償訴訟稱為“私人刑事程序”。〔9〕See Kenneth Mann, Punitive Civil Sanctions: The Middleground Between Criminal and Civil Law, 101 Yale Law Journal 1795,1849 (1992).斯蒂文斯(Stevens)大法官也指出,“刑事制裁(如罰金或監禁)與懲罰性賠償裁決的理由之間幾乎沒有什么區別”。〔10〕See Philip Morris USA v. Williams, 549 U. S. 346, 359 (2007).可見,張勿宜與劉邦亮確實存在遭受一事再罰的可能。當然,在“劉邦亮案”中,判處的8萬元罰金在120萬元的懲罰性賠償金中抵扣,是否意味著已符合《行政處罰法》第29、35條的立法精神?問題可能沒有這么簡單。因為如果懲罰性賠償具有一定的刑事責任屬性,在對當事人作出遠遠高于罰金的巨額懲罰性賠償金裁決時,是否應賦予當事人刑事訴訟法上的程序保障權利?
顯然,懲罰性賠償在上述食品藥品安全(產品責任)領域司法實踐中的相關爭議不會因為《民法典》的頒布而終止。當檢察機關可以在食品藥品安全領域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時,我國產品責任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將本來隱匿于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中的一事不再罰爭議凸顯于同一份判決書中,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民法典》第179條將懲罰性賠償確認為民事責任能否消解懲罰性賠償與罰金并處時的緊張關系。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緣起。鑒于大陸法系國家往往基于損害賠償法的損失填平原則或得利禁止原則否認懲罰性賠償,而在英美法系國家則沒有相應的法理障礙,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領域極其廣泛,故本文將以英美法系的相關理論與案例為鏡鑒,廓清懲罰性賠償與罰金的司法適用關系。
二、懲罰性賠償雙重屬性之演進
一般來說,當遭受社會其他成員的傷害時,人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或體系可供選擇,即刑法(公法)和民法(私法)。刑法和民法有著不同的立法目的與規范構造,它們構成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賴以形塑規則或闡釋規范的分析范式,也構成教科書和學術文獻據以展開知識敘事或理論闡發的文本依據。這兩種分析范式或文本依據在諸如法律規范的內涵界定、司法機關的權力構造、律師職業的專業取向等問題上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原則與專業分工。由此形成的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區別大體可歸納如下(參見表1)。

表1 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區別概要〔11〕同前注〔9〕,Kenneth Mann文,第1812頁。當然,曼恩教授對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的區分也未必全面。例如,違反公共規范也可能產生民事責任;由于無損害后果侵害的存在,民事責任也未必要求對私人利益造成損害。
盡管我國《民法典》第179條將懲罰性賠償確認為民事責任,但是,在以民事公益訴訟的方式主張產品責任領域的懲罰性賠償時,其民事責任屬性并非一目了然,與刑事責任的區分亦非涇渭分明。
第一,就動議方而言,自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訴訟法》第55條創設公益訴訟制度以來,相關立法與司法解釋對公益訴訟起訴資格作出相當嚴格的限制,以至于享有公益訴訟起訴資格的主體僅限于檢察機關、行政機關與法定社會團體,而排斥一般組織與個人。檢察機關由此成為民事公益訴訟最重要的起訴主體,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事公益訴訟“國家化”的趨勢。〔12〕參見陳杭平:《公益訴訟“國家化”的反思》,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8月29日,第5版。這意味著主要由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相應地,也主要由檢察機關主張相關領域的懲罰性賠償。
第二,就定義的不法行為而言,在產品責任領域,《侵權責任法》《食品安全法》《民法典》都對懲罰性賠償提出類似于刑事責任構成中的“明知”違法要件。當然,在產品責任領域主張懲罰性賠償,證明生產者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相對簡單;而證明銷售者在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食品時是“明知”的,確實存在一定難度。法院通常的裁判思路是,銷售者根據《食品安全法》第53條負有進貨査驗的法定義務,如果銷售者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即可認定其主觀狀態是“明知”。〔13〕參見陳承堂:《論“損失”在懲罰性賠償責任構成中的地位》,載《法學》2014年第9期,第144頁。此外,由于法院在計算懲罰性賠償金時不以實際損失或補償性賠償金而僅以商品價款或服務費用為基數,故在作出懲罰性賠償金裁決時,通常不考慮消費者遭受的實際損失。〔14〕參見朱廣新:《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演進與適用》,載《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第110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安全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法釋〔2020〕14號)第10條亦對此作出明確回應,即在消費者主張懲罰性賠償時,經營者不能以未造成消費者人身損害作為抗辯事由。
第三,就目的而言,通常認為刑事責任的目的在于懲罰,民事責任的目的在于補償。然而,在食品安全領域,由于生產或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而承擔懲罰性賠償與行政處罰的責任構成要件完全相同,這意味著該領域懲罰性賠償與行政處罰處理的是“同一范圍、同一危害程度的問題,功能完全重疊”。〔15〕參見趙鵬:《懲罰性賠償的行政法反思》,載《法學研究》2019年第1期,第50頁。就“張勿宜案”而言,生產或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食品的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之間的分界線在于“生產經營的食品貨值金額”(《食品安全法》第123條)或“銷售金額”(《刑法》第140條)的大小。如果生產或銷售金額在五萬元以下,則屬于《食品安全法》第123條“尚不構成犯罪的”情形。循此邏輯,因生產或銷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而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與刑事責任依然屬于同一范圍的問題,功能亦“完全重疊”。而且,這個重疊的功能是懲罰功能。
第四,就救濟方式而言,盡管刑事責任中的罰金刑同樣屬于金錢懲罰方式,且在司法實踐中可能比監禁使用得更為頻繁,但監禁以及與入罪有關的特定污名是實現刑事制裁目的而使用的核心救濟方式。如前所述,懲罰性賠償具有責任歸屬的雙重屬性,〔16〕See Benjamin C. Zipursky, A Theory of Punitive Damages, 84 Texas Law Review 105, 135 (2005).或許這正是有關機關在處理上述“張勿宜案”“劉邦亮案”“江蘇省常州市人民檢察院訴許建惠、許玉仙民事公益訴訟案”中懲罰性賠償與罰金的司法適用關系問題時莫衷一是的原因所在。
懲罰性賠償的雙重屬性表現為一方面具有刑法的、犯罪的和公共的屬性,另一方面則具有民法的、民事的和私人的屬性。“在這種傳統分類的背景下,懲罰性賠償或通過民事程序施加的懲罰似乎是一種反常現象,是一種尋找理由的混合體。”〔17〕See Marc Galanter & David Luban, Poetic Justice: Punitive Damages and Legal Pluralism, 42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393, 1394 (1993).事實上,懲罰性賠償的雙重屬性并非源于上述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中國司法實踐,而是根源于懲罰性賠償特有的域外制度變遷邏輯。
懲罰性賠償制度肇始于英美法系,其起源可以追溯至18世紀中期的英國。〔18〕See Howard A. Denemark, Seeking Greater Fairness When Awarding Multiple Plaintiあs Punitive Damages for a Single Act by a Defendant, 63 Ohio State Law Journal 931, 934 (2002).陪審團當時“有權作出超過所遭受損害的賠償裁決……作為對不法行為人的一種懲罰,以威懾使此后不再發生此類訴訟,并作為陪審團憎惡該行為本身的證明”。〔19〕See Wilkes v. Wood, 98 Eng. Rep. 489, 498-499 (Ct. Com. Pl. 1763).法院也開始將陪審團在加大賠償案件中作出的大額裁決解釋為對原告精神痛苦、尊嚴受損和情感傷害的補償。這些額外的損害賠償被法院稱為懲罰性賠償,大額裁決的目的不僅是為了補償原告的無形損害,而且是為了懲罰被告的不當行為。〔20〕See Note, Exemplary Damages in the Law of Torts, 70 Harvard Law Review 517, 518 (1957).
鑒于英美法系早期侵權法上的實際損害賠償僅僅是對“有形損害”或“實際傷害”作出賠償,而對作為“無形損害”的精神痛苦、尊嚴受損和情感傷害等精神傷害無法進行賠償,懲罰性賠償制度已然成為一種為裁決的賠償數額超過原告遭受的有形損害進行辯護的手段。然而,在整個19世紀,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英國,實際損害賠償的概念都被擴大至包括對無形損害的賠償。懲罰性賠償最初的補償功能已被實際損害賠償功能所取代,如今法院只從報應或威懾的角度討論懲罰性賠償。〔21〕同上注,第520頁。既然實際損害賠償的概念已涵蓋以前無法評估的無形損害,那么懲罰性賠償制度在邏輯上理應消亡。相反,“懲罰性賠償制度被保留下來,并受到了懲罰性理由的滋養”。〔22〕See Martin H. Redish & Andrew L. Mathews, Why Punitive Damages Are Unconstitutional, 53 Emory Law Journal 1, 16-17(2004).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同樣逐漸認識到接受懲罰性賠償制度是“普通法中公認的原則”,〔23〕See Day v. Woodworth, 54 U. S. 362, 371 (13 How. 1851).美國絕大多數的州法院也基于被告的故意、惡意、嚴重的不當行為或不計后果地漠視他人權利與安全的行為而作出懲罰性賠償金裁決。〔24〕See Wayne A. Logan, Civil and Criminal Recidivists: Extraterritoriality in Tort and Crime, 73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1609, 1613 (2005).
實際上,“將懲罰性賠償與懲罰聯系起來,是語言上的意外,也是前現代普通法思維的產物”。〔25〕See Edward L. Rubin, Punitive Damages: Reconceptualizing the Runcible Remedies of Common Law, 1998 Wisconsin Law Review 131, 154.“這種所宣稱的對本質上屬于補償性的賠償責任提供附帶性懲罰效果的目的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突出了現代版本的懲罰性賠償——純粹基于懲罰的目的——與歷史版本的分歧。”〔26〕同前注〔22〕,Martin H. Redish、Andrew L. Mathews文,第14頁。然而,對懲罰性賠償的全面分析至少需要考慮補償、報應和威懾等不同的目的。〔27〕同前注〔20〕,Note文,第520頁。質言之,當懲罰性賠償的現代版本以報應與威懾的雙重目的作為其制度構建的理論基礎時,并不是否定其原初的補償目的。即便精神損害已經成為當今侵權法上獨立的請求權基礎,而不再依賴于懲罰性賠償的補償性功能時,侵權責任法仍然無法對所有的損失予以類型化。例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第1款“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之規定以及《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第2款“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一千元的,為一千元”之規定,就是基于增加的“價款”或“費用”仍無法完全補償消費者所遭受的損失時而對其遭受的機會成本進行補償的考量。
綜上,懲罰性賠償制度經歷了從產生之初的懲罰功能附著于補償功能〔28〕同前注〔22〕,Martin H. Redish、Andrew L. Mathews文,第15頁。到如今補償功能附著于懲罰功能的轉變,標志著該制度的變遷呈現出路徑依賴的特征。當然,這也表明懲罰性賠償的雙重屬性依然存在。為此,學界對懲罰性賠償的責任歸屬進行了不懈的探索。
三、懲罰性賠償責任歸屬的法經濟學解釋
懲罰的理由不外乎報應、威懾、使無能力與改造四種,由于懲罰性賠償不大可能具有使無能力或改造等功能,〔29〕同前注〔17〕,Marc Galanter、David Luban文,第1428頁。而主要服務于“懲罰違法行為,威懾其不再發生”的雙重目的,〔30〕See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517 U. S. 559, 568 (1996).且懲罰主要是通過報應與威懾實現,故下文對懲罰性賠償責任歸屬的法經濟學解釋將圍繞報應與威懾兩方面展開。
(一)報應主體的私人化
侵權責任法主要由“關系性規范”構成,〔31〕See Benjamin C. Zipursky, Civil Recourse, Not Corrective Justice, 91 Georgetown Law Journal 695, 744 (2003).該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關系性規范或行為規范的構建,以及對所規范的不法行為進行類型化。從某種意義上說,侵權責任法是由如何對待他人的法律規范構成,而不僅僅是將損失歸責于私人當事人。由此,侵權責任法中的原告對被告的訴權是一個比矯正正義更為基礎的結構性概念。〔32〕同前注〔16〕,Benjamin C. Zipursky文,第150頁。正如“帕斯格拉芙案”中著名的觀點所闡述的,原告在侵權責任法中只對傷害自己的人享有訴權。〔33〕See Palsgraf v. Long Island R. R. Co., 162 N. E. 99, 100 (N. Y. 1928).也就是說,那種認為侵權責任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賠償遭受損害的原告的觀點,并沒有解釋為什么賠償是由被告而非公共財政或保險機構承擔的原因。〔34〕同前注〔20〕,Note文,第523頁。事實上,我們擁有的是一種將提起侵權之訴的權利配置給被侵權人的制度。從字面來看,強制被告向原告付款是一種對被告進行征收的法律權力,在性質上屬于訴權。〔35〕同前注〔31〕,Benjamin C. Zipursky文,第733-738頁。“這可能是對被告的嚴厲懲罰,就像他不得不向國家支付罰金一樣。”〔36〕同前注〔20〕,Note文,第523頁。
侵權責任法賦予被侵權人訴權的法理是,政治制度禁止私人對他人采取暴力行為,即便是針對他人的不法行為;既然被侵權人不能通過以暴制暴的方式對不法行為人作出回應,那只能授予其民事訴權。有學者認為,民事訴權概念揭示了損害賠償的作用與恢復原狀的理想之間的微妙差別。根據矯正正義理論,恢復原狀是侵權制度旨在實現的終極目標;但是根據民事訴權理論,侵權制度并沒有試圖實現此種實質性的理想,它只是允許被其判定為遭受不法行為侵害的個人向侵權人追償。實際上,恢復原狀概念不是目標而只是一種限制,通常是對原告可能矯正其所受損害程度的限制。人們不能從侵權人處獲得超過使其恢復原狀的賠償,然而任何人都有權獲得那么多。〔37〕同前注〔31〕,Benjamin C. Zipursky文,第738-740頁。
然而,懲罰性賠償“最好被理解為這一正常規則的例外”。〔38〕同前注〔16〕,Benjamin C. Zipursky文,第151頁。對于特定侵權行為,恢復原狀并不是限制,原告有權獲得超過使其恢復原狀的賠償。這種例外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其受到了故意或惡意的不法侵害。在遭受此種侵害之后,原告自己有權從另一個層面進行私力救濟。可見,懲罰性賠償就像刑法上的自衛,是原告的特權,而非國家的懲罰。這可能正是解決懲罰性賠償“雙重屬性”的關鍵所在,齊普斯基(Zipursky)教授認為,“這一問題——雙重屬性——在于如何以一種有助于正確分析懲罰性賠償憲法地位的方式進行闡釋,答案可表述為懲罰性賠償具有主客觀兩個方面的懲罰性”。〔39〕同上注,第153-154頁。具體而言,客觀懲罰性是傳統侵權法學者在將威懾和報應描述為懲罰性賠償的目的時的用語,關注的重點是被告的品行;主觀懲罰性是允許不法行為的受害者享有懲罰的權利。懲罰性賠償的實施反映了這樣一種判斷,即私人有權基于所遭受的不法行為,以超出使其恢復原狀所必需的方式對被告采取行動,補償其所遭受的損害。也就是說,“如果損害賠償裁決代表其他一些東西——如果它確實不同于由國家實施的懲罰,如果它本質上是民事的——那么就不適宜介入刑事訴訟保障措施。問題在于如何解釋‘其他一些東西’可能是什么。主觀懲罰性提供了一個解釋”。〔40〕同上注,第156頁。
當然,也有學者從法律多元主義視角出發,認為懲罰性賠償類似于政府授予的“規制賦權”概念。所謂“規制賦權”,是指授予非政府機構實施其自身規章制度的權力。懲罰性賠償制度并不是規制賦權,但它表現為一種與之緊密聯系的現象,被稱為“實施賦權”。原告及其律師被授權承擔某些重要的執法職能。進行實施賦權與規制賦權的理由在本質上是相同的。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在社會性規制與經濟性規制的每一個領域,政府試圖實施大量規制性法律規范都將顯得捉襟見肘,理應將部分規制權和執法權下放給非政府組織。〔41〕同前注〔17〕,Marc Galanter、David Luban文,第1445頁。“懲罰性賠償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為私人當事人實施法律提供經濟激勵——獎金制度。”〔42〕同上注,第1451頁。事實上,長期以來法院作出的懲罰性賠償裁決,就是將政府公訴職能私人化以實現報應和威懾的典型例子;同樣地,立法機關規定懲罰性賠償制度或多倍損害賠償制度,目的也是為了讓私人訴訟人代位或協助公訴機關。〔43〕See Aaron Xavier Fellmeth,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of A Systemic Social Eあect Theory, 2006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691, 718.
(二)最優威懾的非懲罰性
在懲罰性賠償制度產生伊始,法院就已經賦予其威懾功能。〔44〕See Michael Rustad & Thomas Koenig,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Punitive Damages Awards: Reforming the Tort Reformers,42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269, 1285 (1993).鑒于“侵權責任法的主要目的是使社會福利最大化,那么對懲罰性賠償的恰當衡量就是形成有效威懾所需的金額”。〔45〕See Anthony J. Sebok, Punitive Damages: From Myth to Theory, 92 Iowa Law Review 957, 977 (2007).根據形成有效威懾的最優威懾理論,侵權制度被寄望于強制行為人將潛在有害行為的成本全部內部化。〔46〕See David Rosenberg, Mandatory-Litigation Class Action: The Only Option for Mass Tort Cases, 115 Harvard Law Review 831,853 (2002).波林斯基(Polinsky)和沙維爾(Shavell)教授對懲罰性賠償和最優威懾作了最純粹、最直接的解釋,他們認為懲罰性賠償是過失侵權所使用的漢德公式的拓展;〔47〕See Mitchell Polinsky & Steven Shavell, Punitive Damages: An Economic Analysis, 111 Harvard Law Review 870, 880 (1998).而且,法官和陪審團應在被告事先知道其侵權行為有可能不被發現的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強制施與加害人的全部損害賠償應當與這一損害相當,該項損害增加的倍數與加害人應當承擔責任時裁決其承擔責任的可能性成反比。”〔48〕同上注,第889頁。即便如此,懲罰性賠償可能沒有充分反映應予補償的損失,因為被告仍有可能逃避責任。有學者認為至少在以下三類情形下存在對被告威懾不足的問題。第一類是受害人知道自己已遭受傷害,但是由于可能的補償性賠償數額過低,或者受害人不好訟、不老練、缺乏必要的財力,或者可能遭受了“羞辱性侵權”的傷害,而沒有對侵權人提起訴訟,這類侵權行為源自被告的“公然蓄意的行為”。相比之下,第二類侵權行為屬于“隱蔽行為”,侵權人有機會逃避責任,要么是因為受害人所受的傷害是隱蔽的,或者難以被發現;要么是雖然可以被發現,但隱匿其蹤跡的被告身份不明。第三類侵權行為包含更為“分散性的”社會危害,這些危害既可能來自被告的公開行為,也可能來自其隱蔽行為。〔49〕See Catherine M. Sharkey, Punitive Damages as Societal Damages, 113 Yale Law Journal 347, 366-367 (2003).由此可見,根據波林斯基和沙維爾教授提出的最優威懾模型,在被告的損害很難被發現的領域實施懲罰性賠償是合理的。但是,這一有限的領域沒有包含其他潛在的重要類別,例如存在更為“分散性的”社會危害的情形,或者(相關的)個人遭受羞辱性侵權等情形。
卡拉布雷西(Calabresi)法官在“西羅洛訴紐約市案”的協同意見中首次提出社會補償性賠償的概念。他認為,懲罰性賠償盡管為經濟學家普遍接受并得到許多法院的認可,但其倍增功能的運用充滿了隨意性。這是因為威懾和報應這兩個目的經常被混為一談,在分析上不被視為截然不同的目的。“懲罰性賠償”一詞本身就造成很大的混亂,這一術語傳統上指的是對原告個人所需賠償之外的損害賠償,它不恰當地強調這種超額賠償的報應功能,而減損了其倍增的威懾功能。同樣,它也完全不能解釋在加害人雖然負有責任,但并非故意或肆意違法的情況下不同尋常地適用此種賠償責任的原因。由此,為避免威懾不足而裁決的超額賠償更為恰當的名稱可能是“社會補償性賠償”。相形之下,傳統補償性賠償的目的是為了使受害者個人恢復原狀,而社會補償性賠償的目的則是通過設法確保有害行為的所有成本都由負有責任的行為人承擔從而使社會恢復原狀。〔50〕See Ciraolo v. City of New York, 216 F. 3d 236, 245 (2d Cir. 2000).
隨后,夏基(Sharkey)教授對社會補償性賠償概念進行了系統闡述,并認為社會補償性賠償是一種被忽視的理論。根據該理論,陪審團的補償性賠償裁決將包括兩部分,即旨在補償起訴至法院的受害人的個別賠償,以及旨在補償其他直接遭受損害但沒有起訴至法院的受害人的“社會”賠償。〔51〕同前注〔49〕,Catherine M. Sharkey文,第353-354頁。社會補償性賠償的概念與分散性的侵權損害行為密切相關。這些侵權行為包括以下兩類:(1)被告的單一侵權行為對多個受害人造成損害的;(2)“模式或者慣例”侵權,其由重復的行為構成,對多方當事人造成同樣的影響。〔52〕同前注〔49〕,Catherine M. Sharkey文,第389頁。據此,引發社會補償性賠償的社會危害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即對可識別的個人造成的“特定危害”,以及對社會整體產生影響的“分散危害”。“分散危害”表明懲罰性賠償已不再局限于對遭受損害的特定個人的福利考量,而是面向更為一般的社會福利領域。〔53〕同上注,第392頁。盡管社會補償性賠償概念與侵權法的主要目標相吻合,即對原告之外的同樣遭受不法行為侵害的人進行賠償,但是該概念迥異于現在幾乎不可信的懲罰性賠償歷史概念,即其是對個人補償性賠償的補充。〔54〕同上注,第390頁。由此,社會補償性賠償概念的提出體現了侵權法最優威懾理論的最新發展。
盡管有學者斷言,“關于威懾,民事救濟和刑事救濟在本質上是不可區分的和可互換的”。〔55〕See Mary M. Cheh, Constitutional Limits on Using Civil Remedies to Achieve Criminal Law Objectives: Understanding and Transcending the Criminal-Civil Law Distinction, 42 Hastings Law Journal 1325, 1355 (1991).實際上,民事責任所尋求的威懾與刑事責任所尋求的威懾是不同的。科菲(Coあee)教授認為,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之間的區別在于“定價”和“禁止”。法律制度有時不僅試圖迫使行為人將其活動的社會成本予以內部化,而且還試圖否認其從該活動中獲得的任何好處。在這類案件中,活動的最佳水平被判定為零,因為該活動被認為缺乏任何形式的社會效用(即使它可能為行為人產生效用)。民法通過侵權制度對大多數工業污染者“征稅”,只是希望其降低污染水平,而不是完全停止生產。相比之下,刑法通常希望完全禁止某些活動,例如盜竊、強奸、謀殺和某些形式的環境污染。這種方法(有人稱之為“全面威懾”)認為受害者享有不受被告行為影響的道義權利,不管被告或社會能否從中獲利或得到更大的好處。〔56〕See John C. Coあee, Jr., Paradigms: The Blurring of the Criminal and Civil Law Models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101 Yale Law Journal 1875, 1884 (1992).希爾頓(Hylton)教授同樣指出,刑法文獻中的威懾概念是阻止罪犯從事犯罪行為的“全面威懾”,而侵權法文獻中的威懾概念則是“適當或最優威懾”。〔57〕See Keith N. Hylton, Punitive Damages and the Economic Theory of Penalties, 87 Georgetown Law Journal 421, 421 (1998).
最優威懾并不試圖阻止某種行為,它只是設法確保從事該行為的行為人采取適當的防范措施,并且只在最優程度上從事該行為,所以最優威懾不是一個懲罰性概念。〔58〕See Thomas C. Galligan, Jr., Disaggregating More-Than-Whole Damages in Personal Injury Law: Deterrence and Punishment,71 Tennessee Law Review 117, 129 (2003).然而,全面威懾則是懲罰性概念。當懲罰的目的是以完全威懾的名義實施時,是為了防止不法行為,即為了完全遏制不法行為,〔59〕同前注〔57〕,Keith N. Hylton文,第423頁。無論該行為對違法者(或對社會)帶來的好處是否大于其對他人造成的傷害。在法經濟學的責任模型看來,懲罰性賠償根本就不是真正懲罰性的,“被告的行為可被描述為應受懲罰的,與其自身無關”。〔60〕同前注〔47〕,Mitchell Polinsky、Steven Shavell文,第906頁。也就是說,在確定懲罰性賠償時,焦點應放在侵權人逃避責任的可能性上。
綜上,在英國率先作出懲罰性賠償裁決的兩個世紀里,各國法院從未對懲罰性賠償的責任歸屬這一最為基本的問題予以充分的解答。當學者們試圖通過懲罰性賠償制度所具有的多種目的透視其責任屬性時,報應主體的私人化與最優威懾的非懲罰性最為引人注目,懲罰性賠償的雙重屬性所導致的責任歸屬難題亦因此得以消解。這是因為只有在控方當事人是國家而非個人的情況下,制裁才可能是刑事的;〔61〕同前注〔17〕,Marc Galanter、David Luban文,第1456頁。此外,“將刑事制裁從民事制裁中區分出來的東西,以及所有這些區別……是與之相伴并證明其實施正當性的具有社會譴責性的判決”。刑事制裁是“社會進行道德譴責的正式而莊嚴的聲明”,〔62〕See Henry M. Hart, Jr., The Aims of the Criminal Law, in Abraham S. Goldstein & Joseph Goldstein (eds.), Crime, Law and Society 61, 64-65 (1971).懲罰性賠償追求的是最優威懾而非全面威懾,不會帶來與刑事處罰相伴而來的道德譴責的污名。上述判定懲罰性賠償責任歸屬的方法,則是目前“最有希望的兩種可能性”。〔63〕See Thomas B. Colby, Clearing the Smoke from Philip Morris v. William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Punitive Damages,118 Yale Law Journal 392, 448 (2008).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最優威懾不是一個懲罰性概念,但是“懲罰性賠償確實是一種懲罰……但它是一種與刑法所服務的目的完全不同的懲罰類型”。〔64〕同上注,第436頁。這是因為“報應和威懾在侵權責任法與刑法中有不同的含義,這與法院認為兩個法律部門共享這兩個目的的假設相反”。〔65〕See Mark Geistfeld, Constitutional Tort Reform, 38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 1093, 1099 (2005).
四、懲罰性賠償與罰金的并處模式
(一)一事不再罰障礙之消解
盡管從報應主體的私人化與最優威懾的非懲罰性等法經濟學視角可以證成懲罰性賠償的民事責任屬性,但是其具有的報應或威懾目的似乎為反對懲罰性賠償提供了理由:懲罰性賠償與罰金并處時可能構成一事再罰(雙重危險),即被告在民事和刑事法庭上均可能因同一違法行為而受到“懲罰”,并且民事“懲罰”的實施缺乏刑事程序的保障。〔66〕同前注〔20〕,Note文,第524頁。這使得我們有必要考察懲罰性賠償究竟是否屬于一事不再罰原則所適用的處罰類型,進而消解懲罰性賠償與罰金并處時的法理障礙。
一事不再罰原則起源于古羅馬實行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即對于判決已經生效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定以外,不得再行起訴和處理。這一原則在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制度中都有所繼承。〔67〕參見練育強:《行刑銜接視野下的一事不再罰原則反思》,載《政治與法律》2017年第3期,第126頁。在大陸法系國家,一事不再罰原則規定于憲法或刑事訴訟法之中,體現為對同一犯罪行為不得重復追究公法責任。在英美法系國家,一事不再罰原則體現為禁止雙重危險原則。例如,《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兩次遭受生命或身體的危害”。具體而言,禁止雙重危險原則適用于以下三種情形:宣告無罪后對同一罪行的再次起訴;定罪后對同一罪行的再次起訴;對同一罪行的多重懲罰。〔68〕See U. S. v. Halper, 490 U. S. 435, 440 (1989).此外,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項也作出類似的規定:“任何已依一國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無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懲罰。”盡管我國憲法與刑事訴訟法均未明確規定一事不再罰原則,但是我國已經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意味著我國司法機關理應遵守這一原則。
一事不再罰或禁止雙重危險原則“并不禁止施加‘按一般說法’被描述為懲罰的所有額外制裁”,〔69〕See Hudson v. United States, 522 U. S. 93, 98-99 (1997).其禁止的多重懲罰只是第二次的刑事處罰,且刑事處罰只能在刑事訴訟中實施。〔70〕See U. S. v. Halper, 490 U. S. 435, 441(1989).從而,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間的區別便具有了特殊意義。法律文本上的處罰屬于民事責任還是刑事責任是一個法律建構問題,實務部門通常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其責任屬性進行考察。第一,我們需要確定立法機關在構建懲罰機制時是否明確或含蓄地表示其責任類型。第二,當立法機關表示有意設立民事處罰時,則應進一步考察該民事處罰的懲罰性在目的或效果上是否如此顯著,以至于否定立法機關的原初意圖。對于第一個方面的考察,“只有最明確的證據才能夠在這種基礎上確定法律規范是否合憲”。〔71〕See U. S. v. Ward, 448 U. S. 242, 248-249 (1980).也就是說,當立法機關顯然已經打算構建民事救濟機制時,“只有最明確的證據”才足以推翻該立法意圖,進而將被稱作民事救濟的責任形態轉變為刑事處罰。〔72〕See Hudson v. United States, 522 U. S. 93, 100 (1997).為此,“肯尼迪訴門多薩-馬丁內斯案”(以下簡稱“門多薩-馬丁內斯案”)確立了由七要素構成的判斷標準:(1)制裁是否致殘或限制自由;(2)是否歷來被視為一種懲罰;(3)是否僅因發現故意時才成立;(4)其實施是否會促進報應和威懾的傳統目的;(5)所適用的行為是否已經構成犯罪;(6)所指定的目的能否與替代目的合理地關聯起來;(7)與所指定的替代目的相比,是否顯得過度。該判斷標準的七個要素可能有不同的指向,除非有確鑿的證據表明立法機關關于某法律責任屬性的立法意圖,否則這些要素必須從法律的字面含義加以考察。〔73〕See Kennedy v. Mendoza-Martinez, 372 U. S. 144, 168-169 (1963).法院往往參照上述標準判斷民事救濟能否轉變為刑事處罰,當然,“門多薩-馬丁內斯案”確立的標準“既不是詳盡無遺的,也不是決定性的”。〔74〕See U. S. v. Ward, 448 U. S. 242, 250 (1980).
一項既定的制裁是否是刑事制裁固然是一個制定法問題,但它根本沒有解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即顯然不是刑事制裁的懲罰性賠償,在適用時是否可能如此的背離救濟目標,以致構成一事不再罰原則分析目的的“懲罰”?對照“門多薩-馬丁內斯案”確立的標準,可以發現懲罰性賠償在歷史上一直被視為懲罰性的;它們只有在被裁定為故意的情況下才成立;法院一貫認為它們促進了報應的傳統目的;它們經常被施加于同樣是犯罪的行為;法院也承認它們“與刑事處罰的目的相同”,〔75〕See State Farm Mut. Auto. Ins. Co. v. Campbell, 538 U. S. 408, 417 (2003).而不是服務于其他目的。盡管奧康納(O’Connor)大法官曾在其異議中指出,“根據‘門多薩-馬丁內斯案’確立的標準,很容易得出懲罰性賠償是刑事制裁的結論”,〔76〕See Browning-Ferris Indus. v. Kelco Disposal, Inc., 492 U. S. 257, 298 (1989).鑒于懲罰性賠償制度早于美國憲法而產生的歷史事實,因此“懲罰性賠償一直依賴歷史回避憲法審查,聯邦最高法院從未運用這一標準審查懲罰性賠償”。〔77〕同前注〔63〕,Thomas B. Colby文,第451頁。“懲罰性賠償已被認可很長時間,它們的實施從來都是合憲的。”〔78〕See Pacific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v. Haslip, 499 U. S. 1, 18 (1991).其實,根據《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關于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的規定,金錢處罰明顯是“民事的”,〔79〕See Hudson v. United States, 522 U. S. 93, 103 (1997).該處罰既不會致人傷殘,也不會限制人身自由。
一事不再罰原則禁止的是對同一行為的第二次刑事處罰,既然懲罰性賠償所具有的“懲罰性”不同于刑事責任所具有的懲罰性,且基于其金錢處罰性質,懲罰性賠償不構成一事不再罰意義上的刑事處罰,那么在對同一行為進行刑事制裁的基礎上,并不排斥對其再進行民事制裁。這意味著懲罰性賠償與刑事責任可以共存于同一案件之中。但是在對同一犯罪行為同時或先后判處懲罰性賠償與罰金時,該如何選擇兩者并處的模式,則依然是一個難題。
(二)域外判例與中國實踐
法院在作出裁決時往往會列舉一系列考量因素,以判斷懲罰性賠償金是否過度。例如,法院在“綠色石油公司訴霍恩斯比案”(以下簡稱“綠色石油公司案”)中提出了一個由七要素構成的判斷標準:(1)懲罰性賠償金應當與被告行為可能(或實際)產生的損害具有合理關系;(2)被告行為應受譴責的程度;(3)如果不法行為對于被告而言是有利可圖的,懲罰性賠償金應超過獲利進而使被告遭受損失;(4)被告的財務狀況;(5)所有的訴訟費用;(6)對被告行為施加的刑事制裁可以作為減輕因素;(7)對被告同一行為存在其他民事裁決的,也應作為減輕因素。〔80〕See Green Oil Co. v. Hornsby, 539 So. 2d 218, 223-224 (Ala. 1989).在“北美寶馬公司訴戈爾案”(以下簡稱“戈爾案”)中,法院也提出了一個由三要素構成的判斷標準:(1)被告行為應受譴責的程度,這是懲罰性賠償裁決合理性的最重要因素;(2)懲罰性賠償裁決與原告遭受實際傷害的比例,這是最常被引用的懲罰性賠償金不合理或過度的因素;(3)懲罰性賠償裁決與類似不當行為遭受的行政或刑事處罰的比較。〔81〕See BMW of North America, Inc. v. Gore, 517 U. S. 559, 575-583 (1996).在對“戈爾案”的第三個要素進行考量時,正如奧康納大法官指出的,負責裁定懲罰性賠償金是否過度的上訴法院應就對相關系爭行為實施適當制裁的立法判斷予以“實質性的尊重”。〔82〕See Browning-Ferris Indus. v. Kelco Disposal, Inc., 492 U. S. 257, 301 (1989).在與有關的刑事處罰比較時,法院不僅應考慮可能的金錢制裁,而且應考慮可能的刑期。〔83〕同上注。“可能的公共處罰越高,懲罰性賠償金就應該越高。”〔84〕同前注〔47〕,Mitchell Polinsky、Steven Shavell文,第926頁。
相形之下,在對待刑事責任與懲罰性賠償的司法適用關系上,“綠色石油公司案”第六個判斷要素與“戈爾案”的第三個判斷要素作了截然相反的處理,前者是作為減輕因素,后者則是作為加重因素。有學者認為,由于立法機關依賴于司法機關而司法機關又依賴于立法機關這一循環悖論的存在,法院從公共處罰水平中推斷出的信息很可能是令人誤解的,所以法院不應當將公共處罰作為設定懲罰性賠償的基準,而是應將其作為一種抵扣因素,即在私人訴訟中對系爭行為的任何公共處罰都應折抵根據相關公式計算出的懲罰性賠償金額。〔85〕同上注,第928頁。這個“公式”就是前文描述的波林斯基和沙維爾教授設計的最優威懾模型。由此,“恰當地說,問題并非在于能否提出兩起可能懲罰被告的訴訟,而是在于所施加的總懲罰是否超過報應和威懾之需”。〔86〕同前注〔20〕,Note文,第524頁。
至于懲罰性賠償與罰金的并處模式,“綠色石油公司案”與“戈爾案”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實務進路。“綠色石油公司案”將罰金作為懲罰性賠償的減輕因素,其理論依據在于波林斯基和沙維爾教授所主張的最優威懾模型。同樣地,我國學者也指出,懲罰性賠償具有公法責任的性質,是對刑事責任的補充,故在裁決懲罰性賠償金時不得不考慮該行為是否承擔了公法上的責任。〔87〕參見劉水林:《消費者公益訴訟中的懲罰性賠償問題》,載《法學》2019年第8期,第71頁。“戈爾案”則將罰金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加重因素,其理論依據在于普通法對懲罰性賠償的一貫定義,刑事責任越大,表明其主觀惡性越大,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金也應該越高。
論述至此,可以發現在對懲罰性賠償與罰金司法適用模式的選擇上,美國的“綠色石油公司案”和“戈爾案”與我國的“劉邦亮案”和“張勿宜案”的處理手法幾乎如出一轍。“劉邦亮案”將罰金作為懲罰性賠償的減輕因素,將被判處的8萬元罰金在120萬元的懲罰性賠償金中予以抵扣,最終作出實際支付112萬元懲罰性賠償金的判決;“張勿宜案”則將罰金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加重因素,在判處有期徒刑并處罰金25萬元之后,又作出248528元懲罰性賠償金的判決。
我國《刑法》在原《侵權責任法》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之前就規定了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由此,立法者在確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處罰水平時根本不可能預見到以后對同一犯罪行為另行裁決懲罰性賠償金的可能。也就是說,當時的立法者還沒有意識到罰金有可能是懲罰性賠償的抵扣因素。我國《行政處罰法》第29、35條在對一事不再罰原則予以具體化時顯然作了較為寬泛的處理,沒有像《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所規定的那樣,僅將“罰”限定于對生命或身體的處罰,而是將“罰”擴展至金錢處罰,包括罰款(金)。在并處罰款(金)時,一般按輕罰在重罰中折抵的原則處理,以避免懲罰過度。在懲罰性賠償金被界定為“私法債權”的情況下,〔88〕同前注〔5〕。我國《行政處罰法》所規定的一事不再罰原則理應不予適用。“張勿宜案”的裁判思路與此一致,而“劉邦亮案”則反之。個中原因耐人尋味!
“張勿宜案”與“劉邦亮案”截然不同的處理手法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結果導向的。在“張勿宜案”中,罰金是25萬元,而懲罰性賠償金不足25萬元,如果將罰金折抵懲罰性賠償金,意味著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意義僅僅是要求張勿宜“就其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在國家級媒體上向社會公眾賠禮道歉”,而不能再作出任何懲罰性賠償金的判決。然而,“如果只是賠禮道歉,行為人都已經被追究刑事責任了,賠禮道歉還有多大的意義?”〔89〕胡衛列:《當前公益訴訟檢察工作需要把握的若干重點問題》,載《人民檢察》2021年第2期,第10頁。“劉邦亮案”則不一樣,其中罰金8萬元,懲罰性賠償金120萬元,如果不將罰金折抵一部分的懲罰性賠償金,懲罰性賠償金似乎太高了!當然,在“劉邦亮案”中,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給出的理由是,檢察機關主張追繳的懲罰性賠償金應上繳國庫,懲罰性賠償金的性質由此發生轉化,其與罰金事實上是類似的,故應參照并處罰款(金)時相同的處斷原則。〔90〕同前注〔5〕。若果真如此,“張勿宜案”的處理可能違反了一事不再罰原則。
然而,深層問題依然存在。懲罰性賠償金的性質在檢察機關予以追繳并上繳國庫之后發生轉化,其原因何在?當然,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理由并非“空穴來風”。“如果懲罰性賠償金被分配給國庫,懲罰性賠償金和罰金之間的區別似乎已經完全消失”,〔91〕同前注〔24〕,Wayne A. Logan文,第1610頁。這是因為根據前述報應主體的私人化理論,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的區分基礎在于前者是由遭受損害的個人而非國家來獲得。顯然,造成由國家而非個人獲償懲罰性賠償金是由我國獨特的民事公益訴訟制度設計所致,即目前主要由檢察機關享有民事公益訴訟的起訴資格。本來,根據前述最優威懾的非懲罰性理論,作為社會補償性賠償的懲罰性賠償“可以被理解為集體訴訟機制的理論替代品(或補充)”。〔92〕同前注〔49〕,Catherine M. Sharkey文,第354頁。問題的關鍵在于由誰享有集體訴訟或公益訴訟的起訴資格。“顯然,補償原理只適用于政府本身被欺騙的案件,而不適用于當它采取行動以保護私人公民這一更大的類別;當然,也不能說政府是在為對整個社會造成的危害尋求賠償。”〔93〕同前注〔25〕,Edward L. Rubin文,第137頁。也就是說,當檢察機關代位私人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時,其請求的懲罰性賠償不具有民事補償性,而是具有刑事懲罰性,進而應受到一事不再罰原則的限制。
這一結論的得出本來只需借助于常識。在“劉邦亮案”中,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也作出初步的努力。當檢察機關作為民事公益訴訟起訴人“主張追繳的民事懲罰性賠償金應上繳國庫”時,相關法官已經意識到情況發生了變化,案涉的民事懲罰性賠償金的性質發生轉化,將事實上與罰款、罰金類似,相應地,懲罰性賠償金判決的作出需要受到《行政處罰法》一事不再罰原則的限制。其實,他們本可以更進一步。在由檢察機關提起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既然同一檢察機關在同一訴訟程序中請求同一法院對同一當事人(劉邦亮)處以同一處罰(罰金與事實上類似于罰金的懲罰性賠償),為何不能以簡馭繁,合二為一呢?如果說《刑法》當初規定的罰金已不足以威懾觸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經營者,那么立法機關可以啟動修法程序。
綜上,“張勿宜案”的處理固然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至于“劉邦亮案”,人們可能有不同意見,因為該案的處理至少在形式上并不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但在學者看來,“劉邦亮案”有可能違反《刑法》第5條的罪刑相適應原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94〕同前注〔14〕,朱廣新文,第104頁。本來,決定劉邦亮刑罰輕重的應是其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銷售金額”(《刑法》第140條),后因懲罰性賠償的介入而變得捉摸不定,從而有損法的安定性。仍以“劉邦亮案”為例,劉邦亮生產、銷售100余噸假鹽的“銷售金額”為12萬元,因此被判處8萬元罰金是符合《刑法》第140條規定的,即“銷售金額五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并處或者單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此外,《刑法》第140條還規定了三個法定刑幅度,即“銷售金額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五十萬元的”“銷售金額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二百萬元的”“銷售金額二百萬元以上的”。如果再加上112萬元的懲罰性賠償金,劉邦亮生產、銷售12萬元假鹽的罰金就是120萬元,根據《刑法》第140條規定的“并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的計算規則,對應的“銷售金額”不再是“五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而是立即升格兩個或三個檔次的“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二百萬元的”或“二百萬元以上的”。也就是說,懲罰性賠償的介入造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法定刑的實質性升格。
五、結語
在懲罰性賠償與罰金的司法適用關系上,我國司法實踐與域外判例在兩者并處模式的選擇上雖如出一轍,但法律后果卻有云泥之別。當然,這既不是懲罰性賠償制度自身的問題,也不是《民法典》將懲罰性賠償確認為民事責任所產生的問題,前文對其性質的法經濟學解釋也證實了這一點。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制度與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分別實施亦可相安無事,然而這兩種制度的無意結合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9年10月31日)也只是要求“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實行懲罰性賠償制度”,并沒有提出要將公益訴訟制度尤其是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制度與懲罰性賠償制度嫁接。或許這亦是制度創新的邊界所在。這意味著在公訴機關(檢察機關)對同一行為同時或先后主張罰金與懲罰性賠償時,兩者并處的法理空間似乎并不存在,要么可能違反一事不再罰原則,要么可能與罪刑相適應原則相悖。當然,在私人當事人主張懲罰性賠償時,對同一行為判處的罰金可以作為懲罰性賠償金裁決的加重或減輕因素,只要所裁決的懲罰性賠償金與罰金之和未超過報應與威懾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