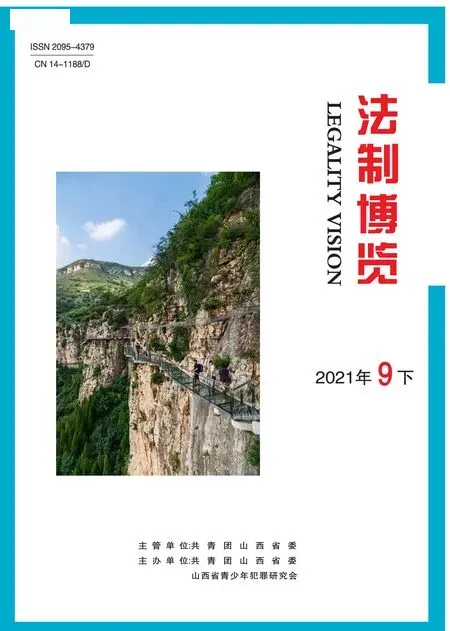痕跡鑒定應(yīng)用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相關(guān)分析
孟 帥
(安徽龍圖司法鑒定中心,安徽 合肥 231600)
現(xiàn)代社會經(jīng)濟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中,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加快,汽車工業(yè)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交通運輸行業(yè)迅速發(fā)展,由此帶來的交通安全問題受到社會越來越廣泛的關(guān)注和重視。但是在相關(guān)數(shù)據(jù)統(tǒng)計中發(fā)現(xiàn),我國每年交通事故量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傷亡人數(shù)逐年增加,造成的直接財產(chǎn)損失巨大,社會影響嚴重,事故分析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在此基礎(chǔ)上,主要通過對一例較典型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件肇事車輛的車體痕跡及輪胎花紋等特征進行檢驗分析,重點結(jié)合人體衣著痕跡比對分析,綜合判斷該起肇事逃逸案件中車輛是否碾壓過人體[1]。
一、案例
(一)檢案摘要
2021年某月某日,汪某駕駛無號牌電動三輪車(以下稱被鑒定車輛)沿道路由南向北行駛至某處時,與路邊行人胡某疑似接觸,后汪某駕車離開現(xiàn)場。交警將嫌疑車輛查獲后,遂委托對被鑒定車輛是否與行人胡某發(fā)生接觸進行鑒定。
(二)胡某事發(fā)時所穿衣著痕跡檢驗
死者胡某外衣左側(cè)前襟見上下方向的輪胎印痕,該印痕寬約10cm,該輪胎印痕中間有間隔距離相等的三條直線狀印痕,每條直線狀印痕寬度相等為 0.2~0.3cm,間隔距離約 0.5cm,在輪胎印痕上部(靠近人體胸部處)見缺損狀孔洞痕跡(見圖1)。

圖1 胡某事發(fā)時所穿外衣花紋印痕照
(三)車輛檢驗
被鑒定車輛車體四周及底板下表面均未見新近形成的異常痕跡。
被鑒定車輛前輪輪胎寬約8cm,其胎冠花紋塊磨損嚴重,胎冠近似為平面狀(見圖2);左、右后輪輪胎寬均約8cm,胎冠有兩條周向貫通且間隔約1.5cm的波浪折線形花紋溝,花紋溝寬約0.5cm(見圖 3)。

圖2 被鑒定車輛前輪胎冠花紋照

圖3 被鑒定車輛左后輪胎冠花紋照
(四)事故現(xiàn)場情況
事故發(fā)生于晴天,道路平直,瀝青路面,事故路段為南北方向,雙向兩車道,道路中間用虛黃線分道,道路兩側(cè)設(shè)置非機動車道、機動車道及非機動車道用實白線分道。事故現(xiàn)場未見被鑒定車輛,死者胡某頭北偏西仰躺在東半幅路面上,其左腳位于道路東側(cè)機動車道與非機動車道的分道線上,在死者胡某身體南側(cè)的路面上遺留有血泊、挫劃印痕及人體拖擦印痕,人體拖擦印痕起點與血泊位置近似平齊并延伸至胡某身體下方,挫劃印痕由南向東北方向延伸并穿過胡某身體下方。
二、分析與結(jié)論
(一)綜合分析
1.被鑒定車輛車體四周及底板下表面均未見新近形成的異常痕跡,說明該車未與其他客體發(fā)生過碰撞。
2.被鑒定車輛右后輪輪胎寬約8cm,胎冠有兩條周向貫通且間隔約1.5cm的波浪折線形花紋溝,花紋溝寬約0.5cm;左后輪輪胎寬度約8cm,胎冠有兩條周向貫通且間隔約1.5cm的波浪折線形花紋溝,花紋溝寬約0.5cm,與死者胡某外衣左側(cè)前襟見上下方向的輪胎印痕,該印痕寬約10cm,該印痕中間有間隔距離相等的三條直線狀印痕,每條直線狀印痕寬度相等為0.2~0.3cm,間隔距離約0.5cm,通過對被鑒定車輛前后輪輪胎胎冠花紋與死者胡某事發(fā)時所穿衣著上的花紋印痕進行比對,分析認為:死者胡某事發(fā)時所穿衣著上的花紋印痕與被鑒定車輛輪胎胎冠花紋不相符。
3.從事故現(xiàn)場情況上可知死者胡某身體南側(cè)的路面上遺留有血泊,路面上人體拖擦印痕由南向北,說明胡某身體被其他客體拖移或推移過,說明胡某身體被其他客體拖移或推移過,而被鑒定車輛底板下表面未見新近形成的異常痕跡,故排除被鑒定車輛將胡某身體推移或拖移一段距離。
(二)結(jié)論
本案中主要通過死者胡某事發(fā)時所穿衣著上的花紋印痕與被鑒定車輛輪胎胎冠花紋進行比對,再結(jié)合事故現(xiàn)場情況和車體痕跡,綜合判斷死者胡某事發(fā)時所穿衣著上的花紋印痕是否為被鑒定車輛輪胎所遺留。分析過程中死者胡某事發(fā)時所穿衣著上的花紋印痕與被鑒定車輛輪胎胎冠花紋不相符,再通過事故現(xiàn)場情況來還原事故過程,并結(jié)合對被鑒定車輛車體痕跡的檢驗,加以印證事故過程,從而排除被鑒定車輛將胡某身體推移或拖移一段距離。認定被鑒定車輛未與死者胡某發(fā)生過接觸,且死者胡某事發(fā)時所穿衣著上的輪胎印痕不是被鑒定車輛輪胎碾壓所遺留。
該起案件綜合運用了多種痕跡檢驗鑒定技術(shù),結(jié)合事故現(xiàn)場情況,對車輛與人體之間的關(guān)系進行分析,從而做出專業(yè)判斷,為案件辦理提供依據(jù)[2]。
三、結(jié)語
在痕跡檢驗的過程中,要求按照相關(guān)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進行實際操作,正確尋找與事故相關(guān)的證據(jù)資料,同時還要認真勘查事故車輛,通過痕跡比對、分析并推斷事故過程,對事故責(zé)任的認定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在上述案例中,人體衣著上的輪胎印痕因造痕體和承痕體具有特殊性,痕跡形成機理較為復(fù)雜,印痕不完整,且邊緣模糊殘缺,反映的穩(wěn)定可靠的細節(jié)特征較少,在檢驗鑒定時存在較大難度。但是通過分析人體衣著上的輪胎印痕,結(jié)合車輛輪胎花紋,遵循造痕體和承痕體之間一一對應(yīng)的關(guān)系,對細節(jié)特征進行比對分析,再通過事故現(xiàn)場情況利用反推思維還原事故過程,更能準(zhǔn)確無誤把握鑒定結(jié)論,保證鑒定的準(zhǔn)確性,從而更好地為案件偵破提供合理、合法、準(zhǔn)確的依據(jù)。這也更加充分地證明,一起交通事故的產(chǎn)生往往是多重因素的組合結(jié)果,事故過程也是極其復(fù)雜和多樣化的,在事故痕跡鑒定分析中,一方面要結(jié)合現(xiàn)場的環(huán)境狀況,包括事發(fā)時的天氣、路況、燈光等因素,另一方面還要對事故現(xiàn)場散落物、輪胎印痕等逐一標(biāo)記,并對相互關(guān)系、形狀形態(tài)予以記錄。現(xiàn)場環(huán)境與痕跡檢驗工作是相輔相成、不可孤立的,否則最終結(jié)果無法為事故責(zé)任認定提供客觀依據(jù),這對于痕跡鑒定人員的專業(yè)水平和職責(zé)技能均具有較高要求[3]。
我國的事故痕跡鑒定工作尚處于初期發(fā)展階段,相關(guān)的法律法規(guī)尚不夠完善,因而難免存在鑒定工作不完善和不嚴謹?shù)牡胤健S绕涫菍τ趶?fù)雜的事故案件,鑒定人員既要充分掌握車輛知識、痕跡知識、法律知識,自身同時又要具備一定的實踐經(jīng)驗,多方結(jié)合之下才能夠保證鑒定結(jié)果的嚴謹和準(zhǔn)確。車輛安全事故無法完全避免,只有通過專業(yè)的技術(shù)分析了解事故成因,才能進一步做好相關(guān)的宣傳教育工作,總結(jié)事故經(jīng)驗、引發(fā)社會關(guān)注,減少事故量,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員傷亡和經(jīng)濟損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