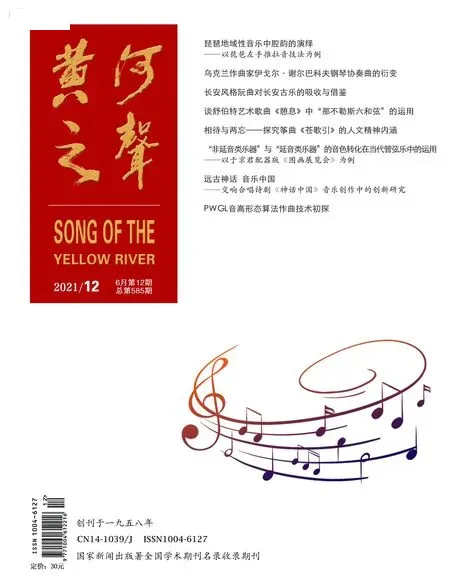相待與兩忘
——探究箏曲《蒼歌引》的人文精神內涵
王 燕
一、現代語境下所鑄造的《蒼歌引》
《蒼歌引》是當代鋼琴青年演奏家、作曲家陳哲于2014年所創作的作品。作曲家時常應邀擔任許多優秀古箏演奏家的音樂會或各大音樂賽事的鋼琴伴奏,經常與國內的著名樂團和著名演奏家委約,創作了大量的優秀的室內樂、鋼琴獨奏、藝術歌曲、器樂獨奏等等各類音樂的創作。作曲家利用自己所學的有關西方音樂作曲的方式和思維,觀察了當代繁忙而又迅速的生活節奏,運用傳統民族音樂元素的同時,又結合了當代人們的音樂審美,運用了復雜的現代作曲手法,又將中國傳統音樂的作曲方式加以改良,使得樂曲演奏技法的難度相比傳統的樂曲大大提升。作曲家充分發揮創新性思維,這也很符合當今的政治背景下所提倡的創新性思維。利用現代創作的技法與中國傳統音樂相融合,以現代人的審美為條件,用獨特的音樂表現手法闡釋傳統的自然觀背后所蘊含的深刻又積極的哲學思想,兼備技術性與可聽性,符合現代人的審美,樂曲所包含的內涵深刻,旋律勾勒出的畫面也十分的震撼,給人以強烈的靈魂上的洗禮,給予靈魂的共鳴。
“穹蒼,蒼天也。春為蒼天,夏為昊天。”這首箏作品的曲名,就選自周秦之際或兩漢之間創作的《爾雅·釋天》,詩集所描述的并不是與樂曲十分的契合,而是以當時生產力落后的現狀,從主觀的角度出發,對自然的一種描述和理解,帶有一定的神話色彩。實際上,樂曲最初定名為《青韶》,寓意著四季當中的春天,處處萌生著生機與活力,“青韶既肇人為日,綺勝出成日做人。”詩中所提到的“人日”,即是女媧造人的日子,這句詩就是出自唐代詩人韋元旦的七言律詩《奉和人日宴大明宮恩賜彩縷人勝應制》,描述的是在春日中清晨,早有人抵達大明宮赴宴,人們準備了上好的菜肴,把酒當歌,摘一枝春梅,吟詩作賦,人們佩戴綺勝,為的就是慶祝女媧造人,人類誕生的這一天。詩中營造了這樣一種富有生機的畫面,在樂曲當中這種生機勃勃的狀態貫穿到了全曲的始終。
通過這兩部詩詞的理解可以得知,《蒼歌引》這首作品充滿人文主義色彩,作曲家將人生分為春、夏、秋、冬四季,寄情的春意也是對青春的回望,在創作時,對筆下用音符描繪的青春進行了一種自我代入,表現出生命的盎然,對生命的敬贊。
二、《蒼歌引》于“相待與兩忘”之境所呈現的情感意象
(一)相待與兩忘
“相待”與“兩忘”是我國文人音樂的美學思想,特別指古琴音樂,體現了中國古代琴者對于樂曲的一種超自然式的理解,同時也是一種演奏樂曲時的超自然的狀態。古代的琴者認為,人與琴本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事物,當藝術家創作出一部音樂作品后,在其演奏的過程中心神沉醉,完全進入在樂曲所塑造的意境,從而達到藝術家主體與被創作的客體渾然一體,物我兼忘的狀態。①這種傳統的美學思想在體現在眾多音樂作品當中,通過演奏者的這種“物我兩忘”的演奏狀態,自然而然會引起聽者的聯覺反應,從而能夠更好的向人們傳遞樂曲所營造的大美之境,傳達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完整的表達作曲家的所思所想,利用音樂中的某種形式,體現出深刻的人文精神內涵。
音樂之中的人文精神,并不能通過聆聽而直接的感受到,由于音樂是一種抽象藝術,它需要結合人的聯覺,從而給予演奏者與聽者極為豐富的情感體驗,產生某種意象,引起靈魂的共鳴。為了更好的傳遞某種意境,樂曲的創作過程就變得十分復雜。在《蒼歌引》這首樂曲之中,帶給聽眾們的色彩是傳統的作曲手法所不能給予的,意象的塑造不僅僅是在于音韻,也在于利用聲音的音響特點來模仿生活中所見所聞,從而用無形的樂音營造或激烈或柔美的氛圍,表達深刻的情感內涵,抒發豁達開朗或悲情斷腸的心境,講述潸然淚下抑或是慷慨激昂的故事,這是樂曲更加豐富的原因所在。
(二)情感意象的呈現
1、傳統與現代碰撞的人工調式
《蒼歌引》這首作品并不是以傳統的固定D大調音階貫穿全曲的,傳統的五聲調式音階,和弦色彩比較單一,已經不能滿足人民大眾所追求的美感。樂曲在倍低音區定弦為“E-F-G-B-C-D”(譜例1),在低音區、中音區、高音區保留了部分D大調音階“D-E-#F-A-B-D”原始形態,整首樂曲屬于非八度周期循環音階,突破了傳統民族音階的界限,擴大了音域,增強了樂曲的厚重感與深沉感,既保留了傳統音樂的“大二度加小三度”的五聲調式,又加入了“小二度加大三度”的音階,增加了樂曲的和聲色彩,豐富了樂曲的趣味性,增強了樂曲的張力,賦予了樂曲創作和發展的可能性。這種定弦的方法既不失民族音樂元素,又凸顯了音樂的現代感與時代氣息,使樂曲所塑造的音樂形象更加鮮明。

譜例1 蒼歌引定弦
2、曲式結構中的創作手法
中國傳統音樂所常用的結構排列規律為“散板——慢板——中板——快板——散板”,作曲家在曲式結構上,利用中國傳統的結構排列規律,進行大膽的創新,將樂曲改為“散板——快板——慢板——急板”。由此可見,作曲家在進行曲式結構的構想上,對于傳統的作曲手法也有著獨特的創作靈感。
樂曲的散板是由一個小三度音程加一個大二度組成的琶音作為動機展開,散板的特點是每個樂匯之間停留的時間相對自由,因此它沒有十分明確的速度,通過人們的聯覺,樂曲在散板1-5小節的琶音,便是給人以深沉寬闊的意象,同時也是作為環境背景出現,表現得是天地寬闊的意象。6-12小節中,大量的搖指以弱音微微的出現,是為了與前面1-5小節的深沉寂靜相呼應,而后漸強是為了營造一種萬物在春雨的召喚下,慢慢復蘇的情景。營造這樣的氛圍并不是簡單的一筆帶過,而是將這一部分分成了兩個小樂句,一步步有層次的描繪春雨的愈演愈烈的情景,在樂句的最后一小節,作曲家對演奏技法又有了新的創作——用力度極強的掃弦來模擬雷鳴陣陣。13-19小節通過運用循環的琶音和左手在箏左由弱漸強的刮奏,塑造自然界的生物破土而生,新芽灌溉著瀝瀝的春雨,不畏懼蒼空中時不時的電閃雷鳴,壯然成長。
整個散板,作曲家描繪了冬末寂靜的大地,萬籟俱寂,一場春雨如夢如幻,如煙似霧,伴隨著陣陣春雷,悄然而至,喚醒了早春三月的晨曦,此為萌動之春。
快板被分成了三個部分,分別以不同的手法,講述不同的情景。
從第20小節起作為快板的第一個部分,從散板到快板沒有傳統的過渡,而是采用直接的方式,運用大量的休止,來增加樂曲的動力性和跳躍性,營造活潑、欣欣向榮的景象。在休止的過程中并不是大量的空白而是將鋼琴伴奏以同樣的形式填補空白,這樣的手法一直持續到第35小節。在第一個部分當中,樂曲所描繪出的意象是花草樹木在一片蔚藍之下,向著東方冉冉升起的旭日,燦爛的茁壯成長。第二個部分的創作手法十分的巧妙,堪稱快板的華彩樂段,大致分為三層,第一層在第一個部分強音結尾結束后,毫無停頓的突弱的進入快速的十六分音符,但由于演奏技巧和旋律安排上的問題,在聽覺上會給人以快速的三連音上的一種效果。緊接著就是第二層的精彩部分,作者運用了“隱伏節拍”的一種創作手法(譜例2),這種手法實際上就是一種節拍中隱藏著另一種節拍,更加突出了強弱上的對比和變化,大大增強了樂曲整體上的張力,在記譜方式上,每小節以完整的一拍和不完整的一拍組合而成,在這種非常規的節奏的沖擊下,豐富了樂曲的色彩,帶給聽眾激情澎湃、耳目一新的氛圍。
在一段流動性的十六分音符的過渡后,樂曲又進入一個更加特殊的結構,這也是是一個難點,有一些演奏者在與鋼琴的配合時需要單獨拿出時間來磨合,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實際上與他的創作手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在這一段落中,作曲家運用了“螺螄結頂”這種特殊的創作技法(譜例3)。所謂“螺螄結頂”,指的是將原有的樂句逐漸緊縮成一個簡潔的頂端,這種作曲手法并不多見,與民族管弦樂曲《金蛇狂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形成最后的頂端之后,樂曲被推向了一個高潮,同時迎來了一個演奏技法上的難點,雙手迅速的在琴弦上來回的交替,音域上的跨度幾乎覆蓋了每個音區,這個樂句的演奏難點就在于要精準快速的將每一個音演奏的干凈利落,突出重音,把握強弱關系,這三層之間聽起來像是沒有關聯的三個層次,但實則層層遞進,節節深入,強弱變化由弱至中強最后將快板的第二部分推向高潮,總的來說,第二部分的結構規律是一段快速的十六分音符接一段特殊的創作技巧,而后再接十六分音符再接特殊結構,最后以十六分音符結尾,這樣的結構有助于推進樂曲整體的高漲的情緒,它所描繪的意象是自然界的萬物仿佛被蒼穹賜予了無與倫比的生命力,它們搖曳著身姿,以驚人的速度瘋狂的生長,即便是伴隨著雷聲陣陣,也不畏風雨,砥礪前行。


譜例3 螺螄結頂
快板進入第三個部分就快要接近快板的尾聲了,作曲家在這一部分的創作技巧上面沒有第二部分所呈現出的那樣華麗,而是用簡單的前八后十六的音符進行簡單的組合,但就是這樣看似簡單的手法,實際上對于演奏者來說,也是一個難點,演奏者除了要準確的把握節奏之外,同時也需要精準的將作曲家特別標注的重音演奏出來,這一部分也可以分成三個小樂句,每一個樂句的力度變化,都有十分明顯的差別,雖然力度變化在其他的段落當中也有出現,但并不作為主要的線條,而在這里,最重要的除了重音的變化的之外就是力度。在這一段落中,呈現的意象仿佛是其他小動物也從沉睡當中慢慢蘇醒,迎著春意,徜徉在茂密的森林中,感受春的美好。在快板的這一部分更像是將自然界中的景物擬人化,像是上天賜予他們人格,世間不在沉寂,萬物一派生機與活力,此為蓬勃之春。
樂曲的高潮達到了頂點,復雜的演奏技巧已經不能夠滿足情緒的頂峰,只能以一段有力的刮奏來中止這樣的情緒,轉換為平靜的小散板,這里的散板起到一個連接慢板的作用,承上啟下,為后面慢板的情緒做了一個鋪墊。
慢板運用了散板的主題材料進行擴充和發展,但在情緒上并不是像散板那樣,寂靜中蘊含著無法估量的能量,而是在歡愉之后的夜晚,微風拂過,空氣中混合著雨后青草味和花香,空中高掛的明月和星空,令人神往,這段樂曲實際上注重的并不是這樣平和悠長的意象,而是以這樣的綿延的意象引發更加深刻的思考,甚至在這一旋律當中,捕捉到了一絲絲感傷,但很快隨著漸漸開闊的旋律轉瞬即逝,樂曲在創作時,融合了中國經典的詩詞和繪畫的創作技巧——留白,這樣的創作手法運用到樂曲當中,更加渲染了唯美的意境,也給人留以無限的遐想。此為深情之春。
樂曲由慢漸漸轉急,又回到了散板當中所運用的“蓄力”,在緩慢微弱的旋律當中逐漸迸發出比以往更加強大的力量,在這段樂曲當中出現了與之前不同八拍子,這更加促進了音樂的律動感和高昂的情緒,也與急板快速的性格相契合,樂曲運用大量的小撮和掃弦這樣的技法,快速、準確的進行演奏,這一段落打破了慢板的和平,生猛飽滿,充滿力量,但又與快板時的力量不同,急板包含的力量是豪邁,是灑脫,強弱對比的變化并沒有快板時的明顯,是由強至更強,將樂曲推至頂點后,與快板的“螺螄結頂”時推向高潮的方式相同——以一個快速的刮奏表示情緒的高漲熱烈,最后猛地煞弦,樂曲戛然而止。樂段當中所描繪的畫面大致上是描繪的是天地間的寬廣,雄鷹展翅,雙鶴朝陽,無拘無束的意象。此為奔騰之春。意象之下,作曲家所向往的即為生命的蓬勃與朝氣,人性的自在與自由。
三、《蒼歌引》的人文精神內涵
(一)生命之贊
《蒼歌引》這首作品通過描寫“春”,表達了對生命的禮贊,感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時也表達了對自然界的崇敬。關于生命,道家對于生命觀的見解有著與本曲有著微妙的聯系。道家將生命產生的根源為“道”,“道”即是萬物之始,萬物之母,在這一觀點的論述上,首先是與作曲家創作時的選材十分默契,道家之于“道”有著神圣和敬畏,而古人之于“天”也有同樣的莊嚴感和神秘感。這也向我們側面的傳達了作曲家所認可的一種人生狀態——對于生命的敬畏。老子的哲學思想更是令作者感到投契,老子認為,“道”既是自然之道,更是生命之道。這其中蘊含了生命無限的創造力。道家所闡述的人生哲學思想的魅力,在于它對于名利和物質的欲望沒有磅礴的野心,對人生的功成得失的淡泊,反而是對純真的人性和人生價值的追求尤為猛烈,這是儒家、法家都沒有的一種人生的態度。在《青韶》時期,正值青春的作曲家就已經對道家這種淡泊名利,追求純真的這種人生觀有著跨越千年的共鳴。
(二)青春之贊
青春之于每一個人,都是人生當中最耀眼的年華,它充滿了無數的可能性.作曲家從《爾雅·釋天》當中取到一個“春”字,詩集當中所提及到的“春為萬物”“春為發生”,意味著春天即是萬物,春天即是開端,作者以“春”為題材,寄情于春,實則也是對年少時意氣風發的形象描述,仿佛充滿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量,就像在曲中作者對于青春的理解,也許沒有已過青春,正值中年的人們理解那樣的更加的透徹,但是恰好是利用年輕時期的審美與時尚的創作手法,借物喻人,近乎完美的呈現出春光大好的青春年華。
(三)自由之贊
青春時期對于自由的渴望是必不可少的,叛逆的青春不希望被人管制,總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想法處理各種事情,實際上這并不是對自由的真正意義上的理解,在作曲家的筆下,自由更多的是有限制的自由,一定的范圍內的自由,一樣可以瘋狂、快樂和驕傲,一樣充滿未知的可能和更多的選擇,哲學家薩特認為,自由是人生來所必然擁有的,但又有法律上的約束。作曲家在樂曲當中呈現出對于青春時期對自由有限度的渴望,就像雄鷹在蒼穹之下展翅翱翔,就像蒲公英那樣隨風飄落,瀟灑自在,坦然灑脫,這也體現了作曲家的純真質樸的個性。
一首《蒼歌引》寫的不僅僅是自然是春意,更是在給聽到的人們傳達這樣一種對人生的崇高態度。從道家的哲學角度上來看這首作品,作曲家正是呈現出一種“天人合一”境界。“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作者在表達積極的人生觀同時,也在對古人的超前智慧,暗暗的贊嘆。作者通過對萬物生機勃勃的狀態描寫,從而烘托出對生命的贊嘆,對自然的敬畏,從而表達了自己對得失名利的淡泊寡欲,對青春的珍惜和正值青春的歡愉以及對自由的羨慕和渴望。
結 語
經典箏曲之所以傳世,是因為富有張力的旋律背后常常包含著跨時代的深刻人文主義精神,具有超脫現實意義的深刻內涵。所有樂曲共同探尋的內核,是“人”這一寬泛的命題,“人”是音樂創作的本體角色,而音樂又服務于人,經典的曲目得以產生,于內讓人了解人性,于外讓社會的生活得以正向發展。箏曲作為傳達精神內涵的媒介,通過新穎的音樂形式,在今天這個契機與危機并存的藝術環境中誕生出眾多優秀的古箏作品,給予了人們一種正確理解世界的一種途徑與方法。■
注釋:
① 語見沈約《郊居賦》云:“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