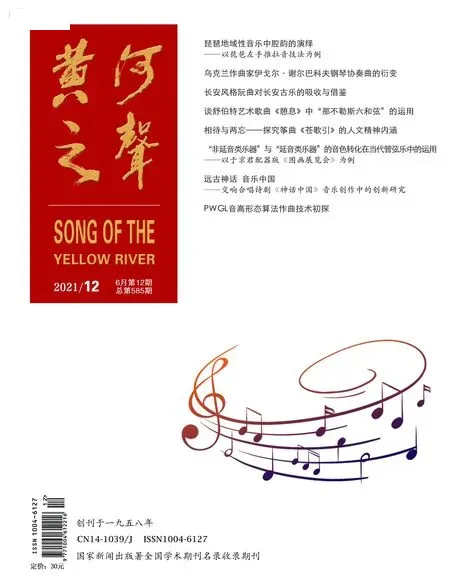《云南紅河縣哈尼族多聲部民歌元素在音樂創作中的實踐與運用》創作成果紀實
——(下·器樂篇)
羅玉蘭/馬千千/楊金凡
一、鋼琴曲《哈巴熱》創作思考
云南,一個美麗神奇的地方。獨特的自然環境,美妙的自然風光,眾多的少數民族,絢麗多彩的民族文化無不展示著它的魅力。自然古樸的少數民族音樂文化讓你驚嘆,會讓你耳目一新、回味無窮。就是在這樣一個充滿好奇的“藝術寶藏”秘境之中,我們才有機會領略云南地區的自然風光和感受豐富的少數民族民間音樂文化,以及最具純樸、原生態的藝術珍品。
(一)靈感的萌發
在云南眾多少數民族當中,哈尼族屬于其中一個較為特別的民族。首先,它是一個跨國境而居的民族。其次,支系繁多。不同的州、縣之間的支系名稱也不相同。例如: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哈尼人互稱覺交、覺圍、雅尼雅等。元陽縣的哈尼人互稱羅比、羅美。最后,它們的音樂文化都是靠哈尼族人民口耳相傳。為此有一部專門集萃哈尼族最著名的各種神話傳說、歌呤體的神話古歌大集《窩果策尼果》,意味“古歌十二調”,記載了整個哈尼族的歷史。
在這樣一個比較特別的文化背景下,哈尼族的音樂文化顯得格外的神秘。中國云南地區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一個以哈尼族、彝族為主要的多民族聚居的邊疆少數民族自治州。多民族聚居體現在紅河地區有10個世居民族。它們分別是哈尼族、彝族、苗族、瑤族、回族、壯族、傣族、拉祜族、布依族、布朗族。正因此,我們的課題采風活動便來到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鋼琴曲《哈巴熱》創作靈感便由此來源。
(二)音樂主題的設計
創作之初,在音樂主題的設計上我首先明確了整個音樂作品的整體風格,即莊重、低沉、歡快、充滿活力。但在真正著手創作之時,我發現音樂作品的音樂語言陳述不是最難的。最難的是將哈尼族歷史脈絡古歌流傳內容與我想要創作的音樂作品相結合。在情感表達方面更能突顯哈尼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向往。怎樣方式地融合,才是最恰當?
在結合了這一系列的問題之后,我最終選取了紅河州哈尼族最有代表性的哈巴曲調作為我整個音樂作品的音樂素材進行創作的一個根本與基礎。在莊嚴場合把酒而歌的為“哈巴”。襯詞一般以“薩衣”起頭,內容多為古代神話、古規古禮和民族歷史。“哈巴”的曲調的旋律與哈尼族語言緊密結合,具有歌唱性與朗誦性的特點。結構較為自由,無統一格律,曲調莊重、低沉,優美動聽。在山野中或談情說愛時唱的民歌叫“阿茨”。曲調活潑抒情。襯詞以“衣嗚”起頭。曲調歌唱的內容主要是生產、生活和愛情。演唱形式分為獨唱、對唱、齊唱等。
為了符合我整個音樂作品的情感內容和色彩基調。我選取了結構較為自由,無統一格律,曲調莊重、低沉,優美動聽的哈巴曲調(即:新的一年來到)為整個音樂主題動機的音樂素材。進行創作。以此來表達哈尼族人民的熱情與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
在作品當中,我選取設計了兩個對比鮮明的音樂主題:一個是通過中速偏慢的音樂情緒來表現,另一個是通過活潑跳躍的小快板來表現。它們都以二拍子為基礎節奏節拍。在主題A當中(第5到12小節),其核心素材就是通過音樂主題動機八度引入長音式保持進入主旋律部分。八度音程的引入是“哈巴調”當中“薩衣”音高距離(見譜例1),是哈尼族音樂音調的特性。在主旋律陳述部分,以#G-#C-#D三個音為一三音組呈下行、上行三連音節奏形態的聲部進行方式。對音樂主題的開篇進提出一個生活的反問與思考(見譜例2)。

譜例1

譜例2
在主題B中,音樂內容包括兩個部分。音樂核心內容同樣是以同名調當中的G-C-D三個骨干音為一個三音組。描繪哈尼族人民歡樂跳舞的場面(見譜例3)。第二個音樂內容是一個新的音樂旋律主題發展部分。音樂內容所要表達的是哈尼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全民一起載歌載舞幸福、和諧、美好的畫面(見譜例4)。

譜例3
(三)創作思考
這個創作思考部分不僅僅是對于我這個音樂作品《哈巴熱》的創作思考。更多的是上升到民族文化、民族音樂怎樣在這個發展變化的萬物之中,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符合時代特點的民族音樂。在繼承民族音樂文化傳統的同時,又可以隨著時代進步產生當下時代審美要求的民族音樂。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在變化中,如何繼承、融合與發展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況且,像云南地區,眾多的少數民族人民共同生活在南亞熱帶季風區、東亞亞熱帶季風區、西藏高原區三大獨特的區域中,并且受到南亞東南亞文化、中原內地文化和藏文化的熏陶。云南民族音樂在這樣的一個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不同的文化接觸與融合之下,自身更具其文化多樣性,并彰顯出它自身獨有的民族特色。怎樣將這些自身獨有的民族特色運用到音樂作品的創作中來,以“中西結合”、“洋為中用”的創作方式,讓云南少數民族音樂文化與西方創作技法更好的結合,是我們文藝工作者一直努力的方向。
在創作鋼琴曲《哈巴熱》的過程中,我對云南哈尼族的音樂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對地域性音樂作品的創作發展有了更多的思考與感悟。有了這次創作經歷,我也更加關注如何將少數民族音樂文化與當代音樂相融合,讓它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同時在賦予其新的活力的基礎上又有一定的創造性。讓它面向世界,博采眾長。在音樂創作中,融合發展問題都需要通過深入地思考、研究、實踐才能實現。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如何實現這些目標,需要我們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努力……
二、長笛與大提琴《田野》創作思考
2018年春,那是筆者初到云南。作為一名在巴山蜀水之地生長的兒女,剛進入云南境內我就被獨特的天然景觀以及氣候所震撼。這里彩云藍天,立刻遍成為我心之所向的一塊圣地。而在今后的求學之際,慢慢地接觸到云南各民族的人文精神及民族文化,我才發現,這里有豐厚的少數民族資源文化。于是,筆者便開始著力研究各民族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哈尼族多聲部民歌是我十分青睞且研究得較為深入的云南少數民族音樂。恰逢《云南紅河縣哈尼族多聲部民歌元素在音樂創作中的實踐與運用》的課題研究有幸在西南音樂研究中心立項,筆者便依托于此次課題,進行了室內樂《田野》的創作。
(一)創作構思
作品《田野》是為長笛與大提琴而作的一部室內樂,作品于2021年4月16日在云南藝術學院安康音樂廳進行首次展演。創作本首作品既是依托于本次課題,也是在經歷采風后筆者內心靈感的一種強烈迸發。在前期研究中接觸到的都是紙質或者音像的資料,從這些資料中獲取的信息實際是較為抽象的。而在2020年秋在去到紅河哈尼族地區進行實地采風后,田野間的壯觀景象才給人內心真正的洗禮,一層層的哈尼梯田景象是肉眼可見的震撼。隨后,與哈尼族多聲部民歌的非遺傳承人們進行了交流,藝術家們演唱一首栽秧山歌《吾處阿茨》,從他們的歌聲中感受他們在田間勞作的栩栩如生景象。于是,我便運用“田野”一詞確定了此次寫作的題目。
“田野”一詞是對哈尼景象的一種描繪,也是筆者內心對哈尼多聲部民歌文化的一種理解。本曲為帶再現的復三部曲式,以哈尼族多聲部民歌《吾處阿茨》為素材進行寫作,作品力求在音樂語言中國化和技巧思維現代化做一些努力和嘗試,力圖創造出民族元素與現代審美相融合的新聽覺感,體現哈尼族人民在田野間歌頌勞動的景象。作品選用長笛和大提琴兩種樂器相結合,模仿在田間勞作的男女,長笛音色高昂清脆,猶如女性嘹亮的歌聲,大提琴音色低沉有力,恰似男性的雄壯歌喉,并運用少量特殊演奏技法模擬場景,使田野間的畫面感增強。
(二)主題音調的設立
《田野》的主題旋律運用五聲羽調式作為基礎,抓住哈尼族多聲部民歌中的特殊變音“#5”,提煉出“1 2 3#5 6”的主題音階為基礎進行寫作,著重突出具有哈尼特點的特性音程“大三度+小二度”的音響(見譜例1)。在全曲的發展上,考慮到現代音樂審美的需求,在此音階上加入了一些外音進行發展變化,達到音響上的新穎性。

譜例1 《田野》第9-12小節
(三)音樂布局
整部作品呈現慢-快-慢的音樂布局,每一個部分都描繪了一個具體的場景。第一部分包括引子和主題部分,引子部分慢且自由地引出本曲的特性音程,長笛聲部運用不方整的起-承-轉-合式的四個樂句,大提琴聲部運用三句式的復調寫法,與長笛聲部形成對比,宛如哈尼男女見到清晨第一縷陽光后,相約去田野間勞作的呢喃景象。在樂曲的一開始,長笛運用泛音與基音相結合的演奏方式,力度緩緩加強,表現出田野間大地蘇醒時的朦朧之感(見譜例2)。

譜例2 《田野》第1-2小節
主題部分便是《吾處阿茨》素材的運用,但在旋律上加入了清角和變宮兩個偏音,在五聲調式的基礎上,向七聲調式轉換,存在調式游離感,使音樂有新的聽覺感受。主題部分由A和A1兩個部分構成,旋律呈波浪式迂回形態,模擬插秧時身體一起一落的狀態。在大提琴聲部,運用了特殊演奏技巧,用雙音滑奏模擬哈尼小伙在休息前的吆喝聲,然后緊接著演奏上用手擊琴板,用以模擬田野間暫時的清凈(見譜例3)。
第二部分為快板樂段,由B-C-B組成,音樂形象活躍,猶如在田野間栽種時的歡樂場面。大提琴聲部做固定音型節奏,長笛聲部運用隱伏二聲部的寫法,將主旋律做級進進行,用以模擬哈尼梯田的梯狀畫面。但長笛的低音持續音聲部依舊遵循大三度+小二度的特性音程特點(見譜例4)。
在和聲的運用上,雖然兩件樂器幾乎都演奏單音線條旋律,但是在縱向上依舊在協和與不協和之前變換色彩,而大提琴在演奏雙音時,則全部運用純四度的疊置,給長笛聲部的單線條營造一種空靈的氛圍(見譜例5)。
第三部分音樂材料是第一部分的縮減再現,依舊是長笛與大提琴對位的寫法,表現哈尼男女在辛勤勞作后進入尾聲的對話場面。在作品的最后,長笛與引子奏法相同,運用泛音的持續音直至音樂結束,大提琴與長笛形成純四度作為低音鋪底,猶若落日余暉后結束了一天的勞作,田野間又回歸于寂靜。
在創作《田野》的過程中,是筆者內心跟哈尼民族精神文化靠得最近的時刻,當然這也是立足于本次課題研究之上的體驗。通過此次課題研究,不僅使筆者在音樂創作上有了新的體驗,更是對哈尼族的民族音樂以及人文精神有深入的了解。在當代中國音樂作品的創作中,新一代的青年作曲家要更多地去挖掘民族音樂的內涵,了解民族魅力,并將其融入現代音樂審美,創作出高質量且有可聽性的作品,為弘揚和發展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而作貢獻。
三、竹笛與鋼琴《阡陌》創作思考
哈尼族多聲部民歌主要流傳于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紅河縣以普春村為中心的數個哈尼族村落中,主要包括歌頌勞動、贊美愛情、描繪山野田園美景等內容。演唱方式分為有器樂伴奏和無器樂伴奏人聲幫腔兩種。這種古老而傳統的音樂形式在被傳承的同時,也在被潛移默化的發展。音樂作品的形成,離不開作曲技法的支撐,而作曲技法的實現又離不開創作理念的引導。所以如何采用新的理念和技法去進行音樂創作,就成為了值得深思的問題。作品依托本次課題《云南紅河縣哈尼族多聲部民歌元素在音樂創作中的實踐與運用》為切入點,特別是在進行實地采風之后,更加有想法將其運用于器樂作品中,將其民族素材與現代作曲技法融合創作。
器樂曲《阡陌》是一首為竹笛與鋼琴而作的樂曲,作品展演時間為2021年4月,作品采用的是帶再現的單三部曲式結構,前有引子,后加尾聲,全曲律動比較平緩悠長,符合竹笛悠揚的音色特點。兩個樂器各自有自己的主題動機和旋律線條,但是又相互呼應。
哈尼族音樂的音階多以五聲音階為主,兼有四聲、六聲、七聲音階及含微升或微降的音階構成的中立音音階,調式會被靈活組合應用。引子部分本來應為七聲音階,但是由于這里我想在模糊調性的同時盡可能的保留哈尼族五聲調式的特點,所以這里省略了“角音”和“羽音”,突出了“變徵”和“變宮”兩個偏音,從七聲調式中提出五聲的假象組合應用,使調式模糊。引子部分使用三度疊加遞增的高疊置和弦,這樣的和聲疊置與聲部進行的方式體現了哈尼族音樂大三度+小三度+小三度+小三度的進行模式,用縱向和橫向相結的形式體現了哈尼族音樂的特點。將其多聲部在橫向進行的同時做一個縱向結合,雙重旋律同時進行,打破了傳統的音響效果,產生新的聽覺特點。
全曲雖然有固定的節拍和節奏,但是在創作的時候,我盡可能的將律動自由化,是樂器更加有靈魂和感情,這樣也符合哈尼族民歌的節奏特點,以四分拍為單位和八分拍為單位的散板也較為普遍,并且哈尼族音樂多用無規則的混合拍子,所以全曲雖然為4/4拍,但是在引子部分就采用散拍子,由鋼琴緩緩走出,營造出一種從遠即近的意境。中間很多部分都采用演奏者自己根據感情的抒發而自由延長節拍。
這樣的安排,極大限度的給予音樂的表現力,因為哈尼族民歌在演唱的時候主體內容長短通常由演唱者自由酌定,靈活性和即興度很高,所以整首曲子的自由度很高,很多地方都由兩演奏者自行控制速度和時長,更加貼近哈尼族民歌的特點。如下圖所示:
旋律發展由級進和跳進相結合。民歌中八度內的跳進十分常見,但是本曲使用了許多超八度跳進,這種八度以上的跳進多見于各類阿哧,其中又常見于曲首的開腔引句。我將這一特點體現在鋼琴聲部中,全曲由單聲部、雙聲部和三聲部旋律線條交替出現形成多聲部效果。
在器樂的演奏形式上,我研究其多種方法來模仿人的特點,因為任何樂器都可以想人一樣表現它的情感。它們是有靈魂的,它們在某種程度更能宣泄一些特定的情感,不同的樂器表達出來的情感截然不同,比如說本首曲子就用了許多演奏形式來變現樂器的情感。
圖①所示,竹笛采用花舌的技巧,吐音是自由做漸快,用這樣的演奏技術來模仿哈尼族音樂中人聲特殊的潤腔方法,類似于喉舌共振法。此處的竹笛像是在于鋼琴敘說著什么,鋼琴則靜靜聆聽;

圖①
圖②竹笛的做自由延長的時候對孔吹氣,制造出風聲,營造一種在田園間空曠的地方,風吹過耳畔的效果,而鋼琴此時要撥動鋼琴琴弦,使琴弦發出泛音,兩者共同營造出一幅山野田間夕陽西下,人身處其中,耳旁傳來風吹動莊稼、草木發出來的種種聲響;

圖②
在哈尼音樂中“咪威威”和“卻瑟赫”兩種都是在情緒上比較悲傷和哀怨的,所以圖③,竹笛用特殊的吹奏技法模仿人的唱腔來表達這類情感,這種演奏形式在《牡丹亭》中被廣泛運用,將虛吹吹孔配合手指敲擊笛身、連續滑音、指柔音等技巧結合運用,從而模仿人聲唱腔,體現出了溫馨場景之中還夾雜著一絲無奈和不舍的哀怨情緒。

圖③
全曲運用了大量不同于以往的演奏技法來體現哈尼族多聲部民歌的特點,用樂器來代替人唱,賦予樂器人的情感和特點。選用竹笛和鋼琴兩種完全不同種類的樂器,一是為了更好的模仿不同的人群的對話,可以體現出不同的特點,二是為了將傳統民族樂器與西洋樂器結合。
通過本次研究,讓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認識到了哈尼族音樂的藝術特點和藝術價值,不僅豐富了自身的音樂積累,還將自己的理解和認識用自己的作品體現出來。在哈尼族音樂元素的基礎之上,運用西方現代的作曲技巧,創造出不一樣的哈尼族音樂。使哈尼族音樂煥發全新的精神與活力,讓更多人聆聽的同時,展現出哈尼族音樂的包容性與生命力。
結 語
綜上,對本項目的三部器樂作品做了解讀,三部作品在創作技法中融入現代作曲思維,具有一定的現代音樂審美。總的來說,通過本次課題的研究,讓團隊各成員在創作少數民族音樂“新”作品的能力上得到提升,同時,筆者也希望本次研究能為后期創作者提供經驗,將新的音樂形式得以推廣,讓更多研究者關注國家非物質文化、關注云南的少數民族文化,了解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音樂,使得云南紅河縣哈尼族民歌文化以及各少數民族音樂得以傳承與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