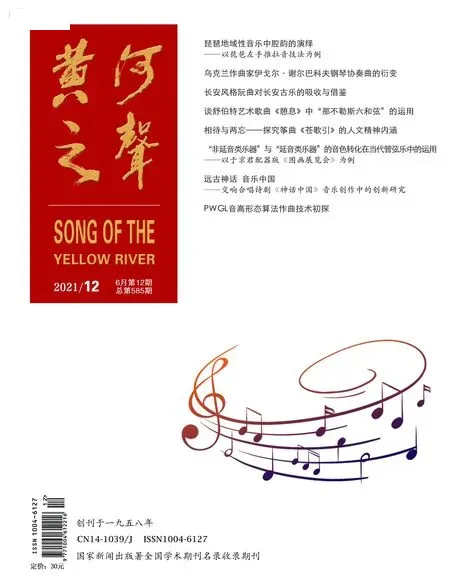滿族生境與民歌生成關系芻議
蔡國慶/徐溪瀅
滿族民歌,是滿族人民歷史、生活勞動的記錄;是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的寫照;也是他們思想感情,意志愿望的表達。①綜觀滿族民歌現有的研究,過分依賴共時態田野資料,不同程度地忽略歷史資料的價值。民歌的蛻變,必然是長期積淀的結果。對一個民族的音樂文化進行綜合性的整體研究,不僅可以了解其音樂的歷史發展脈絡和各種傳統音樂的概況,還能從音樂的現狀中窺見其未來的趨向。生態人類學在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中較好地整合了不同學科的學術資源,立足這一視角,從滿族“生境”切入,對滿族民歌的發展與變遷進行審視,探尋滿族民歌的當代新表達。
一、滿族生境
生境(habiat),意指生物的個體、種群或群落所在的具體地段環境。生境內包含生物所必須的生存條件以及其他的生態因素。在生態學中,特指具體的生物個體或群體生活地段上的生態環境與生物影響下的次生環境(生物本身對環境的影響)。②生態人類學研究中的“民族生境”與生態學所指“生境”有著原則上的區別,被賦予了人文研究特有的語境意義,專門用來指代民族文化與其所處自然生態系統在特定結合部的相互互動關系。也就是說,區別在于,一個民族與其所處自然生態系統并不直接建立關系,而是能動的選擇與自然生態系統建立一個結合部,在結合部中民族文化與所處自然生態系統進行物質與能量交換。一個完整的民族生境包括兩大部分: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換言之,物質與精神的隨機組合,可構成一個民族完整的生境。
滿族的“生境”包含自然生境與社會生境兩部分。從滿族文化變遷中可知,自然生境的變化與社會生境的變化都會引起滿族文化的變遷。就兩種變化而言,不難看出,自然生境較之社會生境的變化速度是相對緩慢的。滿族民歌之所以能夠在歷史長河中穩態發展,未被異民族的文化同化,也得益于滿族民歌的根基——族群所處的自然生境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直到1644年治入關。在此期間,滿族民歌呈現出明顯的變遷,根源在于族群的社會生境發生了很大變化。
(一)自然生境
滿族舊稱滿洲族,亦俗稱旗人。人口為10410585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分布在東北三省和北京、河北、內蒙等地區。因白山黑水(長白山以北、黑龍江中下游、烏蘇里江流域)是其發源之地。故,滿族自然生境應以其所在東北生態系統中所處的生態位為主。生態位引自生態學,埃爾頓將這一概念界定為食物網中的一種“角色”,一種劃定生物之間界限的獨特的攝食對策。楊庭碩認為“不同物種間又不能相互學習和借鑒適應的本領和生存技巧,這就使得每一物種的生存空間都被其自身的生命信息系統控制在一個特定的范圍內。”③將其謂之“生態位”。G·E·哈欽森(1965)指出,把生態位描述成多維歐幾里得超空間的一種體積是有益的。如圖一所示。按照能量學的觀點,生態位是生物對生態系統中有限的能量和可利用營養的分享。資源在規模、顏色、空間和時間分布、溫度、靈活性等方面各不相同,生物賴以生存的那些變量即其生態位。④評價一個民族或族群所處生態位之優劣,可以通過計算用于生計的資源變量總數進行量化分析。生計變量是“豐富度”(所利用的不同資源數)和“均勻性”(每一變量相互依賴的程度)。變量的數目被稱為“生態位幅度”或“生態位寬度”,幅度窄或變量少的為特殊生態位,而幅度寬或變量多的為一般生態位。
滿族祖先發源于“白山黑水”之間,白山黑水地區屬于生計變量幅度較寬的一般性生態位。東北民俗語“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是這一地域自然生態資源富集景況的真實寫照。滿族棲息于資源如此豐厚的生態區位中,也相應的本能選擇了適合本族群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漁獵、游牧、農耕三種生計類型并存的格局。
(二)社會生境
滿族共同體形成伊始,滿族社會開始了由野蠻向文明的急劇過渡,社會生境也呈現出較大的變遷。變遷是指在社會形態或文化模式的某一方面發生的任何有意義的變化,諸如技術、工藝、食物、服飾,以及價值觀、習慣和社會關系方面的變化,也可以用來指整體性的“社會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更替過程”。生物多樣與文化多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滿族社會的文化變遷。大體可以體現以下方面:首先是漢文化,漢族不僅人口眾多,在文化上也是占有領先地位的。所以一般而言,與漢族有所接觸的民族,在文化方面會不自覺的出現一定程度“漢化”傾向,滿族在與漢族學習、效仿、交流的過程中,不斷揚棄那些不適應歷史發展的、落后傳統的過程中,得以崛起、發展、壯大;其次,周邊民族文化對滿族文化的滲透與影響;最后,現代文明對傳統文化的沖擊。
二、生境中的滿族民歌
(一)生物適應中的民歌
漁獵生計是滿族早期社會實行的生活方式。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為主脈聯結而成的密林河谷,是古老的靺鞨、勿吉、挹婁、女真、滿以及赫哲、鄂溫克、鄂倫春等通古斯語族各漁獵民族生息繁衍的地區,也是漁獵文化的搖籃。居住在江河畔的滿族人民大多以捕魚為生,亦被稱之為“漁戶”由當地的衙門統一管轄。在滿語中有許多關于捕魚工具的詞語。按功能分類,小型網具有“渾水內打柳根池細絲粘網”(ulumebutara se surge asu)、“粘網”(又稱手網,eyebuku asu)、“旋網”(sargiyalaku asu)等等;大型網具有“大圍網”(hurhan)、“攔河網”等。在《柳邊紀略》中記載“蓋寧古塔城臨虎兒哈河,冰開后,無貴賤大小,以捕魚為樂。或釣或網,或以叉,或以槍,每出必車載而歸,不須買也。”可以看出滿族人民捕魚的方式多種多樣,捕魚是一種樂趣。滿族人民的捕魚現象不限于文獻記載,在滿族民歌中同樣也體現的淋漓精致。例如:《跑南海》、《拉網調》。
《跑南海》是滿族民歌中僅有的海上作業的號子。1860年以前,海參崴還屬于清朝管轄,這首民歌廣泛地流傳在我國的圖們江口至海參崴一帶。它以歌詠漁民捕撈海產生活而聞名。譜例1中“東南風喂(哎嗨),西北浪來(哎嗨),出南海呀(哎嗨),過山岡啊(哎嗨)”對漁獵活動時的自然環境進行了描述。“大好魚來,大馬哈來,叉海參呀,擰海菜啊。”進一步可以看出,海產品的豐富多產。
《拉網調》流傳于海浪河、牡丹江、鏡泊湖、興凱湖一帶,是滿族拉網時演唱的號子。如譜例2所示:

從譜例2來看,整首歌曲歌詞由滿語構成,“喲哈哈,咿哈哈”是滿語中的襯詞,無實際意義,“哈啦母必”漢譯為“要好好干”。歌詞上表現了滿族人民漁獵時積極向上的狀態,也是其民風淳樸的體現。滿族民歌多以五聲音階和五聲調式的構成,音階使用三度音階、四度音階和五度音階,在勞動號子中,則多以三、四聲的調式音階和音列為常見。《拉網調》骨干音為613,音樂向上以四度、五度進行,向下則以三度進行,節奏規整。音樂旋律走勢由低向高進行,最后回到低音,形成低高低的波浪型音樂進行模式,音樂與江河波浪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月兒圓》是流行于吉林敦化一帶的民歌。歌詞“蛤蜊殼,當水瓢,不怕濕來不怕潮…海螺罐,做水缸,能裝米來能剩糠…燉江魚,用江水,湖鯽⑤熬湯味兒美。”從中可以看出滿族人民對自然生境中的資源利用情況。
在上古時代,滿族先民肅慎人已經會制造“桔矢石磐(弩)”。《竹書紀年》載: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肅慎人以這種獨特的狩獵工具作為友好的信物,通好于中原。《寧古塔紀略》中載,滿人“四季常出臘⑥打圍,有朝出暮歸者,有兩三日而歸者,謂之打小圍”。⑦“四季常出臘”可以看出獵物對滿族人民而言是極其重要甚至是生活必需的。這在滿族民歌中也略有顯露。如《打獵歌》中“哈哈(滿語,漢譯男子)帶著弓和箭,打獵進山谷…拉滿弓來猛射箭,除掉攔路虎…吃虎肉,賣虎骨,全家老少緊忙乎”、還有《大風天》中“刮風我去打老虎,打個老虎做衣衫…抓住黑貂扒了皮,色克(貂皮)正好做耳扇兒。”可以看出滿族人民將狩獵所獲一部分作為生活資料,另一部分則用以買賣交換,并將此作為藉以為生的重要手段之一。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滿族民歌文化在建構之初便體現著對自然生境的一種依賴。正是由于這種依賴,滿族人民常常隨著自然資源的波動而流動遷徙。到了明代后期,女真各部頻繁移動,呈現一種自北向南的整體遷徙趨勢。建州女真定居在今天遼寧省東部的蘇子河畔,自渾河到朝鮮附近的廣大地區;海西女真移居到開原東北、輝發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的大曲折處;野人女真生活在東海部,部分遷入海西,建州舊地。從三大女真遷徙可以看出,野人女真大部分居住在黑龍江下游撒魯溫以北至外興安嶺以南,這里有崇山峻嶺、大海江湖,漁獵資源十分豐富,其所處的自然生境較之遷移前并未有太大變化,故而仍舊以漁獵和畜牧為生計,少部分會進行農耕活動。與野人女真不同,南遷的滿族族群遠離了白山黑水之地,生產方式也由漁獵采集逐步向農耕種植轉變,在此期間,向其他民族學習農耕的先進技術,生產力大幅提高。發展出以定居式農耕為主,畜牧、漁獵為輔的新模式。滿族進入了漁獵-農耕二元文化時代。滿族民歌《慶豐收》便是這一自然生境下的文化體現。如譜例3所示:

“九月里來九重陽,千家萬戶莊稼上場(哲啦啦)”從這里可以看出,基本上大多數滿族人民都以農耕為主。“接姑娘取媳婦,遠親近鄰還有街坊。”自然生境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由遷移式雜居到穩定式定居。滿族人民利用自身地方性知識中所包含的生態智慧與技能,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雙重限制,也從最初對自然生境的依賴中解放了出來。
隨著生產力生產方式的進步,東北地區的各民族人口也在急劇增長。有清一代,不同民族與族群對生境資源的競爭,可謂是逐日劇增。滿族人民對生態系統資源的利用也體現在民歌《抬木號(一)》中。
譜例4中“大伙兒使點兒勁(啊哎嗨喲噢)…訥訥送粘餑餑(喲)…祃祃送煙袋鍋(呀)”曲譜中的“訥訥”、“祃祃”皆是滿語,漢譯為“媽媽”、“爸爸”。從內容上可以看出伐木仍舊是滿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生計方式。不消說,自然生境的改變必然會導致生境內的族群生計方式的調整,進而影響到滿族民歌文化的變遷。
縱觀滿族的社會發展與民歌文化變遷的歷史,不難發現,無論是最初人為改變的自然生境,抑或是族群遷徙伴隨而來自然生境的變化,都是滿族人民為了生存而進行的生物性適應。從漁獵、采集到原始農耕再到精耕細作,滿族人民不斷脫離自然生境的束縛。從生態人類學的視角看,生計方式的調整也是滿族人民面對生境變遷而做出的必要抉擇。
(二)社會適應中的民歌
當滿族文明開始進步、族際文化開始碰撞,滿族各部落族群雜居的形式逐漸發生變化,滿族社會的族群文化發生了較為巨大的變遷,滿族民歌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
由于自然生境的改變,14世紀以后,作為日后滿族主體來源的女真人開始由北向南遷徙。于此同時,中原地區的漢族民眾也開始了北上移民之旅,滿族人民與漢族人民的交往從此日漸頻繁。十七世紀八十年代,東北地區大量荒地被滿族人民開墾成熟,耕地面積大幅增加。漢族流民受東北豐饒的物產和肥沃的土地所吸引“如水歸壑”般爭相出關,越過清政府設立的“柳條邊”。到光緒末年,東北三省的漢族人口,已是滿族人口的10倍有余。滿漢人民交錯雜居,共同參與生產勞動,漢人為東北滿人帶去了漢族文化和生活方式。《吉林外紀》記載“吉林本滿洲故里,蒙古、漢軍錯屯而居。近數十年流民漸多,屯居者已漸習為漢語。”滿漢人民協同奮斗,為東北地區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這一文化變遷也體現在滿族民歌中。如流傳在吉林伊通一帶的《草芽發青》中唱道“草芽子發青燕出關,民人(一般是對漢族人的稱呼)越過柳條邊,跑馬占荒一片片,又開地來又放山。挖的棒槌扛不動,收的糜子滿場院。旗人、民人都好過,有吃有喝太平年。”是對滿漢之交的一次真實寫照。《跑馬占荒山》中“大羅圈,小羅圈,阿瑪跑馬占荒山…種莊田,真有趣,由翻土來又敲棍。”也可以看出滿漢人民在共同勞作中的愉悅心情。
滿族傳統婚姻多以指婚為主,部分地區還存在搶婚的習俗,締結婚姻的形式比較簡單。受漢文化的影響,滿族婚俗日漸與漢族趨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禮”行聘是漢民族由來已久的規定。滿族民歌《要陪送》中“十一月姑娘出了閣,許配女婿真快樂。”而,有的婚配卻是欲益反損的,如民歌《錯配婚姻》中唱道“配婚佬來眼睛瞎,不該把我配給他。叫聲瑪和訥啊,你坑害了小奴家…提起保媒事呀,我到如今還是放不下。東村老馬家,把我提給老葛家。只因為葛家窮啊,俺瑪和訥不讓嫁。”從滿族民歌的內容中不難看出,這種婚禮中有滿族固有的內容,卻也少不了漢文化的“身影”。滿族民間還流傳一些能生動反映旗民通婚的歌謠,如《歌兒亂我心》、《再也不叫尼堪婆》。
毋庸諱言,滿族民歌是滿族生境下的產物。無論是在先民時期,滿族人民依賴自然生境資源生存,還是文化交融之后的漁獵--農耕二元文化時期,依靠自身智慧進行能動適應的生存。滿族民歌都是對所處生境的一種寫實,屬于不同時期生境下的產物。
結 語
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里,滿族人民創造了絢爛多彩的民族文化。滿族民歌作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歷經數千年的傳承、演變、融合與發展,是滿族人民智慧的結晶。從滿族生境與民歌的歷史發展中,總結二者之間的關系,有利于滿族民歌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茁壯生長”。■
注釋:
① 石光偉,劉桂滕,凌瑞蘭香.滿族音樂研究[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172.
② 江帆.滿族生態與民俗文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8.
③ 楊庭碩等.生態人類學導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1.
④ [美]哈迪斯蒂.郭凡,鄒和譯.生態人類學[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93.
⑤ 鏡泊湖的鯽魚.
⑥ 原文中是“臘”,應為“獵”。
⑦ 姜維公,劉立強.中國邊疆研究文庫·初編·東北邊疆卷·第八卷[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