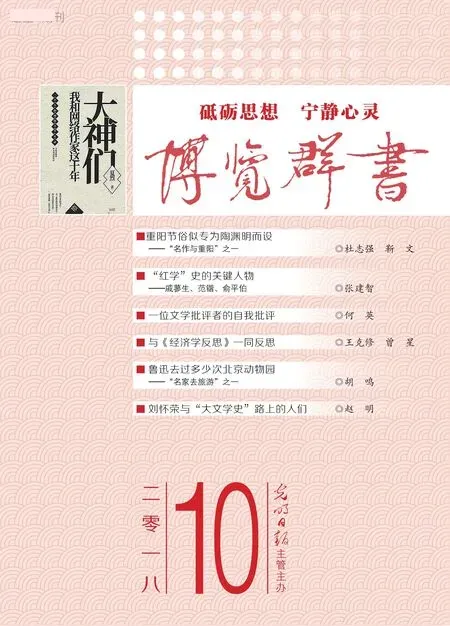曹操用軍旅詩所傳遞的
龍文玲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國(guó)譙(今安徽亳州)人。漢末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xué)家。漢靈帝在位時(shí)期,宦官外戚輪流把持朝政,政治極其腐敗,社會(huì)矛盾日益激化。中平元年(184年),黃巾軍起義,沉重打擊了東漢王朝的統(tǒng)治。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漢靈帝死,17歲的少帝劉辯即位,何太后的哥哥大將軍何進(jìn)謀誅宦官,召董卓率軍入京,導(dǎo)致了長(zhǎng)達(dá)四年的董卓之亂。在討伐董卓過程中,各地軍閥乘機(jī)擴(kuò)大勢(shì)力范圍,混戰(zhàn)連年。為鎮(zhèn)壓黃巾軍起義、討伐董卓、平定割據(jù)勢(shì)力,曹操近四十年戎馬倥傯,直至建安二十五年去世。正如元稹所說:“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曹操的優(yōu)秀詩篇,多為其軍旅途中有感而作。這些詩篇,有的反映了漢末動(dòng)亂給國(guó)家、百姓帶來的災(zāi)難,有的反映了征途艱難和征夫痛苦,有的抒發(fā)了壯心不已的慷慨志向,浸透著深厚的家國(guó)情懷。
《薤露行》《蒿里行》:漢末動(dòng)亂中的憂世悲慨
《薤露行》《蒿里行》是集中反映漢末動(dòng)亂的兩首詩。前一首主要反映董卓亂漢、社稷傾危的史實(shí),后一首則主要反映獻(xiàn)帝初平元年(190)至建安二年(198)九年間的軍閥混戰(zhàn)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zāi)難,被鍾惺、譚元春譽(yù)為“漢末實(shí)錄,真史詩也”(《古詩歸》卷七眉批)。
《薤露行》寫于漢獻(xiàn)帝初平元年。張可禮《三曹年譜》說:“詩寫白虹貫日、董卓焚洛陽、脅天子西遷諸事,均發(fā)生于是年。”(齊魯書社1983年版,P45)在董卓亂漢前后,曹操先是勸阻何進(jìn)招董卓進(jìn)京,未獲采納,后拒絕董卓給他驍騎校尉的任命,逃回陳留募兵討伐董卓。此詩就是他率軍討伐董卓途經(jīng)洛陽有感而作。
全詩分兩層寫作。第一層從開頭至“己亦先受殃”,高度概括了何進(jìn)智小謀強(qiáng)、優(yōu)柔寡斷,致使?jié)h少帝被張讓挾持出走小平津,何進(jìn)本人也被張讓殺害的歷史過程。其中“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強(qiáng)”,對(duì)開啟禍端的何進(jìn)給予了猛烈抨擊;“因狩執(zhí)君王”,將國(guó)家遭難、政局動(dòng)蕩的情景高度凝練出來。其選詞煉字技巧高妙,可見一斑。第二層,從“賊臣持國(guó)柄”到結(jié)尾,概述董卓進(jìn)京把持國(guó)政,廢殺少帝,焚毀洛陽宮室與宗廟,脅迫獻(xiàn)帝西遷,迫使數(shù)百萬百姓號(hào)泣同行的史實(shí),揭露了董卓亂漢的罪行。結(jié)尾“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借《尚書大傳》所載微子作《麥秀之歌》的典故,表達(dá)了對(duì)國(guó)家遭難的哀痛。微子“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曰:‘此父母之國(guó),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dòng)心悲”(《文選》卷六左思《魏都賦》李善注引),曹操路過曾經(jīng)金碧輝煌而今草木深深的洛陽,何嘗也不是“志動(dòng)心悲”呢!詩歌質(zhì)樸古直,高度概括了漢靈帝死后董卓亂漢的前因后果,表達(dá)了對(duì)國(guó)家遭難的極度痛心。
《蒿里行》作于建安二年至建安三年(199)之間。據(jù)張可禮《三曹年譜》考證:詩中“淮南弟稱號(hào)”,指建安二年春袁術(shù)于淮南稱帝事。建安三年“十二月,操殺呂布,明年袁術(shù)卒。疑詩當(dāng)作于上年操征袁術(shù)或是年征呂布欲還時(shí)”(齊魯書社1983年版,P71)。
詩歌分三層,采用先抑后揚(yáng)的筆法進(jìn)行抒寫。第一層為開頭四句:“關(guān)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huì)盟津,乃心在咸陽。”義士,指以袁紹為盟主的討伐董卓的關(guān)東各州郡將領(lǐng)。群兇,指董卓及其部屬。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縣南面。相傳周武王討伐殷紂王,在此會(huì)盟諸侯。乃心,指關(guān)東義士之心。這是用《尚書·康王之誥》“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的典故,說明眾義士忠于王室,其興兵目的在于迎還獻(xiàn)帝重建洛京。咸陽,原為秦朝都城,這里代指王室。“義士”“討”兩個(gè)詞,飽含著曹操最初對(duì)袁紹盟軍的期待和贊許。第二層從“軍合力不齊”到“刻璽于北方”,詩意陡轉(zhuǎn)。“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形象描繪了袁紹盟軍面對(duì)董卓部隊(duì)的怯懦觀望情狀;“勢(shì)利使人爭(zhēng),嗣還自相戕”,深刻揭露了那些所謂“義士”討伐董卓,并不是為了維護(hù)王室、安定天下,而是為了爭(zhēng)奪政治利益,擴(kuò)大勢(shì)力范圍,因此,他們不但未盡力攻打董卓部隊(duì),反而互相殘殺兼并。“淮南弟稱號(hào),刻璽于北方”,是以袁術(shù)在淮南稱帝、袁紹于初平二年刻皇帝印謀立劉虞為證,有力暴露了袁紹、袁術(shù)等軍閥為了各自私利而戰(zhàn)的卑鄙丑惡面目。第三層從“鎧甲生蟣虱”到結(jié)尾,集中描寫了軍閥混戰(zhàn)不休給廣大百姓帶來的深重災(zāi)難。其中“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二句,是對(duì)無辜百姓在軍閥混戰(zhàn)中紛紛死亡、暴尸荒野、千里無人煙的悲慘景象的真實(shí)描寫。結(jié)尾“生民百遺一,念之?dāng)嗳四c”,直接抒發(fā)了詩人對(duì)百姓遭難的痛心。憂國(guó)憂民的情懷,在質(zhì)樸描寫中溢于筆端。
正因目睹了漢末動(dòng)亂中王室孱弱、權(quán)臣誤國(guó)、國(guó)家遭難、軍閥爭(zhēng)利、百姓遭殃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曹操為之哀傷,為之?dāng)嗄c,故而冒天下之大不韙,挾天子以令諸侯,投身到統(tǒng)一北方、安定天下的軍旅生涯中。
《苦寒行》《卻東門西行》:軍旅生涯的悲憫情懷
近四十年的軍旅生涯,不知經(jīng)歷多少艱難困苦,曹操的《苦寒行》《卻東門西行》,就是真實(shí)反映軍旅路途艱辛和征夫戀家思?xì)w的兩首詩。
建安五年(200年),經(jīng)官渡之戰(zhàn),曹操大敗袁紹,奠定了統(tǒng)一北方的基礎(chǔ)。建安十年(205年)十月,袁紹舊部、并州刺史高干聽說曹操將攻打?yàn)趸福e兵反曹,扼守壺關(guān)口。建安十一年(206年)正月,曹操率軍從鄴城出發(fā)親征高干,途經(jīng)太行山,創(chuàng)作了《苦寒行》。
全詩從軍旅路途極端苦寒著筆,分六層抒寫。第一層為開頭四句,極寫太行山路崎嶇之苦。第二句“艱哉何巍巍”,連用兩個(gè)感嘆詞“哉”“何”,凸顯出太行山路艱險(xiǎn)非同尋常。三、四句“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特寫太行山羊腸坂道路極端彎曲狹窄,以至人馬行于其間時(shí)刻有性命之憂。征途的艱苦卓絕,躍然目前。第二層從“樹木何蕭瑟”到“雪落何霏霏”,著力寫太行山的蕭瑟寒冷。北風(fēng)呼嘯,雪落霏霏,足見山間氣候徹骨寒冷,道路泥濘濕滑。中間還有“熊羆對(duì)我蹲,虎豹夾路啼”,更見征途的艱險(xiǎn)可畏。而曹軍不畏艱苦的堅(jiān)韌頑強(qiáng),亦由此展現(xiàn)。第三層從“延頸長(zhǎng)嘆息”到“思欲一東歸”,直抒詩人的內(nèi)心矛盾,此中有面對(duì)極端苦寒的懷鄉(xiāng)思?xì)w,更有對(duì)將士們的關(guān)心體恤,真實(shí)感人。第四層從“水深橋梁絕”到“薄暮無宿棲”,寫出了行軍進(jìn)退兩難的困境:欲繼續(xù)前行,則水深橋斷;欲回師還歸,卻舊路難尋。詩情至此跌落低谷。第五層從“行行日已遠(yuǎn)”到“斧冰持作糜”,寫曹軍面對(duì)苦寒迎難而上、百折不撓:路途艱難,但行行不止;人馬同饑,則鑿冰煮粥。體現(xiàn)了為蕩平叛亂、安定天下不懼苦寒、勇往直前的大無畏精神,詩情由此振起。第六層為最后二句:“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東山》,即《詩經(jīng)·豳風(fēng)·東山》。《毛詩序》認(rèn)為:“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詩人用這一典故收尾,一則如張玉谷所說“援古醒出所以行役之故作收,更得恤下大體”(張玉谷《古詩賞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P176),二則表達(dá)了他期待像周公東征那樣平定叛亂、建功立業(yè)的遠(yuǎn)大抱負(fù)。
正因本著平定叛亂的大無畏精神,曹操及其將士在建安十一年三月大敗高干,一舉平定并州。
《卻東門西行》的創(chuàng)作年代存疑。據(jù)“鴻雁出塞北”“冉冉老將至”兩句推斷,此詩可能作于曹操出征遼東、大敗烏桓之前。詩歌分四層,以結(jié)尾句“故鄉(xiāng)安可忘”為中心,回環(huán)往復(fù)抒寫了征夫懷鄉(xiāng)思?xì)w的強(qiáng)烈愿望。
第一層為開頭六句,以塞北鴻雁起興。“鴻雁出塞北,乃在無人鄉(xiāng)”,開頭二句就以鴻雁來自塞北寂寞無人之地,奠定了全詩清冷凄涼的基調(diào)。鴻雁隨冬春節(jié)令推移,整齊行列,南北遷徙萬里,雖然勞頓,卻終能“春日復(fù)北翔”回歸故里,反興征夫無法返鄉(xiāng),人不如雁。第二層從“田中有轉(zhuǎn)蓬”到“萬歲不相當(dāng)”。“當(dāng)”,指相遇、會(huì)合。這是以脫離本根“隨風(fēng)遠(yuǎn)飄揚(yáng)”、與故根永無會(huì)合之日的蓬草,比喻長(zhǎng)期轉(zhuǎn)戰(zhàn)四方難以回家的征夫。無限傷感,無限同情,全凝在這一反一正的比興中。第三層從“奈何此征夫”到“何時(shí)返故鄉(xiāng)”,直接描寫征夫從軍的狀況:馬不減鞍,鎧甲不離身,冉冉年老,卻不知何時(shí)返鄉(xiāng)。最后一層,從“神龍藏深泉”到結(jié)尾,用神龍藏于深源、猛獸步于高崗、狐貍死前將頭朝向出生丘陵作比興,揭出征夫思鄉(xiāng)的主題。而神龍、猛獸之喻,更于悲涼中見慷慨。
整首詩,善用比興,層層深入,情感真摯,動(dòng)人心弦。真實(shí)傳達(dá)了詩人渴望戰(zhàn)事早日結(jié)束、天下征人得以還鄉(xiāng)安享晚年的美好愿望。
《步出夏門行》:壯心不已的凱旋之音
建安十年,袁紹子袁尚、袁熙投奔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郡烏桓,欲借其兵力東山再起。為徹底消滅袁氏集團(tuán),安定北方,五十三歲的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年)五月率軍北征烏桓,九月大勝而歸。《步出夏門行》就是他凱旋后創(chuàng)作的組詩,真實(shí)表現(xiàn)了戰(zhàn)前的嚴(yán)峻形勢(shì)、凱旋途中的見聞和壯心不已的豪情。
組詩共五章。第一章《艷》,相當(dāng)于組詩序曲。開頭二句“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把大雨滂沱導(dǎo)致出征道路受阻的不利形勢(shì)生動(dòng)形象地描繪出來。面對(duì)惡劣氣候,諸將對(duì)是否繼續(xù)北征態(tài)度不一,詩人亦猶豫惆悵。最后一句“經(jīng)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東海即渤海。表明經(jīng)過深思熟慮之后,詩人仍決意北征,體現(xiàn)了一位統(tǒng)帥周密思索而又果敢無畏的風(fēng)范。
第二章《觀滄海》,將家國(guó)情懷寓于山水之間,書寫了詩人凱旋途中登臨碣石山、遠(yuǎn)眺渤海的所見所思。登臨時(shí)節(jié)雖已秋風(fēng)蕭瑟,但詩人眼中的秋景卻是“樹木叢生,百草豐茂”,一派盎然生機(jī)。被秋風(fēng)吹動(dòng)洪波涌起的大海,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能夠容納無垠宇宙,這是何等的氣魄。這種驚人想象,正是此時(shí)作為勝利者的曹操氣吞山河的情感外化。
第三、四章《冬十月》《河朔寒》,描寫了凱旋歸途之所見。前一章寫孟冬十月北風(fēng)呼嘯,鴻雁南飛,鷙鳥熊羆潛藏,農(nóng)事停歇,商旅活動(dòng)準(zhǔn)備開始;后一章寫黃河以北廣大地區(qū)寒冷異常,土地荒蕪,人民貧困以及由此引發(fā)的社會(huì)治安問題。看似平平,卻體現(xiàn)了詩人對(duì)民生的熱切關(guān)懷。
第五章《龜雖壽》,表現(xiàn)了詩人面對(duì)人壽有盡的客觀現(xiàn)實(shí)依然樂觀進(jìn)取的人生態(tài)度。其中“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四句,取身邊戰(zhàn)馬為比興,言年老伏在馬槽邊的千里馬,仍想要馳騁千里;有為的壯士到了晚年,壯志亦絲毫未減。這是一位久經(jīng)沙場(chǎng)、志氣遠(yuǎn)大的老將內(nèi)心的真實(shí)獨(dú)白。其老當(dāng)益壯的積極進(jìn)取精神,千百年來令人嘆賞。
曹操的這些軍旅詩,反映漢末動(dòng)亂以及軍旅艱難、征夫痛苦者,足以使人認(rèn)識(shí)到戰(zhàn)爭(zhēng)的殘酷、和平生活的珍貴;抒寫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情懷者,更能激發(fā)人積極進(jìn)取、追求遠(yuǎn)大的雄心壯志。這些詩歌,代表了漢末建安時(shí)期詩人們心憂動(dòng)亂、渴望和平、建功立業(yè)的時(shí)代強(qiáng)音,故不僅千百年來為人傳唱,而且凝成了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有機(jī)組成部分,被繼承與弘揚(yáng)。
(作者系廣西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