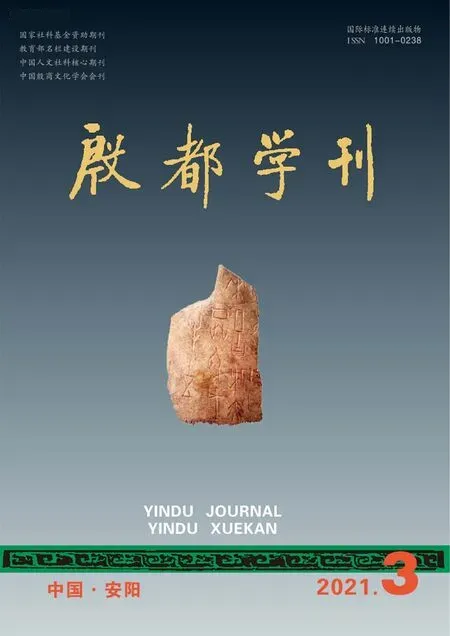亞述帝國王宮出土臟卜報(bào)告中的卜師
劉 健
(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 世界歷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臟卜(Extispicy)(或稱羊卜)是古代兩河流域先民發(fā)明的一種獨(dú)特的占卜方式。通過觀察牲羊內(nèi)臟各器官的大小、顏色、位置、形態(tài)及附著在臟器上的各種征象解釋所占之事。臟卜活動(dòng)長期被宮廷王族壟斷,問卜的問題主要涉及戰(zhàn)爭、宗教儀式、官員任命、重大建設(shè)工程、天象氣候等國家大事,也涉及王宮和王族生活等重要的宮廷事務(wù)。19世紀(jì)中葉,西方探險(xiǎn)者和考古學(xué)者在今伊拉克摩蘇爾附近的亞述都城尼尼微的王宮遺址發(fā)現(xiàn)了10余萬塊刻有文字的泥版,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的臟卜文獻(xiàn)。1893年和1913年,德國學(xué)者J.A. Knudtzon與E·克勞伯(E. Klauber)分別整理發(fā)表了其中的太陽神祭祀文獻(xiàn)和薩爾貢時(shí)期的政治和宗教文獻(xiàn),其中收錄了300篇左右亞述帝國晚期的臟卜文獻(xiàn)。(1)J.A. Knudtzon,Assyrische Gebete an den Sonnengott,Leipzig, 1893; E.Klauber, Politisch-Religi?se Texte aus der Sargonnidenzeit, Leipzig, 1913.1990年,英國學(xué)者伊萬·斯塔爾(Ivan Starr)重新整理、注釋了兩位德國學(xué)者發(fā)表的臟卜文獻(xiàn),并補(bǔ)充了一批未收錄的新發(fā)現(xiàn)或補(bǔ)綴的文獻(xiàn),(2)比如J. Aro,La divination en Mésopotamie ancienne (CRRAI 14, 1966), pp. 109-117所錄臟卜報(bào)告。輯成《致太陽神的問答:亞述帝國薩爾貢時(shí)代的占卜與政治》(QueriestotheSungod.DivinationandPoliticsinSargonidAssyria),該書收錄了帝國晚期埃薩爾哈東(Esarhaddon)(公元前680—前669年在位)和阿舒爾巴尼拔(Ashurbanipal)(公元前668—約前631年在位)兩位國王在位時(shí)期的354篇臟卜文獻(xiàn)。(3)Ivan Starr,Queries to the Sungod. Divination and Politics in Sargonid Assyria,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vol.4, Helsinki: 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 1990.
這批文獻(xiàn)具有很高的歷史文獻(xiàn)價(jià)值。首先,這批文獻(xiàn)記錄了兩位亞述國王下令開展的具體臟卜實(shí)踐活動(dòng),這在其他類型的臟卜文獻(xiàn)中十分少見。(4)Ivan Starr,Queries to the Sungod.Divination and Politics in Sargonid Assyria, pp. lvi-lxv.其次,文獻(xiàn)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兩位國王在位期間開展的軍事行動(dòng)、政策措施、官員任命、宗教活動(dòng)和王室生活等記錄,是復(fù)原亞述帝國晚期歷史的珍貴資料,對認(rèn)識(shí)對外關(guān)系和軍事戰(zhàn)爭史等尤為重要。再次,文獻(xiàn)的格式十分固定,包含起句、時(shí)限、規(guī)定、卜問、結(jié)果記錄以及報(bào)告形成的時(shí)間(包括名年官名、月名和具體日期)、地點(diǎn)、卜師名字等,是十分難得的了解亞述帝國公文格式和官員活動(dòng)的資料來源。最后,文獻(xiàn)所反映的亞述帝國晚期臟卜觀念、技術(shù)的發(fā)展、實(shí)踐活動(dòng)的具體步驟等更是在其他類型的臟卜文獻(xiàn)中少見、甚至未見的信息。
亞述學(xué)界對這部分文獻(xiàn)的研究持續(xù)了一個(gè)多世紀(jì)。主要集中在對文獻(xiàn)的釋讀、解讀和翻譯。對于文獻(xiàn)中涉及的亞述帝國晚期軍事行動(dòng)、對外關(guān)系等內(nèi)容,學(xué)界也進(jìn)行了史料解讀。在有關(guān)臟卜技術(shù)的研究中,伊萬·斯塔爾對文獻(xiàn)的格式、所涉及的臟卜器官和卜辭內(nèi)容進(jìn)行了全面的總結(jié),尤其對文獻(xiàn)中涉及的兆辭進(jìn)行了細(xì)致的分析,且與臟卜工具書類文獻(xiàn)中相關(guān)記錄進(jìn)行比對,進(jìn)而補(bǔ)充、復(fù)原、互證文獻(xiàn)的缺失。(5)Ivan Starr, Queries to the Sungod. Divination and Politics in Sargonid Assyria, pp. xvi-lv.由于文獻(xiàn)涉及內(nèi)容非常豐富,學(xué)界對于這部分文獻(xiàn)的研究以文獻(xiàn)學(xué)分析為主,而對于文獻(xiàn)的史學(xué)價(jià)值、類型學(xué)研究等并不充分,也有一些方面沒有得到重視,比如有關(guān)臟卜禁忌、禱詞內(nèi)涵、時(shí)序規(guī)則、卜師行為等。本文以這批臟卜報(bào)告(6)有學(xué)者認(rèn)為埃薩爾哈東和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的文獻(xiàn)格式有一些差別,不應(yīng)歸為同一類文獻(xiàn)。Ivan Starr將其分別命名為Query和Report。參見p. xiii。筆者認(rèn)為,從文獻(xiàn)類型研究的角度,對兩部分文獻(xiàn)進(jìn)行細(xì)致的類型分析是合理的。但是,從史料研究的角度,利用兩部分文獻(xiàn)復(fù)原亞述帝國晚期政治史和臟卜活動(dòng)的歷史,則不十分必要。兩部分文獻(xiàn)的主體結(jié)構(gòu)大致歷史相同,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的文獻(xiàn)更加注重格式規(guī)制,文獻(xiàn)的起句、卜問時(shí)限、問題、占卜禁忌、問題重復(fù)、兆象記錄和結(jié)論、祝詞、占卜時(shí)間、人員、地點(diǎn)等各種要素十分完備;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的文獻(xiàn)格式則相對簡單一些,大多直接提出問題和時(shí)限,記錄兆象,得出結(jié)論,記錄時(shí)間、人員和地點(diǎn)等。兩部分文獻(xiàn)的功能也比較相似,都是對臟卜實(shí)踐活動(dòng)的記錄和報(bào)告。因此,本文中統(tǒng)稱為“報(bào)告”。為中心,擇取有關(guān)卜師行為的信息,探討亞述帝國晚期卜師集團(tuán)的官員化特征。
臟卜卜師是具有十分悠久傳統(tǒng)的職業(yè),蘇美爾城邦時(shí)代早期(約公元前2900年左右)的職業(yè)詞匯表中已經(jīng)收錄臟卜卜師這個(gè)職業(yè)名稱,阿卡德文寫作bār,蘇美爾文寫作má?-?u-gíd,意思是“將手伸進(jìn)犧牲體內(nèi)的人”。(7)O. R. Gurney, “the Babylonians and the Hittites”, Michael Loewe and Carmen Blacker (eds.) Divination and Oracl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p.147.太陽神沙馬什是臟卜活動(dòng)和卜師的保護(hù)神。文獻(xiàn)記載,沙馬什神是“在牲羊內(nèi)臟上寫下卜辭,并指示占卜結(jié)果的神”。(8)J. Bottéro, Mesopotamia. Writing, Reasoning, and the Gods, (Chicago & London, 1992), p. 133.學(xué)界對于古代兩河流域卜師的活動(dòng)尚無專門的研究。有關(guān)卜師身份、地位、活動(dòng)的研究主要見于文獻(xiàn)和專題研究中。A·奧本海姆(A. Oppenheim)指出卜師是古代兩河流域宗教祭祀體系中的一個(gè)組成部分,他最早提出各類卜師組成“學(xué)士”(ummnu)集團(tuán),發(fā)揮著基本相同的作用。(9)L.Oppenheim, “Divination and Celestial Observation in the Last Assyrian Empire”, Centaurus 14 (1969), pp.97-135; W.G. Lambert, "Enmeduranki and Related Matters",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21 (1967) pp. 127, 31f; U. Jeyes, The Old Babylonian Extispicy, Omen Tex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eiden: Nederlands Historisch-Archaeologisch Instituut te Istanbul, 1989, pp.24-5.帕爾珀拉(Parpola)明確了“學(xué)士集團(tuán)”包含的專業(yè)人士范圍:占星者(up?arru)、臟卜卜師(bār)、巫醫(yī)或魔法師(ā?ipu)、醫(yī)者(as)、吟頌者(kal)、鳥卜卜師(dāgil iūrī)、埃及書吏和驅(qū)魔師(hariibi)、阿拉米書吏(up?arrū Arumu)、智者(hassu)等。(10)Simo Parpola, Letters from Assyrian and Babylonian Scholars,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X, Helsinki: Helsinki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xiv.戴維·布朗(David Brown)對亞述宮廷中占星者的家庭背景進(jìn)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學(xué)士”家族具有職業(yè)世襲特征,或可稱“書香世家”。他們服務(wù)于亞述首都或宗教中心。總體上,臟卜卜師在宮廷中的作用大于神廟。(11)David Brown, Mesopotamian Planetary Astronomy-Astrology, Cuneiform Monographs 18, Groningen: STYX Publications, 2000.上述研究將“學(xué)士”集團(tuán)作為一個(gè)整體看待,認(rèn)為卜師集團(tuán)歸屬于宗教祭祀體系或“知識(shí)分子”體系。盡管學(xué)者們承認(rèn)卜師發(fā)揮著為政治服務(wù)的功能,但是并未深究他們是否具有官員身份,這將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
一、亞述宮廷中的臟卜卜師
在伊萬·斯塔爾整理的354篇臟卜報(bào)告文獻(xiàn)中,有69篇比較完整地保留了卜師的名字,這是兩河流域歷史上留存的最為豐富的關(guān)于臟卜卜師姓名的資料,也是迄今所知唯一保留了卜師集團(tuán)信息的資料。卜師的署名大多在報(bào)告結(jié)尾處,(12)SAA IV 137中納布烏沙里姆的名字出現(xiàn)在報(bào)告的中間。鑒于納布烏沙里姆這個(gè)名字在其他文獻(xiàn)中能夠明確擁有卜師身份,故可認(rèn)定此處納布烏沙里姆應(yīng)為卜師。署名之后,一般署報(bào)告成文的時(shí)間(一般包含名年官名、月名和日期),偶爾會(huì)記錄臟卜活動(dòng)地點(diǎn)。69篇報(bào)告中,屬于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的文獻(xiàn)有40篇,可辨別出至少23個(gè)卜師的名字;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29篇文獻(xiàn)中至少可辨別出15個(gè)卜師的名字。茲列于下:

表1 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留存的卜師名單

表2 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留存的卜師名單
這些名字中,有3個(gè)出現(xiàn)在兩個(gè)國王的報(bào)告中,即巴尼亞(Baniya)、貝爾烏沙里姆(Bel-u?allim)、馬杜克舒瑪烏蘇爾(Marduk-?umu-u?ur)。鑒于這批文獻(xiàn)覆蓋的時(shí)間跨度不大,卜師集團(tuán)中存在同名、同任現(xiàn)象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極有可能這是三名資深卜師,任職于前后兩位國王。
馬杜克舒瑪烏蘇爾顯然是三位中最為重要的一位。(13)巴尼亞的名字僅出現(xiàn)兩次,一次在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SAA VI 157),一次在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SAA IV 285),且均在卜師團(tuán)隊(duì)中位列末席。貝爾烏沙里姆的名字出現(xiàn)在9篇文獻(xiàn)中(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7篇,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2篇)。在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他一般與舒瑪共同工作,署名次位,有可能擔(dān)任舒瑪?shù)闹帧T诎⑹鏍柊湍岚螘r(shí)期,他在兩篇文獻(xiàn)中均排名首位,顯示他可能存在職級(jí)晉升的情況。他出現(xiàn)在兩位國王的27篇臟卜報(bào)告中。種種證據(jù)顯示,馬杜克舒瑪烏蘇爾極有可能是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執(zhí)掌亞述王宮臟卜事務(wù)的主要官員。他是 “大卜師”(Lú.SAG EN- UMU),(14)三篇不同類型的文獻(xiàn)中提及馬杜克舒姆烏蘇爾的“大卜師”身份,參見SAA IV 323,SAA VI 339 r. 7,SAA VII 7 r. ii 7。是少數(shù)能夠獨(dú)立主持臟卜儀式的卜師。(15)SAA IV 124, 148, 306, 318, 323。此外,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能夠獨(dú)立主持臟卜儀式的卜師僅有納布烏沙里姆 (SAA IV 137)、納迪努 (SAA IV 162);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獨(dú)立主持儀式的還有4位,丹納亞 (SAA IV 286, 291, 300, 303)、內(nèi)爾加爾沙如烏蘇爾(Nergal-?arru-u?ur)(SAA IV 305)、尼努阿亞(SAA IV 326)、阿舒爾達(dá)因沙如(SAA IV 337)。在多數(shù)情況下,他帶領(lǐng)一個(gè)由多人組成的團(tuán)隊(duì)完成臟卜工作。
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丹納亞(Dannaya)是最為活躍的卜師,他的名字出現(xiàn)在15篇臟卜報(bào)告中。如果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文獻(xiàn)(SAA IV 57)中殘缺的Dan…名確實(shí)是丹納亞,則他也是兩朝官員。SAA IV 281顯示,這位卜師有可能是太監(jiān)(Lú.SAG),這為研究亞述宮廷中卜師的來源提供了一個(gè)新的思路。(16)臟卜卜師太監(jiān)的記錄也見于SAA IV 337。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的報(bào)告中大多注明卜師的分工情況:區(qū)分為執(zhí)行者(Lú.HAl)和記錄者(EN- UMU),大多由不同卜師擔(dān)任。丹納亞在不同文獻(xiàn)中承擔(dān)了兩種職責(zé),顯示他應(yīng)該是一位經(jīng)驗(yàn)豐富的卜師。
除馬杜克舒瑪烏蘇爾和丹納亞外,還有幾位卜師比較活躍,出現(xiàn)在多次臟卜活動(dòng)中,比如阿卡拉亞(Aqaraya)、貝爾烏沙里姆、納布烏沙里姆(Nab-u?allim)、納西如(Na?iru)、納迪努(Nadinu)、舒瑪(um)、塔伯尼(Tabn)等。
從這些卜師的人名特點(diǎn)判斷,巴比倫人占據(jù)多數(shù),比如馬杜克舒瑪烏蘇爾、貝爾烏沙里姆、納布烏沙里姆等包含巴比倫主要神祇元素的人名都是典型的巴比倫人名。(17)SAA IV 162中,卜師納布沙里姆(Nab-?allim)和阿卡拉亞的名字用阿拉米文書寫,是一個(gè)特例。據(jù)此,有學(xué)者認(rèn)為納布沙里姆應(yīng)是納布烏沙里姆的衍名。Ivan Starr, Queries to the Sungod. Divination and Politics in Sargonid Assyria,p. 174 n.7.亞述首都卡爾胡的納布神廟和尼尼微王宮檔案館所藏文獻(xiàn)也證明,埃薩爾哈東引進(jìn)一大批巴比倫學(xué)者,他們受雇于亞述王宮,教授古老知識(shí),同時(shí)也刻寫泥版文獻(xiàn),保存古老知識(shí)。(18)SAA VIII 499;B.N. Porter, Images, Power, Politics. Figurative Aspects of Esarhaddon's Babylonian Policy. (Philadelphia, 1993), p. 3 n. 3.新巴比倫語是多數(shù)卜師擅長使用的語言,354篇報(bào)告中,用新巴比倫語楔形文字書寫的報(bào)告有223篇,用新亞述語書寫的報(bào)告有123篇,有5篇文獻(xiàn)過于殘破不能斷定使用了哪種方言。如何決定選用哪種語言書寫報(bào)告尚不明確,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選擇原則與人名顯示的是巴比倫人或亞述人無關(guān),“巴比倫人”馬杜克舒瑪烏蘇爾既使用新巴比倫語,也使用新亞述語。(19)比如在涉及帝國西北邊境問題的一組報(bào)告中,馬杜克舒馬烏蘇爾的名字保存在三篇文獻(xiàn)中,SAA IV 18, 23和35,其中前兩篇文獻(xiàn)用亞述方言寫成,第三篇用巴比倫方言書寫。兩種方言必然是同時(shí)使用的,SAA IV 96和99所占之事相同,但分別用巴比倫語和亞述語方言書寫,SAA IV 132和134也是相同的情形。
二、卜師的工作狀況
歷史上,卜師名字只被零星記載。古代兩河流域歷史上最早的卜師名字可以追溯到半人半神的上古王恩美努蘭吉(Emenuranki)。據(jù)載,太陽神沙馬什和雷神阿達(dá)德賜予他油卜和臟卜技藝。(20)Cf. W.G. Lambert, “Enmeduranki and Related Matters”,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21 (1967) pp. 127.有文獻(xiàn)記載的古代兩河流域歷史上有三位國王曾經(jīng)擔(dān)任臟卜卜師,包括烏爾第三王朝第二王舒爾吉(Shulgi)(約公元前2094—前2047年),(21)I. Starr, The Ritual of the Diviners, BM (tablets in the collection of British Museum) 12 (Malibu, 1983), p. 6.亞述帝國國王阿舒爾巴尼拔和新巴比倫王納布尼德(Nabonidus)(公元前555—前539年在位)。但是,國王擔(dān)任卜師并非常例,這三位國王均在文獻(xiàn)中明確表明因聰穎和興趣而習(xí)得這種專門技能。
除此之外,有明確姓名留存的臟卜卜師數(shù)量很少。古亞述王國時(shí)期的馬瑞信件中提到王室大卜師阿斯庫杜姆(Asqudum),國王沙姆什阿達(dá)德(ama?-Adad)(約公元前1813—前1781年在位)派他前往馬瑞輔助王子雅斯馬赫阿杜。另外一個(gè)城市遺址拉爾薩發(fā)現(xiàn)了一枚同一時(shí)期印鑒,印主為卜師南納曼祖姆(Nanna-mansum)。(22)E 4.2.8.2005,拉爾薩泥版上的印痕寫到:“南納曼祖姆,卜者(M.U.GD.GD),南納神[和]努爾阿達(dá)德(Nur-Adad)的仆人”。中亞述王提格拉特皮萊賽爾一世(Tiglath-pileser I)(公元前1115—前1077年在位)文獻(xiàn)記載臟卜卜師沙馬什澤拉伊迪納(ama?‐zera‐iddina)至少編纂了4部臟卜手冊。(23)Nils P. Heeβel, “Assyrian Scholarship and Scribal Culture in Ashur”, Eckart Frahm ed. A Companion for Assyria,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7, pp. 368-377.這些零星的記載很難幫助我們復(fù)原古代兩河流域地區(qū)臟卜卜師的基本情況。法國學(xué)者J·努蓋霍爾(J. Nougayrol)曾經(jīng)明確指出卜師的社會(huì)影響和工作情況尚無從評(píng)價(jià)。(24)J. Nougayrol, ”Trente ans de recherches sur la divination babylonienne (1935-1965)”, J.Nougayrol ed. La Divination en Mésopotamie ancienne et dans les région voisines, XIVe RAI (Paris 1966).
但是,亞述宮廷發(fā)現(xiàn)的這部分臟卜報(bào)告最后一段內(nèi)容包含了有關(guān)臟卜卜師工作狀況的眾多信息,比如卜師的工作方式、職能分工、職業(yè)升遷、工作時(shí)間和地點(diǎn)等,恰好能夠彌補(bǔ)這方面材料的缺失,使我們能夠?qū)τ趤喪龅蹏鴷r(shí)期宮廷卜師的工作狀況有所了解。
亞述宮廷中臟卜卜師最為顯著的工作特點(diǎn)是團(tuán)隊(duì)工作。中國古代文獻(xiàn)和甲骨卜辭中有“二人共貞”和“異史同貞”現(xiàn)象。(25)許子瀟:《商代甲骨占卜中的二人共貞現(xiàn)象》,《殷都學(xué)刊》2019年第3期;牛海茹:《論商代甲骨占卜中的“異史同貞”》,《甲骨文與殷商史》(新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第438-461頁。饒宗頤、宋鎮(zhèn)豪提出存在多人共貞現(xiàn)象,但上揭許子瀟文認(rèn)為上述兩條證據(jù)均為誤讀,不可信。亞述文獻(xiàn)十分明確地記載了兩人、三人或多人共貞現(xiàn)象。在69篇保留了卜師名字的文獻(xiàn)中,僅有15篇顯示問卜儀式由一位卜師主持。另有6篇文獻(xiàn)盡管僅保留了一位卜師的名字,但存在另有一名或多名卜師的名字不可辨認(rèn)的現(xiàn)象,顯示應(yīng)為多人共卜。(26)盡管文獻(xiàn)中的部分人名由當(dāng)代學(xué)者復(fù)原,但是依據(jù)充足,復(fù)原的正確性應(yīng)該不容懷疑。另外,學(xué)者們根據(jù)缺失文獻(xiàn)所能容納楔形文字符號(hào)的數(shù)量判斷殘缺處可能有幾個(gè)名字,如SAA IV 18判斷為至少8人,SAA IV 204應(yīng)有5名卜者,多名卜師參與活動(dòng)的事實(shí)則是明確的。2人組成的卜師團(tuán)隊(duì)較多,尤其是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的文獻(xiàn)中,兩人組成的團(tuán)隊(duì)最為常見,比如舒瑪和貝爾烏沙里姆、納迪努和塔伯尼、納西如和馬杜克舒瑪烏蘇爾、丹納亞和阿舒爾達(dá)因沙如(A??ur-da’in-?arru)、丹納亞和濟(jì)濟(jì)(Ziz)等。稍早一些的亞述國王阿舒爾納西爾帕二世(Ashurnasirpal II)(公元前883—前859年在位)王宮浮雕中的臟卜場景顯示兩人共同工作,(27)Ivan Starr,Queries to the Sungod. Divination and Politics in Sargonid Assyria, pp. xxvi.也證實(shí)了文獻(xiàn)的記載。另外,三名以上卜師組成的大團(tuán)隊(duì)集體工作的情形主要見于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的文獻(xiàn)中。SAA IV 18中,以馬杜克舒瑪烏蘇爾為首,同時(shí)署8名卜師的名字;同樣情形出現(xiàn)在SAA IV 129,至少有7名卜師參與其中;SAA IV 139能夠確認(rèn)的也有7名卜師。
卜師團(tuán)隊(duì)的人員構(gòu)成比較固定。目前所知,馬杜克舒瑪烏蘇爾的團(tuán)隊(duì)中,納西如、塔伯尼應(yīng)是其團(tuán)隊(duì)的核心成員,二人或者三人共卜情形較多。(28)馬杜克舒姆烏蘇爾與納西如和塔伯尼的工作關(guān)系也體現(xiàn)在兩位亞述國王在位時(shí)期的官方通信中,見SAA X 176:3;SAA X 177:2。馬杜克舒瑪烏蘇爾團(tuán)隊(duì)的其他成員還有:阿卡拉亞、馬杜克舒姆伊伯尼(Marduk-?umu-ibni)、巴尼(Ban)(SAA IV 139);納布阿赫巴利特(Nab-ahhe-balli)、納布沙伯什(Nab-?ab?i)(SAA IV 185);丹納亞、辛沙如伊伯尼(Sin- ?arru-ibni)(SAA IV 317)等。
團(tuán)隊(duì)工作必然存在內(nèi)部分工。文獻(xiàn)顯示,臟卜卜師最為重要的工作職責(zé)是觀測、記錄、解釋兆象。牲羊內(nèi)臟的觀測顯然是最為重要的環(huán)節(jié)。在亞述王宮的臟卜報(bào)告中,卜師的名字多數(shù)出現(xiàn)在兆象描述之后。例如,SAA IV 5 r. 8-9記錄臟卜所觀測到的兆象:“【……】右側(cè)‘通道兆’指向【……】。‘通道兆’扭曲。‘口袋兆’右側(cè)有洞。‘輔助兆’、‘武器兆’【面向】‘手指兆’底端”。緊接著,r.10記錄了三名卜師的名字舒瑪、貝爾烏沙里姆、 納布烏沙里姆和臟卜時(shí)間。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的臟卜報(bào)告多數(shù)只記錄卜師的名字,并不明確區(qū)分觀測者、記錄者和解釋者。僅SAA IV 110明確說明馬杜克舒瑪烏蘇爾是臟卜儀式的執(zhí)行者(29)dAMAR.UTU-MU-PAB e-tap-?ú,譯為:“由馬杜克舒姆烏蘇爾執(zhí)行”。。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的報(bào)告中則標(biāo)明執(zhí)行者與記錄者的分工。執(zhí)行者稱Lú.HAL,記錄者稱EN-è-e-me。(30)卜師和記錄者或者解釋者同時(shí)出現(xiàn)也體現(xiàn)在新巴比倫時(shí)期的文獻(xiàn)中。納布尼德哈蘭建筑碑中同時(shí)提及Lú.HAL和Lú.EN. ME.LI,C.J. Gadd, “The Harran Inscriptions of Nabonidus”, Anatolian Studies, Vol. 8 (1958), pp. 62-63。
但是,這種分工應(yīng)該只是在每一次臟卜工作中的臨時(shí)性分工。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的卜師丹納亞既是記錄者,(31)見于SAA IV 286,291,300,303,304,317,324,331,336。也是執(zhí)行者。(32)SAA IV 316。SAA IV 279中,貝爾烏沙里姆為執(zhí)行者,沙拉特薩瑪伊拉伊(arrat-[sa]mma-ila’i)為記錄者;SAA IV 285中貝爾烏沙里姆和巴尼亞(Baniya)均為記錄者。SAA IV 319中大卜師(Lú.GAL.HAL)和記錄者(EN-è-e-mu)并列,卜師的名字未保存,但可印證卜師的職責(zé)包含執(zhí)行和記錄。SAA IV 326明確指明大卜師尼努阿亞(Ninuaya)(Lú.GAL.HAL)是記錄者(EN- UMU)。顯然執(zhí)行者和記錄者的分工并不是嚴(yán)格的職業(yè)的內(nèi)部分工,只是臨時(shí)性的職責(zé)分工。一些記錄顯示,卜師工作團(tuán)隊(duì)內(nèi)部也存在梯次分工。SAA IV 308中區(qū)分了首卜卜師和驗(yàn)證卜師。另外,文獻(xiàn)中還有“驗(yàn)證”、“二驗(yàn)”、“三驗(yàn)”的記載,說明卜師團(tuán)隊(duì)的內(nèi)部存在一卜、二卜、三卜的工作分工。(33)如SAA IV 16有首卜(IGI-ti)、驗(yàn)卜(piqitti)和三卜(?álulti)的劃分。
另外,臟卜過程中應(yīng)該還有其他輔助人員。提格拉特皮萊賽爾三世(Tiglath-pileser III)(公元前744—前727年在位)王宮中發(fā)現(xiàn)的浮雕場面證實(shí),在臟卜前、過程中和之后,都有輔助人員從事宰殺、隨侍和整理工作。(34)Ivan Starr, Queries to the Sungod. Divination and Politics in Sargonid Assyria, p. xxv.臟卜報(bào)告中有關(guān)工作禁忌的記載表明,從選擇卜羊開始,所有能夠接觸到卜羊的參與者都應(yīng)遵守工作守則。伊萬·斯塔爾認(rèn)為“碰觸羊的人”應(yīng)是臟卜儀式的輔助人員。(35)Ivan Starr, Queries to the Sungod. Divination and Politics in Sargonid Assyria, p. xxiv.
可見,亞述帝國晚期宮廷中的臟卜卜師是一個(gè)比較龐大的群體,他們負(fù)責(zé)臟卜活動(dòng)的各個(gè)流程,以團(tuán)隊(duì)工作為主,有臨時(shí)性的工作職責(zé)分工,也有工作流程分工,臟卜卜師的職業(yè)體系比較完整。
三、亞述時(shí)期卜師集團(tuán)的官員化特征
卜師官員化的進(jìn)程早已開始,蘇美爾城邦時(shí)代晚期,拉伽什城邦的統(tǒng)治者烏爾南塞(約公元前2494—前2465年)任命專司犧牲事務(wù)的祭司,(36)O. R. Gurney,“the Babylonians and the Hittites”,Michael Loewe and Carmen Blacker (eds.) Divination and Oracl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p. 148.其中應(yīng)包含臟卜卜師。阿卡德時(shí)期,軍隊(duì)中已經(jīng)設(shè)置專職臟卜卜師職位。烏爾第三王朝國王舒爾吉下令分配60[升]糧食給牲羊做飼料。(37)P. Michalowski, Letters from Early Mesopotamia (Atlanta, 1993), p. 67.M.這說明,這個(gè)時(shí)期牲羊的飼養(yǎng)已經(jīng)是官府的職責(zé)之一,而且此類事務(wù)可能由國王本人直接掌管。亞述王宮的這批臟卜報(bào)告中,卜師集團(tuán)的政治化、官僚化特征十分明顯,我們有可能據(jù)此對卜師制度體系進(jìn)行比較清晰的勾勒和總結(jié)。
首先,卜師所占之事多與國家的軍事征伐、對外關(guān)系、官員任命有關(guān),也涉及宮廷內(nèi)部事務(wù)。帝國的政治和軍事事務(wù)是臟卜問卜最重要的內(nèi)容。伊萬·斯塔爾將亞述王宮中的臟卜報(bào)告按照內(nèi)容進(jìn)行了分類,軍事與政治事務(wù)所占比重最大,有118篇報(bào)告與此相關(guān),包括埃薩爾哈東時(shí)期與安納托利亞關(guān)系(SAA IV 3-17),與舒布里亞(Shubria)、烏拉爾圖、西徐亞和曼奈亞(Mannea)等北方國家和民族的關(guān)系(SAA IV 18-40),與米底關(guān)系(SAA IV 41-73),與伊朗高原埃蘭(Elam)和埃利皮(Ellipi)關(guān)系(SAA IV 74-80),與埃及和黎凡特關(guān)系等(SAA IV 81-93)。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的報(bào)告中僅涉及與沙馬什舒姆烏金戰(zhàn)爭一項(xiàng)具體事由(SAA IV 279-291),但有多篇報(bào)告涉及軍隊(duì)事務(wù)。臟卜報(bào)告中涉及的其他主題包括宗教活動(dòng)、內(nèi)亂、官員任命、王室人員問疾等,這些內(nèi)容均與國家政治統(tǒng)治息息相關(guān)。另外,臟卜活動(dòng)的委托人以國王為主。早在阿卡德時(shí)期,納拉姆辛(約公元前2269—前2255年)文獻(xiàn)記載:“我招來卜師命令他們占卜,我用臟卜卜問了7次。”(38)B.R. Foster, From Distant Days. Myths, Tales, and Poetry of Ancient Mesopotamia, Bethesda, 1995, pp. 171f. 174, 175.他還曾經(jīng)卜問蘇美爾人的主神恩利爾是否可以在阿卡德修建伊南娜神廟一事。(39)J.J. Finkelstein, “Mesopotamian Histori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07 (1963), p. 467.亞述帝國國王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4—前681年)在父親薩爾貢二世(公元前721—前705年)死于非命后曾經(jīng)勘察占問牲羊父親的死因及受到不合禮制的喪葬待遇的原因。(40)Ann M. Weaver, “The ‘Sin of Sargon’ and Esarhaddon's Reconception of Sennacherib: A Study in Divine Will, Human Politics and Royal Ideology”, Iraq 66 (2004) Nineveh. Papers of the 49th Rencontre Assyriologique Internationale, Part One (2004), p. 63.新巴比倫王納布尼德(公元前555—前539年)也熱衷于占卜活動(dòng),這個(gè)時(shí)期的文獻(xiàn)中充滿了形形色色的臟卜活動(dòng)的記錄,神廟興建、落成、祭司擢選等事事問卜。(41)C.J. Gadd, “The Harran Inscriptions of Nabonidus”, Anatolian Studies, Vol. 8 (1958), pp. 62-63.
其次,卜師任職于宮廷中,偶爾出現(xiàn)在戰(zhàn)場上或主要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城市中。埃薩爾哈東和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的亞述都城是卡爾胡,這個(gè)城市是臟卜卜師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地點(diǎn),工作場所大多為王宮,包括新王宮、王儲(chǔ)宮、覲見廳等,似乎卜師從事臟卜工作的場所因問卜的事項(xiàng)而定,并沒有固定場所。其他城市中包含埃爾貝拉等重要的政治或行政中心,也有一些邊防城市。(42)SAA IV 122號(hào)提及占卜地點(diǎn)在卡爾胡;SAA IV 138在覲見廳(ina é.GAL ma-?ar-ti)舉行;SAA IV 155提及塔爾比蘇鎮(zhèn)(Tarb[iu]);SAA IV 156在新王宮;SAA IV 183卡爾胡的覲見廳;SAA IV 185在阿迪安城(Adian);SAA IV 195、324在埃爾貝拉(Arbela);SAA IV 262號(hào)等在王儲(chǔ)宮(ére-du-ti);SAA IV 280在新王宮。一封可能來自戰(zhàn)場的信件表明,軍營也是卜師的工作場所。(43)SAA X 176:3記載:卜師馬杜克舒姆烏蘇爾、納西如和阿卡爾阿亞(Aqar-Aia)報(bào)告國王他們主持的儀式已經(jīng)結(jié)束,但需要國王下令給當(dāng)?shù)亻L官,他們才能夠離開。
再次,亞述帝國宮廷中的卜師已經(jīng)形成一個(gè)職業(yè)集團(tuán),擁有比較固定的出身、培訓(xùn)、晉級(jí)、職級(jí)劃分和規(guī)章制度。亞述王宮臟卜報(bào)告中并沒有記載卜師的個(gè)人信息,但同時(shí)期一些國王與官員的通信中有一些相關(guān)信息。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一封信件中,卜師馬杜克舒瑪烏蘇爾致信國王,抱怨巴爾哈爾濟(jì)(Barhalzi)總督竊取他在當(dāng)?shù)氐呢?cái)產(chǎn),這些財(cái)產(chǎn)是國王父親的賜予。(44)SAA X 173:2顯然,卜師具有較高的社會(huì)地位,能夠因私人事務(wù)與國王直接通信,并獲得國王的賞賜。另外,馬瑞信件中提到古亞述王室卜師阿斯庫杜姆的職業(yè)生涯:國王派他前往馬瑞輔助出使的古亞述王子。他被馬瑞王留在宮廷任全權(quán)大使,居住在王宮附近一座大宅中,參與國家大事。他本人也與一位馬瑞公主結(jié)婚。進(jìn)一步確證卜師擁有較高的社會(huì)地位。因?yàn)檎疾芳妓囀桥c神祇溝通的技藝,必然掌握在極少數(shù)人手中,極有可能是屬于貴族等級(jí)的特權(quán),而且是世襲職業(yè)。(45)SAA IV334載大卜師馬杜克舒姆烏蘇爾之子擔(dān)任卜師。資深的臟卜卜師也是國王的重要顧問,阿舒爾巴尼拔即位之初,卜師ú-MU-SES致信于他,稱贊他的父親和祖父,指出他父親(埃薩爾哈東)曾征討埃及,他應(yīng)完成父親的遺志,繼續(xù)征討尚未臣服于阿舒爾和辛神的地方。(46)SAA X 174:4顯然,這位卜師在阿舒爾巴尼拔的宮廷中擁有一定的政治話語權(quán)。
卜師的培訓(xùn)傳統(tǒng)十分悠久。早在古巴比倫時(shí)期,政府開始組織抄錄編輯前代文獻(xiàn),大量臟卜文獻(xiàn)被重新分類、整理、抄錄,形成臟卜名詞表、臟卜器官分類卜辭、臟卜器官模型、操作手冊、卜辭集成等各種類型的文獻(xiàn)。中巴比倫時(shí)期、中亞述時(shí)期、新亞述時(shí)期,臟卜文獻(xiàn)均經(jīng)過重新編輯整理,臟卜文獻(xiàn)集成(稱Bārtu)分別編纂完成。(47)H. Tschinkowitz, "Ein Opferschautext aus dem Eponymenjahr Tiglathpileser I",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22 (1968-69), pp. 59-62.在此期間,臟卜技術(shù)、臟卜文獻(xiàn)類型、臟卜活動(dòng)的記錄方式等不斷發(fā)展,至亞述帝國時(shí)期,臟卜的技術(shù)體系已經(jīng)十分完備。這些編纂整理的文獻(xiàn)應(yīng)該主要用于卜師培訓(xùn),起到教材、工具書和教具的作用。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由馬杜克舒瑪烏蘇爾、納西如和塔伯尼組成的資深卜師團(tuán)隊(duì)承擔(dān)教學(xué)和培訓(xùn)任務(wù),他們曾聯(lián)名致信國王,匯報(bào)更新課程事宜。(48)SAA X 177:2
除卜師集團(tuán)內(nèi)部存在職責(zé)分工和工作分工外,卜師團(tuán)體內(nèi)部也存在職業(yè)等級(jí)差別。亞述王宮臟卜報(bào)告中有3人擁有“大卜師”頭銜(Lú.SAG EN- UMU),他們是馬杜克舒瑪烏蘇爾、Ninuaya和A??ur-da’’in-?arru,均出現(xiàn)在阿舒爾巴尼拔時(shí)期。大卜師顯然是一種高級(jí)“職稱”,也極有可能是臟卜團(tuán)隊(duì)的領(lǐng)導(dǎo)者。
文獻(xiàn)中對卜師及相關(guān)人員工作禁忌的記錄十分特殊,可以視為卜師工作的規(guī)章制度。這些規(guī)定涉及臟卜卜師及助手、卜羊和占卜場所。克勞伯和伊萬·斯塔爾對其進(jìn)行了十分詳細(xì)的研究和分類。(49)Ivan Starr, Queries to the Sungod. Divination and Politics in Sargonid Assyria, pp. xxii-xxvii.總體來說,臟卜卜師在開始占卜工作之前應(yīng)當(dāng)避免以下行為:(1)用于占卜的羊不潔或有其他問題;(2)碰觸卜羊前額的人身穿(不潔)常服;(3)卜師本人穿(不潔)常服;(4)卜師飲食和接觸不潔之物;(5)卜師更改占卜程序;(6)卜師妄言卜辭;(7)卜師在夜間看到恐怖之事(做噩夢?);(8)卜師碰觸到用于祭奠的啤酒、mashatu面粉、水、容器和火。
綜上可見,亞述帝國時(shí)期的臟卜卜師已經(jīng)是亞述帝國官僚集團(tuán)的一個(gè)組成部分,已經(jīng)形成具有專門職業(yè)背景和職業(yè)分工的集團(tuán),他們擁有較高的社會(huì)地位,參與國家政治、軍事、行政、宗教和宮廷內(nèi)部事務(wù)的決策。當(dāng)然,亞述王宮中的卜師做為具有專門職業(yè)技能的特殊群體,與帝國祭司集團(tuán)、其他“學(xué)士”集團(tuán)的關(guān)系仍然是需要繼續(xù)深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