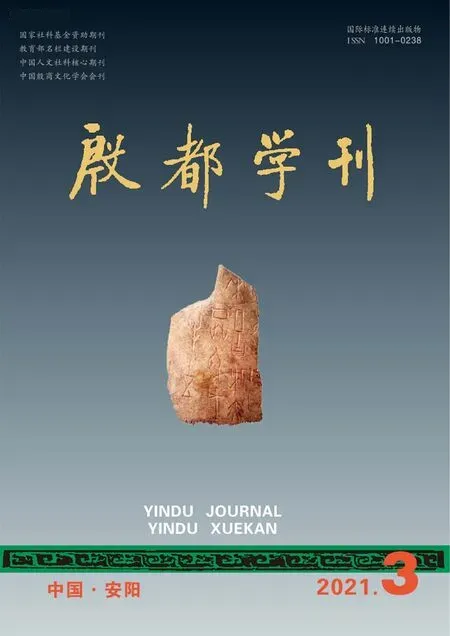歐陽修《春秋》學指瑕
劉越峰
(沈陽師范大學 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歐陽修作為“慶歷新學”的執(zhí)牛耳者和宋學的重要開山人物,在宋代《春秋》學研究方面可謂開風氣之先,他的代表作有《春秋論》3篇、《春秋或問》2篇、《石鹢論》、《辨左氏》等。另外,他的部分散文和《新五代史》中也有論及《春秋》的內容。歐陽修重要的《春秋》學觀點,如對眾多所謂春秋“書法”的批駁、理論上既不信傳又不廢傳的治經理念等,都深遠地澤溉后世學者,前賢時彥對這些方面的論述可謂詳備,此不贅言。這里要補充論述的是歐陽修在治《春秋》學的過程中存在的一些瑕疵,而對這些瑕疵的關注在《春秋》學史上,甚至是在中國學術發(fā)展史上有著重要意義。具體而言,這種瑕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以偏概全,錯點“三傳”
在《春秋》學的研究中,“三傳”觀點各異,每一處細小的差別都應該引起研究者的關注,由此才有可能無限地接近“真理”,即所謂圣人本意。如果不精細品讀,就會在論述過程中犯以偏概全的毛病,而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論述就會變得根基不牢。作為文學大家的歐陽修在論述《春秋》學觀點時也未免此病。例如,歐陽修在《春秋論下》中論述道:“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1)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308頁。這個觀點似出《公羊傳》,但也并非《公羊傳》全貌,而只是其中部分觀點的表述。《公羊傳》在宣公六年“晉趙盾、衛(wèi)孫免侵陳”經下說:“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2)王維堤、唐書文:《春秋公羊傳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頁。而歐陽修所持觀點在《左傳》和《穀梁傳》中均未提及,況且“三傳”之說要遠比這個“不討賊”觀點復雜許多。歐陽修不將“三傳”觀點條分縷析地進行闡述,而是抓住某傳一端籠統(tǒng)指責“三傳”過失,以偏概全,有失公允。
此類論述不夠嚴謹的問題在歐陽修《春秋》類文章中還有表現。歐陽修在《春秋論上》中稱:“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之謂公,而從三子謂之攝。”(3)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05頁。在《春秋論中》的最后一段,歐陽修論述道:“難者又曰:‘謂之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于己,舉魯之人聽于己,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4)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08頁。這兩段關于魯隱公繼位的論述,實際上是有問題的。歐陽修明言“三傳”同稱隱公攝政,這里又是“三傳”并提,與事實不符。其實,在《公羊傳》和《穀梁傳》中根本沒有提及任何隱公攝政方面的內容,所謂“攝政”說當源自《左傳》和《史記》。
在《左傳》中記載:“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9頁。楊伯峻先生云:“攝,假代之義,下文‘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可證。《魯世家》亦云:‘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6)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9頁。《史記》采信了《左傳》的這一觀點,據《史記·魯世家》記載:“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7)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529頁。也就是說,歐陽修所謂“三傳”都認為魯隱公攝政的說法其實并不成立,“三傳”中只有《左傳》持此觀點。其實,在《春秋論中》的最后一段中,歐陽修記辯難者的觀點時已明確提到:“謂之攝者,左氏耳。”(8)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08頁。歐陽修在《答徐無黨第一書》中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稍做了修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余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與諸候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于其卒也,書曰‘公薨’,則圣人何嘗異隱于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跡”(9)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1011-1012頁。。但與前段論述相比較又有了第二個問題,前面論述《公羊》《穀梁》時,歐陽修認定隱公“假立”,這里又言隱公乃為“讓”。《公羊傳》云:“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10)王維堤、唐書文:《春秋公羊傳譯注》,第2頁。《公羊傳》認為隱公本不想自立,但考慮在當時情況下桓公不一定得立,因此隱公暫為桓公“假立”,并未見有“讓”之義。在這個問題上,《穀梁傳》與《公羊傳》的觀點并不相同,《穀梁傳》稱:“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11)載承:《春秋穀梁傳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穀梁傳》只是說隱公不想為“公”,如今得立,“將以讓桓也”,這種表述自然與《公羊》“為桓立也”的“假立”不同。《穀梁傳》的觀點應該是“立”后有“讓”,況且《穀梁傳》中明言:“(惠公)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正表明《穀梁傳》中認同息姑為“公”,根本沒有表現出任何隱公“假立”之意。
總括而言,歐陽修論述隱桓一事,以“隱公攝”為“三傳”觀點不妥;以“隱公假立”同為《公羊》《穀梁》觀點不準確;以“隱公讓”同為《公羊》《穀梁》觀點亦有不嚴謹之處。歐陽修以上所論似乎都存在以偏概全,錯點“三傳”之嫌。
二、錯綜“三傳”大義,并未透析“三傳”本真
“春秋三傳”觀點雖有相同或相似之處,但在未透析“三傳”本意的情況下,斷章取義地將“三傳”觀點混同、拼接成一個整體論述,這樣無助于新觀點的生成。
歐陽修在《春秋論下》中說:“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12)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08 頁。接下來是一串語氣強烈的反問句:“以盾為無心弒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后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13)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08頁。歐陽修據經文中有“弒”字,認定趙盾弒君無疑。其實,歐陽修的這一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元代趙汾就從遵信《左傳》的角度指出歐陽修只信圣人經文的悖謬之處:“《左傳》趙盾事首尾皆實,不備,故學者多疑之。若曰:‘越竟者罪乃免’則語意備矣。又趙盾之罪與欒書、中行偃不同,書、偃親為弒逆,然經卻又只書晉弒其君,又不曾書討弒君賊。當是時,莫是書、偃為政而別不曾討賊,則弒主非書、偃而何?此等處雖不信《左傳》亦不可也。若歐陽修只據經文,則書、偃得免于弒君之罪,如此卻出脫了多少惡逆之人。”(14)《春秋師說》(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平心而論,遵信圣人經文本無大錯,關鍵是歐陽修在理解“三傳”的真正含義上存在問題。我們還是從品讀“三傳”對趙盾弒君這一問題上的態(tài)度說起。《左傳》“晉趙盾弒其君夷皋”下文,一方面列舉了晉靈公“彈丸”取樂,殺宰夫,欲殺趙盾等“不君”的惡行,另一方面列舉了趙盾進諫、恭敬愛民、如何受部下愛戴、救助的事實。在提到“弒君”這一問題時寫到:“乙丑,趙穿殺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詩曰: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1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662-663頁。由引文可知,《左傳》雖在一定程度上認同趙盾弒君,但與以往所批判的十惡不赦的弒君“大惡”不同,因為重要的是,傳文在認定董狐秉筆直書的同時,也認定趙盾為“古之良大夫”。
《穀梁傳》在此條經文下也認為:“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避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穿弒公,而后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16)載承:《春秋穀梁傳譯注》,第386頁。《穀梁傳》中這條傳文的真正意思有以下三點要重視。首先,《穀梁傳》認為趙盾實際上沒有弒君,但史官記錄其“弒君”。其次,在對趙盾“天乎”“天乎”的慨嘆中顯示傳主對趙盾弒君記錄的錯愕之情。最后,認為趙盾是“忠臣之至”者,因其本未弒君還必須背負罵名,趙盾實際上是史書中對臣下求全責備書寫筆法的犧牲品。
《公羊傳》在宣公二年的經文下無傳,對趙盾的評價在宣公六年“晉趙盾、衛(wèi)孫免侵陳”經文之下:“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獆。’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我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17)王維堤、唐書文:《春秋公羊傳譯注》,第311頁。接下來詳細記錄了趙盾在晉國的一系列忠善之舉。《公羊傳》的主要觀點也相當明確:趙盾因不能討賊而被定“弒君”之名;記錄了趙盾對自己被冤枉的抗爭;這個“弒君”之臣多有善行義舉。這三點表明《公羊傳》對“趙盾弒君”也同樣存有惋惜之情,至少不認為趙盾是十惡不赦的真正弒君的惡人。聯(lián)系以下兩點似乎更能表明《公羊傳》的這個立場。第一,《公羊傳》在宣公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獆”這一關鍵經文處并未發(fā)傳指斥趙盾。第二,按《春秋》慣例,弒君者不再見于經,而《公羊傳》在宣公六年又探討這個問題本身就表明對趙盾弒君這一事件性質認定的復雜性。
歸納《左傳》《穀梁傳》和《公羊傳》的大義,可知“三傳”雖認定經文記錄趙盾弒君不錯,但都表現出了對趙盾“為法受惡”的惋惜,甚至認為這樣的趙盾可算“忠臣之至”者;相較而言,《穀梁傳》有更明確肯定趙盾的成分。這樣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歐陽修在論述這一問題時的瑕疵,歐陽修有言:“既而以盾非實弒君,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首先,其中所言趙盾事“復見于經”似針對《公羊傳》而發(fā),但如上所述,《公羊傳》僅就宣公六年經文發(fā)傳評價趙盾,表明對趙盾弒君評價的復雜態(tài)度,不存在“明盾之無罪”的成分。“而明盾之無罪”則近似《穀梁傳》的觀點。其次,“三傳”都認同經文中所言“弒”這個事實,但包括肯定趙盾無罪的《穀梁傳》在內,并沒有欲赦免趙盾的意圖,更不存在“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的矛盾,“加之而又赦之”的觀點實際上是《公羊傳》對許世子嘗藥一事的評價,歐陽修則將這一觀點錯置在此處。再者,“三傳”忠實地分析、記錄了《春秋》筆法與實際情況的矛盾復雜,除了表明《春秋》重人情的特質之外,還有尊王、對臣子求全責備等思想的體現,歐陽修所論“其于進退者皆不可,此非《春秋》意”的論述自然不能成立。綜而論之,歐陽修在未透析各傳本意情況下,錯綜“三傳”串講大義,未免有不當之處。
三、廢傳太過,忽視深入思考
宋人治《春秋》以不信“三傳”開始,這種理念的創(chuàng)新意義不言而喻,但必須指出的是,廢傳太過容易走向求真務實的治經目標之反面;更嚴重的是,簡單地廢傳而不作深入思考,還會導致對圣人經典的闡釋回到不可說解的原點。歐陽修雖在理論上不廢經傳,但在治《春秋》的實踐中卻已見廢傳太過、忽視深入思考的端倪。
例如,昭公十九年《春秋》有“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18)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400頁。的經文,這條經文之下,《公羊》無傳(《公羊》在“葬許悼公”經文下發(fā)傳,有“藥殺”“赦止”等觀點)。《左傳》解釋說:“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19)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402頁。表明許世子并無弒君之實,本是“盡心力以事君”的人,而書為“弒”,是責備其在進藥過程中出現了疏忽。《穀梁傳》在這個問題上說得更加明確:“日殺,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20)載承:《春秋穀梁傳譯注》,第649-650頁。《穀梁傳》甚至在“冬,葬許悼公”經文下發(fā)傳表達了責備許悼公之意:“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21)載承:《春秋穀梁傳譯注》,第651頁。歐陽修完全不信“三傳”所言,堅持認定許世子弒其君,他在《春秋論下》中論述道:
難者曰:“圣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圣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后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惡矣,圣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22)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09-310頁。
這樣論述至少有三點是可疑的。首先,“三傳”皆言許世子因未嘗藥而致君買亡故,《春秋》經文載:“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而歐陽修只強調“嘗藥之事卒不見于經”,并未就“三傳”所言提出更扎實的質疑與考證。“三傳”對許世子嘗藥而致君買亡故的事實均無異辭,當有“老師宿儒”之所傳,歐陽修也曾自言:“司馬遷之于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23)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895頁。奈何歐陽修信司馬遷一家之言有“老師宿儒”之所傳,而于無異辭的“三傳”觀點獨不取信,豈不怪哉?
其次,歐陽修論曰:“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24)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09頁。這種歸納也是誤解“三傳”本意。如前所言,勸人侍君父、進孝道、親嘗藥物,只是“三傳”垂教后人的一個方面,《公羊傳》在“昭公十九年葬許悼公”經文下發(fā)傳稱:“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25)王維堤、唐書文撰:《春秋公羊傳譯注》,第472-473頁。
傅隸樸在《春秋三傳比義》中贊揚《公羊傳》道:“春秋之義,君弒,賊不討,不得書葬。許悼公之卒,經既書弒,未見討賊,如何得書葬呢?公羊此問極有道理。因書葬,就表明了世子并未弒君,但許悼公飲其藥而卒,則藥之不適應病癥,顯然無疑,許止雖無弒君之心,也不能逃過失殺人之責,故經書弒,以見春秋筆削之嚴,經書葬,以見春秋存心之恕。公羊此解,深得圣人之用心,其略于書弒詳于書葬,也繁簡得體。”(26)傅隸樸:《春秋三傳比義》(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33頁。這里既包括對許世子過失殺君的指責,又有對許世子非本意弒君的寬恕。可見,“三傳”對許世子嘗藥的闡釋,絕非教人知嘗藥盡孝一端。
再者,歐陽修論述道:“圣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27)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09頁。歐陽修論圣人經典風格簡潔明白,但獨論《春秋》有“隱微”之特質,例如,他承認“昔孔子大圣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于人,第口受而已”(28)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888頁。。他在《崇文總目·春秋類》中也明確指出:“孔子大修六經之文,獨于《春秋》,欲以禮法繩諸侯,故其辭尤謹約而義微隱。”(29)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1883頁。因此,歐陽修在這里所說的“圣人一言明以告人”,是與《春秋》特質不相符的。歐陽修拒不遵從“三傳”對圣人隱含之義的探討,有不明經義“微而隱”的嫌疑。
與不信“三傳”相聯(lián)系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即面對史料不足而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上,歐陽修多采取“闕如”的態(tài)度。誠然,在學術研究上嚴謹誠實的態(tài)度,確實比求新求奇的逞臆胡說大有可取之處,因此歐陽修的這種治學精神也受到了歷代學者的贊揚。但是,回避問題關鍵,對重要問題不作深入思考,常常處之以“闕如”的態(tài)度實際上有過于率意之嫌,同樣也不利于學術的推進。在《春秋》學研究上,歐陽修似也不免此病,例如,歐陽修在論述趙盾弒君的問題時說:“問者曰:‘然則夷皋孰殺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30)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09頁。接下來他連用三個類比(“父病,躬進藥而不嘗”“父病而不躬進藥”“操刃而殺其父”(31)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09-310頁。)引出許世子嘗藥的話題,并得出結論:“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32)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09頁。
這種解釋至少有兩點可疑。第一,趙盾所為史有明文記載,歐陽修論述中所類比的三個例子,無論是父病進藥而不嘗、父病不躬進藥,還是持刃殺父,都與趙盾弒君沒有可比性。如此回答趙盾是否弒君的問題,若非出于文章傳錄有誤,實在讓人匪夷所思。第二,上述三個類比更像是為說明許世子弒君所設,但也只是表明孔子記作弒君肯定是有原因的。這樣解釋問題其實是回避了問題的根本,甚至是同義反復,有率意武斷之嫌。
據前論可知,歐陽修在魯隱公問題上既不同意《左傳》隱公“攝”的主張,又不同意《公羊》的“假立”和《穀梁》“真立”而復有“讓”的解說,更沒有看到“三傳”對魯隱公事復雜情緒的表達,而只是一味混同“三傳”觀點,指責它們矛盾混亂。這樣一來,歐陽修對隱公事情的評價,除了指責懷疑的情緒,沒有更多有益于學術發(fā)展的主張,實為憾事。不僅此例,歐陽修在論述《春秋》諸多問題時往往表現出能破能疑而不能立的論述傾向。如:“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于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注]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10頁。“或問:‘《春秋》何為始于隱公而終于獲麟?’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注]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第310頁。凡此種種,對“三傳”已有成說幾乎完全否定。這種破而不立、不作深入思考的態(tài)度實不可取,北宋蕭楚就曾批評歐陽修說:“經曰狩,不言所獲,惟‘西狩獲麟’,其年只書此一事。如此,則謂終之無義為不可也。”[注]蕭楚:《春秋辨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當然,論述歐陽修在《春秋》學論述上的瑕疵,并不是要否定歐陽修在《春秋》學研究上的開創(chuàng)之功。相反,關注這種瑕疵本身對宋代《春秋》學,乃至對中國學術史,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第一,片面地打著“信經”的旗號對“三傳”已有觀點不逐一作精詳的考證分析,不僅不能把《春秋》學研究推向深入,反而會導致學者對《春秋》經的迷信。第二,在治經實踐中忽視傳統(tǒng)的注疏之學,尤其是在《春秋》學領域內表現出的不信“三傳”的傾向,勢必會帶來論述根基不牢的弊端。第三,宋代知識分子以文人身份進行學術研究,喜憂參半。可喜的是,他們從新的視角關注學術問題,引發(fā)新觀點的出現,指引后學走出新的治學路徑,如歐陽修對《周禮》真?zhèn)蔚呐袆e、對《詩經》本義的論述,就是從“人情”的角度入手,確有化繁為簡、直指問題本真的功效;再如從文理、氣脈等文學角度出發(fā),斷定“十翼”非圣人所作,具有振聾發(fā)聵的創(chuàng)見之功。但是可憂的方面也非常明顯,如歐陽修在《春秋》學研究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文本以偏概全、不求甚解、主觀臆斷,直接導致其后繼者騁臆出奇、主張“六經注我”等不良傾向。治經風格有漢、宋之分,如果說漢人多以官員身份治經,導致經學政治化傾向嚴重,那么宋人以文人身份治經,在帶來經學闡釋新奇化的同時,未免有空疏之病,這非常值得后世學者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