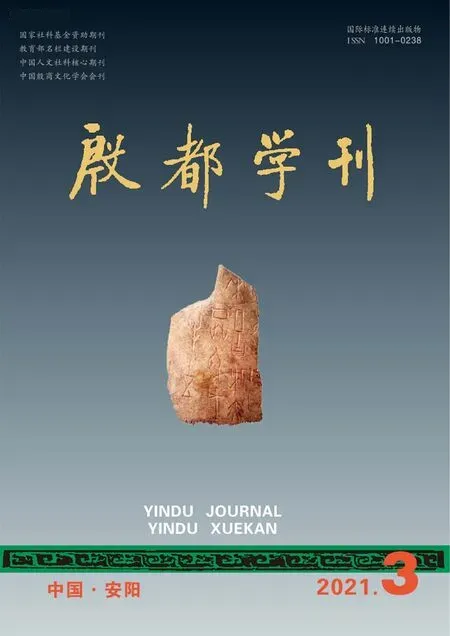甲骨文“象”與象范疇生成的關系
李安竹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外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080)
作為中國古代文論元范疇的“象”字,在甲骨文中主要指大象,尚不具備理論上的抽象概念和思想,這與甲骨文“美”“文”“藝”等字不同。先民們并未將他們的思想觀念直接反映在“象”這個字上,但其潛在的審美觀念、思維方式卻凝定在了這個字上。先民運用想象、抽象、象征等思維方式對大象進行模擬并畫成其物,這就是“象”字。“象”最初實指動物大象,殷商時期普遍存在于中原地區,但商周之際的氣候劇變迫使大象南遷,中原地區的人們很難再見到大象,從而引發人們由死象之骨想象、聯想生象之形。因而“象”被賦予了想象意義,成為心物之間的橋梁。古代學者對此已有明確認識,并用“象”字來描述意象思維的生成機制。在對“象”字的認識基礎上,古代學者又以“象”術語(象形、象意等)來闡述文字構形的基本特征,使“象”成為具有抽象概念的專屬性術語。
一、甲骨文“象”字集釋
在甲骨文中,“象”這一概念明確指動物大象。它從側面對大象的自然神態進行了生動的描摹。許慎《說文解字》曰:“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尾之形。凡象之屬皆從象。”(1)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九篇下《象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59頁。據文獻考證,殷商時期,有大象生活在黃河流域,先民也獵取過大象,且用象牙制成了精美的工藝品。“象”字見于甲骨文,象形見諸尊彝,亦是習見之事,商代銅器就有一個雙象尊。象的遺跡近年亦屢有出土發現,殷墟發掘中出土的動物群,其中就有大象。(2)楊鐘健、劉東生:《安陽殷墟哺乳動物群之補遺》,梁思永、夏鼐編:《中國考古學報》(第四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49年,第147頁。作為當時生活中尋常之物的大象,較廣泛地進入了先民的生產生活中,它為“象”的意義延展創造了生活基礎。

(一)動物名,大象
1.狩獵對象
“象”作為狩獵對象出現于田獵活動中。
(2)《合》4611:“貞令亢目象,若。”
(3)《合》10222:“今夕其雨,隻象。”
(4)《合補》2612:“……冓……獲象。” (《合補》2612=《懷》306)
(5)《合補》2610:“獲象。”(《合補》2612=《懷》308)
(6)《屯》2539:“丁未卜,象來涉,其乎射鹿射。”“己未卜,象,射鹿既其乎……”
以上辭例說明商代晚期有大象作為狩獵對象的情況。甲骨文中關于“獲象”的記載,辭條并不多,且沒有對獲象數量的說明,估計獲象的數量應該很少。這與殷墟考古出土的象骨在哺乳動物中的數量是一致的。(5)參見楊鐘健、劉東生:《安陽殷墟哺乳動物群之補遺》,第147頁。獲象數量少,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在安陽一帶,象應該可以算是瀕危動物。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這或是由于商周之際大象逐漸南遷所致。
2.貢品
(7)《合》4611:“貞生……月象至。”
(8)《合》8984:“戊辰卜,雀不其以象十二月?戊辰卜,雀以象。”
雀是商晚期南方諸侯方伯,雀向商王朝進貢象,側面說明這一時期黃河流域所產之象已經不能滿足殷商王朝的需求或黃河流域的象已經滅絕,所以需要從南方方國進貢。
(9)《合》9173:“貞不其來象。”
“來象”大約是各地奴隸主貴族向商王進獻大象。
3.祭品
(10)《合》8983:“……賓貞……以象侑祖乙。”
將這條卜辭與《合集》8984所說的“雀以象”相互解讀,可知這條卜辭所說的大概是雀納貢了象,侑祭祖乙。江玉祥根據古文獻中使用象牙制作禮器的記述,認為這條卜辭中的“象”很可能是象牙。(6)江玉祥:《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象牙》,李紹明等主編:《三星堆與巴蜀文化》,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第201頁。象作為祭品祭祀先公先王這一情況與考古發現的結論一致。在殷墟的考古遺址中發現有動物埋藏坑,“這種商代的動物埋葬坑被推測是當時使用獸牲祭祀的遺跡。”(7)岡村秀典:《商代的動物犧牲》,劉慶柱主編:《考古學集刊》(第十五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17頁。殷王陵區發現有兩座象坑。1935年第12次殷墟發掘,在王陵區東區M1400號大墓附近,發現象坑一個,內埋一象一人,(8)胡厚宣著,胡振宇編:《古代研究的史料問題 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 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 殷墟發掘》,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30-331頁。乃祭祀祖王的犧牲。1978年在王陵區西區東南方約80米處,又發現象坑一個,內埋一象一豬,象體高約1.6米,身長約2米,門牙尚未長出,系一幼象。(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發掘》,《考古》1987年第12期,第1065頁。據學者考證,這片遺跡當為殷王室祭祀祖先的場所。(10)楊錫璋、楊寶成:《從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隸社會的人牲》,《考古》1977年第1期,第14頁。而這一帶先后發現的兩頭象,就是商王祭祀祖先的犧牲品。可知殷商先民用象祭祀雖少,但卻是確切的。
(二)氏族名
(11)《合》13663:“貞 :令象……”
(12)《合》4609:“ ……惟象……勿惟象……”
這是“象”作為氏族名的辭例。“象”氏族在賓組刻辭中出現的頻率并不算少。考諸商代銅器銘文,目前已知“象”氏族有三組:第一組,安陽薛家莊M3出土了一對爵與觚,銘文均為族徽“象”;第二組,有兩件爵上的“象”字寫法相同,尾巴皆分為三叉;第三組,有銘文“象(族徽)祖辛”(《集成》1512),包括一尊、一卣與一鼎。商貴族的族徽有一種是“職事性”符號,“以事為名”,多以官職作為氏族的名字,他們有自己的領地,是商王室的異姓臣屬,肩負著執行各種勞役的義務。因此,以“象”為族徽,也可能表明“象”這個氏族的主要職責是為商王養象,并負責管理豢養象的眾人與奴隸。
(三)方國名或地名
(13)《合》32954:“于癸亥省象,易日。”
甲骨文中差不多所有的專有名詞,所代表的意義,不僅是一個人或一個氏族,而同時還代表著一塊或大或小的地方,那就是這個人的采邑、封地,或出身所在地。(11)張秉權:《卜辭中所見殷商政治統一的力量及其達到的范圍》,宋鎮豪、段志洪主編:《甲骨文獻集成》(第二十八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03頁。那么“象”這個地方或方國應該就是“象”氏族的所在地。
可以看到,作為大象這一詞義和后兩個詞義之間存在著一定聯系,這種聯系體現在大象圖騰或族徽的使用是“象”作為氏族名、方國名、地名的前提條件,而其背后,蘊含的是廣泛存在于先民意識中的原始思維。眾所周知,古代氏族名常得名于圖騰,各氏族一般選擇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事物為自己的圖騰,并以此為宗神。在原始思維神秘性和互滲律的影響下,他們多認為氏族與某種動物具有親緣關系,祖先就是來源于某種動物。甲骨文記載了殷商時期中原地區有大象生活,且與先民們的生產生活有著密切聯系。因此,某氏族選擇“象”作為他們的圖騰或族徽,該氏族即“象”氏族,其所在地即“象”方國或“象”地。并且,有學者認為“用象形符號表示族名,很可能是原始表意文字產生的一個重要途徑。在商代文字里寫法特別古老的族名金文大量存在的事實,對我們的這種推測是有力的支持。”(12)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1978第3期,第167頁。
二、從大象到觀物取象


在從動物大象到觀物取象的演變過程中,除了“象”具有目視之意以外,更重要的是由大象而產生的“想象”“聯想”“象形”之意。在由“大象”到“想象”這一詞義的引申中,就思維而言,常是因相關聯想、相似聯想而起,與接近律、類似律、因果律等聯想法則有關。這一點,在《韓非子》中就已有論及。
《韓非子·解老》說:“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18)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卷第六《解老第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48頁。在《解老》篇中,韓非子用“意象之象”來解釋老子的“恍惚之象”,這里的“意想”的詞義范圍甚廣,幾乎無所不包,可以把想象、現象、抽象等詞都包括進去。“人希見生象也”的原因,《呂氏春秋·古樂篇》記載:“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逐之,至于江南。”(19)呂不韋著,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卷第五《古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0頁。認為是由于周人的驅趕,以致周代及以后在中原地區難以見到大象。然而,大象南遷以致絕跡中原的主要原因應該是商周之際氣候的劇變。殷商晚期,中原地區氣候突變,在文獻記載中有嚴重的旱情發生,(20)關于殷商時期旱災的記載主要有如下文獻:《尚書大傳》《竹書紀年》《呂氏春秋》《墨子》《尸子》《淮南子》《說苑》等。甲骨文中也有“暵”的記載。此外,中原一帶氣候的變冷也是迫使大象南遷的決定性因素,而地理環境的逐漸變化,也加速了大象南遷的進程。(21)王宇信,楊寶成:《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討》,胡厚宣等著:《甲骨探史錄》,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第488頁。“入周以后,服象之事,漸次絕跡于中原”,“暨戰國時,黃河流域居民,已不見生象”。(22)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56,57頁。大象南遷,并不意味著大象從中原先民的文化記憶中消失,而是以其他形式存在于先民的集體記憶、思維方式和文化觀念中。因為“已不見生象”,所以黃河流域的先民只能憑記憶與想象,根據“死象之骨”的圖案來想象“生象”之形,“死象之骨”和“生象”之形就通過相似聯想和相關聯想并借由人的主觀構建結合在一起。“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這里的“象”不是指客觀事物本體,而是指事物在人們頭腦中反映的產物,是指人頭腦中的心靈之象。由“案其圖”而“想其生”正是始于對客觀物象的觀察,通過聯想或想象而形成的具有相似性的“意想之象”。這種“意想之象”是虛構的,是融入了人的主觀創造和思維加工的,是由相似引發的對“生象”的象形構建。久而久之,“象”的“象形”之意開始引申,用以指稱根據相似聯想對客觀物象進行模擬取象;“象”的“想象”之意也開始引申,用以指稱一切經過臆想作用而呈現于意識中的主觀形象。
韓非子這一論述從“象”這一文字本義出發,在對老子“恍惚之象”的解釋中探討了“象”或“意象”的產生機制,以及與后世藝術審美相關的“意象”和“想象”等問題。這一論述的出發點在于,形象的“象”是從動物的“象”演變過來的。這是符合語言發展規律的,在一對同源詞里,較抽象的那個,多從較實質的那個孳生出來,是一種相關引申,例如抽象義的“結果”是從植物義的“結果”演繹而來的。因此,作為當時中原之地常見的大象寫生符號的“象”字,在一系列思維活動中逐漸被賦予了“想象”“聯想”之意,并蘊含了客觀物象和主觀形象的相似性和相關性。此一意義與目視之意相結合,便形成了“觀物取象”。“觀物取象”反映了各種屬性之象的內在聯系,揭示了事物的本質屬性,因此它超越了時空,成為后世象范疇生成的重要運思方式,“象”也成為后世人們論及“形象”“想象”“意象”“象似”等詞的重要語源。
三、甲骨文“象”字觀物取象的構形方式




先民以點、橫、豎、撇、捺等符號相互組合,創造出具有特定語音、形象和意義的“象”。這是“觀物取象”的生命創造,其對物象的呈現不是寫實而是寫意,既是對生活的摹擬,也是心靈的創造,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體,也是先民“立象盡意”的最高形式。
四、甲骨文的象形性構形
作為一種成熟的書寫系統,甲骨文通過描繪對象物來表示該物體的種屬,它“按照客觀事物的形體,隨其圓轉曲直描繪出一種具有形象感的代表符號,以表達語言中的詞義”(35)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7頁。。因此在造字時,為了突破空間、時間的限制而達到互相溝通、交流、交際的目的,先民們在字形的選擇上也必然選取熟悉的東西為藍本。這些熟悉的藍本是先民造字時思考的出發點,也是《易傳》所謂“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造字來源。首先,“近取諸身”指參照人體自身的各個部分和人使用的各種器物進行擬象構形。在甲骨文中,直接由人體形象或包含人體各部分形象來表意的字,占總字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取象有源自人的身體結構和人體器官的,有源自人的動作情態的,有源自某類人的抽象概念的,有源自人使用的各種器物的,如服飾裝束、起居飲食類器具、勞作狩獵類工具、武器刑具、禮器樂器等等。“遠取諸物”則是以與人類生存息息相關的自然界的各種物象作為構形的出發點,有鳥獸蟲魚,有花草植物,還有山川地貌等。從下表所列的字例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到甲骨文的構形來源,所包甚廣且物態多變。

表1 甲骨文取象字例


古人要在字形和詞義間建立聯系,所以表意方法體現的主要是據形知義,而非據形知物,換句話說,字形是為了表達詞義。甲骨文中的象形性構形,都是用抽象的線條組合以標識事物的形體特征,從形體特征出發,表達對現實中存在的“物”和較抽象的“事”的認知,由此進入到對于人的生命意識的表現。甲骨文中的象形性構形不僅數量多,還具有派生性,其他各種構形都從它派生出來。所以象形是甲骨文構形的本質屬性,是甲骨文以形表意的核心,它反映了當時人們的觀念,其審美趨向是由外到內、由實到虛。
五、以“象”術語表達對造字法的認知
甲骨文“象”字鮮明地體現了甲骨文的基本構形法,即“象形”。這一點前已詳述。甲骨文以象形為構形的基礎,只要有形可象的事和物,都可以用簡筆勾勒,畫成其物。韓非子用“案其圖以想其生”概括性地揭示了“象”字意象產生過程中所遵循的“類似聯想”原則,在對“象”或“意象”產生機制的描述中也揭示出了古人造字的規律。由于“象”字顯示了古人“觀物取象”的造字方法,所以后人也用“象”術語來表達對造字法的認知。
六書是文字大備以后,人們所歸納出的條例。“六書”最早見于《周禮·地官·保氏》,但《周禮》既沒有記載“六書”詳細的名稱,也沒有對“六書”進行解釋。班固《漢書·藝文志》,因承劉向、劉歆,分析漢字的結體構形為“象形”“象事”“象意”“象聲”(40)《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20頁。,特別看重“象”的統攝作用,尤其注重“象”所蘊含的摹仿創造意義,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古人對文字構形的基本認識。“象”的概念,在文字學史上,一開始就被響亮地提了出來,昭示了它的突出地位。
和班固同時代的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的論述雖和班固略有差異,但也屢屢言“象”。《說文解字·敘》中“象”字凡7見,有三種含義:第一,形象、現象。如:“文者,物象之本。”第二,法象、仿效。如:“依類象形,故謂之文。”“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屈。”“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第三,意象。如:“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段玉裁注:“古人之象”,“即倉頡古文是也。”(41)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十五卷上《敘》,第754頁。認為文字是一種意象。
《說文·敘》明確提出:“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42)同上。文字的創設源于先民的仰觀俯察,由觀象而取象,最后符號化而形成文字。創制象形文字的契機,即“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及鳥獸“分理之可相別異”。這可從考古發現得到側面印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遺存證明,除了漁獵以外,家畜特別是豬的飼養已成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已經有了原始農業。從考古發現的殷代遺址看,殷人非游牧民族,畜牧業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史實說明從鳥爪獸蹄印跡獲得創制文字的靈感是完全可能的。古人將鳥獸之跡等一切自然事物的形狀通過模擬轉化為符號,定形成為最初的象形字,這就是“依類象形”。“依類象形”的結果被稱為“文”,而后來“形聲相益”的符號則被稱為“字”。
《說文·敘》用“象”闡釋文字的生成機制,并進一步闡說文字與“象”的深層淵源。第一,文字以“物象”為根本,客觀的事物或現象是文字的創構源泉和依據。第二,文字的構造方式、手段為仿效、法象。它是聯結物象與意象的實踐中介。第三,見諸書寫材料,映于認識主體眼前的是由人創造、代表著一定思想內容的書寫形態,即有意義的符號形式——文字(字象)。“象”在這里便蘊含了由物質根源到手段中介再到符號目標的具體內涵。
在象形這一概念中,蘊含了“觀物取象”“立象以盡意”的深刻運思模式。《說文·敘》指出周易和文字在“觀物取象”“立象盡意”的表現方式上有共同的文化心理淵源。先民用“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43)王弼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八《系辭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6頁。的方法,對宇宙自然中的萬物萬象以及人自身進行反復觀察體悟,然后根據先民所知所感,運用模擬比類的方式來構造自己的符號系統,并用藝術的方式呈現出來。在對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觀察中,人類發現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圖像特征,發現了動物、植物與人身的諸多不同特征及其留下的不同的痕跡,通過對外界事物和自然的觀察、模擬、比類來構造字形和創制卦象。取象是一個抽象的過程,但這個過程并非是邏輯理性的抽象,而是先民的比類思維的體現,它體現著對外物特征的概括,蘊涵或象征著先民對外物的情感和思想,以此來表達對神秘宇宙的崇敬和因認識而產生的愉悅。因此“取象”既不是脫離物象的純粹抽象符號,也不是對事物外在形象的簡單模仿,(44)劉元根:《漢字對先秦類推方法的影響》,《云南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第114頁。而是從自然現象中,獲取與人相關的信息和規律,各種形象的象征屬性有相像相似之處的,則歸納于一類。這一“取象”的過程,有模擬、擬象、仿效、象征的意義,可稱之為“以象歸類”或“比類取象”,這一過程將客觀的物象轉化為意象,并根據意象創造字象,其中意象思維起著重要的作用。漢字源于物象,成于意象,定于字象,“象”一開始就被置于重要地位。可以說,從“觀”到“取”的這一過程,是造字的基本思維模式,是造字的初級階段,在此基礎上,通過綜合“取象”實現事物的抽象表達和文字的意象表達。
在對漢字六書的分析中,學者以“象”術語來表達對造字法的認識,“象”成為古人摹仿創造活動的概念表達。這正好與甲骨文以“象”來構形的特征一致。甲骨文中象形字約占總字數的三分之一,據學者統計,象形字有314字,整體象形的有274字,部分象形4字,襯托象形41字。(45)申小龍:《漢字思維》,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8頁。其中獨立的象形字不僅數量多,而且常作為形符參與到文字的構形中。從“象”的詞性來看,作動詞時,往往是及物動詞,它的動作要有承受對象。在語言運用中,往往組成如下結構模式:象+X(名詞,賓語),所表達的意思并不是與X相似或描繪X,而是以符號去象征X或以符號去表現X或以符號去體現X。當X是有形之物時,象+X=象形。當X是無形之物時,則可以表示象聲、象事、象意等。鄭樵《六書序》:“書與畫同出,……六書也者,皆象形之變也。”(46)鄭樵:《通志二十略·六書略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34頁。象形字產生以后逐漸成為漢字孳生和發展的基礎,成為會意字、形聲字的“字源”;后來的指事字除去符號之外的主構形、會意字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分構形、形聲字的形符和聲符,大都是象形性符號。可以說,甲骨文的造字“六法”幾乎都離不開“象”,都是通過“象”來達“意”,均緣“象”而生,從構思到形成,其出發點和歸趨都在“象”。這一“象”是表象之象、符號之象,是《易傳》所說的“立象以盡意”之象。
文字以客觀的“物象”為本根,客觀的事物或現象是文字的創構源泉和依據。文字的構形方式為仿效、法象。它是聯結物象與意象的實踐中介。見諸書寫材料,映于認識主體眼底的是由人所造、代表著一定思想內容的書寫形態——意象,即有意義的符號形式——文字。它是文字創構的最終目標。那么,“象”這一文字學的基本概念,在以《說文》為標志的漢字學創立期便包含了由物質根源到手段中介而至于符號目標的具體內涵。
結語